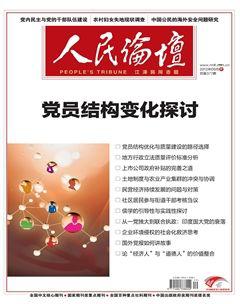对家庭暴力有关问题的思考
胡健
【摘要】家庭暴力概念在比较法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国内对其内涵的理解也存在争议。对家庭暴力内涵的界定,既要借鉴域外立法成果,也不能脱离我国传统的婚姻价值观念,家庭暴力主体范围不宜过于宽泛,应对精神暴力做限缩性解释,并将家庭暴力与一般的家庭矛盾加以区分。
【关键词】家庭暴力 主体范围 行为方式家庭矛盾
我国对家庭暴力法律问题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尤其是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推动了对家庭暴力的理论研究与立法实践。2001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对“家庭暴力”的含义进行了界定,但是,该解释一出台便受到法律学界、社会学界等方面的质疑,因此,对家庭暴力内涵的界定仍有继续探讨的必要。
家庭暴力的主体范围
家庭暴力的主体范围是指家庭暴力防治法的适用对象。英国《1996年家庭法法案》规定:“家庭暴力包括个人为了控制和支配与之存在或曾经存在过某种亲属关系中的另一个人所采取的任何暴力或虐待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感情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将前配偶和曾经同居者也纳入家庭暴力的主体范围内。美国法律中对家庭暴力的主体规定更为宽泛,“家庭暴力所涉及的对象是家庭中的亲密者,如配偶、同居者、父母、兄弟姐妹、孩子、祖父母、孙辈、半血缘父母或兄弟姐妹”。新西兰将这一范围扩大至作为“伴侣”和“任何按照婚姻的本质关系共同生活(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无论现在还是过去是否缔结婚姻关系)的人”,暴力主体不再局限于异性夫妻。这些国家对主体范围规定显然是更注重是否存在“亲密关系”,而不以有无亲属关系为必要条件。
但是,也有一些国家将家庭暴力的主体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如日本2001年的《关于防止配偶暴力及保护受害人的法律》将调整对象范围限定在现时的丈夫和妻子,包括事实婚姻,但不包含婚后的丈夫和妻子、情人、订婚者。韩国1997年的《家庭暴力惩治专项法案》将家庭暴力的主体范围也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
我国婚姻法解释将家庭暴力主体范围也限定于家庭成员之间,而且一般理解为合法婚姻家庭的成员之间,与日、韩的界定相近似,近似的传统家庭观念和文化使然,似乎反映出东方国家在家庭观上与西方国家存在的某些差异。
本文认为,对家庭暴力主体范围的界定应当考虑以下方面:
首先,探讨家庭暴力,离不开对家庭概念的理解。在我國家庭虽是一个法律概念,但是尚没有一个规范的界定。通常认为,“家应指同居的共同生活的亲属团体”,系实质意义之家。形式之家即户,实质上纵为一家而在形式不属同一户籍,则不能成为一家。狭义的家的概念框定了家庭的主体要素为亲属团体,也就是家庭成员。本文认为,家庭暴力防治法应以该亲属团体成员为主要适用对象,但根据该法主体范围扩张的立法趋势,将适用对象扩大至非共同生活的亲属较为合适,因为通常人们认为这些属于广义的家庭成员。
其次,家庭暴力防治法应该是通过消除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发生,实现合法的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与纯洁,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实现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统一。所以,其立法本意包含维护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促进家庭和谐。基于这种认识,如果将家庭暴力的主体范围扩大至离婚的配偶、曾经同居者以及恋爱、已订婚者,既造成家庭概念的混乱,也会颠覆社会公众对家庭的认知,而且,从家庭暴力防治法维护家庭和谐的目的考虑,将适用范围夸大到家庭之外也似乎超出其应当承载的负荷。
再次,家庭法与其他法律相比受本国本民族传统文化影响更深,家庭暴力防治法作为家庭法,当然不能脱离本土文化的土壤。同居被许多国家所认可,将同居者纳入家庭暴力主体范围可以理解,但我国不承认这种两性结合形式的合法性;前配偶或曾经同居者之间不存在婚姻家庭法观念下的法律关系,将其纳入家庭暴力主体范围,不符合我国传统家庭观念。家庭暴力防治法重在对合法婚姻家庭关系的调整,所以,不能脱离我国的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念和现行婚姻家庭法的框架,简单移植国外法的做法。
家庭暴力行为的界定
对暴力行为的界定需慎重,这关系到公权力对家庭生活的介入。家庭生活相对于社会生活而言,具有私密性和自治性。在家庭暴力成为正式的法律概念之前,国家公权力对家庭的介入更多地表现在对家庭成员间犯罪行为的惩治,给家庭留下较大自治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家庭成员自由权和隐私权的尊重。但是,随着人们权利意识的增强以及妇女维权运动的高涨,家庭成员尤其是配偶间权利平等观念的张扬,人们对家庭关系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社会不能继续容忍家庭中强势一方(主要是丈夫)对弱势成员(主要是妻子)恣意控制,因此,公权力介入家庭生活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这势必出现公权力对家庭生活的干预与对家庭自治、家庭隐私权的尊重之间的冲突。在处理这种冲突中,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因为法律措施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家庭成员权利平等从而促进家庭的稳定与和谐,这才是家庭成员长远利益所在。保留适度的家庭自治也具有一定的消化家庭矛盾促进家庭稳定的作用。所以,对家庭暴力行为的界定必须考虑这些因素,使公权力在介入家庭生活时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对家庭暴力范畴内的肢体暴力和性暴力的界定,从主流观点看没有太大的争议,这两类行为构成的家庭暴力目前已经形成共识。本文仅对精神暴力行为发表浅见。精神暴力是指对受害人造成精神上的伤害行为。有不少国家称之为心理伤害,国际社会也用“心理伤害”表述精神暴力造成的后果。我国目前对精神暴力纳入家庭暴力的范畴,意见尚不一致,在立法中是否应当对精神暴力作出规定也存在争议。本文认为,鉴于家庭中确实存在家庭成员间心理伤害的事实,以及比较法上许多国家将精神暴力进行立法的基本趋势,尤其是我国作为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共同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参与者和倡导者,没有理由再将精神暴力排除在家庭暴力的范畴之外。但由于对精神暴力具体内涵的界定比较困难,因此精神暴力并没有一个系统的概念,各国立法中也多采用列举的方式对精神暴力的行为方式进行规定。
通常认为,精神暴力方式包括对家庭成员威胁、恐吓、辱骂、当众或私下恶意贬低、挖苦、嘲笑等属于针对精神的作為,以及对对方漠不关心、疏远、停止或敷衍性生活等属于针对精神的不作为。本文认为,精神暴力一方面不像肢体暴力或性暴力行为伤害那么容易表现于外在,它无法量化。另一方面,如果对心理伤害行为不作限定,将诸如纠缠、唠叨、沉默不语、不断打电话、威胁、恐吓等等让人郁闷的干扰,宽泛地界定为家庭暴力行为,那么家庭暴力就会变得非常普遍,这种泛家庭暴力使公权力过度介入家庭纠纷,反而不利于家庭的稳定。所以,对肢体暴力行为方式的界定可适当宽泛,而对精神暴力行为的方式应当从严掌握,做限缩性解释。
应当将暴力行为与一般家庭矛盾区别开
长期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冲突常常会发生,这也符合矛盾论。家庭成员遇事都能理智处置可能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方式,事实上,偶然的过激言行在所难免。因此维持家庭的稳定与和谐就需要彼此的宽容与谅解,来自家庭成员的小的或偶然的心理痛苦与不快,只要没有造成明显的伤害后果,或可予以“容隐”。否则,如果家庭暴力规定的过于宽泛,会造成公权力轻易地介入家庭生活,未必有利于家庭的稳定与和谐。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其固有的伦理性及情感因素具有自我消化家庭矛盾的功能,不能将这种消化功能简单地理解为弱势一方的隐忍或者强势一方的有所收敛与慈悲。而更多地是基于“恩义情爱”而激发出的体谅、宽容与眷顾的心理在发挥着作用,这就是世界各国在没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的情况下,多数家庭能维持和谐与稳定的缘由。所以,应当客观看待这种家庭矛盾的自我融化功能,不能不加区分地将家庭中出现的冲突都归为家庭暴力。
任何类型的暴力行为的界定,应该考虑一个程度的问题,虽然这里的程度并不要求构成目前国家法律规定的伤害程度,但还是要避免把偶然的、单次的轻微的过激行为划归家庭暴力的范畴内,尤其是对于精神暴力,要突出行为的“持续性”和发生的“连续性”。
结语
家庭暴力的适用对象不能超出通常意义上的家庭成员的范畴,不可以将家庭成员的外延的理解突破“亲属关系”这个大的范畴,否则势必出现法律虽然调整了人与人之间因暴力侵权所产生的法律关系,但与维护家庭的和谐却没有关联或没有直接关联的情形。对于什么样的行为由家庭暴力防治法来规制,应该重点对家庭中强势一方为维持和达到对家庭控制的暴力进行遏制或消除,而对于一般的家庭矛盾与冲突不宜纳入家庭暴力的范畴进行调整,无视家庭对家庭冲突或家庭矛盾的自我消化功能,或者简单地从负面理解这种功能,势必造成家庭暴力防治法的越俎代庖,不仅不能起到维护家庭权益的目的,反而有可能激化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会对家庭成员的隐私权和家庭自治权益造成损害。
(作者单位:中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