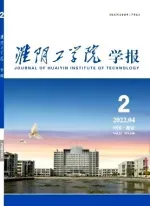中西饮食文化差异之跨文化比较
戴跃侬,陆 涓
(1.扬州大学 组织部,江苏 扬州 225009;2.扬州高等商务职业学校,江苏 扬州 225009)
饮食文化虽然在分类上常被定位为表层文化,但其各个层面无不受到深层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价值观的支配与引导。在任何文化体系中,价值观是最稳定的,不会轻易因外来文化影响而改变,因而一个民族的饮食文化传统也不会轻易地被同化。从中西方不同价值观的角度去审视彼此饮食文化的差异,并且遵循一定的交际原则,来关照不同饮食文化所体现的价值诉求与文化内涵,不仅可以提升跨文化交际的意识与能力,而且可以增强对不同民族饮食文化的宽容、理解与鉴赏。
1 中西方饮食文化语义表达的特点与差别
由于地理分布导致的自然环境差异等原因,不同民族形成了具有各自特点的文化体系。中华民族主要在陆地、平原上生活,并以种植为主,因而其文化形态是一种农耕与陆地文化;西方民族主要以游牧与捕猎为生,因而其文化形态则是一种畜牧与海洋文化。[1]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充分反映了彼此在生活场所、自然物产和生产方式上的差异,这些差异也在饮食文化上得到充分体现,并且可以从有关饮食文化的一些基本语义的表达上得以甄别。
1.1 中华饮食文化基本语义的表达特点
从词源分析,关乎饮食文化的关键词分别为“烹饪”、“饮食”以及“餐饮”。宋代编纂的《集韵》中云:“烹,煮也”;[2]《说文》中云:“饪,大熟也”;[3]简而言之,烹饪就是“将可以食用的原材料运用特定的加工方法将其做熟”之意。“餐”在汉字里是形声字,从“食”之声,本义指吃。《说文解字》释义为:“餐,吞也”,《广雅》中则注为:“餐,食也”。可见,“餐”最初既有进食之义,又被引申指称所食之物。“饮”和“食”在汉字里均为会意字,从出土的甲骨文中可以看到:“饮”象征人以舌取坛之酒,表喝之意;而“食”则从“饣”声。段玉裁注“饮”为:“可饮之物,谓之饮”[4]。由此可以推断“饮”、“食”两字在古代既是动词,亦是名词,而且“饮食”一词在流传下来的文献中屡见不鲜,说明我国早已使用该词。如《宋史·司马光传》中就有:“饮食所以为味也,适口斯善矣。”之类的描述。综上所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常以“餐饮”和“饮食”两词来表达“吃喝”之意,并兼具名词与动词的含义。当然,“饮食”一词由于出现较早,而且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内涵较为丰富,使用较为广泛;而“餐饮”一词随着时间的推移,则引申为专指提供食物这一行为,并成为一种行业的指称。
1.2 西方饮食文化基本语义的表达特点
从英语有关表达饮食文化基本语义的一些字义分析可知:表达烹饪之义的单词分别是“cook”和“cuisine”。“cook”原本源自拉丁语“coquere”,所要表达之意为“A person who prepares food for eating”或“To prepare food for eating by applying heat”;[5]而“cuisine”则源自俗拉丁语“coquia”,意为“food、fare”或“A characteristic manner or style of preparing food”。[6]而表达语意为饮食的词组则分别为“food and drink”、“bite and sup”。其中“food”一词是由中古时期的英语“fode”演变而来的,并且“food and drink”的含义较为宽泛,比较接近中文里的“饮食”一词;“bite”来自远古时代的英语“bitan”,“sup”则源于中古时期的英语“soupen”。因此,在英语中“bite and sup”不仅是指饮食这一活动,更是将与之相关的礼仪也蕴涵其间。而表达语意为“餐饮”的单词或词组有“catering”和“food and beverage”,其中“catering”的原型“cater”来自古法语“撒(achater)”,“beverage”则源自古代的法语“beverage”。对英语词义中有关饮食和餐饮之类的词或词组进行溯源,可以发现其所代表的意义中,商业性、服务性的功能较汉语更为突出。[7]
1.3 中西方饮食文化基本语义表达特点的差别
通过比较中西方饮食文化基本词源字义的表达特点,可以不难得出结论:西方基本语义中食物的功利性成份占据着主要位置,饮食行为满足人的生理营养需要的功能更为突出。因而西方人加工食品时,为不致破坏营养,烹饪过程较为简单,有些食物甚至多为生食。而中华民族则既有形式美的内容也有主体美的内涵,以满足生理和心理等方面的需求,故将加工饮食称为“烹调”。所谓“烹”是将食物做熟,而口味变化,则主要靠“调”。“调”可以说是中华饮食特有的方法。所谓“调”就是指食物原料之间、原料与配料或原料与调料之间相互配伍,并通过各种加工方法,使之成为美味可口的食物,给品尝者以愉悦的过程。这显然比西方所谓的“cook”要技高一筹,并且包含了其难以理解的蕴味。因为“cook”只是将食材弄熟而已(只包含烹的部分),而“调”则是将食材审美化、艺术化,从而创造出美味佳肴。食物原料有各种不同的性能和味道,“调”就是去掉这些异味,使之更合口味。此外还要调色、调形,其中最重要的是调味。“味”大多只有通过“调”才能实现,亦即通过人为加工,使原料和佐料的气味相互渗透,进而达到美味的境地。这种调和五味的方法,实际上是“天人相应、阴阳和谐”的理念在饮食文化中的体现。从文化史的角度考察,烹调是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民族才具有的能力。动物只知食而不知烹,文化发展水平低的民族知道“烹”但不会“调”,所以“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高层次的生活艺术。“调”的产生是有条件的,一方面,它以人的味觉发达程度为基础,随着人类的不断进化,人的各种感官和感觉的敏感度也越来越高,人对感觉对象的要求也日益提高;嗅觉、味觉的进化,也要求人们想方设法做出更加香醇美味之物,烹调也就应运而生;另一方面,人们对于自然万物的认识越来越丰富,为烹调技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天地。如何将各种食料和佐料有机地合成崭新的味道,不仅需要长期实践经验的积累,而且需要富有创造性的艺术想象力与审美思维。正如不是各种颜色搭配都会美观、所有声音合奏都会悦耳一样,味与味的调和亦非都能可口,不顾原料和调料间的味性是否相配,一味将好味道的原料混在一起,而不注意各种原料间的搭配与比例,尽管都是上佳的原料,但调制出的食品却不一定气香味美,更勿论艺术形式。因此,在跨文化交流时,不仅要注意介绍中式烹调中刀工、火工、调味等特点,还要注意其中所贯穿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天人相应、阴阳和谐”等理念。因此,中西方饮食文化不仅在基本字义上存在着差异,而且在核心概念上差异更大。西方看重“烹”,而忽视“调”;中华民族不仅重视“烹”,而且更加侧重“调”。
2 中西方饮食文化差别及其外在形态表现
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经过长期筛选并积淀下来的生活方式之总称,这其中包含了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虽然文化没有国界,但各个民族的文化又是以一定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因而必然具有本民族的鲜明特点。饮食文化同样也是如此,当一个民族在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餐饮理念、烹饪工艺和饮食习惯后便构成了自身的饮食文化。中西方民族由于传统文化的不同,造成了彼此在饮食文化上的差异,具体表现在饮食观念、内容及方式等方面。
2.1 中西方饮食文化在观念上的差别
中华传统文化在发展进程中十分注重筛选与积淀:一是讲究实用。对于那些看似与生活无关或者认为不实用的东西一概摒弃,这就形成了一些与生活相关的实用技术自古以来就十分发达的现象。烹饪技艺由于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故其发展水平毫无疑义是其他民族只能望其项背的。对此,孙中山先生曾感慨道:“我国近代文明,事事皆落人之后,唯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经历了鸦片战争的耻辱和抗日战争的残酷,中华文明在近代被西方冲击得七零八落,然而中国餐馆却在每一片大陆上落地生根、兴旺发展,如此强烈的对比,足见国人对饮食的重视程度和中华饮食文化的生命力。但是,一些与人们生活不大相关的非实用技术在中国则未必重视,如火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西方用之造成了枪炮弹药,而我国却更多地用于烟花爆竹制造。二是追求仁爱。孕育于民族文化传统之中的饮食文化观念,虽然是在食物加工及品尝鉴赏过程中形成的,但却深受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思维的影响,因而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理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饮食观念自然也就存在一定的差别。中华民族崇尚自然,强调天人合一,以社会为本位,认为求同存异才是美、内外和中才是善,于是在生活中倡导以和为贵,在烹饪上则主张以五味调和为美;西方民族强调天人分离,崇尚个性,于是在生活中追求新奇独特,在烹饪上则以简单、生冷为美。
2.2 中西方饮食文化在内容上的差别
美国民俗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性格文化模式”理论认为,中国人所具有的文化性格是类似于阿波罗式的古典风格,而西方人的文化性格则近似于浮士德式的现代风格。这种文化性格上的差别也导致了饮食文化上的差异,中华民族在选择食物时以植物为主,而西方则是以动物为主,因此有学者认为这种不同的饮食结构也塑造了不同文化性格——中国人性格类似植物,而西方人性格则类似于动物。而且这种不同类型的文化性格还会投射到价值观及其行为特征上,外在区别就是:中国人喜欢安居乐业,安分守己;而西方人则更具有冒险精神,喜欢征服。孙中山先生曾在《建国方略》中对中西方饮食文化的差别作过深入的研究和精辟的阐述,他指出:“中国常人所饮者为清茶,所食者为淡饭,而加以蔬菜、豆腐。”而“欧美人之所饮者独酒,所食者腥膻。”[8]在对食物的选择上,中华民族受佛教的影响较大,认为动物是“生灵”不可杀之而食,而植物则是“无灵”之物可食。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所以从先秦开始就形成了少肉多粮、以谷蔬为主的饮食结构。西方民族则秉承“实用主义”思想,重视饮食的营养价值,力求口味清淡和膳食结构上的营养成份均衡。在食物选择上以肉食为主,在饮食风格上以简单快捷为主。林语堂先生曾评价说:“西方人的饮食观念不同于中国,英美人仅以‘吃’为一个生物的机器注入燃料,保证其正常的运行,只要他们吃了以后能保持身体健康、结实,足以抵御病菌、疾病的攻击,其他皆在不足道中。”[9]
2.3 中西方饮食文化在形式上的差别
各民族不同的饮食观念及其投射到文化内涵上的差别也决定了它们在饮食风格与方式的差异,而这些不同的饮食方式,又反过来会对民族的性格产生影响。在饮食加工方式上,中华民族一直视烹饪为艺术,并且创造出诸如蒸、煮、焖、炖、煨、烧、爆、烤、煎、溜、炒、烹、炸、拌、烩、拔丝等多种多样的烹饪方法,而在原材料的粗加工上又有片、块、条、丁、卷、段、末、汁等多种多样的形状区别,制作出来的花式品种也是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同时,由于制作者对原材料、调料、食谱的理解与把握的不同,即使同一道菜也会有不同的口味或造型;而西方民族只关注食物成份够不够营养标准,而不在意食物的种类、样式和工艺。整个烹调过程都严格按照科学标准去制作,主料、配料、调料的量精确到克,烹调的时间也精确到秒。西餐原材料的粗加工一般只有片、块、丁等几种简单的形状,烹调手段也只有煎、烤、焖、炸等可数的几种工艺方法。在餐具的选择上,中国人无论是在平常的家庭用餐,还是正式的宴会场合中都习惯于用筷子,其它餐具虽然比较简单,但讲究与食物之间的搭配和谐,因而会备有各种质地、规格、造型、颜色各异的杯、盘、碗、勺、碟等,让人们在品尝美食的同时,进一步从与之相呼应的盛器中感受到艺术之美;西方民族则习惯于以刀叉为主要餐具,再辅以各种类别的杯、盘、碟、匙和盅。西方人虽然对食物的制作不是太重视,但却十分注重对餐具的设计与制作,一般将之分为瓷质餐具、金属器具、玻璃器皿、上菜盘和厨房用具五大类,并力求使之更具有观赏性和趣味性。其中各种器皿又有着其各自不同的种类和用法。如瓷器多用作茶杯和咖啡杯,玻璃器皿多为酒杯和水杯,刀叉多为金属器具。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爱得华·霍尔(Edward Twitchell Hall Jr)曾提出“单一性”和“多样化”两种不同的文化模式,认为前者严格守时不失约,后者则常不守时而爽约。前者多为西方人,而后者以亚非拉地区的人居多。如是,中国人在赴宴时常“姗姗来迟”,而在西方国家,若被邀者迟到10分钟以上则被视为没有教养、不懂礼仪,或者不尊重他人。在用餐的座次安排上,中西方也有着较大差别。中国人通常视面南为尊、面北为卑,因而按“南尊北卑”的习俗来入座,与“面南称孤”、“面北称臣”的官场文化一脉相承。而在西方社会,提倡人格平等,其座次安排并无高低贵贱,而以人身安全作为首要条件。因为西方人持刀叉就餐,为了不致让客人产生不安全感和防范意识,常将主宾安排在主人的右侧,以消除持刀右手有可能构成的威胁,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以右为宾、以左为主的礼仪。
3 中西方饮食文化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别
价值观是文化体系内涵中最深层的部分,也是跨文化交流的核心。台湾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一书的序言中说:“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10]正是由于中西方民族文化传统存在一定的差异,因而在饮食文化的价值取向上也同样存在着种种差别。
3.1 中西方价值观导致各自对待饮食持不同态度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之说,足见饮食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之高。中国人将饮食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它不仅是维持人生存的基本手段,而且还有用以维持身体健康之功能,所以又有“药补不如食补”之说。中国人认为饮食之目的除了果腹充饥之外,更重要的是满足人们对美味的追求。因而讲究“色、香、味、形、器”,注重“五味调和”是中华饮食文化的精要之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饮食行为在中国早已不再是停留在果腹充饥或者说满足口腹之欲层面上的生理需求,而是更多地将其上升为诸如社交沟通、表达情感等超越了一切物质形态或工具层面上的精神需求,这种现象也充分反映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其中最为典型而又常见的现象是:中国人见面寒喧时的那句“吃了吗?”由此可见一斑。而且以饮食行为表达人们情感的活动几乎伴随着人的一生:从婴儿呱呱坠地到满月、从一周岁生日到以后的每一届十的生日,诸如弱冠、而立、不惑、知天命、花甲、古稀之年等(有人甚至更为频繁),都要觥筹交错庆贺一番;结婚时要大设酒宴以示喜庆,及至寿终正寝也得大摆筵席聊表追思。“有朋自远方来”先“接风洗尘”,后设宴“饯行”;人逢喜事要把酒临风,心有不爽则借酒浇愁……。总之,饮食活动背后赋予了各种丰富的心理预期和文化意义,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于饮食行为的重视程度。[11]而在西方国家,饮食仅仅作为一种生存的必要手段和交际的方式。因此,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划分为五个层次时,饮食则被视作最低层次的需求划在第一层,其它需求则均在其之上。
3.2 中西方价值观导致了饮食行为取向上的差别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强调整体功能,倡导“天人合一”,追求“阴阳平衡”,认为只有“和”与“合”才是人生追求最美妙之境界,体现在饮食文化上就是讲究“五味调和”;而西方国家重视形式结构,主张“天人分离”,反映在饮食观念上则是突出个性。可见,中西方不同的哲学思想不仅影响到其民族文化理念与思维方式的形成,而且会在各自的饮食观念上产生较大的差别。在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上,则明显体现出“和合”与“分别”两种不同的文化特征。[12]这种价值观上的差别投射到菜品的制作上,则可以看到中西餐外在形式上的明显差别。因而在中餐的制作上无不体现出“和合”的理念:中国人在烹制食物时,非常强调在保留原料自然之味的基础上,要用“阴阳五行”的原则来指导,从而达到“五味调和”。这种调和行为既要注意时序,又要合乎时令,才能达到“美味可口”的烹调标准。所以,中国人喜欢用至少两种以上的原料和多种调料来调和烹制菜肴,如此一来,虽然各种原料或辅料都几乎失去了各自原有的本色,但却会产生一种全新的美味。如福建名菜“佛跳墙”,内有山珍海味等多种主料,还有各种各样的辅料和调料。因而从这道菜里再也辨不出各种原料的本味,品尝到的是一道美味佳肴。这样烹制出来的菜品,虽然个性全被湮没,但整体上看却令人叫绝,这与中华传统文化中贬抑人的个性、强调均等、重中和的中庸之道是相通的。而西方人做菜的原则是泾渭分明,在西餐正菜中,各种原料是互不相干的:鱼就是鱼,决不会像中国人那样富有想象力,加入羊肉后而谓之“鲜”,纵然原材料之间有搭配,那也是各自烹制加工好后混合而成,只有罗宋汤之类的少数汤菜,才有可能将不同原料混在一起。西方民族重分别与突出个性的价值观由此一览无余。此外,在用餐方式上,可以更加明显地看出中西方价值观念在饮食文化上表现出来的差别,可以说是哲学思维、社会心理、民风民俗等方面的文化差异的集中投射,从而成为中西方饮食文化中最明显的差别之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采用聚食制,这种用餐方式得以长期流传下来,也是中华民族重视血缘亲属关系和家族观念在饮食文化上的反映。西方人通常采用分食制,习惯于各人独盘独碟。在家庭用餐时,每个人的食物都是提前分配好种类、定量的。在聚会时,主宾双方也是各点各的食物,不必考虑客人的口味喜好和食欲需求,用餐时主宾只食用自取的食物,不会相互谦让,餐毕也是各付各的账,最具有代表性的形式就是自助餐。西方人用餐时喜欢环境安静幽雅,且没有固定的座位,如果想清静,可以选择偏僻的位置独自用餐;如果想凑热闹,或者利用用餐时间与他人交流,也可以自由走动,这种用餐方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人对个性、对私人空间的尊重。当然,无论中西方民族,举办者都会抱有一定的目的来设宴,通常都将此作为交友沟通的手段,只不过在中式宴会上更加注重与所有出席者的交谊,而在西式宴会上更多的是重视相邻宾客之间的交流,并没有像中国人那样从文化的意义上将一次宴请赋予具有丰富内涵的“使命”,一般他们在用餐时只是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一些简单的交流与交际,更多的场合是喜欢独自用餐、享用美食。[13]总之,中西方饮食文化在形式上的差别,集中体现了东方重“和合”,西方重“分别”的不同民族价值观。
[1]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68.
[2]张玉书.康熙字典[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1034.
[3][4]许慎.说文解字[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1250,2635.
[5][6]霍恩比.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6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486,561.
[7]杨铭铎.饮食美学的内涵剖析[J].扬州大学烹饪学报,2008(2):5 -7.
[8]黄丽.从饮食文化看中西方价值观的差异[J].安徽文学(下),2008(1):258.
[9]林语堂.生活的艺术[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45.
[10]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37.
[11]周延.谈“吃”文化在中西文化中的差异与翻译技巧[J].首都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360.
[12]蒋艳.中西饮食文化差异的原因分析及其研究意义[J].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7(4):61.
[13]卞浩宇.论中西饮食文化的差异[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