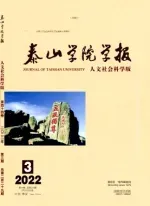芦墟山歌《五姑娘》中的生态意象解读
蒋玮
(苏州博物馆民俗部,江苏苏州 215001)
一
芦墟山歌主要指流传在以苏州吴江市东的芦墟镇为中心的分湖流域,用芦墟当地方言传唱的吴语歌谣,是吴语地区民间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乾隆吴江县志》卷39“声歌”载:“吴江之山歌,其辞语音节尤为独擅,其唱法则高揭,其音而以悠缓收之,清而不靡,其声近商,不失清商本调,其体皆赠答之辞,或自问自答,不失相和本格,其词多男女燕私离别之事,不失房中本义,其旁引曲喻,假物借声之法,淳朴纤巧,无所不全,不失古乐府之本体,实能令听者移情。”[1]给予了吴江山歌很高的评价。而据徐文初先生考证,芦墟山歌正是吴江山歌的源头。可见最迟至清乾隆年间,芦墟山歌已呈风行之势。
自清中期伊始,吴歌《五姑娘》便在吴越两地普遍流传,以五姑娘和徐阿天的“私情”为主线,以五姑娘等对哥哥杨金大、嫂嫂“辣椒心”的抗争为主题,描绘了19世纪中叶江南农村的生活风情。但各地流传的版本并不一致。如无锡的五姑娘仅为中篇,结尾是个大团圆结局;在青浦、嘉善、吴江另有一些百余句长的五姑娘,多用十二月花名套唱,较为简略。而由陆阿妹演唱,张舫澜、马汉民、卢群等在苏州市吴江县芦墟、莘塔、北厍一带搜集,并于1981年整理定稿的长歌《五姑娘》,则无疑是这一民间口传作品较为完整而详实的版本。
芦墟长歌《五姑娘》中所蕴含的生态意象,归根结底是与吴地深厚的文化积淀紧密相关的。自三千多年前泰伯南奔自立勾吴,江南地区原有的地方土著文化与泰伯、仲雍兄弟带来黄河流域的先进的中原文化便在吴地相交融。从源头上看,早期吴文化包孕了南北特色,兼容并蓄。在历史发展中,吴文化先以泰伯最早的建都地无锡梅里为发祥地,后随着都城的迁至阖闾城而将核心也移至苏州。苏州自此而成为吴文化鼎盛时期的典范。浓郁的水乡风情、丰富的历史和自然遗存、秀丽雅致的生存条件都为苏州塑造着吴地典型的带有江南风貌的人文生态环境,一直影响至今。这些吴地特色也深深影响着芦墟山歌的传唱。而吴地各区域间的自然地理、语言氛围、生活习俗等大同小异,但山歌“五姑娘”在各地的版本却不尽相同,特别是芦墟长歌《五姑娘》,结尾带有沉重却似乎已释然接受的悲悯情怀,除了宗教影响外,也许还与历史上苏州城屡建屡毁、又屡毁屡建,苏州人民看尽繁华又须面对满目疮痍,不得不形成的坦然、坚忍的文化氛围相关。
长篇《五姑娘》是芦墟山歌中极为珍贵的代表作品,它的发掘出现,打破了吴歌史上无长篇叙事诗的说法,甚而引发了吴语地区长篇吴歌的搜集热潮。自清中期伊始,吴歌《五姑娘》便在吴越两地普遍流传,版本不一。但在1963至1981之间,由陆阿妹演唱,张舫澜、马汉民、卢群等于苏州市吴江县芦墟、莘塔、北厍一带搜集整理的版本无疑是《五姑娘》这一民间口传作品较为可靠、完整的版本。本文以金煦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中国·芦墟山歌集》中收录的《五姑娘》为主要的文献来源,依次从人文建筑、自然意象、人生境界等三个层面入手,意在对《五姑娘》中的生态意象做出解读。
二
人文建筑是《五姑娘》之生态意象群落中的主体成分。所谓人文建筑,在《五姑娘》中,例如桥。吴文化的特质在乎水,是水非海水、江水,乃河水、湖水、塘中之水,所以,桥是吴地人家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和真实写照。在《五姑娘》中,故事演进的点滴里,几乎处处不离桥。桥是《五姑娘》之生态意象群落的主要成分,意味着吴文化之生态视野并非荒野哲学之荒野,而是以民居为灵魂的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总汇。
桥蕴含着故事的由头。在《五姑娘》的“歌头”部分,首段便写到:“山歌勿唱忘记多,搜搜索索还有五千零四十八只响山歌,吭嗨吭嗨挑到吴江东门垂虹桥浪去唱啊,解开叉袋口汆满东太湖。”[2]《五姑娘》在哪里上演、唱响?垂虹桥,这样一个由叙事者首先拟定的叙事场景。垂虹桥,位于吴江松陵东门外,初建于北宋庆历八年(1048),南宋德祐元年(1275)毁于兵乱,重建为85孔,元大德八年(1304)年增至99孔,泰定二年(1325)年改建为连拱石桥,72孔,长500米,桥中有方亭,亦名“垂虹”。明永乐二年(1404)年改砌桥面,翼以层栏,明成化、清康熙及嘉庆年间经历过不断修缮。《五姑娘》在这座桥上被讲述、被聆听、被传唱,可以说是随意借着一个由头,但似乎寓意着一种文化沉积的深厚力量。因为正是在这里,米芾题有:“垂虹秋色满东南”[3],陆阿妹与米芾使用了同一个动词:“满”,而姜夔则道:“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3]姜夔欲发布新作的地点,亦是此桥。是故,笔者尝想,芦墟所谓山歌,形似水调,亦或抒情叙事者的桥头讲唱,在这种文化氛围里,山毕竟是遥远的,与人们息息相关的,实乃水,以及水上之桥。
在《五姑娘》的第3章“结识私情”第2节,有一段细节非常重要,即五姑娘的爱侣阿天剪了一块湖色纺绸送与五姑娘,五姑娘继而要求阿天买来“百花三姐里格小炉灶浪格只绣花针”[2],决定亲自在这块纺绸上刺绣的一段,该段讲唱,使得我们得以窥见五姑娘对于一个艺术化了的彼岸世界的全面构想。五姑娘到底想绣些什么以表达自己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在接下来的大段文字里,可知她期待视野的主体部分包括:1.杭州西湖景致六条桥;2.外、里六桥;3.十八只麻雀;4.嘉兴府的三塔湾、四城门、五里亭、六里街、七仙浜、八仙桥;5.东西塔;6.南小巷搭北三泾、青石港上端木桥;7.王江泾长虹桥;8.平望南北大桥;9.八坼吥不桥;10.吴江三里桥;11.夹浦桥;12.七十二孔长桥;13.苏州觅渡桥;14.苏州七塔八幢九馒头;15.三百七十二条桥;16.上下水桥;17.苏州文昌阁; 18.无锡皇甫墩;19.丹阳县;20.登州府;21.南京十三层宝塔;22.北京三城;23.镇江江口[2]。以上23条基本项目,共同组成了五姑娘内心的“天上人间”,而其中近半数,皆为本文所着重强调的核心词:“桥”。换句话说,五姑娘所追求的奇幻“梦境”中,罕见奇花异草,而多有各式各样的跨水之桥。事实上,由桥以及其他人文建筑构成的世界正是五姑娘真实存在的现实世界——她的理想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升华,她的破灭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疏离。在《五姑娘》的“歌尾”部分,天色大变,“飞沙走石碗口粗格大树连根起”[2],听众的视角被带到了乌云阵阵,风阵阵、雨阵阵、雾阵阵,迷迷茫茫天地昏沉的太湖,在这里,浪高三尺如怒吼之声、撕裂之身——没有桥,没有桥的世界是一个陌生的,令人恐惧和哀伤的世界,属于死亡的世界,而隔离于生生不已生生不息之生态世界。
三
自然意象是《五姑娘》之生态意象群落里的内在逻辑。所谓自然意象,在《五姑娘》里,季节和劳动对象得到了特别强调。吴文化是重视节令、岁时节俗的文化,这不仅是因为此地四季分明,更是吴地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把时间物态化,把习俗时间化的结果——它不是一个物理结果,而是一种心理结果、文化结果。在《五姑娘》的叙事层面上,被时间化了的自然意象成为推动叙事的内在逻辑线索。另外,《五姑娘》中的自然意象大多作为劳动对象的面目得以呈现,它们亲近于人类世界,拒绝荒野。
自然意象是被安排在时间序列中的。《五姑娘》第6章“姐妹相会”的第3节,描述了五姑娘的姐姐,四姑娘被姑嫂迫害后数年来的苦难命运。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苦难命运的时间跨度长达8年,且在这8年中,四姑娘被贩至远离吴文化区的广东,但对于这8年的异乡苦痛经历,讲唱者却以“十二月花名”做出了本地化的简笔勾勒。它包括:正月茶花开放满园红;二月杏花一开白洋洋;三月桃花开来满枝梢;四月蔷薇花开放墙浪爬;五月石榴一开红似火;六月荷花开勒池塘里;七月凤仙叶子长;八月桂花开放香飘飘;九月菊花开勒庭院中;十月芙蓉花开朵连朵;十一月水仙花开白片片;十二月腊梅一开风雪来。[2]这便促使我们思考以下问题:十二月份与十二花种是否具有某种固定的组合?答案是肯定的。显然,该组合并非《五姑娘》之特例。正如,1987年11月,由沈三宫演唱,唐守成采录的《珍珠塔》,同样提到正月茶花、二月杏花、三月桃花、四月蔷薇、五月石榴、六月荷花、七月凤仙、八月桂花、九月菊花、十月芙蓉、十一月水仙、十二月腊梅之序列,对于各花种的样态描述与《五姑娘》基本一致;另1985年8月,由赵永明演唱,郁伟采录的《玉蜻蜓》,采用的也是十分接近的组合,区别仅在于把正月列为梅花,八月列为木樨,此种安排亦可见于1987年7月,由蒋连生演唱,袁永观采录的《十二对夫妻》。进一步考察芦墟山歌便可知道,类似十二月份与十二花种之固定组合甚夥,为什么?“十二月花名”是一种套唱方式,究其缘由则在于此系与吴越区域性的物产、风俗密合,蒋连生另有《各地名优物产歌》,可应证这一结论。这意味着,四姑娘8年来居留于广东的过往,被浓缩了,被异地化了,被一种强大的包容裹挟着自然意象的时间“套路”囊括和穿透了,在这一片段里,我们读到的是个人对于文化统序的自觉让步和地域对于自然生命的吸纳与融摄。
在《五姑娘》中,人物形象可位列于两种极端:非劳动者与劳动者。非劳动者与劳动者或许可以阶级的观念来加以区分,但更是一种与自然物象接近程度的分判。嫂子“辣椒心”与哥哥杨金大构成了非劳动者集团;长工徐阿天、五姑娘和四姑娘构成了劳动者集团;嫂子与阿天分处于此二集团的“极端”。嫂子作为非劳动者的代表,完全脱离于自然劳作,她拥有来自家族荫承的财富,哥哥艳羡、屈从于这笔财富,财富本身却代表着绝对的恶。阿天作为劳动者的完美表帅,最大程度地接近于自然,是道德的体现者,他的外在形象丝毫没有因为身处底层而受到损害,反而被唱成“相貌堂堂格徐阿天”[2],甚至一度诱发了嫂子“查特莱夫人”般的性幻想。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有三个过渡性人物:哥哥、四姑娘、五姑娘。哥哥的“变质”仅仅服从于戏剧化、面具化的角色安排,值得注意的是,首章“杨家门墙”中提到,“金大种田、烧窑、贩盐里里外外生活做,两个阿妹勒拉田沟沟里捉行蟆,行蟆大仔变田鸡,巴望阿哥早早成亲有个相帮日脚越来越好过。”[2]但迎娶嫂子后,哥哥却突然变得昏聩、暴戾与无能。这在某种程度上仅仅是为了服从于文意需要,故而使哥哥这一形象显得扭曲、扁平。四姑娘是五姑娘的角色延伸,她每每作为事件的“触须”、铺垫者和帮助者出现,故在叙事的过程中显得零星而闪烁;五姑娘不仅接近阿天,且与后者组建家庭,几乎使爱情成为劳动能力的体现。可见,与自然世界接近的程度与人格德性的量度成正比。只不过,所谓的自然世界非自然物本身,而集中表现为劳动对象。五姑娘和阿天脱离苦海后,他们来到太湖,在西山脚下过起了期盼已久的田园生活,长达三年,但叙事者仅用3段12行文字对这段经历加以概括。当自然作为人类行为“操弄”的“途径”时,是会被人类的意义世界所忽略的。
四
人生境界是《五姑娘》之生态意象群落的深层内涵。所谓人生境界,在该文本中,特指一种带有悲剧性的寂灭情怀。在生态的世界里,所有的生命都值得尊重,不仅包括自然物,也包括人。人的命运通常被表现为进化论式的成长,亦或循环论式的补偿,但在《五姑娘》中,人的命运往往带有一种生命耗散体验的苍凉与悲苦。这意味着,吴文化中潜藏着佛教超越于福佑、报应,更深层次的内心的彻悟感,这种彻悟感使人物更加接近其在生态世界中的自然实相。
“中国式”的悲剧从来都不“彻底”,落实下来,无论是窦娥冤还是杜十娘,往往用阴魂来充当补偿性力量,惩恶扬善,实可谓悲剧之“道德性”的高扬和“悲剧性”的退让——传统中国文化一向追求“团圆”——在结尾处,谋求一个合乎社会道德规范的交代,才是唱而不衰的歌。然而,《五姑娘》,起码在芦墟山歌的版本中,“悲剧性”得到了彻底贯彻。为什么?因为吴文化中有佛学的底色。2004年2月,郁伟采录了一首袁大觉演唱的儿歌《太阳亮堂堂》,这首儿歌唱到:“太阳出来亮堂堂,翻转屁股朝里床,里床一个蛋,蛋里有个黄,黄里有个小和尚,钻出头来吃礱糠,屋里礱糠全吃光,端起碗来喝黄汤。”[2]这不是一般的儿歌,颇有佛学之意,这是西域佛教中“吐火”异相所形成的“吞吐”信仰。屁股、蛋、黄、小和尚、礱糠,是一是异?非一非异,非非一非非异,此乃薪火相传的无我论,般若一系的中观道理,而这样一条深不可测不可知的道理,通过吴文化的演绎,简化为一首琅琅上口的儿歌。这就是吴文化的魅力,对《五姑娘》亦有深层次的影响。也正是因为这种影响,人们才能真正认识到人类自身的局限性,驱除人类中心主义的魔咒,复归于他本真的自然模样。
五姑娘死了,阿天死了,四姑娘死了,被溺死,被处死,被烧死,上文所述的“正义”的集团,皆归于寂灭、死亡,且几乎共同具有主动赴死的自杀意味。同样是儿歌,2000年5月张俊采录过一首13岁女孩姚霞清的儿歌:“萤火虫,夜夜红,飞来飞去捉青虫,青虫捉勿着,野菱戳只脚,到荷花塘里讨膏药,膏药讨勿着,烂脱半只脚。”[2]五姑娘,就是一只萤火虫,只不过她的“创面”较大,以至于连带至姊妹及爱人,皆灰飞烟灭,然而,这是谁的过错么?这是生命的实相。萤火虫知道自己脚要烂掉,会不去捉青虫?不会,因为它必须去做这件事,这是生命本能使然。一个细节启人深省,四姑娘事实上遭遇了比五姑娘更凄惨的命运,五姑娘可怜,但她起码还有过爱情,以及爱情的结晶,而四姑娘连爱情都没有,在整个事件中,她死得最早,死于虚无。《五姑娘》采取的是一个复仇失败的话语模式。四姑娘死后,阿天和五姑娘去“寻找”四姑娘,本身就带有复仇以及拯救意味,只不过,叙事者自己也意识到,阿天和五姑娘不具备复仇者所应当具备的力量,不得不以失败告终。笔者常怀想,如果这是一个简单的叙事文本,故事也许会在阿天和五姑娘逃离虎穴、到西山过上世外桃源般的生活时便结束,但《五姑娘》没有,它选择继续说下去,直到所有的希望都破灭,所有有自然、道德、社会价值的人都死去了。这就是悲剧,真正的悲剧,命运悲剧也好,性格悲剧也好,人生脆弱的一面就这么真实地被展露出来。这种基调应该是沉浸于佛教的吴地人民特有气质在民间口传文学中的具体实践:某种意义上,人生本来就是悲惨的。《五姑娘》在不同的文化区间里皆有流传,但坚持如是结尾的,只有芦墟山歌的版本。在这一层面上,芦墟山歌《五姑娘》无疑具有深远的宗教意义。
[1]陈荀纕,丁元正,倪师孟,沈彤.中国地方志集成·乾隆吴江县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2]金煦.中国·芦墟山歌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3]刘伟明,朱威.苏州古桥文化[M].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