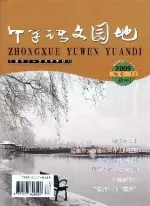称呼变化有意蕴
徐德湖
文学作品中称呼的变化,往往蕴意丰富,如《一面》中,阿累称鲁迅为 “同志”“朋友”“父亲”“师傅”“战士”“先生”,《我的叔叔于勒》中,菲利普夫妇先称于勒为“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人”“好心的于勒”“有办法的人”,后又称之“贼”“讨饭的”“流氓”;再如鲁迅之称阿长,朱自清之称梅雨潭的绿,胡屠夫之称范进,奥楚蔑洛夫之称小狗,夏洛克之称鲍西娅等。但有些作品中的称呼,由于不如以上例子变化多而明显,或由于主要人物、主要事情的“遮蔽”,容易被读者忽视,教学中需要予以关注。现举出初中语文教材中几个例子,并简要加以品析。
一
吃完豆,又开船,一面洗器具,豆荚豆壳全抛在河水里,什么痕迹也没有了。双喜所虑的是用了八公公船上的盐和柴,这老头子很细心,一定要知道,会骂的。然而大家议论之后,归结是不怕。他如果骂,我们便要他归还去年在岸边拾去的一枝枯桕树,而且当面叫他“八癞子”。 (鲁迅《社戏》)
1.前文曾写道:“忽然间,一个最聪明的双喜大悟似的提议了,他说,‘大船?八叔的航船不是回来了么?’”选段“我”所称的“八公公”,双喜称“八叔”,可见双喜长“我”一辈。这暗应了上文“我们年纪都相仿,但论起行辈来,却至少是叔子,有几个还是太公”,“然而我们是朋友,即使偶而吵闹起来,打了太公,一村的老老少少,也决没有一个会想出‘犯上’这两个字来。”从看戏、偷豆等情节可见,孩子们确实是平等友好,而不论辈分上下的。
2.这里以“我”为叙述者,写双喜所虑。“老头子”其实是转述双喜对“八公公”的称呼,一是“八公公”年龄大了,俗话说,越老越糊涂,但他反而心细,这是反衬,所以说“一定要知道,会骂的。”二是这种“不好”的预感,使双喜改称“八叔”为“老头子”,似乎有些没大没小,不恭不敬,而且似乎 “我”的情感也被双喜同化了——不过这也体现了“我”和小朋友们是“一气”的——但孩子们情之所至,率真直言,又总让人感到纯真可爱,感到他们与“八公公”之间并无生分,也没有所谓“犯上”的禁忌,没有世俗的辈分秩序。“会骂的”前面没有说“一定”,可见只是用多了盐柴,有些心虚的推测,并无其他依据。孩子们议论之后,还想出了一旦被骂的对策,即“当面叫他‘八癞子’”,是“叫”,而不是骂;只是果真挨骂,才用出这种办法。由此,孩子们的天真、单纯可见一斑。结果到底如何,小说在这里留下了悬念。
3.“第二天,我向午才起来,并没有听到什么关系八公公盐柴事件的纠葛,下午仍然去钓虾。”按理说,八公公很细心,不会不知道盐柴的事,怎么没像孩子们预想的“会骂的”呢?六一公公的出场,使得我们恍然大悟。因为“我们”偷了六一公公的豆,他只是为“我们”“不肯好好的摘,踏坏了不少”,而感到惋惜,有些责备,其它并无什么;反而还送来 “一大碗煮熟了的罗汉豆”,给“我”和母亲。他是那样的宽厚、淳朴和善良。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测,八公公也根本没把盐柴的事放在心上,孩子们的担心多余了。有趣的是,八公公和六一公公两个人物,一暗一明,一虚一实,互相补充,互相映衬,展现了水乡劳动人民美好的心灵世界。孩子们称呼变化中所包含的“不良”情绪,对这两个人物形象,都起到了很好的反衬作用。
二
船长本已不耐烦我父亲那番谈话,就冷冷地回答说:“他是个法国老流氓,去年我在美洲碰到他,就把他带回祖国。据说他在哈佛尔还有亲属,不过他不愿回到他们身边,因为他欠了他们的钱。他叫于勒………姓达尔芒司,—也不知还是达尔汪司,总之是跟这差不多的那么一个姓。听说他在那边阔绰过一个时期,可是您看他今天已经落到什么田地!”(莫泊桑《我的叔叔于勒》)
1.船长在不耐烦“我”父亲那番谈话的情况下,称于勒是法国老流氓,说“法国”,是对于勒所在国籍的通常称法。后来说把于勒带回法国,称的却是“祖国”,这与前面称呼“法国”给人不同的情味感。祖国,自己的国家,是一个人的出生地,是故乡和家园所在。其中蕴含着船长对于勒的恻隐之心、怜悯之情。这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印证,一是船长“去年在美洲碰到他后”,就将于勒收留,直至现今;二是船长所说,“听说他在那边阔绰过一个时期,可是您看他今天已经落到什么田地!”“可是”“已经落到什么田地”,饱含着对于勒现状的慨叹,大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味。这或许就是船长要收留于勒,将它带回祖国的原因。
2.船长与于勒显然非亲非故,他要把于勒带回祖国,回到故乡,回到亲人身边,完全是出于同情,出于人道;而作为于勒亲人的菲利普夫妇,却避若瘟神。这其中隐含着的对比与衬托,同样从侧面突出了菲利普夫妇自私、冷酷的性格,增添小说哀婉凄凉的意味。
三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苏轼《记承天寺夜游》)
1.作者见“月色入户,欣然起行”,闲适可见。“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这里叙述兼有说明,所以称朋友为“张怀民”,“遂”,有不假思索意,隐含了两人交情深厚。“怀民亦未寖”,“亦未”,照应作者由“解衣欲睡”而“欣然起行”,蕴含了禁不住的欣喜之情。作者深感张怀民与自己志趣相投,同是沦落天涯的知音,而不由得直称“怀民”。范仲淹说“微斯人,吾谁与归”,苏轼也一定会感同身受吧。
2.正因如此,两人才没有见面的寒暄、絮叨等,而是心有灵犀,直接“相与步于中庭”,流连于明月清辉、竹柏影里。这如同影视镜头的切换,一切都显得十分自然。这样,文末“但少闲人如我两人者耳”中的“我两人者”,也就有了含蓄的铺垫。由此可感,称呼变化中蕴含的知己之情,在全篇也是意脉相承、婉转相生的。
四
可是每天早晨,我起来观看这被幽囚的“绿友”时,它的尖端总朝着窗外的方向。甚至于一枚细叶,一茎卷须,都朝原来的方向。植物是多固执啊!它不了解我对它的爱抚,我对它的善意。我为了这永远向着阳光生长的植物不快,因为它损害了我的自尊心。
……
临行时我珍重地开释了这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
离开北平一年了。我怀念着我的圆窗和绿友。有一天,得重和它们见面的时候,会和我面生么?(陆蠡《囚绿记》)
1.第一段文字中,“绿友”加上了引号,有两层特定含义。作者说“绿色是多宝贵啊!它是生命,……”他喜爱绿,渴望与常春藤为友;移情于景,而情景相生,所以,感到“绿叶和我对语”,感到常春藤十分的友好。这是一层。
更主要的是,由于“一种自私的念头”,“我”企图通过囚绿,来充分满足对绿的欲念,然而,却发现它总是向着窗外生长,并且总是那么固执,不能领会“我”的善意,损害了“我”的自尊。原来,常春藤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朋友。这是又一层。
2.“我”偏执的愿望,终于成了一种伤害,使“它渐渐失去了青苍的颜色,……好似病了的孩子。”直至临行时,“我”才“珍重地开释了这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永不屈服”,表明尽管“魔念在我心中生长了”,仍旧囚着它,但常春藤一直总是不屈不饶;“我”由此领悟到了它“永不屈服”的“人”的精神品格,所以称它为“囚人”,而且在开释它时,怀着“珍重”,“致以诚意的祝福”。其中蕴含着敬仰之情,不舍之意。
3.就在这囚绿的过程中,作者对常春藤的认识终于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不只是生命、希望、安慰和快乐,而分明是一种“永不屈服于黑暗”的精神化身。在异族入侵,祖国受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作者“赞颂中华民族渴求自由、坚贞不屈的精神”,(袁振声《〈陆蠡散文选集〉序言》)从常春藤身上找到了这种精神的象征意义,或者说感悟到了常春藤与自己深沉情感的契合,而视其为生命中的真正朋友。所以,北平沦陷一年后,作者说“我怀念着我的圆窗和绿友”,“绿友”上不复再加引号。
文本中称呼变化,形成差异,就会生成艺术空白,产生文本张力,而召唤读者结合语境和相关背景,揣摩、品味其中的意蕴。教学中,就可以作为教学内容选择与教学方法设计的关注点,作为引导学生解读文本的一种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