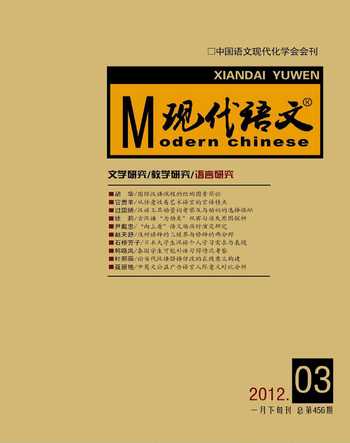文体学视角下《西风颂》两家译本之比较
毛跃祖 段汉武
摘 要:《西风颂》是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名篇。诗人借西风之名抒革命之志。诗中的西风在诗人的描绘下闻之有音、望之有形、念之有意,是一篇以文体见长的佳作。该诗由郭沫若第一次介绍到中国后,陆续出现了许多译本。本文选取两篇较有代表性的译文比较评析,探究两位译者在保留原诗的音韵、形式和意境方面的得与失,以期对提高英诗汉译水平有所启示。
关键词:《西风颂》西风雪莱
一
《西风颂》是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名篇。一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不知被多少人传唱,它激励着人们要在逆境中看到希望。西风在诗中作为“破坏者兼保护者”的形象具有“摧枯拉朽”的强大力量,诗人正是借助了西风这一形象来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呐喊助兴。全诗共分五节,前三节描写了西风横扫落叶的澎湃气势以及其风卷残云与翻江倒海的壮观场面。后两节将“我”引入诗中,颇有一番“与西风共舞”的豪迈意境,同时也很好地表达了诗人对革命的迫切向往之情。可以说,诗人和西风在诗中是一体的,诗人正是借助西风这一生动意象来抒发自己强烈的革命激情和愿望。然而,对于译者来说,在顾全诗歌的音律和形式的基础上,传神地表现出原诗的意境却并非易事。这要求我们在翻译诗歌的时候不仅要达意,还要求韵和重形,从而使“读者知之,好之,乐之”。[1]有人说,“诗歌不可译”,这是因为好的“诗歌的翻译则不仅要有文采,还应有意境。”[2]然而,诗歌并非绝对的不可译,只是对译者本身的要求也极高,一名好的诗歌译员也必定是一名优秀的诗人。
二
自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第一次将《西风颂》介绍到中国后,学界陆续出现了许多的译本。其中以郭沫若的译文最早出现,此后王佐良、江枫、卞之琳、查良铮以及杨熙铃等人均陆续翻译过该诗。这些译文各有所长,也各有劣势,体现了不同译者对诗歌文体的不同理解。鉴于篇幅限制,本文选取诗的第五节,通过对郭沫若和王佐良两篇具有代表性的译文的分析比较来理解译文在传达原诗的音、形、意方面所做的努力。下面我们先来品读雪莱的原诗:
Make me thy lyre, even as the forest is:
What if my leaves are falling like its own!
The tumult of thy mighty harmonies
Will take from both a deep, autumnal tone,
Sweet though in sadness. Be thou, Spirit fierce,
My spirit! Be thou me, impetuous one!
Drive my dead thoughts over the universe
Like witherd leaves to quicken a new birth!
And, by the incantation of this verse,
Scatter, as from an unextinguishd hearth
Ashes and sparks, my words among mankind!
Be through my lips to unawakend earth
The trumpet of a prophecy! O Wind,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王佐良译文 郭沫若译文
让我做你的竖琴吧,就同森林一般,
纵然我们都落叶纷纷,又有何妨!
我们身上的秋色斑烂,
好给你那狂飚曲添上深沉的回响,
甜美而带苍凉。给我你迅猛的劲头!
豪迈的精灵,化成我吧,借你的锋芒,
把我的腐朽思想扫出宇宙,
扫走了枯叶好把新生来激发;
凭着我这诗韵做符咒,
犹如从未灭的炉头吹出火花,
把我的话散布在人群之中!
对那沉睡的大地,拿我的嘴当喇叭,
吹响一个预言!呵,西风,
如果冬天已到,难道春天还用久等? 请把我作为你的瑶琴如象树林般样:
我纵使如败叶飘飞也是无妨。
你雄浑的协调的交流
会从两者得一深湛的秋声,虽凄切而甘芳。
严烈的精灵呦,请你化成我的精灵。
请你化成我,你这个猛烈者呦。
请你把我沉闷的思想如象败叶一般,
吹越乎宇宙之外促起一新生。
你请用我这有韵的咒文,
把我的言辞散布人间,
如象从未灭的炉吹起热灰火烬。
请你从我的唇间吹出醒世的警号。
严冬如来时,哦,西风呦,
阳春宁尚迢遥
许渊冲教授认为诗歌的音韵不可丢,“如果没有押韵,也不可能保存原诗的风格和情趣。”[3](P69)可见,韵律对于诗歌,尤其是对于诗歌译文的重要性。诗歌有别于其他文学体裁的独特之处便是韵律,韵律为诗歌增添了音乐性,且对诗人感情的传达和意思的表达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西风颂》的格律采用意大利三行诗节隔句押韵法(Terza rima),韵脚为aba bcb cdc ded ee,对比王佐良和郭沫若的译文,我们不难发现:王译很好地保留了原文的韵脚,译诗呈aba bcb cdc ded ee的韵脚排列,而郭译则没有明显的音律编排。此外,王译较好地保持了原诗的诗节、诗行编排,而郭译未能保留原诗的体式。据此可以判断王译在对原文文体的继承上做得相对出色,尤其是在诗歌的音韵方面。然而,郭沫若并非完全摒弃了原诗的格律,而是追求了诗歌整体上的神韵,他曾谈到:“译雪莱的诗,是要我成为雪莱,是要雪莱成为我自己。译诗不是鹦鹉学舌,不是沐猴而冠。我爱雪莱,我能感听得他的心声,我能和他共鸣……他的诗便如像自己的诗。我译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在创作一样。”[4]基于这样的理念,郭沫若在译诗的时候格外注重诗的内在气韵的传达,而一旦译诗的外在气韵,即诗的头韵、尾韵与内在气韵相冲突时,他毅然舍弃了韵脚。
在形式上,原诗的编排十分工整,采用的是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体(Sonnet),即每章十四行,五个诗节,其中四个三行诗节,一个双行偶句(couplet),按3、3、3、3、2的顺序排列。在分节建行上,原诗较多地使用了跨行乃至跨节的诗行,句法严谨而又富于变化,不仅表现出了诗歌的乐感和节奏感,还体现了西风势不可挡的气势。细观王佐良的译文,可以发现王译较好地保留了原诗的十四行诗体,译文也是按照3、3、3、3、2的方式排列。从整体上看,王译在顿数和字数方面也跟原诗大致相同,诗行整齐美观,结构抑扬顿挫,使读者能感受到原诗的韵律之美和形体之美。笔者认为,这与王佐良的翻译理念不无关系,他认为“适合就是一切,译者的任务在于再现原作的面貌和精神,原作是细致说理的,译文也细致说理;原作是高举理想之翼,译作也高举理想之翼。”[5]所以,对于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王佐良持不认同态度。然而,郭沫若却赞同严复的翻译标准,他认为除了直译与意译外,还有另外一种译法叫做“风韵译”。在翻译《西风颂》时,他未按照原诗的韵律和节奏编排,而是讲求译出原诗的“风韵”即可。当然,这与当时郭沫若所处时代有关。20世纪20年代,当时白话文运动刚刚起步,现代汉语发展还不成熟,所以在郭沫若的译文中我们还能发现不少文言文的影子。当时郭老将一批外国诗歌引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年轻人投身新文化革命,在这些条件的影响下,格律和形式上的工整便显得不那么重要,其诗歌内部的深层含义和译文的影响力才是最重要的。一定程度上,雪莱的《西风颂》书写的对象和时代背景与当时郭沫若所处的时代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所以与其说是郭沫若的译文,不如说是郭沫若的再创造。也难怪有人读了他的译文后,“深感译诗气势豪放,音调雄厚,犹如暴风驰骋,神韵不减原作,不少词语笔力雄厚,诗意盎然,也和原诗不相上下。”[6]
在诗歌翻译时,优秀的译本不仅要传达出作者所有表达的文体和思想,而且还要确保原诗的意象和意境是否传递表述到位。因为诗歌不仅是一种讲求格律的文学形式,还极其注重意境的表达。在《翻译的艺术》一书中,当谈到翻译的“三美”时,许渊冲认为“‘意美是最重要的,是第一位。”[3](P60)所以,评价一篇译文的好坏,大抵可以看其是否译出了原诗的意境之美。雪莱的《西风颂》就是一篇以描写意境见长的诗歌,如在该诗第一节中,诗人将西风比作秋天的气息“Breath of Autumns being”和狂野的精灵“Wild Spirit”,西风将“落叶一扫而空,犹如法师赶走了群鬼”,在西风的吹送下,种子也像插上了翅膀。这些超现实的意境将大自然中本不具生命的存在激活并以诗意的方式呈现,带给读者的是真实的现场感受和独特的阅读体验。因此在译诗过程中,译员应不可避免地思考该如何保留这些优美奇特的意境。笔者认为,译词的遴选至关重要,只有选词精准才不至于原诗意境的丢失。如在诗歌第五阙第一节第六行写道:“Drive my dead thoughts over the universe”,对于其中的“my dead thoughts”,王佐良将其译成“我的腐朽思想”,而郭沫若将之译成“我沉闷的思想”。笔者认为,将“dead”一词译成“腐朽”有待商榷。因为诗中该词出现之前,诗人刚刚咏唱完自己的激情愿望,所以诗人的思想不应是“腐朽的”,而应当带着“郁郁不得志”的苦闷,据此,与王佐良相比,郭沫若的译文与原诗的意境稍近。在对原诗意境的整体性保留上,王佐良做得较好,如诗中尾处有一句:“Be through my lips to unawakend earthThe trumpet of a prophecy!”王佐良的译文是:“对那沉睡的大地,拿我的嘴当喇叭,吹响一个预言!”不难看出,王佐良的译文保留了原始所有的意象,意境的传达也是相当精准。再看郭沫若的译文:“请你从我的唇间吹出醒世的警号。”很明显,郭沫若的译文未能译出“unawaken'd earth”,对“prophecy”一词的翻译也不够恰当,但郭沫若的译文自有一番意境,可以说是在原诗基础上附加了自我发挥的成分,短短“醒世的警号”五个字即囊括了原诗中“unawadend earth”和“the trumpet of a prophecy”的意象,而且读来颇有古文的意蕴。
三
综上所述,由于时代背景、语言习惯和译者对诗歌的理解不同,译诗也会呈现出不同的文体和风韵。郭沫若的译文用词典雅,追求原诗气韵的传达,不拘于诗词之间的韵律形式限制,在用词方面较多地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意韵,如最后一句中的“西风哟”,便有民歌的味道。而王佐良的译文追求诗的“歌性”的保留和传达,所以他的译文读来就有原诗的韵律和节奏,形式上也几乎与原诗无异。王佐良的用词力求通俗易懂,略偏向口语化,如诗中最后一句的翻译“如果冬天已到,难道春天还用久等?”相较与郭沫若半文半白的译本更易于为大众读者接受和理解。
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序言中说得好:“即使是最优秀的译文,其韵味较之原文仍不免过或不及。翻译时只能尽量缩短这个距离。”[7]可见翻译之难,译诗则是难上加难,要使原诗的音韵、形式和意境在翻译过程中丝毫不见得遗失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尽管如此,王佐良和郭沫若等前辈还是力图通过他们的译文来传递原诗的精神和风韵,在不可能中寻求着最大的可能。
注释:
[1]许渊冲:《新世界的新译论》,中国翻译,2000年第3期。
[2]王佐良,丁往道:《英语文体学引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1987年版,第512页。
[3]许渊冲:《翻译的艺术》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版。
[4]郭著章:《翻译名家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第70页。
[5]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版,第15页。
[6]袁锦翔:《郭沫若翻译初探》,翻译通讯,1984年第9期。
[7]许渊冲:《三谈“意美、音美、形美”》,深圳大学学报,1987
年第2期。
(毛跃祖 段汉武浙江宁波 宁波大学外语学院315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