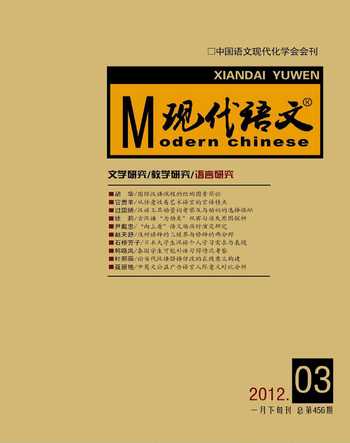从并列式复合词的建构看汉民族的整体思维观
摘 要:文化影响到词语的产生、发展和消亡,不同民族的文化不仅生成语言的特殊语义成分,而且对语言的建构模式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以同、近义语素组合,偏义复词及对立、相反语素的组合为例,探讨了其背后蕴藏的整体思维观及深层文化内涵。
关键词:并列式语素组合整体思维观
著名语言学家陈原先生指出:“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词汇,常常最敏感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变化”[1]。词语的建构也不例外,并列式复合词建构的背后是汉民族的整体思维观。整体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础和核心,是中国古代所具有的独特思维形式,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倾向于对认知客体作综合概括,以整体性的观点来认识世界。在中国古典哲学中,不论是讲气、讲道还是讲理都是从一元论出发,认为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种思维方式无疑影响到语言的建构和发展,反过来说,“一个社会的语言能反映与其相对应的文化,其方式之一则表现在词汇内容或词汇上”[2],下文将以具体实例加以探讨。
一、同、近义语素组合镜射出的整体思维观
同、近义语素组合指的是有着相同或相近意义的实词作为词根并列组合成词的一种组合方式。以“思想”“道路”“丰富”为例简述之。
《说文解字》载:“思,容也。从心,囟声。凡思之属皆从思”;“想,冀思也,从心,相声。”“思”与“想”不只义近且有部分义项相同,都有“想念、怀念”义,如“子惠思我,褰裳涉溱”(《郑风·褰裳》)、“望风怀想,能不依依?”(《李陵答苏武书》);也都有思考、思索义,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入景响之无应兮,闻省想而不可得”(《九章·悲回风》)及“思来想去、冥思苦想、左思右想”等等;“道,所行道也。从辵从首。一达谓之道”(《说文解字》),虽有道路、途径、规律、学说、说讲等多义,但本义还是指“路”,如“会天大雨,道不通”(《史记·陈涉世家》);而“路,道也,从足从各”《说文解字》,如“平原忽兮路超远”(《九歌·国殇》)。可见,在“道路”这一义项上,“道”与“路”同。而“丰,草盛丰丰也。从生,上下达也。富,备也。一曰厚也,从宀,畐声”(《说文解字》)。古汉语中,“丰”与“豐”不为一字。这里的“丰”繁体为“豐”,与“富”义近。如“今年幸少丰”(《田家》),“城小粟富”(《马汧督诔》),两者都有多而充盈义。除此,还都有富足、富裕之义,如“家家丰实”(《齐民要术序》),“俾尔寿而富”《鲁颂·閟宫》。其他不一而论。
以上各组语素,它们的客观概念意义几近相同,情感色彩基本一致,通过这种选择,把一个个松散凌乱的字词串连成一群群形散神不散的同、近义词族,且可以自由构成不同的词性(如名、动、形等)。词语之间各语素的意义可以形成相同或相近的交互映射,使之构成一个难以分割的融洽集合体,于整体统一之中使意义的表达更为充分,这不能不说是汉民族整体思维的结果。一事物或个体通常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另一事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往是一个联系网络上或整体结构中的事物,离开这种网络或整体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把多样性的事物和现象归结为一,也是先秦以来源远流长的一种思维模式。庄子将万物归结为道,得出了万物皆一的结论;玄学家王弼直接阐述了一与多的关系;隋唐佛学中的华严宗提出了月印万川、一多相摄的观念,认为一即多,多即一。这些都昭示了汉民族重整体的思维模式,于并列式复合词的建构之中可见一斑。
二、偏义复词镜射出的整体思维观
偏义复词是指由意义相关或相反的语素构成的词。从词素看,两个语素各具实义,各具地位;从词义看,却一轻一重,一虚一实。如“国家”“窗户”“质量”等。
“国家”,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天子诸侯曰国,大夫曰家。”“国”指天子诸侯统治的范围,“家”按段氏说法最初可能指猪圈,后来逐渐指人居住的地方。随着私有制的确立,“家”不管指一门一户的小家,还是指卿大夫的采邑,它都是“国”的政治、经济的基本组成单位。“国家”放在一起泛指“国”,说明古代汉民族认识到个体命运与家族、国家的命运是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这大概与我国古代“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结构亦不无关系。“窗户”一词只有窗之义,却“窗”“户”并举,“窗,通孔也。从穴,忽声。户,护也。半门曰户”(《说文解字》)。窗用于采光、通风,户用于有防盗、保安全等,各有分工。显然,窗与户是作为房屋这一整体而言的。同时,户也有洞穴义,如“蛰虫咸动,启户始出。”(《礼记·月令》)、“百虫蛰伏,静居闭户”(《淮南子·天文》)。户之失义,可能与此义与窗近有关;“质量”虽只有质之义,却离不开量的存在。量变引起质变,质变又引起新的量变,质量互变规律说明,只有质与量保持一定的平衡,物才成其为物。显然,质与量是事物内部矛盾变化的两种属性,是就物之整体而言的。
由此,不论偏义复词偏向哪个语素的义,但就其构成而言却都是对整体的一种观照。明明只有一个语义在起作用,却要把相关或相反的事物并列提及,以显示对事物的一种整体把握,体现了整体性思维的特点。它不把人和自然看作各自独立的两种事物,而是看作一个互相兼顾的有机整体,两者具有同构性,有时可以互相转换,是一个双向调节的系统,这恐怕与汉民族“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是分不开的。纵观汉民族的繁衍史,汉族先民自古就在华夏中原的沃土上自足地生存,东临不可逾越的大海,西阻于群山,封闭自足的环境使汉民族逐渐形成整体、统一的意识;在社会组织形式上,华夏民族从原始家族制度到封建制度,个体命运同家族命运浑然一体,形成部分与整体交融互摄的思维模式;在人生观上,先民认识自然,感慨于天地交感而万物生长繁茂;而且,人生于天地之间,“赞天地之化育”,天地人交融互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融为一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样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也使得汉民族的思维模式趋于整体化。
三、对立、相反语素组合镜射出的整体思维观
汉语对偶性的形成,尤其是并列式结构的组合与汉民族的辩证对立观念不无关系。8世纪的日本弘法大师曾有过精辟的讲述,他在《文镜秘府论·论对属》中指出:“凡为文章,皆须对属,诚以事不孤立,必有配匹而成。……及于偶语重言,双声叠韵,事类异众,不可备叙。”反映在汉语词汇中,表现出了两个对立或相反的词语往往同时出现,对称使用。细观“东西、始终、反正、开关”等可见端倪。
这类词往往选用意义相反或对立的语素相互组合,从而构建一个新的词义。如“东”“西”对举,构成“东西”,意为“东边或西边”或“泛指各种具体或抽象的事物”;“始”“终”组合成“始终”,意为“从开始到最后”;一“反”一“正”结合,意为“表示情况虽然不同而结果并无不同”或“表示一种坚决肯定的语气”;“开”“关”对立构成“电器装置上接通和阻断电流的设备”之新义。词语建义上往往两个语素共同发挥作用,或兼指、或泛指、或虚指;架构上往往一体两用,相反相成,一反一正,一阴一阳,既辩证对立又相互补充,两两相照,共同构成一个统一谐和体。这说明汉民族认识事物善于从整体着眼,兼顾矛盾双方且注意到了事物的二元结构。
整体思维是在二元结构中发展起来的,二元结构最简单最普遍的图形就是对称性。中国哲学的本体是整一的,无论称其本体为天、为道、为太极阴阳或为理、为心、为气,都具有冯友兰归结的大全、一的性质。一幅太极图把一个整体中相互对立的有机联系及其相互包容、相互依存性表现得再明白不过了。汉代大儒董仲舒说:“天地之气,合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3]我国古代哲学一开始就把世界看成以阴阳二气交感运动为始基的对立统一体。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可谓是对阴阳关系的最精辟论述。“道者,规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而万物生”(奚侗《<老子>集释》)。这就表明,中国先民认为世界是在两种对抗性的力量运动之下孳生、发展与变化的,而且只有在相互对立的双方贯通、联接、合作、平衡、统一的情况下,事物才能顺利发展,“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周易·系辞上》)。所以,既要一分为二,又要合二为一,这就叫“道源于一而成于两”。这一学说影响到了汉民族的思维、言论与处世的诸多方面,也影响到了汉语的诸多层面,特别是词汇方面。
总之,世界是通过语言来反映的,这在词汇体系中表现得相当突出。研究词语结构的组合、内在关系及其所蕴含的深层文化内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词语的意义,对于语文教学、对外汉语教学也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期待有更多的同行投入到这方面的研究中来。
注释:
[1]陈原.社会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美]C·恩伯,M·恩伯.文化的变异[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3]董仲舒.春秋繁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参考文献:
[1]邵静敏.现代汉语通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2]苏新春.文化语言学教程[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3]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4]祝西莹,徐淑霞.中西文化概论[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5.
[5]王钟坤.从偏义复词看中国传统思维方式[J].桂林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学报,2003,(2).
(伊志乌鲁木齐 新疆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830054)
——针对对外汉语语素教学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