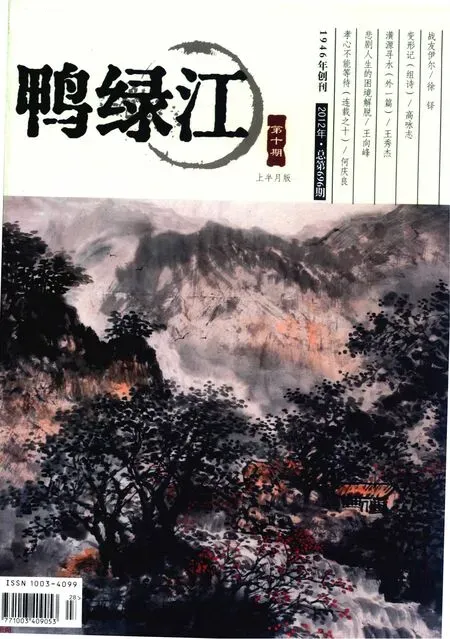歌唱,沉默或抚摩:关于救赎的几种方式
贺颖,中国作协会员,辽宁省作协特邀评论家,诗人,调兵山市作协副主席。
小说以全文中惟一激化的冲突为开篇,看门见山地对读者做出了阅读的邀请。是什么样的婚姻,让一个女人宁愿放弃生存的全部,也要以死相拒?让一对父母宁愿牺牲自己甚至女儿的生命,也要拼死捍卫?何以如此惨烈?毕竟自古以来,人类的生命无论多么灿烂与凡俗,终究没有比死亡更能令其现出本真自相。没有假设,女主人公刘平忽然发现,婚姻与死亡,一夜之间,陡然成了两个必须二选其一的人生命题,或者,也许根本就没有选择,因为她比谁都更加知晓,横竖都是不归路,而选择婚姻,她尚可以自己的悲情奔赴,挽留包括自己在内的三条性命,更重要的是完成了对父母的果报。而若抗拒,她也知道,那不是她的避难所,是她必将以浩大的死亡,踏上以几生为之赎罪的漫漫荒途,她不敢,不能,也不可以那样做。
作者以此为开篇,为文本提供了一个以道德人伦为概念的叙述框架,同时也为读者设置了一个悬而未决的哲学困境:即当个体与道德,灵魂与人伦不可避免的形成无处可藏的危机,作为个体生命的存在,到底该不该、能不能以神明的本意独善其身?还是终将告别无谓的挣扎,献祭于道德的浩浩洪炉?此刻,妥协的刘平踏入婚姻的背影,仿佛一个黑暗的预言,令读者陡然心生的呼号,愈加无力而哀恸。
也是这背影,让人想起另一个故事,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的,哈萨克辽阔的草原上,吉尔吉斯斯坦作家艾特玛托夫的小说《查密莉雅》。女主人公查密莉雅,同样被爱情与命运,道德与人性,伦理与灵魂,不由分说地安放着她的宿命,而最终,以爱之名,她以越规愈矩的终结,以一生的非议为代价,悲情地逆转了自己的命运航线,也捕获了灵魂中一闪而过的真谛,却也让无辜的母亲,有了夜夜的哀伤与哭泣。生命与灵魂的自由,爱与痛的悖论,人类为此付出的代价,从来没有停止,也从来无法估量。或者,这几乎就是全人类的宿命吗,也未可知。艾特玛托夫所赋予查密莉雅的,便是如此这般的困境中的吟诵:“在这样的夜里不能沉默,在这样的夜里要歌唱”。
是的,正是在这样的歌声中,在这样母性的巨大情怀中,我们的主人公刘平,也完成了她必经的终结和逆转:终结了自己与父母的死亡之行,逆转了命运中可能的残骸与破碎,开始了全新的不可知的生命行走。当遥远的哈萨克的查密莉雅,以悲情的自由,游走在草原和群山之间,而刘平,这个生活在北中国大地上的女人,有着“哈萨克草原上的查密莉雅”一样的魂魄,一样无法脱逃的、悬置于偏见与异类之中的、宿命之身的女人,却以自己毕生传奇般的历程,诠释着情爱与大爱,信念与信仰,责任与人心。将一个平凡的生命,在更为平凡细碎的生活中,努力绽放出的天然的、甚至诗意的光亮,将人性以至真纯净、甚至牧歌般的美德,完成了凄苦年代的背景下,人心却本能地向着光明向着温暖行进的、全部的内在需求。从对婚姻的以死相拒,到洞房夜表哥的心迹表白,只隔着短短的一夜,而正是从这一夜,刘平揭开了她一生传奇命运的幕闱。她有着查密莉雅一样的爽直和干脆,无畏与激情,也有着与生俱存的深沉的善良,或者说是内心的弥足贵重的和谐。生活的磨难与艰辛,繁复而无休止,而在她可以抵达的简单而正义的思忖之间,一切苦难对她的挑战似乎都是无效的,因为在灵魂的出发处,她已经是自己的赢家,除了死亡,没有什么能让她称败,而如今已经放弃死亡的她,在渐渐经历了生活中的爱恨仇怨以后,无疑已经换骨脱胎一般。重生的她,或沉默如大地,或歌唱如查密莉雅,总之早已无须依赖自身以外的东西,获得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也许这是一个平凡的生命,在凄苦的年代里,撑起一片传奇天空的情由,这样一个不可能的命题,就这样被她不自觉的完成了。
而面对这样的不自觉,除了让人想起康德说的:“……一切不自觉的美德和善良,才值得颂赞,因其最接近高贵与神性”,也将作品的气蕴,映衬得如此饱满而激荡,引人遐念。甚至整个苦难,包括那些在苦难中摸爬滚打的人们,那些在人性的较量中,或输或赢的人们,都成了一副画作的远景,而整个画作,因一位女性灵与肉的在场,而悠扬,而宏阔,而牵动人心。
准确地说,刘平的情感转变,乍读时似觉兀然,当你渐渐深入情节,直至读过全文,才有如河涌峡谷,畅然而激荡了。以此说来,小说的文本结构,极似一轴画卷,只是这绳结打得极深极巧,且要费些思量方能打开,而一当打开了,也遍尽可畅快展开去,尽意领略其间妙处,甘苦人间,喜乐人生,皆尽显笔端,赏来无不令人喟叹,感怀良深。
像微笑一样流泪,像铭心一样遗忘,像沉默一样言说,像幻灭一样希冀。这一切所有,仿佛一组美奂的吊诡,颠倒也重复着作者与读者,同样熟知的预言及审美。当我们和刘平一道,如此地在生活的沃土上,播种着灵与肉,在足印中捡拾汗水与泪滴凝聚的珠串,其实作者此刻所力求表达的,也许是世间更多的刘平的生活与生命中,那所有关于爱与痛的悖论。仿佛成了秋夜里,月光下的独白,清澈、微醺,弥散着“哈萨克草原紫丁香般的、雾霭霭的气息”,以及“库尔库列乌河在峡谷中的奔腾与安谧”……
作者从未对主人公的命运做出任何反复的强调与刻画,只放任其在时间的结构中自在行走,仿佛一个娴熟的牧羊人,在不可知的草地上,优雅地牧放自己的羊群。这是作家对自己心灵力量的美妙信任,更是对文本的抒情般的期许。当然,这其间不乏有无法阐释的煎熬,有幻灭和无助,冲突、和明暗相映的温情,也正因为如此,小说也具有了叙事与文本上的双重意义,而这一切,在时间中的进程,就犹如时针走过钟表盘,甚至能听见滴滴答答的声响,是刘平,和她的生活中所有的人,以及更多生命的细碎经历,是一个个瞬间集结而成的永恒,也是未来某些不可磨灭的证据。
文中不难分辨的,还有一直隐匿着的音律,正如昆德拉说的:音乐可以让人瞥见隐藏的忧伤。而这旋律,这忧伤,便是那些生活的水流,裹挟着人类行进中永恒的存在与时间,泪珠与欢乐,于日夜不息地奔行时,所发出的旋律。这样的安置,显然既是叙事的,也是反叙事的。作者除了力图从这样的叙事与反叙事中获得意义,或者说获得叙事的内核,似并不存有更多的目的。这样让作品本身更值得人为之敬重。
整个作品几乎是一段时间的编年史,有着硬朗的骨骼,听得见岁月的风雨,正呼啸其间;更有无限温存的白描般的细微节奏。既像一颗泄密的心,又仿佛是对生活中的秘密藏而不露的一次叙事潜流,如午夜流动在大地上的河水,游走着微妙而强烈的涟漪。
但几乎没有苦难题材中易于表露的反讽,隐喻,甚至都少有修辞,一日日一年年的时光,泪珠和欢笑,有如大地上密密匝匝的荆棘、麦田、也有林木中的喧哗与骚动,更有草场般的旷远无垠。一步一步前行中,一寸寸打开了画卷,而于结尾处,作者从容而善意地将我们引入一片大地上的葵花林,太阳炫目耀眼的光,打在每个闪烁的叶瓣之上,再折回到我们的眼底心间,仿佛人性的永不消逝的光亮,无论经由多少黑暗,终将在人类前行的路上,守候每个无助的心灵。不逃避时间,不阻止命运,亦不深刻追问生命的意义,或爱恨之间的万千情由,只为一切存在于尘世中的人心,提供着碰撞和暗涌,以及对自性之间的忘我回顾,为文本的旅程,消解着审美的障碍。这样的人性之光,映照的是刘平,和她的生活,是更多那个时代背景下鲜活的每个人,或者是包括读者的每个人,既有着对身份分裂的心灵楚痛的揭示,更有着从自我拯救,到对整个生活的深情救赎。也或者是对人性本身的自我救赎,犹如对时代粗砺的伤痕,一次又一次,或沉默着的、或歌唱着的百转柔肠的诗性抚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