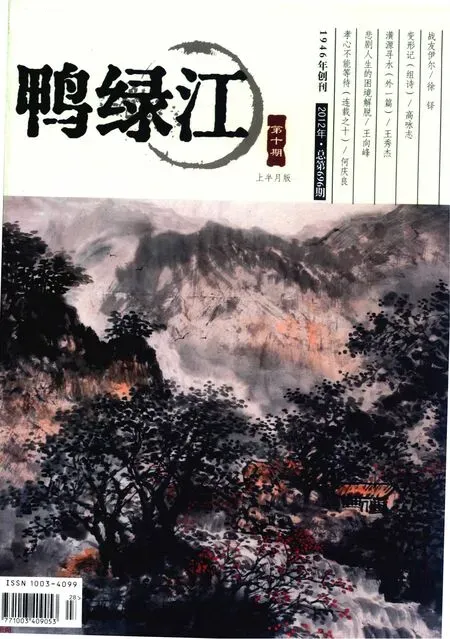王立光散文两题
王立光,男,1952年生。东北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哲学硕士。当过知青、教师,长期工作在县区党委、政府,现供职于中共营口市委宣传部。从事散文创作多年,多篇作品发表于《长江文艺》《鸭绿江》《辽宁散文》等文学期刊。并著有散文集《留白》和理论文集《流痕》。
根在民间
存在电脑里的记忆可以一键删除,而留在脑海里的记忆却不会轻易删除得了,特别是那些印象深刻的人和事,比刻在石头上还经久。在我回顾自己成长轨迹的时候,我发现,青年时期留在脑海中的一些形象仍然栩栩如生,鲜活自然。在不自觉中,他们竟然至今还影响着我。
一
1968年9月26日,还差一个多月我将满16岁,和同学们一起下乡到盖县太阳升公社科头寨大队,迎接我们的是大队革委会主任贾连生,他是个老荣军,带着大墨镜,一脸的刚毅,短短的头发直竖竖地立着,“嘿嘿,你们是毛主席的客人,就是我们的客人,来到我们大队就是到家了。今后有什么困难就找大队,谁敢欺侮你们,就找大队。嘿嘿。”话一出口,掷地有声,亲切中充满威严,就像父亲。“我们要互相学习,嘿嘿,我们教你们种地,分清什么是谷子,什么是稗子,你们教我们文化,怎么写批判稿,嘿嘿。完了”于是,我们便被参加欢迎会的各个生产队队长分别领走,三个人一铺炕或四个人一铺炕,安置到老百姓家。
第二天,大队对下乡知青进行集中教育,由老贫农忆苦思甜。鲍大爷,干净利落的老头,放蚕的嗓子,说话也流利。
他说:“旧社会苦啊诉不尽,受压迫,没有自由,老百姓挨欺负……要说挨饿,要数低标准那年……才好了几天,别好了疮疤忘了痛……”
这时,下面有窃窃私语,“说错了,说错了!低标准是哪一年?”
“不要说话,不要说话。不要乱讲。”主持人提高了嗓门,他面向鲍大爷。
“实事求是,实事求是,让人讲完。嘿嘿。”贾主任说。
“孩子们,我讲不好,讲不明白,你们可得听明白。完了。”
鲍大爷紧张了,匆匆走下讲台。
会后,组织讨论,有人说“讲得好,挺生动的。”有人说“净瞎讲,讲不明白还要我们听明白。”还有人说“他反动,攻击新社会,得批判他。”传到贾主任耳朵里,贾主任说“批判什么,是人家爱讲吗?还不是咱们请人家来讲,不入耳了就批判,以后还有谁敢讲真话?”
秋收后,进入冬闲,天短夜长,大队经常利用晚间开会学习。一次大队召开批判反动路线大会,青年们按要求都写了批判稿。会议刚刚开始,有些青年却把十几个“四类分子”挂着牌子押进会场,有的甚至拳打脚踢,几乎就在同时,贾主任也气喘吁吁跑进会场,一边跑,一边喊:“XXX,XXX,你他妈搞什么名堂,谁叫小青年把‘四类分子押进会场,都他妈给我放了。”他箭步冲上台,接着说:“我早告诉过你们不打无准备之仗,准备好了的仗你们不打,偏打无准备的。你们安什么心?”他压低了声音,放缓了语气,“我们准备了那么长时间,写好了批判稿,是挖反动路线的老根,你们把“四类”弄进来,还能批深批透吗?这不是干扰斗争大方向吗?”他接着说:“为什么要文斗不要武斗,打天下的时候要武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现在咱们坐天下了,就得文斗,触及灵魂嘛,拳打脚踢能触及灵魂吗?能把反动路线批倒批臭吗?”贾主任完全站在了理上,谁也不敢吭声。于是“四类分子”放了,批判会接着开,青年们一个接着一个上台念从报纸上抄下来的批判稿。
贾主任是个老英雄,三里五村有很多关于他的传奇故事,说他是年轻时参加了吕正操领导的大刀队,有武功,并且身手不凡,能背着手爬上电线杆,身上留下无数刀疤枪眼,就是要不了他的命。解放战争的时候当挺大的官,在一次战斗中右眼珠被流弹崩出来的时候,他竟然一把将眼球拽下来撰在手心继续战斗,因此影响了治疗,成了独眼龙。国家养着他,可他闲不住,大家选他当书记,造反派想打倒他,他说:“打倒我?嘿嘿,想得美,天下是我们打下来的,交给你们?也不照照镜子。打倒我?我就不倒。”
贾主任的嗜好就是抽烟,一颗接一颗地抽,抽烟时一言不发,皱眉思索,老百姓们拥护他,不论谁安排什么事,都要顺口问一句,“老贾知道吗?”四类分子们围围他,有点什么风吹草动就往他家跑,或者让老婆孩子去报信。造反派们都怕他,老贾头不让干的事,他们怎么变着法也干不成。就连公社革委会的领导见了他也低眉顺眼。有的造反派提出要脱产闹革命,贾主任说:“不要工分?行。”造反派不干,贾主任说:“谁养活你?”贾主任在大会上讲:“不干活,公粮谁来交?官猪谁来交?官菜谁来交?我们要当好革命的后勤部。这就是干革命。”
二
1970年春节后,我转到盖县芦屯公社官屯大队太平庄小队,第一天领着我干活的是“老劳模”,老劳模六十多岁了,足有一米八的大个子,花白的胡须修剪得整整齐齐,穿着传统大勉裆棉裤,扎着裤脚,家做的圆口棉鞋,腰间系着青布腰带,腰板笔直,大嗓门,满嗓灌。青年们谁都不愿意跟他一起干活,说是跟他干活累死人。
老劳模是土改时参加县里开展的劳动竞赛夺得个头名状元,成为劳动英雄,被评为劳模,为村里挣得了荣誉,全村的人从此就再也没有称呼他的名字,无论老少,无论辈分,一概称他“劳模”。后来,劳模年龄大了,在劳模前又加个老字,成为“老劳模”。
从成立生产队那天起,老劳模就是生产队长,一直到文革,造反派说他是假劳模,给他罢免了,但老劳模不承认,他说,“我劳模是县里评的,当队长是大伙选的,你们几个山猫野兽说不让我干我就不干啦?我就偏干给你看。”所以,老劳模一直在管事,一天也没耽误。社员们也照常听他的。
第一天干活是席地瓜,在队部窗前,用土坯砌成半尺高的池子,填上沙子,把选好的地瓜种摆进去,再盖一层沙子,罩上塑料布提温催芽。社员们说,“这是好活,有地瓜吃了。”按老劳模的吩咐,我搬坯,挑沙子,累得够呛。在摆地瓜时,趁老劳模不注意,我拿了一个小地瓜就想往嘴里填,“放下。”老劳模大吼一声,“这是队里的地瓜种。”我连吓带羞,只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往脸上涌。下午接着干,我仍然打不开精神,只见老劳模从怀里掏出两个地瓜递给我,说:“吃吧,烤的,是城里孩子的稀罕物,趁热吃。”我接过带着老劳模体温的烤地瓜,一声不吭,也不动。老劳模象隔着山沟喊话一样,说:“愣什么?还生气哪?大荒身子干农活吃不消,进屋歇歇。”说着就把我推进屋里。
说“跟老劳模一块干活累死人”,这话一点也不假,我不仅一次领教过,特别是铲头遍地,十几个人,老劳模打头选好垄,然后大家一字排开认准垄,齐头并进,铲到地头拎过来,仍按原来的阵势铲回来。这在当时叫“拎飙”。好家伙,累死你,谁也夹不了馅,一直到秋都知道那条垄是谁铲的。谁铲地慢,到拎飙的时候就给你留下一垄,大家收工了你也得铲完。谁英雄谁好汉,一上飙就看出来了,手慢的,到这个时候就请假了。老劳模总是第一个到地头,然后到后面检查质量,或者帮助别人接接垄。有人提出少铲一垄行不行,老劳模马上会说,少给你记工分行不行?有一次有两个青年活干到一半就请假到大队参加批判会,老劳模说:“开批判会能当饭吃啊?活给你留着,上哪都行。”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找借口的了。
那几年,太平庄的一个工分值一角三四分钱,是远近闻名的富裕队,而且工分毛,一个壮劳动力一年能挣七八千工分。姑娘们都不肯嫁出去,因此村里大姑娘多,小伙子早早就结了婚,太平庄成了全公社著名的亲家村。那年我家插队,队帮公助盖房子,拉下了一千多元钱的债,我挣了8000多工分,年底分配,一下就还上了饥荒。
三
1973年8月,市里召开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和熊岳公社金星大队党支部书记“老党”住在一个房间。老党姓徐,叫徐崇让,是山东人,旧社会逃荒过来的,土改时候入党,老两口,没有子女。因为办事坚决,讲原则,老百姓都称他为“老党”,久而久之倒把他的大名给忘了。他带领群众从互助组,合作化,到人民公社,一直担任村里的党支部书记。老党太出名,全县全市没有不知道的。
金星村是熊岳城边子村,以果树为主,地少人多。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到七十年代初,老党把全队的青壮年劳动力组织起来,先到离熊岳三十里外的仙人岛拦海造田,后又到六七十里地以外的盖州西海拦海造田,住窝棚,种水稻,声名远播。这次“积代会”是要他来“讲用”的。可是会前“调讲”后,又通知不要他讲了。本来不算什么大事,可是那个时候,对老党来说可非同小可,老党觉得这是路线问题,心里想不开,坐在床上,一个劲地抽烟。晚饭后,市里领导来看望代表,老党才下床站起来,领导们和老党都熟悉,说话也随便。只听老党说:“经验材料都是事先审查好的,又叫改,不改就不让讲,我干的那些事还对不对?”当时的市委书记是军代表,安慰老党,“都是大会秘书组的意见,对不对先不论,你讲不讲都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送走市领导,老党又点起了一支烟,不等一支吸完接着又续上一支,不间断地抽,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就为那么一句话,就为那么一句话,就非得改,本来就是这么回事。‘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改了,我那些事怎么讲?不能改,不让讲也不能改。”
第二次见到老党是在1982年冬,落实中央1号文件,进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我来到了熊岳金星村,老党思想有点不通,他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下子分了,心里有点舍不得。但是不分,也很难撑下去。”后来金星村很快就把责任制落实到位了。
1984年我调到熊岳镇工作,转过了年熊岳乡又拼入熊岳镇,老党已经退下来,接替他的是老党亲自选的当年拦海造田时的突击队长。一天,老党坐着“驴吉普”来找我,进门就说:“我来上访。”我慌忙给他让座,他依然站着,说:“虽然联产承包了,可那是使用权,所有权还是集体的对不对?”我还未来得及回答,他又接着问,“土地撂荒了管不管?责任田插葡萄拐子管不管?果树不剪枝,不刮腐烂病管不管?”……一连串的问号,我连忙回答:“管管管。”“好,这可是你说的,管不好我还来找你。”
都是过去的人和事了,一想起他们我总是由衷地佩服,贾主任,老劳模,老党,他们都没有念过书,一直在最基层工作,除了贾主任外,老劳模和老党,到死也没有享受到退休金,没报销过医药费,我常常想,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为了我们的事业而忘我地终身努力奋斗呢?在文化大革命中,很多老干部被打倒了,靠边站了,可他们却打不倒,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们永远挺立着呢?贾主任和老党都是外来户,在村里队里没有家族和亲属,可他们在群众中一呼百诺,是什么法宝使他们具有这么崇高的威信呢?
答案,我,寻找着……
回到原点
从前,这个世上无比地宁静,起伏的山峦,浩瀚的大海,湛蓝的天空,皎洁的月光从山巅爬起,悄然又消失在海天之间,人们饱享着这世界不可比拟的贞洁。
一
再往前的事情记忆就不太清楚了,大约是在五岁左右的时候,父母把我送到老家住了两年,我对这个世界映像,是从老家的草房开始的:土墙纸窗煤油灯,冬日里北墙上白惨惨的挂霜,还有跟着堂兄到南山坡打疙瘩,苞米秸篱笆被风吹得吱吱叫……春天来了是孩子们最好的日子,打开窗子,屋里屋外尽情地疯,可是风雨天还得在窗前放下草帘,怕风雨把窗纸打破,屋里又被挡个黢黑,于是我便跑进风雨中疯而把衣服和鞋子湿透,遭到伯母的责备。草房后有几棵大梨树核桃树,房前还有一棵花椒树和几棵山楂树,门前那条小溪哗哗地流淌,机警的鱼儿摇摆着身躯,自由自在,不时惊恐地逃避着鸭子的扑食和孩子们的草网。那几年,亲昵着柳枝吐绿,野草萌动;和声着秋蛐清唱、河塘蛙鸣。夏夜中有熏风沐浴,篝火里烧毛豆;冬日里在河面溜冰,火盆中埋红薯。从小的日子在头脑中始终挥之不去。
有一次,一匹青马跑进院子,撒着欢咻咻地叫。祖父忙从屋里出来,拿着一个苞米棒塞到马嘴里,叫我过来,让我摸摸马的大嘴唇,对我说:“这是咱家的马,入社了,动不动还往家里跑,就是离不开这个穷家。”我摸着那马,那么温顺、机灵、通人气。那马垂下头,嘴唇差不点贴到我的脸,方才那股疯劲一下子不见了,突然打了一个响喷,吓得我忙把手缩回来,那马的氣息至今还存在我的鼻孔里。以后,那马三天两头往回跑,我不止一次看见祖父抚摸着马背与马交流,那马驯服得像个孩子,默默地倾听。有时祖父不在,我曾企图独自走近它,像祖父那样和它亲昵,然而恐惧使我终未成行,只是远远地看着它咻咻地叫,与它的大眼睛对视,那里透出了祥和亲切情意绵绵和稳健与诗意,我甚至在想:“我要做一匹马。”
那年的一个春日,伯父弄回了一垛稻草,一把一把地挑选穿成帘苫房顶,我想起姥教过我的一首儿歌:“大瓦房,亮堂堂,背着书包上学堂……”城里的房上都是瓦,那瓦一块压着一块,像河沟里小鱼身上的磷片,下雨时,雨水顺着瓦垄沟流淌成一条直线,落下房檐时像一串断了线的珠子,硬是把屋檐下砸出来无数个小坑。我指着草帘问伯父,“怎么不像城里一样换上瓦呢?”伯父说:“等你长大挣钱了给我换。”我小时候的理想,就是快长大,挣钱了给祖父再买匹马,给伯父的草房换上瓦。
二
在学校时我曾经在图书馆借过一本《新旧约书》,当时并不知道那就是圣经,书上说,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人与自然是和谐相处的,没有欲望,没有追求,我以为那大概是最早的公社,最早的村庄。上帝告诫过人们,唯有树上的禁果不能动。但是夏娃还是禁不住毒蛇的引诱,她偷吃了禁果,结果祸患横流。上帝是想毁掉这个世界的,事先叫诺亚造个方舟,洪荒淹没了这个世界,直到放飞的鸽子衔来一片橄榄叶,才知洪荒已经退去,躲在方舟上的万类万物才重回这个世界。然而,这个世界仍然没有回到从前。
我还读过《桃花源记》,陶渊明先生塑造的那个公社,那个村庄,那是个和谐的社会,没有批判,没有斗争,没有尔虞我诈,人人过着安然自得的生活。是何等的好啊!“不知有汉,何论魏晋。”“黄花垂髫,怡然自乐。”我向往着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地方。
当我下乡当知青的时候刚刚十七岁,美好的理想暂时搁浅了。阶级斗争天天讲,想保个平安可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大队书记是个老荣誉军人,烟瘾很重,“红玫瑰”、“大生产”一支接一支,猛劲儿地吸,总是低头想着什么。我的父亲也吸烟,却常常抽老旱,有时用烟斗,有时用纸卷。父亲插队后,我从青年点转回家里,和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是邻居,我为了靠近组织求得进步,常常去副主任家套近乎。副主任每天晚上都端坐在炕桌前,夫人给端上酱猪蹄、酱排骨,或者盐爆一盘花生米,喝着当时凭票供应的瓶装高粱烧。一边吧嗒着嘴,一边和来访者交谈,分析着阶级斗争新动向。父亲也喝酒,但只是逢年过节时才买上二两散白酒。那时的理想,就是将来日子过好了,能够让父亲也能抽上带把的烟,喝上瓶装的酒。
三
参加工作以后,并且很快走进了县级机关的大楼,使我这个本来就生长在小县城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一下子就算有了出息。父母骄傲,同学瞩目,自己也满足。然而,少儿时的梦幻和青春期的漂泊,就像一颗杂交的种子,早早在心田中播种。大梨树上的果实和大青马的咻咻呼唤,矮矮的草房和溪沟中的小鱼,总是让我怀念。可是,时间就像一个锻造工,不知不觉中便把人来改变,渐渐想法多了,追求也多了。先是自己的工作,再是部门的工作,再是一个地方的工作,无休无止的忙碌,父亲提醒:“莫要急,欲速则不达。”老婆抱怨:“这个家就是你的旅馆!”女儿怀疑:“不知道爸爸是否真的喜欢我。”亲友们生气:“不提亲戚还差点,挂上亲戚更不办。”……总是希望自己能做更多的事,希望群众领导都满意,我发现,自己的情感就像一滴离开了老家门前那条小溪的水,正在慢慢地风干,像杨花四处飘逝。
人,往往在跨越了他的真实面以后,无论怎么努力去追求更加完美,无论是多么勤奋,表现得怎么自如,其结果必然是累积沉重的负担。我觉得自己像那匹入了社被套上夹板的大青马,被无形的鞭子驱赶,没有尽头地奔波,却越来越不自如了。人哪,就是这么一种东西,无止境的追求,而道路上却是布满了障碍,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在我以为,这就是工作。工作就是完成一项任务接着又一新任务,解决一道难题又面临一道难题。因此,人生,总要有几个坐标,以规划和提升生命的质量,标识和指明人生的阶段和重要节点。
四
人生中的每一个时间节点,对个体的人生来说,都是之前所无比重要的。对多数人来说这时都要换一种活法。特别是当掌声消失了的时候,荣誉也将蒙上灰尘。成功者和失意者都将很快被遗忘。我想到了回归原点。对于我们这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民族来说,那是个人生命轨迹的归属,她包涵着这个民族流程和人的发展本质性,并正在发生着与现实社会的结合与沟通。清明,当我面对身前身后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与富强而死难的逝者墓碑默然树立时,我已经实在感觉到了内心的激烈碰撞,我们确实应该换一种活法。
回到原点,注定是一种情结。对于每一位成功或者失败者来说,都是如此。都要回到从前的地方,是那里培育了我们一生的朴素和善良,并眼巴巴地盼望游子的归来。典型的例子比比皆是,像杨善洲,当了几十年的县地委书记,退下来之后,回到家乡种树,一种就是二十几年,到最后,回报乡亲们的是一座林场和座座青山。他把生命的链条拉长了,我以为他最后的二十年较之以前更精彩。
一次,我的朋友和我谈起了以后的生活,他说:“你敢不敢写‘留黑?把内心深处的东西写出来?”一下提示了我,在我看来,写作就像照镜子,一个能够站起来对着镜子打量自己的人才更自信,一个敢于在朋友面前真实剖析自己的人才是真勇敢。
原来,这世界上和社会中,每一种绚丽的表象和神秘的声音,都与人的生命和心灵息息相关,并能够通过观察、聆听和感悟而作出不同的解释,因此,作为一个正常人,不仅要有明亮的眼睛,敏感的耳朵,更重要的是要有善于思考的头脑和一颗联系、宽容世界的心。
我顿时感到一阵清凉的风吹过……
回到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