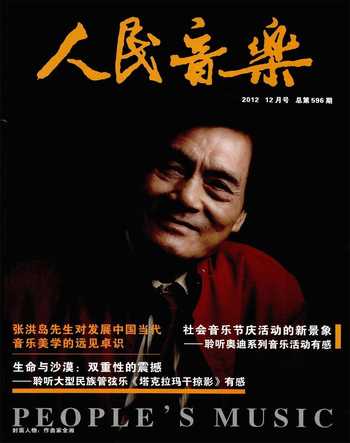试论歌剧《丑角》中的人物塑造及戏剧结构
孙逊
为19世纪晚期兴起于意大利的真实主义?穴Verismo?雪歌剧的代表作,由意大利作曲家莱昂卡瓦洛(Leoncavallo,1857—1919)谱曲并自编脚本的《丑角》(IPagliaacio,1892)叙述了一个由爱生恨的情杀悲剧。该剧情节紧凑、笔法直白尖锐,脚本结构采用了戏中戏套叠结构。通常情况下,“丑角”多是与讽刺、嘲笑、滑稽、荒诞等词相关联,而在此歌剧中,作曲家赋予了“丑角”以更深层次的内涵——不再仅仅秉承着讽谏时事、滑稽调笑的传统,而是通过这一特殊社会角色折射出主体人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追问。在歌剧中,“丑角”作为历史文化的承载者完成了对自身的超越,作为戏剧的特定角色,其含义通过人物性格塑造及隐喻手法而获得延伸。
《丑角》中的人物塑造及戏剧套叠结构分析
(一)“丑角”的人物塑造
该剧是作曲家根据卡拉布莱地区发生的一起凶杀案改编而成。故事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的意大利,流浪剧团班主卡里奥带领团员到卡拉布里亚村演出,发现妻子内达和村中青年希尔维奥偷情,正当卡里奥愤怒之时无奈演出即将开始,他们上演的戏剧恰好讲述了由内达扮演的妻子科隆宾娜,背着由卡里奥扮演的丈夫帕里亚乔与情人幽会被发现的场景。恍惚间,卡尼奥将演出与现实混为一体,竟真的将剧中妻子及其情人杀死。
与传统意大利歌剧不同,《丑角》并不以咏叹调来表达和塑造角色,而是采用宣叙调与咏叹调结合,并将日常生活中的喊叫和哭泣声融于其中。器乐伴奏服务于歌剧剧情,具有明确的戏剧性。其中,男主人公卡尼奥是个点题角色,他的剧中唱段“我不是丑角”可以说是作曲家自我“丑角”意识的认知、转变。
第一幕《穿上戏装》(Vestilagiubba)
这段描写的是卡尼奥发现妻子的出轨行为以后,却要穿上戏装强颜欢笑的一段内心独白。一方面,妻子突如其来的背叛带给他巨大痛苦;另一方面,演出在即他必须掩盖内心痛苦而强颜欢笑。此时的音乐以弦乐为主,手法简洁地呈现出卡尼奥内心苦闷情绪,随着情绪的推进,旋律也逐渐出现起伏并推向戏剧高潮。唱段采用传统的宣叙—咏叹调模式,经过10小节建立在a小调上的宣叙调,旋律转到了建立在e小调上的朗诵式咏叹调。旋律中的增音程和大幅度的强弱对比,使卡尼奥内心的悲痛得到进一步强化。
托尼奥与佩里退场之后,小提琴声部用断断续续的音型刻画出卡尼奥内心情绪的不平静。紧跟着低声部沉闷的大鼓声预示着演出即将开始,密集鼓声营造出一种紧张的气氛。此时宣叙调以弦乐伴奏,与旋律声部级进的八分音符相对应的是伴奏织体扩大时值的二分音符,时值的扩大给人以丰满的音响感觉。(见谱例1)
随后,卡尼奥越说越激动,当发出感慨:“必须强迫自己,你算什么人?你是个丑角!”时,音乐以一连串短时值音的级进上行,来表现唱段中标注的“暴怒”①情绪。此时伴奏声部的弦乐用短小而强有力的和弦以及铜管乐的加入,对旋律起到了强化和助推的作用。
经过一段的情绪起伏,卡尼奥以夹杂着伤心、痛苦、绝望的音调,唱出贯穿于全剧的“丑角”动机,仿佛一声声叹息,达到情绪的至高点(见谱例2)。这一动机在序曲中就已使用,在随后的托尼奥开场白、间奏曲以及剧情发展过程中卡尼奥的多个唱段中亦多次出现。动机的反复出现,一方面不断强化着卡尼奥内心的忧郁情绪,另一方面也不断加深了观众对戏剧悲痛基调的感受。作曲家在这里明确标注着“哭泣”②,而唱到此处卡尼奥已经泣不成声。旋律转由弦乐进行诠释,反复奏出哀愁沉寂的《穿上戏装》的旋律主题,已经完全取代了声乐部分,最后结束在贝司低沉的“丑角”动机之中。
(二)戏剧套叠结构的分析
莱昂卡瓦洛在《丑角》中采用了套叠结构,即剧中剧结构。戏剧内外情节交叠,现实与舞台混淆,戏剧上的复调结构及精神上的悲喜二重性,使得全剧充满了戏剧性张力。表演过程中,卡尼奥扮演的帕里亚乔疯狂地逼问内达那个情人是谁,而内达试图用语言唤醒他:“你是帕里亚乔!”正是这句台词让卡尼奥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扔掉丑角的帽子,歇斯底里的大喊大叫。此时,台下观众却不明事理以为是演员故意添加的喜剧效果而开怀大笑。台上卡尼奥越痛苦,越想冲出“丑角”帕里亚乔的樊篱,台下观众越觉得他的表演诠释真实。在这段音乐处理上,莱昂卡瓦罗运用了简洁强烈的手法表现出音乐情绪风格的鲜明对比,悲喜之间的微妙处理彰显出作曲家出色的驾驭音乐与戏剧关系的能力。例如:在第二幕的咏叹调《我不是帕里亚乔》(No,pagliaccio nonson),与“穿上戏装”相比,其音响中更加强调管乐的作用,显然弦乐音色已不能充分表达卡尼奥内心强烈情绪。唱段一开始,内达提示性的“帕里亚乔”过后,弦乐在打击乐的不安敲击声中,用持续的颤音,渲染出此处的气氛(见谱例3)。卡尼奥用下行音调唱出:“不!我不是帕利亚乔!”弦乐与管乐共同奏出此唱段中的主要伴奏音型(见谱例4)。手法巧妙,笔触简洁,将卡尼奥近乎崩溃的痛苦心绪表现得真切动人。弦乐采用震弓奏法,持续一种不安、紧张的因素。与之呼应的是铜管乐跳跃式音型的进行,在弦乐昏暗浓厚的音色下,铜管先是一个跨越八度的八分音上行级进,构成逐渐增强的力度,紧随其后的符点八分音以快速下行与前小节形成鲜明对比,同时又与弦乐构成对峙,力度由强至弱。这两个主要伴奏音型贯穿全段,并采用调式调性的移位表现出卡尼奥内心情绪的不断变化。
卡尼奥的一段抒情内心独白过后,内达试图将卡尼奥拉回剧中“唱着一曲俏皮的嘉禾舞曲‘没有想到你如此残忍(Suvviacositerribile)。”③音乐由紧张、恐怖的情绪突转到以轻柔可爱的弦乐音色为衬托,轻松、滑稽的舞曲气氛中。但此时的卡尼奥早就不可抑制自己心中的疼痛和愤怒,他用近乎嘶吼的声音盘问着内达,伴奏织体表现为管弦乐队的齐奏。音乐节奏更加紧促,伴随着卡尼奥歇斯底里的喊叫,乐队以快速的十六分音符级进上行紧接其后,音乐再次将我们带入不安的情绪中。这里的卡尼奥自身所具有的“丑角”因素已经和戏剧表演中的丑角合二为一,卡尼奥作为生活中的丑角,与戏中的丑角帕里亚乔融为一体。
与此同时,内达与卡尼奥的关系彻底决裂并爆发,她用“尖叫”对抗卡尼奥的愤怒。乐队伴奏同样采用两个八度连续十六分音符半音阶级进上行与尖叫音调配合。内达的反抗声、混杂着观众的质疑“他们还在表演吗?芽还是当真了?”④加上希尔维奥的自言自语、台旁佩里和托尼奥对白的插入,将戏剧推至高潮。最初内达的陈述,由弦乐以同音反复的连奏烘托,而随着情绪的起伏,弦乐持续连奏保持紧张、恐怖的气氛,而管乐与打击乐逐渐加入,似乎预示着内达不可逃离的厄运。台上的演出与音乐织体的变换将观众与角色的心连在一起。戏剧最终以内达的死宣告结束。场面一片混乱,甚至观众还来不及想是怎么回事,内达与希尔维奥已双双死在刀下。
《丑角》人物塑造及套叠结构的内涵
通过以上具体分析,我们可清楚地看到真实主义歌剧主张的美学观念:力图逼真、不加修饰地再现生活。艺术家们基于这样一种追求,将原样生活甚至于一些暴力、血腥场面直接搬上舞台,以至于有学者称“真实主义歌剧是电影电视恐怖片的无辜的祖先。”⑤处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真实主义歌剧,其风格理念在后世的许多歌剧流派中都可寻见踪影。就整个音乐史发展来看,它为表现主义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但历史中似乎更多关注其表现手段而未深究它背后的审美理念及所折射出的思想内涵。
(一)审美价值——审美主客体关系的拓展
作曲家独特的音乐语汇以及巧妙的戏剧构思,在审美过程中导致了审美主体下意识的心理距离消逝。由于《丑角》的戏中戏套叠结构,因此在欣赏过程中涉及到两个审美主体,即戏内观众和戏外观众。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述审美主体是指戏外观众。导致审美主体心理距离消逝的原因,是主体在审美过程中的投情。在审美过程中,我们可以将主体意识分为三个转化阶段:自我、他我和本我。自我,是主体从自然中脱离出来以后所具有的意识阶段;他我,是主体意识客体化的阶段;本我,即超越自我,回归心灵原初及本真的意识阶段。在欣赏过程中,由于音乐对人物复杂矛盾心理的形象刻画,使审美主体投情于作品,造成审美主客体的在欣赏过程中的同化、互溶,使
欣赏者忘掉自我、变成他我,最后回归本我。
《丑角》中,音乐不仅作为重要的戏剧表现手段,而且作为观众理解歌剧内容的媒介,通过音乐特有的方式对人物心理进行形象刻画。剧中唱段无论优美高雅还是平铺直叙,经过作曲家的精心描摹让我们在其引领下深入剧中。音乐的塑造使主人公卡尼奥陷入一定的情境,从而曝露他最内在的本质。舞台上发生的一切事件都是为了使他产生激烈的内心冲突,而音乐的细腻刻画让听众完全投情于剧中角色而发生位置转移。这种独特的音乐语汇及巧妙的戏剧构思,由于人类审美判断所具有的“共通感”⑥以及社会坐标的相似性⑦而使审美主体在感知过程中获得了对客体的认同感。莱昂卡瓦洛塑造的人物特性并不是标签式、脸谱式的,由于他曾在咖啡馆任职钢琴师,对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生活有切身体验,因此能在剧中准确地把握下层艺人复杂的心理。而作为同一社会背景下的普通百姓,在审美体验中便不会将人物隔离化、艺术化,不会抽身游离于背景之外。真实主义歌剧是19世纪晚期意大利现实生活在艺术上的产物,作曲家通过作品揭示了尖锐的社会矛盾下小人物生活的痛苦和无奈,他对底层百姓的同情引起了他们内心最大的反响,使处在同一社会环境下的欣赏主体通过理解和体验剧情而直观生动地把握住作品
的内在精神品质。
(二)思想价值——“丑角”的精神内涵
莱昂卡瓦洛正是通过“丑角”形象所表达的苦难和矛盾,引起人们对社会下层小人物的关注,同时展开对生命价值的深层追问。
1.对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终极关怀
剧中男主人公卡尼奥作为点题的角色,被塑造成现实与戏剧中重叠交织的丑角。作为现实中的丈夫,他的妻子有了私情,人性受到挤压;作为舞台上的丑角演员,即使伤心欲绝,也要在戏中逗引所有人发笑。通过对卡尼奥不同唱段的分析,我们可以鲜明地体会到作曲家对于其自我“丑角”意识认知的
心理状态的把握。
卡尼奥在戏中的内心独白及其表现,已经超出了戏中之戏帕里亚乔的身份定位。他在倾诉发自内心的苦痛,但这一切又都完美契合:内心流淌的是帕里亚乔的悲哀,更是自己的苦痛。卡尼奥意识到自己不仅是戏中逗人发笑的丑角,更是现实生活中帕里亚乔可笑身影的折射。通过作曲家不同音乐
素材的塑造,两个丑角融为一体。
歌剧的悲剧主题表现出卡尼奥对冲破丑角自我的强烈愿望,这种希望的渴求又处在与整个社会无法调和的冲突之中不得化解。在剧中,表现的是所有人的悲剧,每个人都是得不到完满需求的个体,蒙在鼓里的卡尼奥、遭到拒绝的托尼奥、恋情不被允许的内达和希尔维奥,所有的人都体现出本身的丑角性因素。由于《丑角》技法上的独特性,造成了空间上戏剧与现实的错位,致使剧中观众的愚昧显现。结合当时意大利具有批判现实主义风格的“真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以及意大利矛盾交织的社会背景的特殊性,不难想象,作者也展现出人民大众的丑角性心理,所隐喻的是人民大众的悲哀。或者正是带着真实主义文学“流露出的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不可避免地悲观失望”⑧风格,又或者瓦格纳悲观哲学对于莱昂卡瓦罗的影响,作曲家揭示了人性中具有“丑角”特征的一面,正是人自身的“丑角性”导致了悲剧的发生。由于莱昂卡瓦洛对卡尼奥的人物及其命运悲剧的社会成因表现出无可奈何的困感和迷惘,卡尼奥的悲剧一方面来源于“他重返戏剧音乐的绝望企图。”更重要的是,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就是生活中的帕里亚乔,无论生活还是舞台,自己都是个丑角。在他人心目中,卡尼奥首先是一个歌手,其次才是一个人,这是他根本的悲剧。这就展开了对人类自我生命价值的追问,对生活本质
的探寻。
2.对生命价值的终极追问
由于《丑角》悲剧主题的哲学意蕴,作者展开的是对人类生命价值、生活本质的追问。莱昂卡瓦洛以悲剧的角度刻画世界,把他对于“丑角”悲剧的哲学理解贯穿在整部歌剧中。那个由二度级进音程构成的“丑角”动机在序曲中作了初步呈现之后,一直伴随着卡尼奥贯穿全剧的始终。《丑角》骨子里流淌的是古希腊悲剧的哲理性与悲剧精神,它宣泄净化人们
思想的同时,更让人们反思。
《丑角》作为真实主义歌剧的代表作,体现着对小人物的终极关怀。作者以女主角内达的死来推进男主角卡尼奥的悲剧性,把卡尼奥塑造成反对社会虚伪道德的形象。音乐在“丑角”动机的反复下使人们陷入悲痛阴郁的绵延之中,意味深
长。死亡即意味着失去,内达的死并不能化解卡尼奥心中的仇恨,反而进一步加深了卡尼奥内心的伤痛。
在《丑角》中,“人物”与“戏剧”发生错位,通过立与破的统一,悲与喜的交融,美与丑的对立的悲剧性塑造,歌剧以人与现实、自我与假面丑角的冲突为主题,表现置身于紊乱的客观现实里的人被迫带上种种面具,在虚幻中寻求真实,却永远失去自我,被现实所抛弃的悲剧。这种戏与人生的错位,产生对错综复杂社会的展示与质问,对生活本质、生命价值的追寻。由于《丑角》这种悲剧主题的哲学意蕴,它与观众是共时的同时又是历时的。它所揭示的是人类社会错综复杂的社会本质,展开的是对人类自我生命价值的终极追问。具有时代
的特殊性,又兼有历史的普遍性。
结 语
无论是戏剧名称自身的寓意,还是特性音乐语汇以及套叠戏剧结构造成的深层哲理升华,《丑角》都必然使成为歌剧史上经久不衰的剧目。其深刻的悲剧性凸显出人类对自我的追寻,进而引发人们对当下的思考。人类成就了社会,却又成为它的牺牲品。人性被压抑着而扭曲了本来的面目,我们在扮演着不为人知、不为己知的角色。谁又能否认在自我的多重身份中不曾扮演过“丑角”身份呢?可是,你会为你的丑角身份痛苦吗?会为自己是帕利亚乔而忧郁吗?这一系列的疑问正是《丑角》带给观众更深层的精神震撼,随着不同时期、不同审美主体以及不同审美角度的切入呈现出意义的多解性。内达的死并不意味着卡尼奥人生悲剧的结束,那么,如何理解人生的“丑角”?当我们正处在自我“丑角”身份的时候,是以阿Q精神重返“喜剧”之中进行自我蒙骗,还是要冲破牢笼进行自
我破解?这是值得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