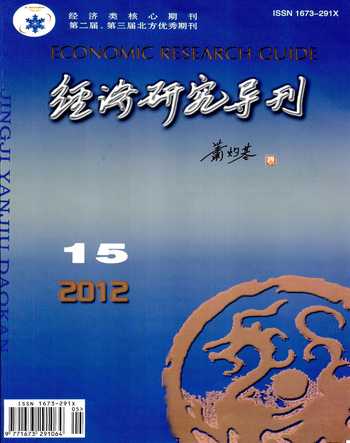从对人类中心论和环境伦理学的哲学批判看马克思自然观的现实意义
李爱华,孙晓艳
摘要:国内面对全球生态危机形成的“人类中心论”和“环境伦理学”本质上都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抽象的、形而上学化的解读。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完成了对作为“人类中心论”和“环境伦理学”之本质的理性形而上学的清算,在本体论上确认了历史与自然的统一,在此基础上的生态思想,才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与可持续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生态危机;自然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5-0223-03
怎样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当前全人类所必须予以解决的最基本问题。20世纪后期,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遭到愈来愈严重的破坏,全球生态危机作为人类与大自然矛盾冲突的一种后果,开始凸显出它对人类的严重威胁。人们已清醒的意识到,克服生态危机,除了依赖经济和法律手段,还必须有理论支持。国内在研究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础上,出现了两种生态理论,“人类中心论”和“环境伦理学”。①这两种理论对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生态问题有着积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但是笔者认为,这两种理论都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抽象的、形而上学化的解读,对解决当代生态问题不具有现实意义。
一、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境域对“人类中心论”的哲学批判
本文在广义上,把旧人类中心主义、新人类中心主义和国内新近提出的人类中心观点统称为“人类中心论”。之所以作此归统,是因为几者的共同本质乃是西方近代形而上学。
西方近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是主—客二元关系型。这是由西方近代哲学两大流派共同创立的。经验论的开创者培根首先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主张通过对自然秩序、自然规律的认识来获得支配自然的力量。唯理论之父笛卡儿则以“我思”确立了主体对作为客体的自然的终极裁判权。前者使自然作为客体向人敞开,后者则使人作为主体登场,并最终确立了其对于自然客体的至尊权威。这种主—客对抗的关系型作为西方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实质是确立了人征服自然的强势态度,这正是后来人类中心论的滥觞。
新旧人类中心主义的概念,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哲学家布赖恩·诺顿(Bryan Norton)对“强式人类中心主义”(旧人类中心主义)和“弱式人类中心主义”(新人类中心主义)的区分,前者是“仅从人的感情偏好、感性意愿出发,一味纵容和姑息人们那种把大自然视为满足人的感性偏好的原料仓的掠夺性的开发方式”;后者是“从理性偏好出发,理性偏好是一种经过审慎的理智思考后才表达出来的欲望或需要,它不仅能满足人的偏好,而且能根据一定的世界观对这种偏好本身的合理性进行评判,这就使得它能够对那种一味掠夺大自然的行为提出批评,从而从源头上防止人们对大自然的随意破坏”[1]。旧人类中心主义在它的时代对于突破以神为中心的宗教统治是有积极意义的,它让人类发现了自己,充分展示了主体的力量,从此人类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自然的支配,有利于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但是这种主体性后来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对它的过分强调进一步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引起了人类发展中更深层次的矛盾,即人与环境的矛盾,进一步破坏了人的可持续发展。这种转变根源于旧人类中心主义在本体论上对人类与宇宙万物的中心与从属、征服与被奴役的关系的确认,它也由此成为当代生存危机的深层根源。新人类中心主义是在对前者批判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称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新人类中心主义主张应从历史观和价值论的意义上来研究人类中心主义,而不再从本体论、认识论意义上来使用这一概念。它强调的是人类整体利益和需要。在价值观层面对“合理性评价”的引入,实质是以理性对人类依据感性偏好随意破坏大自然的行为作出限制,避免了前者仅强调人作为感性欲望主体的片面性主张。理性的限制的确有助于缓解人对自然无所顾忌的掠夺,但不能从根本上使生态危机得到解决。因为无论是感性的偏好,还是理性的偏好,终究是人的偏好,通过协调人的感性与理性,以感性与理性达到“和谐”的人去善待自然,仍然保留了人对自然先验的优先权。这仍然没有脱离近代形而上学之主体性哲学的窠臼。
国内学界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上提出的“人类中心”观点,否认了一般存在论意义上“中心”的存在,这无疑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那么,“人类中心”如果不是在存在论意义上的中心,它将在何种意义上成立呢?中国政法大学的李德顺教授认为,所谓“人类中心”的真实含义,只能是“人是人类全部活动和思考的中心”,“人是人的世界的中心,人是人自己的中心”。这一定位的实质是:尽管在事实领域,包括人在内的任何事物都不能成为中心,但在价值领域,人是必须居于最高的、主导的地位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观念:人类中心可以抛开现实世界,而在价值观的领域独立成立。笔者认为,价值观作为人对世界和自身的总体看法、目标和理想,固然具有对于现实世界的独立性,然而这种独立性终究是相对的,以人本身为目的、尺度、标准和根据的实现是有前提条件的,这就是作为社会、历史和自然相统一的外在世界的辩证运动。诚如马克思所言,如果没有人感性的实践活动,人的直观能力也不可能存在,遑论人的价值观念的成立。所以,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2],因为他看到的只是在感情范围内抽象的人,而全然不考虑人所处的社会联系、生活条件等因素所构筑的现实的社会系统。同样,剥离了“世界存在与事实”(作为人的实践活动,而非作为抽象的事实描述)的价值概念,也只是在理论领域的自圆其说,它仍然是形而上学的,实际上重返了费尔巴哈。因而即便在所谓“应然”的意义上,“人类中心”也是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提这样的旧形而上学概念,在今天根本没有什么现实意义。
二、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境域对“环境伦理学”的批判
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潮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依照其立论基点的不同大致可分为生命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前者认为所有生命个体都有维护自己生存的道德优先性,因此主张把道德关心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生命界。后者依据莱奥波尔德在《大地伦理》(1949)中提出的基本道德原则“当一事物有助于保护生命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时,就是正当的;反之,就是错误的”,认为应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和整个生态过程都当成道德关心的对象。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潮的兴起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挑战和批判起过积极作用,它批判了人类是宇宙中心的论点,批判了人类只图自身利益而征服自然的利己动机,批评了人类过于自信的将经济增长作为唯一发展目标的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人道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道德观对于人类道德完善和道德实践都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
西方非人类中心主义(non-anthropocentrism)思潮中,环境伦理学居于主流[3]。① 按照多数学者的说法,环境伦理学是指研究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和受人与自然关系影响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的应用伦理学科。但是,这门学科在短短的历史中已陷于实践和理论的尴尬境地。这是其在理论上的片面性和乌托邦色彩以及实践中的信仰主义特征共同导致的结果。从理论上讲,伦理是指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其主体是人,客体也是人及与人相关的社会。环境伦理学将“自然、生态”当做伦理主体来看待,这虽然对克服人类中心主义有积极意义,但是,本身却违反了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以生命或生态为中心,将生命和生态提高到超越人类的高度,单纯强调自然、生态的利益而弱化人类的利益,力图将人类消融在自然之中,虽然有着高远的境界和浪漫的情怀,却忽视了现实生活中人与自然关系背后的人与人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忽视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地位、不同文化所带来的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理解的差异。这些现实情境上的差异,使现代人的价值理念在当前时代在一定范围内还具有正当性和自我更新的弹性,然而,非人类中心主义者却对此采取断然否定的态度,拒绝考虑这种现实,这使其不仅在理论上陷入困境,在实践中也难以施展。环境伦理学目前在实质上还只是作为激进环境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在少数组织范围内被遵奉,难以对主流社会的环境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
总而言之,《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二十年》对环境伦理学的评价具有根本意义:环境伦理学是“传统伦理学在环境问题上的应用,它没有任何根本性的变化,只是把环境、生态、自然当做人对人履行道德义务的中介;如果说它有什么新的特征,那就是它看到了伦理学还必须关注基于环境上的人的义务、基于自然可持续利用上的当代人对后代人的义务,而这恰是传统伦理学所忽略的地方”。这一评价,一方面指出了其理论与实践上的乌托邦和信仰主义特征,另一方面肯定了其把自然生态原则引入伦理领域的积极意义。
三、人与自然在实践关系中的和谐共生——马克思自然观的现实意义
人类中心主义与环境伦理学的共通之处在于,二者都是以“中心化”为基本的思维方式。而中心化正是形而上学的根本特征。海德格尔把形而上学的本质概况为“超越”之思、“根据”之思、“人本”之思、“存在者”之思,由此可以归结出形而上学的根本标志——为世界设定一个终极根据。在西方哲学中,无论是第一原则、逻各斯、神,还是先验理念、绝对精神,都是为世界设立的终极根据。“中心”作为世界的“公分母”,把作为其分子的一切事物不能与之通约的部分都无情切除。人类中心意味着,凡是不符合人类利益的“自然”,就要被牺牲掉;生态或生命中心同样意味着,当人类的利益与自然利益发生矛盾时,人类的利益也要被放弃。可见,建基于形而上学的“中心化”思维模式之上的生态观,不可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可持续的发展,在实践中对于生态、环境只能是破坏性的,这意味着对人类也终将是毁灭性的。因此,“去中心化”即超越形而上学、回归生活世界,是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生态观的根本要求。
可持续发展的使命不断激发着哲学家的焦虑。然而,“中心”雄踞千年的历史向我们宣告了“去中心化”而可持续发展之道路何等艰难,人类中心主义和环境伦理学尽管都难逃其臼,但是不可否认其都是在这条道路上的一次(片面化的)尝试。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西方思想史上一次革命性变革,从对资本主义时代之形成的深刻理解中扬弃了西方近代理性形而上学传统,产生存在论新视阈,以此确认了生活世界本身之实践批判的超逻辑性质:感性意识的解放与革命。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之建基的“实践”概念,把人与自然共同纳入在实践关系中的感性存在,取消了人与自然作为“主体—客体”的抽象对立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抽象“中心”。马克思以感性存在为基础对历史与自然的统一所做的本体论论证,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哲学根基,由此构成了对上述形而上学生态观的超越,从而使人与自然可持续的和谐发展成为可能。
首先,自然不是作为任人宰割的抽象客体,而是“现实的自然”,即“历史的自然”。马克思是在与抽象的自然界的对立中,来说明现实的自然界的。他在《巴黎手稿》中写道:“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正像自然界曾经被思维者禁锢在他的绝对观念、思想物这种对他本身说来也是隐秘的和不可思议的形式中一样,现在,当他把自然界从自身释放出去时,他实际上从自身释放出去的只是这个抽象的自然界,只是自然界的思想物。”[3]可见,抽象的自然界绝非现实的自然界。对马克思而言,“现实的自然”即“历史的自然”——“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4] 这表明,自然在其现实性上不能与人相分离,自然是在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生成着的存在,“被抽象地理解的、孤立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5]
其次,人不是作为自然统治者的抽象主体,而是“对象性关系中的主体性”。 “人靠自然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表现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身体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5]这段话表明:第一,自然界是人类的无机身体,人类依赖自然而生存,破坏自然就是破坏人和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第二,“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应把人看做“自然存在”、并且是“活生生的自然存在”、“活动的自然存在”[5]。所以,“人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这对象是引起他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5]总之,自然本质上是人的生命活动的表现,人作为“对象性活动中的主体性”而存在。
概而言之,人通过实践实现自己的对象性存在的活动,乃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既是人的产生过程,也是现实的自然界的生成过程。这两个过程是同一个过程。马克思以实践即感性活动为基础,把人作为“对象化活动的主体性”,把自然作为对象化活动中的“现实的自然界”, 从本体论上确认了历史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并通过这一论证实现了人与自然在实践关系中的和谐共生,使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完成了对作为“人类中心论”和“环境伦理学”之本质的理性形而上学的清算,在此基础上的生态批判思想,才对从根本上解决全球生态危机具有真正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单桦.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的权利观转变[J].理论前沿,2006,(9).
[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G]//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陈剑澜.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批判[J].哲学门,2006,(4):178-179.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8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5-178.[责任编辑 王玉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