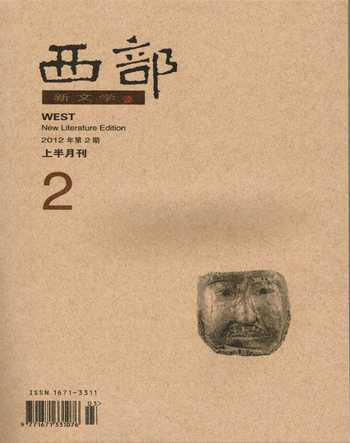魔术工业:约瑟夫.布罗茨基
德里克.沃尔科特
一
“八月,”一位俄罗斯移民诗人向我解释,“是一个说俄语的男人,”“因此当你在诗里说‘女仆,八月……他抱怨。”在俄语里,月份有性的区分。名词有阳性或阴性词尾,但除非在拟人的情况下,月份只是名词。当然,在田园生活传统中,月份有传统的化身。五月是阴性的,一位身着白衣的白皙女子站在开满白花的草地里;六月的玫瑰在雷声中颤动,叶片舒卷,向她的情人敞开心扉;十二月是个毛发灰白,胡须如冰柱的老人。但这些化身只是月历意象,并非语法的。在俄语里,如果八月是一个男人,对这位流亡诗人来说,他是做什么的呢?革命招贴画中一个手执干草叉,长着浅黄色头发的工人?
我把八月视为一个女厨师,她黑檀木似的头颅包在白方巾里,在临海的一座房中从晒衣绳上抽打床单,这种方式就像暴风雨在飓风的月份从加勒比海的地平线驱赶航船一样。在这个月的刺耳声里,有干草的沙沙声和洗好的衣服突然抖动的声音,以及浪花拍岸的丝丝声,但是如果这个英语单词可以将它的阴影转变成俄罗斯的风景,转变成被想象的夏天,我就可以把它拟人化为男人或女人。八月,这个男人,本应成为契诃夫戏剧中那些厌倦的,无聊的知识分子之一,用一种像树叶一样令人平静,甚至催人入眠的声音说话,但八月也是《海鸥》中的尼娜,一个菜粉蝶似的姑娘,系身于特里戈林的肘上,在一个受惊的湖畔。对我来说,理解米哈伊尔的痛苦或对月份名字的恼怒是不可能的,但它是随着翻译而产生的废墟之一。
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集《致乌拉尼亚》延长了这种挑战:逐行,逐词,逐字。当然每个有责任心的译者都能忍受这种挑战,但可以感到布罗茨基希望这本书被作为英语诗来读,而不是被翻译的俄语诗。这有它的困难,它的麻烦,但这些麻烦令人感激:这些诗句的粗糙绒毛并未因运用同样的英语措辞而消除,那种决定性的水准测量如此频繁地使他的同胞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甚至像曼德尔斯塔姆那样严格的诗人,在翻译中获得了贺卡的光辉和色泽。这种翻译使日瓦戈医生变成了奥马尔·谢里夫(电影《日瓦戈医生》主演)。
钟表停滞的这个月。只有一只苍蝇在八月
干燥的玻璃瓶喉咙中嗡嗡地唱着热闹的
赞美诗。
这两句诗出自布罗茨基的《罗马哀歌之二》,是他自己译的。当然,这个苍蝇并非“在”八月,而是八月本身。这个昆虫将这个月拟人化了,但它这样做并未区分性。在英语里,这个声音是雌雄同体的,家蝇的性——不像女仆的性——是未鉴定的,也是不重要的。译者追求的是部分谐音的同时性,其部分谐音源于英语名词的刺耳声和丝丝声。这种梦幻感被昆虫的忙碌所强调,嗡嗡声被包含在“热闹”和“它的”声音中,“赞美诗”这个被扭曲的回声来自“钟表”,这种努力从这行诗一开始就需要将“这个”扩展到“月”里,所有这些,具有权威地,用一种过继的语言,形成了懒散的风格。甚至玻璃瓶的喉咙包含了一种灰尘弥漫的回声,读者干燥的喉咙里也感到那个昆虫的嗡嗡声在搅动。这样,读者不仅惊奇在俄语原文中辅音的丝丝声是否有布罗茨基的英语诗这么丰富,而不是相反。
这不仅令人赞赏,而且令人惊奇。
一位诗人翻译自己的诗,牵涉的不仅是语言的变化,还包括翻译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与另一个地方的交叉,气质的调适,在原诗停顿的边界造成敏感性的遮蔽,每一个被提供的凭证都必须被认真地,甚至是残酷地检查,不是被友好的或敌意的权威,而是由作者自己检查。这是一种普通的经验,如果一个人把原诗仅仅视为双语隔行对照的等价物,然后提升,润色,就像一张伪造的护照相片。非同寻常的是,事实上其努力是惊人的,正是对诗歌进行翻译——几乎是移交——的决定,使诗歌从原来的语言变成那个新国家的诗歌。给一部作品同时提供两种母语。
卷入布罗茨基这本诗集的巨大劳动会给人留下异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布罗茨基是一个复杂的,要求极高的诗人,如果这些诗仅仅是被译得很负责,甚至很美丽,那么它们就不会有这么多由布罗茨基本人进行的再创造,这种成就使他成为一个更伟大的诗人,超过了我们对他那种不以为然的承认。一位伟大的现代俄语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继承人,比别人一生做的事还多,但从原来的俄语中重新创作一首像他的《牧歌五:夏天》那样视域宽广,植物学般的精确,韵律令人愉快的诗,然后,想到埃德蒙·斯宾塞的鬼魂在书页背面沙沙作响,在他们自己的语言里召回济慈和克莱尔,这都远远超过了改写的技艺。对一个读者来说,根本不存在对俄语原文的渴望,没有空缺感,以及若有所失或未被翻译的感觉。这是魔术的工业。
夏日的曙光飘动窗户的饰带!
寒冷的地下室塞满了牛奶壶和莴苣,
一条关于斯大林或赫鲁晓夫的最新
消息,被嘎嘎的持续蝉鸣声压住:
那些自制的野果冻罐向椽子们眨眼;
石灰围绕着苹果园的脚踝猛击
看着白色逐渐变暗,就像慢跑者
跑过了道路的尽头;
在逐渐发蓝的夜晚,那些榆树
全身上下越来越像真实的食人魔。
——《牧歌五:夏天》(由乔治·克莱因和诗人翻译)
更加令人钦佩的是布罗茨基决定继续做下去,把它神圣化,通过他的崇敬,他的手艺史,各种语言中神圣的,试验过的形式,凭借维吉尔和斯宾塞,用颂歌和牧歌,以及他诗节的那种牢固,精致的建筑。乔治·克莱因是《牧歌五:夏天》的合译者,但任何一个和布罗茨基合作翻译布罗茨基诗歌的人都知道原诗经历了混乱的变形。因此这种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他的合译者必须与此保持同步:首先是逐行对译,其次是变形,第三,借助运气和布罗茨基孜孜不倦的作风加以完善。
另一种语言的才能如何可以获得?它是通过崇拜获得的,通过所有诗人都有的那种对不同语言中大诗人们的良性嫉妒。这种崇拜可以通过记忆,通过背诵,通过翻译而永久不忘,并通过拥有榜样,可以用来在两种语言中获得发展。布罗茨基是个流亡诗人,不是小说家或科学家,他像帕斯捷尔纳克一样翻译了几位现代英美诗人的作品,包括约翰·多恩的,而当他选择用英语写一首诗,像他为罗伯特·洛威尔写的挽歌。这里面并不存在有人指出的对其他作家——包括奥登——的模仿或蒙恩。
在秋天的蔚蓝中
在你教堂蒙着头巾的新
英格兰,豪猪
顶住波士顿的砖
磨尖了它金色的刺
成为一束无人需要
却令人眩目的光
无论何时布罗茨基听起来像奥登,这种声音并非出自模仿,而是源于崇敬,而这种崇敬是被公开承认了的。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英语写作所做的是对一种语言的赞美,就像他非常热爱的俄语一样。而且,对这种语言的热爱扩展了他的精神经历,并非由于移民的犹豫不决,而是出于惊人的愉快。这是他从流亡中获得的幸福。
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马雅可夫斯基,无论前苏联怎么对待他们,他们都留在俄罗斯,留在他们祖国的语言中。布罗茨基的情况不同。舞者的身体语言无需翻译,科学家的公式也是这样,小说的力量可以通过情节和人物得到理解,但是将诗歌的本能嫁接到一个在政治上不具形体,并被剥夺公民权的躯干上,嫁接到除了记忆没有行李的心灵上,这需要一种首先使自己惊讶的力量。
语法是历史的形式,布罗茨基这位自译者深知这一点。因为他是一个诗人,不是小说家,他关心的不是句子里的行动,被语法释放的历史,而是从接近的音节中生成的动作,不管俄语月份或蛾子的性别,如果有人批评布罗茨基说“这并非英语”,这位批评者是对的,却是以错误的方式。从历史和语法的意义上,他是对的,这样说并非意味着语法错误,而是一种特定的语调。这并非“平常的美语,狗和猫都能看懂”,作为大众思想家,作为单音节的专制者,这位诗人具有粗野的、沙文主义的吹嘘习气;但是同样的批评者,在早些时期,可能对多恩、弥尔顿、布朗宁、霍普金斯说过同样的话。
对布罗茨基的英语来说,有一种声音是他特有的,而这种声音通常是难度之一。我本应写成“那种最诚实的难度”,因为在诗人中诚实是负于变化的,而变化可以变成——像奥登为了删去它们而破坏他自己的风格一样——谎言。
另一种容易的打发方式是把难度称为“纯哲学的”,当然,还会把费解归因于翻译的错误。但多恩也是一个翻译自己作品的诗人,他向我们表明,当他努力追求意义时,那种努力就会进步。布罗茨基做了同样的事:
于是,深受光,热,
冷或黑暗的速度之害,
太空中的球体,没有制造者
旋转复旋转。
——《七首希腊古歌》(由保罗·格拉夫斯
翻译)
或:
暴躁源于灵魂向一种无形
或膨胀的心境乞求怜悯。
不过如果它一语中的,蓝色的塑胶
皱成卷云暗示着上帝,
说,“赐我力量以承受痛苦,”
并记住它,像一首极好的抒情诗。
——《六重奏》
二
布罗茨基的榜样,奥维德,《农事诗》的维吉尔,普罗佩提乌斯,甚至他的大型颂诗《立陶宛夜曲》里的品达,都是挑战性的古体;一个现代诗人可能证明他们甚至如此自以为是,而且那么倔强。由于现代主义的喷流,由于庞德、艾略特,以及威廉姆斯引发的巨变仍然令人作呕,在一个将古典与古董混淆的时代里,它把正常或反常的生活紧紧放置于一个理想但迟钝的过去旁边,布罗茨基与哀歌的诱惑已经毁灭的看法相对抗。反而,他用好战的蛮性使它们的氛围粗糙了,这种蛮性来自早期的俄罗斯草原或森林或木制的城镇。他咀嚼和吞咽过去的声音清晰可见。他将自己被毁坏的牙齿比作帕台农神殿;他的塑像被它们的无花果叶片遮蔽了,它们有丫叉,但这种粗野当然只是一种行为。不过,这要比希望过去消失好,或者,像艾略特和庞德在他们拜伦式的浪漫主义时期所做的,它可能回归。布罗茨基的画眉鸟在柏树的“发型”中歌唱,而且,他的风景不是对着蓝色大海的一排破损圆柱;它不是部落的,祖先的荒漠。它是暮色中广阔的俄罗斯乡村。
每个诗人的灵魂中都有一种特殊的曙光,对布罗茨基来说,它不是深黑色的大海,在海边为古典帝国的落日而悲伤,而是为了那个哀歌因天空和地平线的音叉而从中产生的时刻;在他的书页中,当三角形树林的旗帜变成轮廓并进入夜晚,一个人听到的是针叶林那种令人不快的声音。
帝国的夜晚,
在一个贫困的省。针叶树的力量
涉过涅曼河——密布黑色的长枪——
带走三层楼高的古城考那斯……
——《立陶宛夜曲》
或者风景会在遮盖一切的雪中变白,如同茂密的森林从古斯拉夫语字母的灌木丛变成这张白纸。在此过程中,诗人的声音嘶哑了,变成了低语。
那是一首牧歌的诞生。而不是牧羊人的信号,
一盏灯突然亮起。古斯拉夫语字母——
仍在无知地奔跑
在路上,仿佛想逃脱追捕者——
比著名的预言家知道更多的未来:
知道如何变黑,以反对白色,
只要白色在延续。直到最后。
——《牧歌4:冬天》
民主国家对它们的艺术是专制的。最安全的艺术确保共和国的永久,极度平庸的监视,或报酬,而对布罗茨基来说,他的在两个自我理想化的民主国家——美国和苏俄——写作,移民的角色只能继续变暗,不只是因为他对这两个国家都不赞美,而是因为他好像居住在他自己的国家,咕哝着复杂的独白,这并不简化它的引文,他的精神似乎并不悲伤,而是珍惜父子关系的断绝,他游移在既不神圣也非不可知的土地上,换句话说,一个自我。如果他充分利用自己的经历——一个俄罗斯的犹太人、一个美籍俄罗斯人、一个古典的现代主义者——他将会成为一位次要诗人,而那个自我,公开地、万分愤怒地不去做最容易的事,并声称“我拒绝服务”,因为“我拒绝服务”是自我的情节剧。它却拒绝愤怒,它不热情地奉承拷问者或体制,也不迅速缩进自由女神雕像的低矮怀抱里,因为它可能担心被她的火炬灼伤。最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布罗茨基的自我是匿名的:正是这一点使它成为古典的。不那么高贵,因为那个声音在哀号,在抱怨,这确定了它的主人通常是一个逐渐秃顶的发牢骚的人,一个脾气暴躁的客人。
这些天来,傍晚的太阳依然使公寓的骨牌
失明。
但那些爱我胜过爱他们自己的人已不再
活着。猎犬,已经失去它们的目标,
用报复将余生挥霍——在这里它们确实
与记忆,以及所有事物的命运非常相似。
太阳
落了。远方的声音,这样喊着“人渣!
别烦我!”——用的是外语,但它合乎
情理。
而这个世界最好的咸水湖伴着它金色的
鸽子
笼,它闪亮的光芒足以让瞳孔转动。
至此一个人再也不可能被爱了,一个人,
憎恨逆流游泳,毕竟太清楚
它的力量,将自己隐身在远景里。
——《在意大利》
酸酸的有些拜伦的味道,太聪明了以致预见官僚势力的诡计,在《致乌拉尼亚》的城市间游荡。这种印象暂时被韵律增强了,长长的诗句伴以阴性词尾,以及它们在俄语原作里三连韵的回声,它们并没有《唐璜》的仓促叙事,而是比较轻松,像“爱之航”(Amours de Voyage)的峡谷。然而,那一股酸味逐渐消失了。呼吸中并没有酒气,也没有因摆脱流亡而醉酒的感觉。这种被翻译的俄语的危险,通常体现在六韵式的押韵方案中,而在英语里韵律通常和喜剧、戏仿或讽刺联系在一起。没有一个现代英国诗人或美国诗人敢这样冒险--用阴性词尾是绝对严肃的,试图达到崇高和高贵的效果,并没有衰微的虚假人性,以及能伸缩的自负。押双音节韵和长句子威胁了当代英语诗歌,在奥格登·纳什戴眼镜的阴影下,更不用说拜伦饶舌的精确了。因此巧智已经成为押韵的方式。玄学派诗人的巧智,按照艾略特论多恩的文章,是每个现代诗人尝试的东西,但这类诗大多没有诗歌的历史,没有警句式的插入语的感觉;事实上,这种插入语成了现代诗歌的主体。
大多当代诗是一种旁白之作,大多现代诗可以作为插入语放进括号里。布罗茨基诗歌的智力元气甚至对他的诗人读者也是太惊人了,因为它包含了手艺的历史,因为它公开尊崇它的遗产。但——这样一来的回报是——这种巧智建立在诗人过去常常提高手艺的基础上,通过智力,争论,一种对当代科学的意识,与其说是注重对过去的感觉,不如说总是必然把过去从语法上描述为现在时态。这就是他使自己成为一个如此丰富的诗人的原因;一个人感到他已经写了这么多诗,大多数很长,因为它们充当了反对现代的堡垒和要塞。这样一种勤奋需要大量的精力,就像它需要大量细节一样。这是一系列累积的旁白,渐进的观察,不仅通过隐喻,而且通过隐喻的影响,以及隐喻所能引起的矛盾。从预期的感觉来说,它决不能是美的,用同样的方式,多恩的诗会很丑陋。
这是布罗茨基为这个行业设置的致命的范例。他向我们展示了我们的才智是多么的偶然,因此又是多么的徒劳。他转向训练以达到它应有的效果,创造性的极度痛苦。而他将会完成这件事,不以自传为道具,不把自己被驱逐出境作为国际性的戏剧。
流放的戏剧远去了:对布罗茨基来说,它各方面都已经被盘剥了,那个国家驱逐了他,又接受了这位被驱逐的人。流放的戏剧远去了,但伤痛犹在,这就不是戏剧性的了。父母去世了,悲伤令人心碎,暴君隐匿难见,新的罪恶是一个办事员把要求传递给另一个办事员--没有内疚,隐身,面无表情,更不包含任何个体责任或原罪。国家留给他们的是什么?母语。故国景色中映出她的形象:在流放、起床、吃饭、写作时,透过泪水,他时刻看到的只有母亲。
对你的思念正在后退,犹如听到吩咐的女
服务员。
不!就像铁路站台,印着大写字体的德文
斯克或塔特拉斯
而古怪的面孔隐隐逼近,颤动着,那么庞大,
还有地形,昨天才进入地图册,
于是充满了真空。我们中没有人完全适合
雕像的形象。也许我们的血管
缺乏硬化的石灰。“我们的家庭”,你曾说过,
“没有为世界贡献将军,或者——如我们
许愿的——
伟大的哲学家。”不过,幸好:涅瓦河面
洋溢着“平庸”,已不能再承受另一个倒影。
在刊登着她儿子进步、前景逐渐广阔的日
报中
什么可以留给整日围着平底锅的母亲?
——《纪念》
当一个人得知这里的母亲指的是诗人的生身之母,也是他的祖国俄罗斯,这种痛苦就会加深。儿子的进步也是俄罗斯的进步。
在《立陶宛夜曲》中,布罗茨基写给另一位流亡者。他宣称俄罗斯的土地具有超越政权的维度,并超越了他和他的流亡朋友托马斯·温茨洛瓦共有的悲伤。
在有些地方
事物并不变化。它们是一个人
记忆的替代物。它们是固定物
取得的尖酸胜利。每英里
有条纹的栅栏如此清晰……
一个寂静的,惊愕地张大嘴的夜空朝这节诗中的皱纹呼吸。
帝国的夜晚,
在一个贫困的省。针叶树的力量
涉过涅曼河——密布黑色的长枪——
带走三层楼高的古城考那斯;当黑暗降临
一阵懊悔的脸红掠过灰泥,
而那些鹅卵石像网中的鳊鱼一样闪光。
这首诗预示了黑暗,像河流一样私语,它不曾通过突然从云端传来的无比快乐的短号声而得出结论,也不曾通过它的音调陷入泛神论的感伤而得出结论;反而,它具有那种揭示真理的稳定而持续的低音,诱惑听到的人牢记于心。
在天空下面
远在立陶宛山峦之上
有个声音听起来
像为整个人类祈祷,声音低沉凄凉,飘
往库斯卡亚方向。这是圣·卡西米尔
和圣·尼古拉斯在他们难以抵达的处所喃
喃自语
在那里,注意黑暗的经过,他们细察
时光。缪斯!来自你居住的
高处,超越任何教条的平流层,来自你稀
薄的以太,
看,我为你祈祷,和
他们两个一起,
在这些安静下来的凹陷的平原和阴郁的
诗人后面。
不要让手工的黑暗笼罩他的椽子。
让你的哨兵在他后院站岗。
看,乌拉尼亚,在
他的家和他的心后面。
《致乌拉尼亚》的第一首诗,《1980年5月24日》,已经超出了暴怒的范围,似乎它是由皇帝的世纪唤醒的。这个流亡的犹太人在那边独处荒野,使犹太人和犹太人迫害者的专业人士同时大为恼怒的是,这个被驱逐者竟然在享受这种荒凉。《1980年5月24日》是一首生日诗。是一首伴随着玩笑的哀史。这位流亡者从种族的集体抱怨中后退了。
我勇敢面对铁笼,因为笼中并无野兽,
将我的期限和绰号刻在座位与屋椽上,
临海而居,在绿洲中迅速打出爱司球,
和魔鬼熟悉的人一起吃块菌,身着燕服。
从冰川的高度我目睹了半个世界,尘世的
宽度。两次淹死,三次让刀子耙出我的本质。
离开这个生我养我的国家。
那些遗忘我的人将建立一座城市。
我跋涉在草原,看见在马鞍上叫喊的匈奴人,
到处都穿着现在又流行起来的衣服,
种植黑麦,在猪圈和马厩的屋顶涂抹沥青,
狂饮暴食各种食物,除了干水。
“那些遗忘我的人将建立一座城市。”将一瓶伏特加酒和看不见的未来留给了俄罗斯,从“像鱼子酱一样变黑的城市”——用一首早期诗中的短语来说——的标准来观看,这首诗结束于这位流亡者的呕吐,其中有“棕色的泥土……塞满我的喉咙”,这种不敬无疑源于对任何政府或种族的恼怒。
布罗茨基将会被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流放,不只是从苏俄,一个人从心里感到他现在宁愿流亡。最远的流亡是死。
布罗茨基的诗留下了死亡感的痕迹。时间磨损肉体,拆掉针缝的线后留下的纹理,但没有灵魂能逃出身体被弄皱,被抛弃的衣服,像蝴蝶一样因轻盈与透明而颤抖。不像他的导师多恩,他保持着一种维度,无论他可能被它多么为难,他认识到这一点,出于经验,出于没有前途的现在时,一个没有复活,没有预言的人。十四行诗和喇叭号声鼓吹信仰,来自多恩开场白的序曲,像一段经过华丽挂毯的文章片段:
因为我去见那神圣的罗马人,
……
死亡并不值得骄傲,尽管有人认为你
强大,令人恐惧…
在这个浑圆的地球上被想到的角落里,在
你的喇叭下面,天使们……
数世纪之后,我们现代帝国--那些西方和东方的帝国--的理性辨证法已经形成了这种唯文学是信的状况,使诗歌像挂毯一样古色古香,华丽但不真实。但诗歌与过去都不是挂在墙上的装饰品,这不仅符合布罗茨基的见解,也符合他的体质。疾病遮蔽了他的书页,可是诗歌却显得毫不慌乱。事实上,他诗节设计的牢固建筑,错综复杂的三连韵,是牢固的、具体的,没有一颗心灵对它们的才能产生丝毫的怀疑。
不过,没有渴望,这些诗也包含了天使,六翼天使,但不是里尔克式的人的理想化,而是作为事实出现的,作为穿着白色战斗服的滑冰者,作为窗帘后面的沙沙声,或者只是作为雕像。布罗茨基的心灵进入雕像,没有任何祈求美化它们的想法。在他心灵的住室里,六翼天使和水壶变成了寻常之物,而在外面的天气里,
似乎水银位于它舌头下面,它不愿
说话。似乎它括约肌里存着水银,
不能移动,在一个叶子覆盖的池塘附近
一座雕像站成一片白,像枯萎的冬天。
下了那么多雪以后,世上真的一无所有数
世纪
的里里外外,被纠缠的石南花。
那是即将到来的圆环包含的寓意——
当你的面容开始模仿天气,
当皮格马利翁消失。你可以随意
弄乱你的衣褶,露出肚脐。
最后是未来!也就是说,在“决不”(never)
这五个字母中是冰川的白色碎片。
因此,一位绝世美女——她的娘家姓是雪
花石膏——
的日常生活是让穿粗纱的小学生借助
脸面的中心和膝盖的温度填饱肚子。
这就是处女内部看上去的样子。
——《加拉泰亚重临人世》(用英语写的)
一只蝴蝶飞落在坦克的加农炮上,它颤动的翅膀可能看上去更加脆弱,但只是在一个方面,因为蝴蝶可以通过它们适应的柔韧性,通过让它们的本性屈服于自然力,从而在暴风雨之后活下来。而坦克却可能由于自身的重量陷入泥潭。这就是现代俄语诗歌的力量,它的诗人具有飞落在加农炮上的蝴蝶的矛盾,面对苏联国家机器的军事力量,他们的脆弱不是难以琢磨或负于幻想的,而是对它的无边草地,以及锯齿状的森林的自然表达。站在讽刺的电线上的一只蝴蝶是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阿赫玛托娃是一只飞在监狱高墙底部的蝴蝶,她在那里探望她的儿子;甚至还可以加上一个翅膀合拢的蝴蝶:茨维塔耶娃,她自缢了,通过那个令人痛苦的动作释放了她的灵魂。通过他们,俄罗斯在外省保留下来,而地方特色正是每个诗人的天然真理。
它们就在那里,结满蓝莓的森林,
在河里人们徒手捉鲟
或者在城镇,你已不再扮演主角
电话薄也显得乏味;再往东奔腾着
褐色的山脉;野母马畅饮
在高高的莎草里;当它们越聚越多,
面颊骨变得越来越黄。在更远的东边,是
蒸汽无畏舰或巡洋舰,
而这广阔的区域逐渐变蓝,就像网眼内衣。
——《致乌拉尼亚》
这种军舰就像坦克,其履带就是它们的踪迹,一个遥远的,平淡无奇的中心区域,奔腾的马群和蓝莓丛,无视它们。俄罗斯太宽阔了,不适应任何政权的界限,而蝴蝶,无论如何,离地面是较近的。
触摸我——你就会触到干燥的牛蒡茎,
第十三个月后期的傍晚固有的潮湿,
城市的采石场,宽阔的俄罗斯大草原,
那些不再活着却被我记着的人们。
——《后来》(由杰米·甘布里尔和诗人翻译)
这是飞落在阿富汗的坦克转动炮塔上的蝴蝶,但那也是被坦克运载的,在布罗茨基构思宏大的诗篇中,坦克意味着重物,泥沼,稳定的抬升和笨重的运动。它们宽阔的履带压过的地方并不平坦,由于沉重,它们有时停止转动,呻吟着,齿轮摩擦着,穿过分号的荆棘丛。我们随着诗行抬升,休息,推进,但它们总是清晰地出现。它们已经选择了难走的地形。
正是这种重量、宽度、坚定的方向,各种语言的诗人钦佩布罗茨基,一个关于英雄级别的典范,他的自我征召,他日常的军人作风,背后却没有任何军队,除了这个种族最伟大的诗人幽灵之外,他们从每个时代向他发出呼唤。他的祖国不再能够遗弃他,像奥古斯都时代的诗歌可以流放奥维德那样。他有自己不可改变的俄罗斯,正是通过她,通过对她的孩子们——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消瘦的曼德尔施塔姆——的款款柔情,他的抒情诗用他们的力量,他们的脆弱和友谊触动了我们。
又一个圣诞节结束了
对条纹和星星的浸泡。
我所有的波兰朋友们
正在监狱的铁窗后面,
像乌有一样被锁入
某张愤怒的图表:
作为一种惩罚
奴役胜过数学。
……
比你的或我的
思想深度还深的
是在未耶克矿井里
死亡的长眠;
高过你的租金的
是那只手,它的手艺
使别人屈身——
就像被拍下来的。
无力的是话语。
不过,它胜过泪水
试图达到的,
穿越国界,
为了我波兰朋友们
沉重的心。
又一次考验开始了。
又一个圣诞节结束了。
——《一首军事法颂歌》(用英语写的)
《致乌拉尼亚》中,并非所有诗歌都是由布罗茨基翻译的。因为他是一个如此苛求而具有扩张性的诗人,我们感激这种相当大的劳动,在许多译作中,哈里·托马斯(Harry Thomas)的《高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Gorbunov and Gorchakov)达到了忠实的精确和匿名,这是一首四十页的诗,被依据诗节的韵律重译,杰米·甘布里尔(Jamey Gambrell),简·安·米勒(Jane Ann Miller),乔治·克莱恩(George L. Kline),阿伦·迈尔斯(Alan Myers),和彼得·法郎士(Peter France)的译作也是这样。它的译者们与这本诗集的性情已融为一体,而且没有增加他们自身的癖好,《致乌拉尼亚》有如此统一的声音,这个事实证明了它们的透明度。即使这里没有一首诗达到理查德·威尔伯(Richard Wilbur)在布罗茨基的前一本诗集《言辞片段》中的《六年以后》取得的改写奇迹,然而,从美国当代诗人的眼中来看,那本诗集在布罗茨基诗歌收集的多样性上未必有这么理想。《致乌拉尼亚》绝对是一个整体,正是这一点不仅丰富了它本民族的文学,而且丰富了这个国家的文学,在这个国家里,一个确实伟大的诗人,一种近乎卓越的智慧,使我们感动,并感动我们当中那些打着另一种公民的幌子的人。
栏目责编:皮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