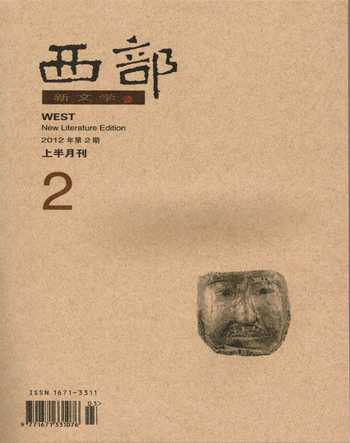微观都市五记
颜炼军
死者的位置
刚到杭州生活不久,住在一个比较老的小区。小区里老年人很多,不免常看到小区单元某间房子的窗外挂着花圈,在不适宜的高度,宣告死神的莅临。楼层低的人家,花圈拴在钢窗外,有时下面还用一根杆儿顶着。楼层高一点儿的,可能就得想别的办法把它固定住。好在,这是一个九十年代初建的小区,楼层都不高。因此,花圈或高或低地挂着,至少可以让路人看到它们的象征意义。比起街市的喧哗,小区里很安静,傍晚,楼房间的林荫空地上,处处可见白天奔跑后停息下来的车辆。有时,还有死者家属和亲友在此举行超度灵魂仪式,祈祷着另一种休息。
当然,在更多的地方,则并不宽敞。尤其对于那些居住在临街小区或楼房的居民,如果家里有人去世了,举办仪式的场地就很逼仄。家门外放着花圈,陌生人路过,要仔细看才分得清,这到底是花圈店的摆设,还是有人去世的标志。死亡在城市社区里,变得不清晰,除非碰巧看到超度或祭奠仪式,我们才能确信有人离世了。
有一天晚上,大雨滂沱,我在体育场路边看到一个规模不小的超度仪式。在以休闲天堂名世的杭州街头出现此景,真让人有些意外。这是通往另一个天堂的蹩脚仪式:十几个尼姑、和尚围着一张临时拼成的长条桌念经,家属们簇拥其间,似乎也在跟着默念。雨很大,主人家在桌子上方搭建了一个遮雨棚,为死亡仪式圈定了一席之地,这也多少占去了本来就不宽的人行道。行人、自行车、电动车挤在一起,有人还停下来看看。丁丁当当的铙钹声、木鱼声和念经的腔调被暴雨声冲得七零八落。靠在楼脚下成排的花圈,黯淡地对着前面宽阔的马路上闪烁而过的车流。一旁装饰香艳的冷饮小店,为驱散死亡的气息对自家生意的弥漫,把张韶涵的歌放得异常响亮,似乎在抢回属于自家的地盘。这一切,相互冲突地凑在一起,有点热闹,有点凄凉,唯独少了死亡的庄重。在这个空间形态中,仪式的操办者、参与者、旁观者、过路者,甚至看不见的亡灵,草草地邂逅,充满尴尬、冷漠和陌生。
在传统的中国乡村社区,丧葬和祭奠依然遵循着一套礼仪,其中包含了复杂的象征系统。但这些礼仪和象征系统,都有着空间制度上的充分保证。中国人常说“人命关天”、“死者为大”,其中便包含有这层意思。在乡间,几乎每个村都有举行丧葬仪式的固定场地,比如寺庙、自家的院子或其他公用场地,更不用说每家每姓都有祖坟地。因此,乡间的空间布局,让每一个邂逅葬礼或祭奠的人,都升起一种面对死亡的庄重和礼貌。在这种空间布局的保证下,死亡是葬礼上统摄一切的主题,即使其中有必要的嬉笑和喜剧情节,也不失庄严。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丧葬仪式和制度依存的空间系统,西方国家承担这些职能的社区教堂和教会机构,就更不用说了。
现在,中国在大规模地城市化,中小城市因为与大量的乡村毗邻,丧葬仪式与制度内在的冲突还不算紧张,因为,乡村社区还勉强可以承担死亡仪式的空间功能。但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因为空间的紧张而“死不起”,已成一种公共性困境。如我们常常感觉到的,城市里正在形成的丧葬仪式和制度,多少都呈现出缺少空间的焦虑感。因此在越来越多的大都市里,还没有一套合理的仪式和制度来得体地保证死者的位置和尊严——它们是生者的位置和尊严的延伸和折射。记得多年前,作家吴洪森先生曾有一篇妙文,建议北京市政府把城市西北不远的沙漠开辟为墓地,鼓励各家各户到沙漠上开辟自己的新墓地,并在上面植树造林,这样既可以解决死者“拥挤”的问题,也可以解决生态问题,如今看来,真乃理想家的高见。
近几年的楼市大跃进,催生了无数的新城市社区,更加证明了吴先生当年的担心。街上琳琅满目的楼盘广告卖力地展示各种“魅力”和“诱惑”,炫耀各色“前景”和“未来”。只是,在这些对家的更新和重构里,都来不及考虑死者的位置。长此以往,如果这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对死亡的观念、习俗、仪式和制度不像他们目前的生活一样,很快地变得纯粹的物质化(毕竟,死亡更是一个精神问题),那么,随着中国老龄社会的来临,笔者所见的杭州大街上的尴尬祭奠仪式,可能会有逐渐增多的趋势。能拥有一个和谐的空间仪式的死亡,将越来越稀罕,如果我们的现代化城市生活中,没有及时给每一个死者,也就是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安排一个合理的位置的话。
当食物都摆在超市货柜上
假期,朋友带三岁的女儿回乡下。路上,女儿见到一只鸡,就很兴奋地喊道:“爸爸,爸爸,看那只鸟。”爸爸苦笑道:“那是鸡。”
“鸡是用来吃的,鸟不是。”听了女儿争辩的话,有农村生活体验的父亲羞愧不已。
在超市货柜面前挑选各种肉类时,我不时想起那只不幸的“鸟”。古时,男人去丛林或江海渔猎,女人负责采集、编织;后来,一部分动物被驯养了,男人耕种田地,女人从采集中解放出来,继续居家编织;进入后现代社会,动物驯养、植物的培植采集和编织业被规模化,它们彻底离开了许多人的日常劳动。尤其在城里生活的人们,日常生活所需都有了一个更为便捷的来源——超市。超市让所有千差万别的物,都沦为食品和用具,构成了一个新的秩序。上述小女孩眼中的“鸟”和“鸡”,正是来自超市冷柜里的动物秩序。
超市的丰盛,意味着令人感伤的丢失。过去,大部分人得历经许多食物的培育、采集、养殖、制造、烹饪等等几乎所有工序。比如,农民从养母猪开始,配种、产仔、饲养、屠宰,几乎要见证这一生命体的所有行程。我曾亲眼见过,在猪被杀死的那一两分钟里,家里的主妇是很紧张的,为了缓减猪的痛苦,她虔诚地跪在灶王爷面前,为这头不幸遭杀的猪祈祷,希望此生悲惨的它在下个轮回转世为人。在藏族、回族和许多其他民族的习俗里,屠宰动物都有相关的灵魂超度仪式。由于浸淫在这种生活方式里,人与物之间有一种特别的关系——学时髦话说,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主体间性。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生活方式里,人把一个动物当做另一个活生生涌现的生命。人在屠杀和食用它时,感受到某种亲验性的生命痛感,将之仪式化,并形成了许多关于物的观念,比如“敬饭得饭吃,敬衣得衣穿” 。
现在,这一切渐渐被赶走了。在超市里,活生生的动物变成被蜕皮、肢解的肉,放在冷柜里,添加在各种加工食品里,从全国乃至全世界调度来的各种生活用品在不同的货架区域陈列。原始人面对的丛林乃至无边的自然,碎尸万段于此间。进入这被肢解、分割的动植物的丛林和水土中,顾客被各种商品吸引,只需选择和付钱,便可把物品带回家。付钱或刷卡,让人想起远古时期的猎人射出的箭簇。网络购物的出现,愈发简化了这个程序。人们足不出户,便可以享受送货上门的待遇。据说,在曼哈顿,一切可以想象到的物品和服务都可以在网上预订。
就这样,站在消费的终端,我们的生产功能与消费需求过度分离。物的经验在这样的日常生活结构里单一化了。过度便捷也会带来枯燥。因此,在瓜果成熟的时节,城里人去采摘水果,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享受采摘的乐趣。人们养宠物、养花草……甚至早就建立了作为动植物纪念馆的动物园和植物园,某种意义上,都是为了怜惜、修复与已经沦为食物的动植物之间的主体关系。当然,比起我们听闻和见证的那些大规模的动物屠杀、森林砍伐而言,这一切都只是枉然的追悼性行为。
食物都摆在超市货柜上,经过各种物流手段,最后进入不同的胃。因不能亲验动植物诞生、成长和死亡的生活,人们把食物单纯地视为食物。绝大部分吃肉的人从来没有见过自己吃的那头动物长什么样子,绝大部分吃蔬菜的人不知道自己吃的那棵菜是如何长大的。它们作为生的丰繁和死的痛苦,被集约为一种丧失了劳动本色的生产、运输、销售、加工,而不再作为日常生活必须的部分一次次地提醒和教育我们的内心。当人类失去了与事物之间的主体间性(脱离这蹩脚的翻译,用中国古人更为乌托邦的话说,就是“仁性”),就不得不长久地面对自己的孤独。现代日常生活的无生命化,已经成为我们生活悲喜剧的重要来由之一。
公园手记
这座公园像一个被部分实现的愿望,经历几劫几世之后,终于把自己安放在遮天蔽日、甚嚣尘上的闹市中。上百年的皇宫古迹、八方路过的鸟类和进出的游人过客让这里成为一个时空的焦点。
亭台楼阁、水榭歌台、湖光山色,构成了大自然在城市里的最后丰碑,它们不仅默默表达着人们对南方的精致的思念,也让观赏它们的游人回归山水或洞穴中,模仿着他们遥远的祖先。习惯以各种机械代步,携带各种通讯工具的人们来到这里,犹如梦见自己回到了祖先学会点火的洞中。游人对暂驻枝头的画眉鸟嘘一声,孩子扔一枚石头惊起水中病恹恹的鱼群……弥久不死的自然,让人不断摆脱心物勾结成的诸般枷锁。
是的,所有的尘世的念想,在进入公园之后,将会染上山水树木和虫鱼鸟兽的气息。在竹林中,林荫道上,荷池边,假山上,虽然常常弥漫着落空的理想,初开的情窦,流产的功名利禄,烦躁的灵魂,但这里至少是一个从容的展露和言说之地,有多少个在尘世中隐藏起来的秘密自我,在这里的某一个角落获得露面的机会!
练功者在这里暂时忘记通往死亡的路途,在天地间比划出自己的健康。缺爱者在这里思量、倾诉、盘桓,寻找爱的幻觉。当然这里也孕育着一场场偷情、谋杀。许多故事从这里开始,许多故事在这里结束。许多人在山水树木的影子里体悟到上帝的必要,成为基督徒。
这里也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常去休息的地方,城市里大概只有这样的地方不收费了。他们在这里思念家人,重温土地的味道,抚摸疲惫的手背,谋划着怎么讨回自己微薄的工资。
这里也是盗版书贩做生意的地方,他们在这里秘传盗版的文化知识,与城管进行着无尽的斗争。他们有时是不是也预想,有一天老去的时候,他们可能与那些追赶他们的人成为某一个城乡结合带的邻居,或者两个阳台上互视的老人?
当我作为一个公园的过客想到上述事情时,无数过客想到的一定更多。它们没有机会被说出来,就消失在记忆之林中。我说的,只是最为庸常的部分。
长途汽车站
长途汽车站有位出行的少妇,有两个人为她送行,一个男孩,一个老妇人。男孩也许是她弟弟,或者她的儿子?从外表看不出来。从举止猜测,老妇人该是她母亲。她们面色焦虑地交谈,母亲的嘴断断续续地在风中嚅动,少妇隔一会儿就低头一次,或者朝四周张望一番,可能在等待一个送行迟到的人,或者看看车可要启动。无心留意的旁人听不清楚她们谈话的内容,即使要仔细听,也不一定能听见,风把没来得及传远的话吹散了。男孩穿着灰旧的牛仔,头发被风吹得有点凌乱,手中的提包似乎有点重,两个肩膀一上一下,嘴角的微笑中绽放着迷茫和期待。突然,人群骚动起来,车站旁门开出一辆乳白色中巴车,停在始发车位。男孩迅速把包递给少妇,母亲也推了一下她,她被推到上车的人群中,不由自主地走向车门……
看到此景,我们多么想有奇迹发生!希望那身份未明的男孩手中的提包变得轻些,那么他可以站直一些,少妇的出行也可以轻松一些;我们多么希望那位母亲对女儿的前程多一些希望,少一些愁苦;多么希望一位英俊的男子出现在车站门口,向少妇挥手,给她身后的牵挂加一点点重量!
每个人在一生都会有出行的这一幕。喜怒哀乐大抵相同,只是道具不同。而我们对与自己有关的送别,有缘关注的事物,总能够感同身受,体察入微,以饱满的热情和悲情,把我们意识和观察到的描绘出来,自以为世界饱满如此,心灵充盈如此。
可是,旁边还有许多人在送行道别。我们的一双眼睛只能专心看一件事物,在短暂时间里我们只能被一件事迷惑。所有其他的事物,虽然就在周围,但都与我们无关。从这个角度上看,每个生命都是单薄的,厚此薄彼是其真实处境。
时间外套的温暖
乌托邦处于线性时间的末端。在这种线性时间的幻象之下,日常生活却有自己的时间规则。今天的城市生活已然形成了独有的时间规则,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背叛了线性的时间流程,将自己缝合于另一种时间外套的温暖中。
今天,大部分城市人成了上班族,尤其是二十岁至四十岁的人,他们代表了城市生活的主流。上班、下班、加班和周末构成了紧密的时间链条,环绕着上班族,将他们的生活内容和愿望都裹在其中,日复一日,每星期代表了一个小的轮回,每个月代表一个大的轮回,人们在此间的时间感呈旋转状,围绕在周围,直至积累成一个更大的时间单位。积累的过程形成了城市上班族日常生活的时间观念:时间是环形而非线性地驱使我们向前,像乡村儿童手里滚动的铁环。这种环形的时间流动方式切割了上班族的生活内容。
上班时间具有系统的、机械的和理性的特质,它被赋予了集体乌托邦的内涵。上班族必须严格地按照这样的时间方式来看管好自己的生活:约会、购物、聚会、旅游、娱乐等私人生活都必须服从于因上班而来的时间机制。人们必须尽量将私事安排在上班时间以外,上班时他们必须服从工作程序,听从(哪怕在表面上)领导安排,配合同事的工作,或者安排好下属的任务。早上固定时间起床,完成每天的工作任务、周计划、月计划……完成和自己物质利益紧密相关的集体任务,并被这些计划和任务牵引向前。
而下班后是另一种时间。城市发达的超市、酒吧、剧场、网吧、饭馆、歌厅等构成的夜生活,郊区或者外地的休闲风景区和度假村贯穿着另一条时间脉络,它留给下班后的人们用以宣泄激情和排解烦闷,驱赶无聊。庞大的城市肌体给了这一部分时间足够的机会满足人们见异思迁的本性。这一时间脉络中包含着的生活随机性,以及多层次的、不断变幻的消费内容,给城市机械的时间方式中注入了新型的想象力。下班后的时间、周末或者节假日给了上班族新的狂欢形式,这些时间被赋予了一种间于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意义:现实就是工作,而对工作的超越或远离,无论在多大程度存在,都具有一种亚乌托邦意义,它弥补了被现实/被动的集体工作淘空和硬化的心灵。确切地说,这段时间包含的是一种更富个人意义的瞬间乌托邦。下班后的时间里,个体不必再局限于某种被动的集体行为中,而是被身体的需要消费——各种消费场域预设和虚构了愿望和由愿望集合而成的消费乌托邦,与此同时,在这种消费中,个人消费的乌托邦随同上下班时间交替带来的激情在消费中被及时释放了,每天、每周或每月完成的逐级轮回时间以及乌托邦生成和瓦解的周期使得人们不再有凌空高蹈的激情,所以,在这样的城市时间模型中,很难积累起强大的社会逆反力量,只会给人历史和生活终结的幻象,从而促成庸俗生活的遍地滋生。
在这样的城市生活中,时间再次被分成了理性和非理性两个部分,它们蕴涵着推动当代城市日常生活运转的两种乌托邦力量。今天,尼采笔下的阿波罗依旧光照上班族,但它不再是高悬的太阳神,而是悬浮在城市空气的粉尘中,提醒每一个上班的人必须花一部分时间上班;而酒神成了夜间、周末和节假日的常客,他跟随着躁动的人群,从办公室走向酒吧和歌厅或者其他休闲场所,从喧闹的城市走向贫瘠安静的乡村。上班和下班的时间轮回构架,规定了城市人的乌托邦形式:薪水,奖金,和与它们相关的单位远景目标或年终利润计划,成了上班族对生活的基本企盼方式,这些企盼慢慢改变着他们应对世界的方式,在理性时间中,他们为低悬的理性目标努力;而在非理性时间部分里,他们乐意通过消费、娱乐、狂欢等动物性欲望的满足,来融化理性时间带来的成就、烦恼,以便最终愉快地回到理性时间中去。这种时间轮回的方式,决定了当代城市生活乌托邦的身材:不断虚胖,继而不断瘦身。工作、计划、利润、奖金、房子、车子、票子消耗和制造激情,构筑起理性时间的堡垒。而非理性时间转到了这座堡垒之外,它要彻底粉碎或者远离理性的堡垒,在非理性时间中遵照娱乐至死的魔法建立另一容身之所。在现代城市生活中,两种时间将永远吵闹下去,他们组成了一个失和的家庭:前者为丈夫,后者是妻子,他们可以破坏家具,撕破对方的脸,但任何人都不能摔门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