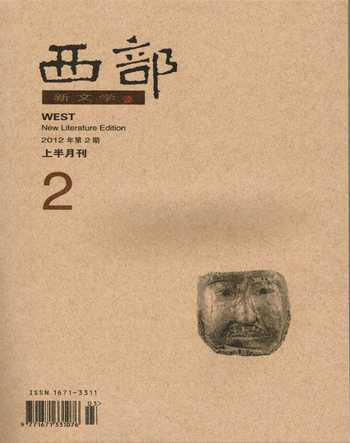水乡记忆
李清明
故乡,在洞庭湖的南岸,是一个十足的水乡。蓝色的资江与浑黄色的湘江在临资口古镇边交汇,缠绕半周后,青黄色的彩带才一步一回头地飘向浩渺的洞庭湖,流入长江,最终投归大海。
水乡自古民风淳朴、文化传承,曾是湖湘文化重要的发源地之一。乡人们热爱生活、注重人生礼仪,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继而在生命的历程中,形成了一种丰富、庄重、独特的礼仪文化。
浩瀚洞庭,千年月色,到处都被一缕缕怀旧、怀乡的微光所烛照。
埋胞衣
在洞庭湖长年淤积的湖洲上,围垦而建的家乡,常常水满为患。一部水乡史,写满了家乡人民与洪水作抗争的汗水与血泪。
或许是为了传承,抑或也是告诉后人:你来自哪里,将要去向何方?于是,早有心理准备的乡亲们,每有婴儿出生,总是会将小孩的胞衣置于一个崭新的陶罐之中,趁着茫茫月色,深埋在房屋边的一棵高大的树木底下。寓意树高千尺,人高万丈。
成年了,当有同乡问及你或他来自哪里?被问者十有八九会将人领至一处高高的堤坝上,指着围垸内一处房屋集中、炊烟袅袅、树木葱郁的地方,自信而骄傲地说:“看,那里就是我‘埋胞衣罐子的地方!”一个人离家久远,如果做了一些对不起社会和家乡的事情,则多会遭到年长者指着鼻尖的一顿训斥:“小子哎,你对得起你丢胞衣罐子的地方么!”言下之意,是指做人做事,不能对不起故土和祖宗。
水乡人家,凡有婴儿降生,须请一位有经验的接生婆,先备好一脸盆清水、一盏桐油灯、一把剪刀、一只陶罐、一大堆草纸(卫生纸)。孩子出生后,先把剪刀在油灯上烧至通红,权当消毒,用于剪断婴儿的脐带。胞衣的处理则更为讲究:先用草纸包好,置于陶罐内密封,在天亮之前(避免被人看到),由家族中一位长者,选择在祖屋边的一棵大树下,像种树一样深埋起来。按老人们的说法,这是埋“血根”。如果埋浅了,被野狗、野猫、老鼠们叼吃了,这个人就会从此失去记性,就会将魂魄丢掉走远了便找不到回家的路!
水乡多有长年漂泊在洞庭湖中,一年四季难得靠岸的渔民。他们若有婴儿出生,程序与住在岸上的乡亲们一样,十分庄重而喜庆,只是在胞衣的处置上有所不同:密封好胞衣罐,将船划至宽敞湍急的大河边,由父亲捧着站在船头,使劲扔进波涛滚滚的河心之中。扔得越远,这个孩子将来就会越有出息。
一位马姓诗人,在他的一首题为《胞衣罐》的诗中这样写道:我愣愣地望着水波/想象那当时的情形/我想那明明净净的河面/一定有好一阵不平静/胞衣罐装着我的混沌世界/和最初睁眼看世界的记忆/还有我的第一声啼哭/乃是我来到这世界的宣言/我与母体分离的正式仪式/应在父亲憋足了劲的一扔/他把一生最完美的弧线/画在阳光灿烂的朝霞里/天上又多了一条绚丽的彩虹/我的心就完整地陪伴故乡了/从此后无论我漂流到哪/都连着那根剪不断的脐带……胞衣罐系着每一个父亲的责任啊/胞衣罐刻着我们代代相扣的传承。
胞衣,又名胎盘、胎衣、胎胞,也是一味名叫“紫河车”的中药。胞衣在母体中有脐带相连,胎儿由此摄取营养。药用有温肾、益精、补气、养血等功效,可提高人体的免疫能力。在水乡,人们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与生俱来的精、气、神。神指元神,即胎神也。相传人身上的胎记,便是神留下的印记。
胞衣是神的代表物,也是母亲用血肉为我们制作的第一件衣裳。
至今,我对都市一些医药机构专门花钱收购婴儿的胞衣,制成美容口服产品,特别是一些餐厅酒家开设高价“胞衣宴”的行为,一直难以释怀。婴儿的胞衣无疑极富营养,但它和我们的生命一起来源于母体,曾是生命的保护伞和加油站,亵渎了它,岂不是亵渎了生命的本身吗?
夜色茫茫,月光笼罩,婴儿的长辈在十分虔诚地安置好小孩的胞衣罐后,大多数父亲第一件事便是借着煤油灯的光亮,把小孩的生辰八字以及出生地点,工工整整,或书写、或雕刻于存放衣服的木柜门的内壁上(过去,水乡人家稍许值钱的家当,首属木衣柜)。如此这般,于水乡的人们来说,故乡就是他(她)埋胞衣罐子的地方(也称“胞衣迹”)。自己历史起源,便是那个刻着生辰八字的木柜,即使被洪水冲走,经泥水泡过,太阳晒过,洗一洗,擦一擦,仍可认出木板上的文字,知晓自己的历史。
久居都市,自从生命从一个叫医院的地方出来,胞衣就不见了踪影,从此“胎神”远遁,“血根”无踪。我真有些担心:孩子们啊,你们走远后,还会有故乡的记忆,还能找到回家的路么?
洗三朝
水乡习俗,婴儿出生的第三天,族人均要为其举行较为隆重的“洗礼”,又称“洗三”、“洗儿”、“洗三朝”。民间传说,婴儿系送子娘娘所送,出生三日,她要亲临凡间察看,如见有婴儿家不从或不敬者,必将受到惩罚。
洗礼开始,婴儿家要清扫房屋,焚点香烛,宰杀好鸡鸭,备好鸡蛋……做好宴请亲朋好友的准备。女眷们则忙着往土灶上的大铁锅内,放进艾叶、昌蒲、金银花、樟树叶、紫苏、雄黄等物料,倒进几大桶清凉的井水,将水煮沸。待水温降至适度后,用木瓢舀进一只用开水消过毒的木制洗澡盆中,便开始给初生的婴儿洗沐。
洗礼一般由年长的婆婆、奶奶主持,边洗边吟唱一些诸如“洗洗头,做王侯;洗洗身,做富翁;洗洗手,荣华富贵全都有;洗洗腰,一辈更比一辈高;洗洗脚,身体健康不呷药……”等赞语。在洗沐礼赞的同时,还要拿根筷子点上些食物饮品,象征性地在婴儿的嘴巴上涂抹一下,也是边涂边念:“呷了鱼,有富余;呷了糕,长得高;呷了糖,保健康……”也有的还会给婴儿的嘴唇上涂些黄连,意味着小孩将来的日子先苦后甜。同时,黄连也可以消除婴儿从胎内带来的内热。
洗毕,年长的妇女还会用煮熟后去壳的鸡蛋为婴儿滚身。白嫩、滑溜的鸡蛋从婴儿的头部滚至脚跟,又从脊背滚至臀部……不断地重复,叫做“滚屁股蛋”。用以去除胎毒,白嫩肌肤。据说,滚过婴儿身子的鸡蛋送给祈子的妇女,吃后便可如愿以偿哩。同时,主家还会在许多煮熟的鸡蛋壳上涂上红色,一是分赠看热闹的亲友、乡邻,二是由父亲用提篮装上到婴儿外婆家去“报喜”,俗称“吃红鸡蛋”。难怪清朝诗人冯朝吉在《锦城竹枝词百咏》中,曾形象地描述了当时人们举行“洗礼”的场景:“谁家汤饼大排筵,总是开宗第一篇。亲友人来齐道喜,盆中拿掷洗儿钱。”
这时,被更换上崭新的衣帽和襁褓,戴上银镯、银锁、银脚铃的婴儿便会交到父亲手里,抱至堂屋中竖着祖宗牌位的神龛前,跪敬祖宗,禀告祖上,家中添丁添福的喜讯。婴儿降生时,如有不速之客进屋,称“逢生”,来客就是婴儿的干爹干娘,以后成为亲戚来往。也有的在洗三朝之日,抱着婴儿拜石头、树木等做“干爹”、“干娘”的;还有的在给小孩按辈分排列起好“大名”的同时,也会叫些“牛伢”、“狗仔”、“铁蛋”、“石头”等“小名”,以示小孩将来成长经打经摔、经风经浪,易长成人。
洗礼之日,若是男孩,有的人家还会将其手脚用绒丝带捆绑束缚一些时日,让其戒玩戒躁,从小养成稳重踏实的性格。长大后,凡是喜欢顽皮胡闹、撩手撩脚、不听招呼的男孩,惹恼了人家,十有八九都会招来一句精典的“乡骂”:“你这个猪×的,怕是没有洗三朝的吧!”
婴儿的三朝洗礼过后,紧接着便是“抓周礼”、“拜孔夫子礼”、“割礼(也叫成人礼)”等诸多礼仪,相伴人的一生。礼仪程序周密,形式庄重,充分体现了人们重视人类的延伸,对生命的尊重和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也寄托着对未来美好的希望,令人刻骨铭心。
漫步水乡,过去被视为良好文化传统的许多人生礼仪,也搭上了社会精简、杂交、享乐、刺激等快速轨道,早已不知所踪。所见所闻,叫人总想情不自禁地蹦出那句经典的“乡骂”,让人不胜唏嘘哀叹。
喊魂
临水而建的家乡过去总是十年九涝,不得安生。
汛期一至,浑黄色的湖水便会将过去还是牛羊成群、柳枝吐蕊、草木茵茵的湖床抬高许多,人工围起来的垸子像极了一个个在洪水中颤栗的盆罐。一旦垸溃,整个家乡便会一片黄汤,树枝瓜藤、木柜门板,还有用茅草和树木结成的整个屋顶,都会随风浪吹送至残剩的垸堤边,极目苍凉。洪水消退,每一个村庄的坟场都会增添好几座覆盖着黄土的新坟。
水乡人们大都称被水淹死的人为“水鬼”,男的死了来年要找一个女的做伴儿,女的死了要拉一个男的同眠。每当听到这些,小孩们便会心存恐惧地哆嗦着双腿,往人多的地方移动,害怕“水鬼”来找“替身”。
夜幕降临,一镰冷月和稀疏的星星倒挂水中,光淡水远,魅影重重,偶或传来一阵阵鱼鹰“呱……哇……呱……哇……”的鸣叫,在水波的回应下,声音凄厉而悠长……水乡月色,一切静谧而悚然。
这时,出来游玩的小孩,大都容易受到惊吓,睡到半夜往往会发低烧、说胡话,甚至梦游。老人们便会说,孩子的魂魄在外游荡,遇见了水鬼在追赶……要赶紧“收吓”,将孩子在外面游荡的魂魄喊回来。有时白天,小孩们因钓蛙、摸虾、抓田螺、捉泥鳅,突然从草丛中摸出一条水蛇;或摘桑椹、捣鸟窝、偷菜瓜遭遇菜花蛇、竹叶青蛇和毒蜈蚣、毒蜜蜂等,也会惊恐不已,魂逸魄飞,大半天回不过神来,晚上难以安睡。
遇上这些情况,孩子的母亲大都会按照祖辈遗传下来的方法:借着月光,抓一件小孩穿过的内衣,用手帕包着一小包大米,找到小孩受惊吓的地方,点上几根香烛,烧上几串纸钱,一边沿途用手向天空抛撒着大米,一边拖长着声音,十分虔诚而又满怀期盼地喊道:“宝宝哎——回来哦,宝宝哎——回来哦……”这时,坐在小孩睡床边的奶奶或姥姥,便会回应道:“回来哒——回来哒——回来哒哟。”
寂寥的夜空下,一个母亲的喊声往往引来好几个母亲在喊:“宝宝哎——回来哦,宝宝哎——回来哦……”母亲呼唤孩儿的声音在孤星残月的夜晚,经水波回应,由小变大,由近而远,慢慢地便带着一种哭腔,天地也为之动容。
小弟二毛五岁时的一个夏日中午,在河边游玩,不慎溺水,傍晚才被好心的邻居捞起。当时小弟的腹部隆起,身体僵硬,悄无声息。父亲和邻居们把他趴扣在牛背上反复颠压,吐出了好大一滩暗红色的血水……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血腥味的死亡气息。天完全黑下来了,母亲悲戚地将小弟抱起,轻轻搂在怀里,任邻居怎样拉扯也不愿松手……
后来,心存最后一线希望的母亲,又转回屋内找来一件小弟穿过的内衣,牵着我的小手,来到小弟白天溺水的河边,边走边喊:“宝宝哎——回来哦,宝宝哎——回来哦……”一声连着一声,一声比一声凄厉,一声比一声悠长。母亲绝望般的喊声,喊醒了水草、喊飞了水鸟,也喊碎了一湾河水……四处一片哀然。
似乎直到我长大之后,才渐渐地明白和理解,为何水乡的人们爱唱花鼓戏,又总是选择一些有悲苦剧情的曲目,然后将唱词变换成一种长长的哭腔,拉得很长很长……也许那是他们对长期遭受苦难的一种渲泄和倾诉啊!
如今的水乡垸堤加固了,汛期也少了,就连过去通往境外的水路也都由政府花巨资建成了四通八达的钢筋水泥大桥。虽久住都市,但只要回到水乡,凝望着自己“埋胞衣罐子”的地方和曾经“洗礼”用过的木盆,开启着早已油漆斑驳、总是吱呀吱呀叫唤的木柜……那种回家的感觉便会油然而生。
只是自己偶染风寒,当年迈的母亲拿着我的内衣,借着冷月寒星发散出的微光,走在房前屋后到处都是水泥楼房的缝隙中叫着我的乳名,一声声唤我回来的时候,声音虽然依旧慈爱而凄长,但回应的却是满耳的喧嚣和嘈杂……
责编: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