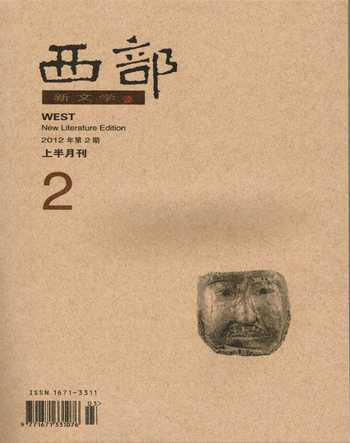碾碎的杭城
王诗客
一
2006年初,我在杭州定居下来。我的“定”,并非定于“居”,只是被定于这座城市而已。作为一个无新房、无旧产的外来人口(即所谓的“新杭州人”),我居无“定”所,飘蓬辗转于城市的各个角落。所幸,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暂为圆心,让我不至于飘出这座城市。好在也有同类:千百年来,漂泊江湖如我者,岂可胜数?
杭州是座美丽的城市——千百年来,这句话已经成为一个集体的判断,而非个体的感慨。杭州这两个字,自从与浙江东北平原上围绕着西湖的这座城联系在一起后,就慢慢在人们心里生成了许多以“美”为核心的集体无意识。在这种无意识的浸染下,我也开始慢慢认识这座城市。
认识从我上班的地方开始。遥想两千多年前,嬴政首次统一中国建立大秦,彼时,后来赫赫有名的杭州才开始建钱塘县,我上班的大学所在地还是一片海域呢。
当时的钱塘,还只是一个海边的山中小县;它位于西湖的西岸,北以今天的岳庙一带为界,西至今天的灵隐一带,南面则被西湖群山所环抱。西湖此时尚未完全成型,只是杭州湾的一个小海湾,因此,西湖的东岸是一片海滩,涛声此起彼伏;如今汇集杭城绝大多数高校的下沙高教园区,还在一片蔚蓝的海水之中。当时人们对大海的想象恐怕还处于“恐怖主义”阶段,而非后来令人神往的美丽的海洋世界。阵阵涛声,海水起伏涨落,不舍昼夜年复一年地拍打着西湖边的滩涂,日积月累,泥沙淤积,渐渐拱出一大块平地,看看今天江干一带的兴盛繁华,这就是沧海桑田。
我日日在开往江干下沙的快速公交上奔波往来,要在先秦时代,可能得步行或骑马到某个码头,再坐船一两日,才能抵达目的地。去干什么?我希望是打渔——堵车拥挤导致的眩晕,常常被我切换成当年的无边的涛声和渔汛,虽然我此刻是拥挤的公交车里行将闷死的沙丁鱼。
二
最近三个月,我家招待了两拨外地来客,前一拨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少妇,原籍广西,现居北京,开公司做生意;后一拨是六十岁左右来自云南大理的少数民族老太太。令人惊讶的是,她们都说想去看断桥,看雷峰塔。年轻少妇是赵雅芝叶童版《新白娘子传奇》的忠实粉丝,少数民族老太太们则把京剧《白娘子》唱了二三十年。
此雷峰塔已非彼雷峰塔。雷峰塔初建于西湖南岸南屏山净慈寺前。虽然这是佛门前的一座塔,但千百年来却成为爱情的象征。历史书上记着,公元977年,吴越国王钱■因其爱妃黄妃得子建造了这座纪念塔,命名为“黄妃塔”。塔坐落于南屏山的雷峰上,因此,民间逐渐称其为“雷峰塔”,而淡忘了原来的名字。
雷峰塔声名远播,全得益于白蛇传故事。这个浪漫爱情故事究竟源于何处,众说纷纭,因为全世界都流传着各种蛇女嫁人的故事。随着宋都南迁,这个故事也不知从何处传到江南,在这里改头换面,深入人心。据说,南宋皇帝赵构喜阅话本,白蛇故事是他的最爱。白娘子传奇在杭州地区流传开来,越传越精彩,越来越多地掺入了本土色彩。久而久之,断桥就成了白娘子和许仙的相会之地,而雷峰塔则成为彻底埋葬这段爱情的罪证。即便在现代化如洪水猛兽的杭州,远道而来的人们大都不会忘记去看看镇压白娘子的地方,表达内心的怜悯。
伴随雷峰塔而来的,是杭州的黄金时代。五代吴越和南宋均建都于此,杭州的城市版图也正式成型。吴越王钱■曾先后两次扩建杭州城,“发民夫二十万及十三都军士筑杭州罗城,周七十里”。经此扩建,杭州的城市版图扩大了一倍,盐桥河已成为城市的中轴线,而非隋朝时的城东界河。可以想象,以当时之力,要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扩建,绝非易事,必然造成巨大的劳役之苦和税收负担,百姓苦不堪言。千年后,百姓的苦和怨早已随着历史的尘埃消逝,今天依然可见的,是当时创建的城市格局和立着伟岸英俊的钱■像的钱王祠。钱王祠初建于北宋末年,位于南山路上柳浪闻莺附近,祭奠吴越国三世王朝的五位钱王。它的原址已毁,今天的钱王祠为近年重建之作。
与雷峰塔齐名的保■塔也建于这一时期。虽建于同一时期,但风格各异,“雷峰如老衲,保■如美人”。遗憾的是,当初的“美人”千年后依然婀娜于北山上,眺望着断桥,而与之隔湖对望的,却已几度易容。因屡遭盗挖,雷峰塔于上世纪初坍塌。1999年,杭州市政府决定沿袭原塔风貌,重建雷峰塔;三年后,新塔落成。据说,这座雷峰新塔耗资一点五亿,为了让新雷峰塔不重蹈旧塔覆辙,塔内部承重结构均为现代化的钢结构。
几年前,为了陪外地来访的朋友,我去过一次雷峰塔。过了售票处,就正式进入雷峰塔景区了。塔悬于五段台阶之上,每段台阶约十五级,在靠近塔门口的三段台阶中间还配备了现代化的扶梯。在入口处仰望,显得异常俊美高大。进入塔内,一层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宽敞明亮,正中央是一个由钢化玻璃和钢筋支撑的巨大的八角形的罩子,雷峰塔遗址藏身其中。大罩子四周分布着四部观光电梯,闪烁上下。雷峰塔旧时 “重檐飞栋,窗户洞达”的风采,已然不再。雷峰塔遗址里封存的是大量的土砖。就这样,雷峰塔的过去,仅存的一点点过去,被隔离在后现代风格的玻璃密室中,里面是雷峰塔的少少的、流芳天下的旧,外面是满满的、效仿着旧的新。往来如织的游人们,路过玻璃罩子时,能够留下的,多是匆匆一瞥和一两个钢■,就直奔玻璃罩子四侧直通塔顶的电梯了。可不是吗?多数导游留给游客在塔内自由活动的时间不超过半个小时,不抓紧时间登顶远眺怎么行!
也许是人妖情未了,也许是现代社会的新迷信,昔日传说中许仙和白素贞邂逅之处,离雷峰塔并不太远,今日已成为杭州最大的相亲集散地。令人惊奇的是,到这里相亲的,大多是年长的男女。哪来的这么多鳏寡之人?他们并非为自己相亲,而是为儿女相亲。现在城市里许多大龄青年男女,到了婚龄却没有适合的机会和人选,自己不着急,可愁坏了父母。这些父母们举着牌子,上面写着自家儿女的生辰八字、身高、工作情况,甚至照片。写到这里,我真希望昔日人妖之间的历尽艰辛的美好缘分,能够惠及这些可爱、可怜的父母们。
三
漫步西湖边,常能看见一辆辆的观光电瓶车缓慢驶过。它们统一为绿车白座,往返于西湖沿线的各个主要景点。如果你走累了,不妨挥挥手,拦一辆车,它们招手即停,花上十块钱,即可绕上一大圈,“烟水茫茫,百顷风潭,十里荷香”的西湖,就这样缓缓在你眼前流淌。其实,这样的游湖方式并非新近的发明。早在元朝,杭州就已有这样的游览项目——乘车骑马坐轿游逛城区——“慢慢走,欣赏啊!”记得朱光潜先生曾为欧洲阿尔卑斯山下一块写有这句话的指示牌动心不已。闲逛,也是灵魂天然的诉求。
元朝时,杭州就已是世界级的大都市了。无论宋都南迁背后有多大的无奈和屈辱,但迁都杭州后的南宋的确繁荣富庶。由于金人占据了北方,西南被大理国掌控,所以南宋时期国土锐减,耕地也随之减少,丝绸之路被迫中断。好在北宋时期指南针的发明已使中国进入海洋时代,远洋贸易为主的商业经济已经得到解放。据说,当时远洋的商船已有六层桅杆,四层甲板,十二张大帆,可容纳一千余人,到达许多国家,令当地人惊叹。据后人估算,南宋的经济总量占世界总值的一半,位居十二世纪的发达国家之首,杭州则是“世界上最富庶的、遍地黄金珠宝和香料的城市” 。不要忘记,此时,欧洲还蹒跚于黑暗的中世纪。这时的杭州在服饰、美食等各方面都领一时之尚,而这一切在元朝被发扬光大。通过一大批传教士的记录,关于杭州的种种神话在西方世界广为传播,甚至让今天的人们都浮想联翩。
南宋政权被推翻后,来自北方的蒙古族建立了政权,并实现了最大范围内的统一。此时的杭州,也迎来了它的白金时代。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此时的杭州东至艮山门、西到西湖、南至凤山门、北到武林门,该格局与民国时期的杭州版图的差别已经不太大了。就在这一时期,杭州的人口亦创历史纪录,超过一百一十万。这一数字在明清两朝急剧下降,直到建国后,杭州的常住人口才急剧增加。
如果说今天的纽约是一个国际大都会,吸引世界上各色时髦前卫的人,包容各种不同地域、宗教的文化,那么当时的杭州也是这样的一个大熔炉。据学者考证,在一幅新近在巴黎发现的目前最早的世界古地图上,已经标注有杭州这座城市。
和其他南方城市不同,杭州人的饮食习惯中有不少异域特色。比如,杭州人爱吃面,片儿川、虾爆鳝面都是今天极具杭州特色的美食,也有如“奎元馆”这样的面店老招牌。据说,杭州人爱吃面的传统始于南宋,当时,江南百姓聚会都爱吃面;到了元朝,这样的生活方式才被杭州地区的精英阶层接受,馄饨、腊鸡、驴肉、羊肉、烧鸡等北方食品也从此时在杭州流行,今天,杭州依然盛行“杭州大馄饨”、“吴山烧鸡”、“杭州白切羊肉”这样的地方小吃。元时的杭州不仅吃食丰盛,各种美酒佳酿也应有尽有,比如本地人爱喝的红曲酒、梨花酒、秋露白、米酒。据马可·波罗记载,当时的杭州虽没有生产葡萄酒的能力,但也能买到进口葡萄酒。如此富丽的生活,吸引了一大批传教士来杭游历。
1271年,一位十七岁的意大利少年跟着爸爸和叔叔,带着罗马教皇的礼物,向东方出发,经过四年的艰难跋涉,他们终于来到中国。少年在中国生活了十七年,他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马可·波罗。公元1284年,江淮行省改称江浙行中书省,省府也从扬州迁至杭州,马可·波罗被任命为江浙行中书省的枢密副使,在任三年,因此,他对杭州的熟悉程度和感情非同一般。在其著名的游记中,对杭州的赞美之词占全书的十五分之一。他把杭州描绘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庄严和秀丽,堪为世界其他城市之冠。这里名胜古迹非常之多,使人们想象自己仿佛生活在天堂”; 杭州的居民也非常时髦,男士英俊,女士动人,而且他们“衣丝着罗,通体绫罗绸缎”。以《马可·波罗游记》为代表的一系列东方游记,为刚刚从中世纪噩梦中醒来的欧洲人构建了一个似乎可及的海市蜃楼,催促着他们开拓殖民地的梦想。正是受到这样的蛊惑,十五世纪另一位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也将杭州列为自己的目的地。在到达古巴的时候,他以为自己已经到达了忽必烈大汗的地盘,以为离杭州不远了。
马可·波罗与中国的渊源,一直传至今日,即使在今天的威尼斯,依然被人铭记。几年前,我去意大利旅行,漫步在威尼斯的阡陌小巷里,迷失在威尼斯幽长交错的巷子里,时空交错之感顿生,于是,我迷路了,也迷失在久远的历史中。随口向一位当地人问路,他说,在威尼斯,即便迷路,也很美丽。这个意外的回答,顿时让那个下午有趣起来。当他得知我来自中国,自然地提到了马可·波罗,并很热心地给我指其故居所在地。遗憾的是,当时没问他是否听说过杭州——东方的威尼斯。不知道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后,是否曾把自己的家乡称为西方的杭州。
四
拆,是中国城市现代化中最痛的字眼儿。
到明朝时,杭州的城市发展已趋于稳定,十个城门把守着这座古城,有这样一首小曲展示了当日之繁盛:“百官(武林)门外鱼担儿,坝子(艮山)门外丝篮儿,正阳(凤山)门外跑马儿,螺蛳(清泰)门外盐担儿,草桥(望江)门外菜担儿,候潮门外酒坛儿,清波门外柴担儿,涌金门外划船儿,钱塘门外香篮儿,太平(庆春)门外粪担儿。”
就是在天堂神话的诱惑下,康熙曾五次到杭州,乾隆更是造访了六次,杭州“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诱惑他们再造了一座皇家天堂——北京西郊的颐和园。
岁月悠悠,历史营造的一切美丽注定是易碎而脆弱的幻境。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同年11月,杭州光复;1913年,民国政府为了改建道路,开始有计划地拆除了旗下营,以及清波门、涌金门、钱塘门和若干段城墙;随后又拆除了凤山、武林、望江、艮山、候潮五门。旗下营位于今天的湖滨一带,是清朝八旗兵在杭的驻防营地——如今驻扎在此的已不是骁勇善骑或遛鸟闲逛的八旗兵了,而是Hermes、D&G等一干世界顶级名牌,它们以新的隐形的威慑统治着人心。大概上了年纪的老杭州人,还会管这里叫“旗下”,但更多的年轻人可能只知道这里是奢华的湖滨名品一条街。这些被拆除的城门作为公交站名或地名依然活跃于杭州人的话语中,但其真迹已如楼兰古国,虽考古学家亦难以暇顾了。
1917年,杨善德调任浙江督军。那年,他买了一辆汽车。据说当时的道路不宜汽车通行,于是下令大规模改造旧城区,在市中心城头巷、佑圣观、板儿巷一带修整道路,共建成宽六点四米的马路十三条。两年后,杨善德卒,而杭州的现代化之殇才刚刚拉开序幕。
1958年,城东、西、北的断墙残垣被彻底清除,修建了环城东路、环城西路和环城北路。
1970年,吴越国时的子城南门、南宋时的朝天门——鼓楼被拆除,就此,杭州的城垣被清理干净了。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对中国展开“破冰之旅”。杭州是尼克松访华的第二站。为了迎接美国总统的到来,杭州做了认真充分的准备:首先,扩建了笕桥机场,这是当时杭州唯一的机场,原为军用,没有候机大厅,亦不能起降大型飞机,因此,在前一年底,国务院就下达了关于扩建笕桥机场的紧急指示,还在机场周围种植绿色常青植物;其次,重修了杭州饭店、中山公园、花港公园、苏堤、三潭映月等处的码头,三潭映月的九曲桥原为石块石条搭建,为了保证安全,改由钢筋水泥土重建;最后,还定制了一大一小两艘游船。然而,尼克松还是留下了这样一句话:美丽的西湖,破烂的杭州。
这句话,深深地伤害了杭州人受馈于祖先的自豪感。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杭州街头最常见的一个字就是红色的画着圈的“拆”。
1979年后,各个单位开始修建经济适用房、福利房,不久,商品房也开始进入市场。一开始,受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小区多建于城边的农田和闲置土地上,今天人丁兴旺、生活便利的翠苑、古荡在当时都是一片片农田。
1984年,胡庆余堂药厂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决定拆除河坊街大井巷“胡庆余堂”的古楼,幸得毛昭晰先生的呼吁,才得以保住。
1986年,杭州市政府提出“住宅建设实行改造旧城与建设新区相结合,以改造旧城为主”,于是,大学路、松木场等更多的城市中心地段被开发。
1999年,拆迁部队进入古城中心河坊街、吴山广场,几个月内,河坊街一侧的清朝建筑、民国店铺等被拆除大半。
……
就这样,老城墙、小弄堂变成了大厦小区、街头绿地,杨善德修建的街道早已不足应付超过七十万的车流量,于是,更多幽长的雨巷改造成了通衢大道。我们或许可以去崭新的“南宋御街”租借劣质的皇帝皇后服装拍照留念,以一己之欢挽祭前尘旧梦,但更多的杭城往事已被埋在西湖盈盈水波、团团绿色构成的巨大沉默之中。
当年鲍照哀扬州成为芜城而歌曰:“千龄兮万代,共尽兮何言!”现在,一切早已埋魂幽石,委骨穷尘。令人哀伤的不是另一座芜城,而是一座失忆的城市和一个失忆的时代。
五
这让人想起近人李叔同多年前关于杭州的伤感。1912年,刚回国两年的李叔同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音乐图画老师。那时,他住在钱塘门内,那里“还有城墙及很多柳树,都是很好看的。除了春秋两季的香会之外,西湖边的人总是很少,而钱塘门外,更是冷静了”。闲暇之余,他爱去钱塘门外的景春楼喝茶,眺望湖景,很是惬意自在,这样“一直住了近十年”。1930年代,他再度来杭州时,杭州的变化,令他失望不已,“西湖边上的马路、洋房,也渐渐修筑得很多,而汽车也一天比一天地增加。回想到我以前在西湖边上居住时,那种闲静幽雅的生活,真是如同隔世,现在只能托之于梦想了”!
寻梦早就开始了。清人王雨谦在《西湖梦寻序》中记录了一代名士张岱这样的感慨:“张陶庵盘礴西湖四十余年,水尾山头,无处不到。湖中典故,真有世居西湖之人所不能识者,而陶庵识之独详;湖中景物,真有日在西湖而不能道者,而陶庵道之独悉。今乃山川改革,陵谷变迁,无怪其惊惶骇怖,乃思梦中寻往也。”
如张岱者,在改朝换代之后,惊惶骇怖,声声哀叹需往梦中寻找西湖,他将前朝梦忆留在了纸上,“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如我这般后辈,却只能惘然地痴迷于张岱梦中纸上的西湖。
今天,在各种城市排行榜上,杭州常居宜居城市榜之首。这样的名号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和移民。杭州,如一艘吃水深重的轮渡,悬着大幅美丽的旗帜,在卖力前行。现在,杭州的早晚高峰变成杭州一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得不实行限号通行、外地车牌限行。很难想象,如果张岱、李叔同穿越时光回访二十一世纪的杭州,被誉为“中国休闲美食之都”、举办过休闲博览会的杭州,会发出什么样的感慨?五千年的古典社会赋予了杭州种种美好的印迹,然而,当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席卷杭州时,杭州之“古”被碾碎了。
今天的我们,只能捡拾零星碎片,来拼凑那个充满了昔日美誉的杭州。《诗经》中有这样的句子:“谁谓河广?一苇杭之。”黄河虽然宽广,可一条小苇筏,依旧可以横渡。家父曾告诉我,杭州之“杭”原来是“航”,因为这里是入海口——他是听他的老师夏承焘先生上课时讲的。是的,杭州城,就如同这样一叶小筏,在历史的洪流中“杭”行穿越;滚滚红尘中,无数琼楼玉宇、风流人物、草莽英雄,皆已被卷走,城墙、城门也拆了建、建了拆……杭州这个名字,也被历史洗涤净化,最后结晶成为一个优雅而空荡的符号,伴着那一汪湖水,亘古不变地悠悠荡漾着的湖水,依旧吸引着现在的人们,进入人类沧海桑田中的这一隅。
责编:舒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