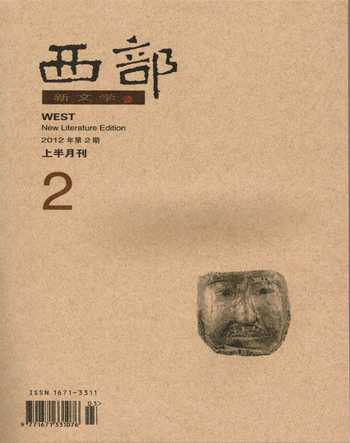穿过镜头的马群披光而去
蒋蓝
成都市公安局警察训练基地位于双流县牧马山一线。牧马山原名谊城山,因诸葛亮在此牧马、演兵布阵,后演变为牧马山。来自朱提(今云南昭通)的古蜀王杜宇娶了一个名“利”的女子为妻,她是从江源(今成都祟州市)的一口井里飘升出来的,这暗示了女人之于井的隐喻。杜宇自立为蜀王,称为望帝。其都城——瞿上城遗址就位于牧马山东北方向。但历史难以复制,同样来自昭通的农民兄弟李永和、蓝朝鼎诸人,1859年进攻四川,历时六年,始终无法进入这座他们梦寐以求的大城市。训练基地的警官朱林是我朋友,他在基地开辟了一间画室,静谧的林间雾霭将阳光漂白,扑窗而来,裹挟着让人伸手可及的历史烟云。
酷爱摄影的朱林去过很多地方,近十年来出版了多部人文地理的著作,也是国内多家人文地理刊物的主要撰稿者。我们谈及顶上的康区,谈及高原驾驶感受,谈及被绛红环绕的五明佛学院,他渐渐地沉默了。我们谈鳖灵外出治水,望帝与鳖灵的妻子发生了关系,后来望帝觉得自己的德才不如老鳖,便将国事托与鳖灵,归隐西山(即龙门山,古代叫茶坪山、湔山),像尧将帝位禅让给舜一样。鳖灵继位之后,自号开明帝,建开明王朝,正是蜀王的祖先。我说,这不过是一个堂皇的体面的台阶,估计是后者谋杀篡位的遮羞布,因为帝王幸大臣的妻女不值得说,反其道而行之才值得一记。不然的话,劳苦功高、忍辱负重的老鳖在历史里如何名头不响呢?另外,《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任豫《益州记》谓广都“县有望川原”,《水经注·江水》亦有此语,其地即今双流县牧马山。“望,出亡在外,望其还也。”(说文)但是,据说是为一个女人而自我放逐的望帝,却在人们望眼欲穿中,只以回环的鸟音在低空铺排开层层悲苦。那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呻吟么,还是欲说还休的怪叫?难怪诗人杜牧在《杜鹃》里感叹:“ 杜宇竟何冤,年年叫蜀门?至今衔积恨,终古吊残魂……”
朱林说:“我记得希腊神话里的杜鹃是另外一种向度。你的《动物论语》就提到了这个情欲分野。”宙斯爱上了赫拉,化作一只被暴风雨淋湿的布谷鸟坠于赫拉面前。赫拉出于怜悯,拾起瑟瑟发抖的小鸟放于乳房取暖。宙斯于是显形,赫拉羞愧难当,答应嫁给宙斯,成为宙斯第七位妻子——正室妻子。而他们相遇的地点——阿尔戈斯地区索那克斯山,也因此改名为布谷山。杜鹃即布谷,但希腊的布谷性欲强烈,远非蜀国的杜鹃那般凄苦。唯一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情欲的“木马”。
阳光打在朱林半张脸上,另外一半滑入阴影,与他身后的巨幅油画半成品构成了一种“互文”的关系,让我联想起三星堆出土的那些诡谲的青铜面具。光堆积起来,他的平头针芒涌立。这时,一只杜鹃鸟在持续鸣叫,既不悲伤,也不欢快。这只杜鹃可能不是望帝那一只,叫声把斜挂的阳光剖开,鸟声白亮,宛如劈空逶迤的经幡,多少还是让朱林感到了一些异样。“他一定知道自己会死在路上,可是他还是上路了。”我好像看到经幡的丛林阴影在朱林眼中往返周折,被风拉斜,又借助弹力回到神赋予它们的位置。朱林缓缓地对我说:“经过了两件事情以后,我几乎不再摸相机,照片能告诉我们的太少了。你在面对属灵的人与事按动快门的同时,借助机器带走的只是褪去神光的表皮,甚至可能就是一次对灵的冒犯!”
朱林向我讲述了2004年他在甘孜州西部巴塘的一次经历——
朝圣者的木掌
每年七月份,也是青藏高原最为绚丽和煦的时节。早晨的清冽之气带有特殊的高旷之感,直逼肺腑。我独自驾车去藏寨。刚铺的柏油公路在冷峻的山野蜿蜒,无始无终。
被高原托举起来的事物,由于总需要仰视,需要加速呼吸和屏息凝目,就让人感到陌生和敬畏。因陌生而簇新的景致,宛如背光的心事突然在劲风里招展或沉降,在雪松上牵挂出诡异的缕缕“龙须”,透过它的间隙,雪色和波浪在远处一片烂银。2004年7月的一个中午,我站在充本拉山的山肩,那里意为“商人之山”,又叫小朔山,是大朔山的左岭脊,最高海拔五千一百八十六米,昔日到理塘必须途经此地。我突然与两只灰白色的野鹿相遇。它们突然启动,地精一般匿身于茫茫山林。几只松鼠大胆地跳到我们的汽车前,审视着汽车这个奇怪的动物,久久不愿离开。
我远远看见一个朝觐者投射在大地上的长影,贴在地上,比经幡还要薄,随风起伏,以一种我不知晓的旗语在风中喃喃自语。我越走越近,看到那是一位磕长头的藏族老人,鸠形鹄面,腰身佝偻,他的动作已经完全变形,三步一磕几乎要竭尽全力。
他手上套着木掌手套,这便于他在地面匍匐。手套上钉着一层铁皮,“啪”、“啪”、“啪”,在高原上这声音脆而悠远。第一声响过,他双手高举过顶相击;第二声响在额际;第三声则在胸前。这是对佛、法、僧三宝的顶礼。三次合什后,他向前迈出一步的同时,陡然扑倒,前胸的牛皮拍打起薄薄的飞尘。
我站在老人身边,干咳几声,老人毫无知觉。不但对我,就是对天空、大地也全没有放在眼里,他的眼睛是一池莽水,空洞而又空荡。我有一种“捕捉到难得镜头的冲动”,这可以上《人民画报》啊,至少可以上《中国国家地理》!我急忙举起了相机。我下蹲,我俯仰,我手忙脚乱,还刻意选择远处的一抹雪峰作为照片“人文”的背景。我使用两台相机轮流狂按快门,自认抓拍到了一组富有“人文含量”的影像。
老人一脸皱纹,褶皱发黑,似乎阳光的沉淀物就是这黑色的尘埃,我联想起没有打磨的铜雕。他弯腰驼背,在快门声里动作没有变化,悲切、艰难、迟缓,像一个负重者,湿牛皮一样泼出去,发出摩擦、撕裂的沉重之声,接着,是他的膝盖骨、手肘触地的声音。他的手掌上套着两块木掌,接近于以前四川农村人修建房屋在转角处使用的木砖,木掌已磨蚀得发出铜光。他的衣服早已破烂不堪,远远可以闻到他散发出来的膻味。
我可以说几句简单的藏语,但此刻我找不到话,他看都没看我一眼。这就如两个寻找家园的陌生人在路上的偶遇。打了个照面,他在一步一步走向他的圣地,我在一点点接近我心目中的“人文制高点”。在我回到汽车上时,我莫名其妙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一路上,老人混浊的眼睛中透出的苍凉与空荡,在大脑中闪现,挥之不去。
三天之后,我在藏寨拍摄了一千多幅照片,收获颇丰。我一路轻松原路返回成都,从巴塘到理塘。那是一个上午,我又看到了那个生发摄影“人文价值”的地方,少不了多瞄几眼。那是一个在山峰之间的凹地,没有一棵树,也没有石头。我突然看见一长块黑色的青石卧睡在公路边,像一匹沉睡的马。我停车,哦,我看到的是那个磕长头的老人蜷缩的遗体。他手上还套着木掌,三天了,他走了不到十公里。谁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但我知道他要到哪里去。
我估计老人应该是在今天早晨过世的。老人半睁着眼睛,空洞而空荡,他放大的瞳孔就像一只张开翅膀的秃鹫,他在望什么啊?他被巨大的翅膀带到了圣城!高原上空气稀薄,声音可以传出很远。几道敲击声让我回过神来,我才发现不远处有几个人正在路边挖坑,估计是与老人一路的朝圣者,他们准备埋葬死者……
我举起相机,略有点逆光,散布在远处的二三十匹马都在低头吃草,但马群突然立起了头,注视着我身后的山口,它们加速,往一个坡地急冲。不带缰绳和鞍的马是世界上最美的动物了,我看见穿过镜头的马群披光而去。奇怪的是,我拍摄了好几张,回到成都却一张也没有了,这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情,算天意吧。
不知什么时候,那只鸣叫在朱林画室外的杜鹃已飞走了,杜鹃缺位,只是把叫声铺成的招魂经幡挂在树梢。“思归,思归,归朱提;思归,思归,归朱提……”可是,永远无法顺水回到故土朱提的望帝,只能死在路上。也只有这样,他的魂才能安然回家。没有女人的牵扯,没有权欲的纠结,灵魂如经幡那样波动向前,把一股股事物的波浪送出去,画出了它们的胴体和长发,那是一轮一轮的蓝。望帝远不像列夫·托尔斯泰那么焦急。
托尔斯泰日记显示,获知妻子索菲娅·安德耶维娜·巴赫丝读到他离家前的信件“就大声叫喊,朝池塘方向跑”。他整天都感到异常苦痛,“在路上,我一直继续想着要从我和她的境遇当中摆脱出来,但终于什么也不能够想出来。可是,不管我们是否愿意,它还是一定要来的吧 。”
那一天终于来了。而这样的时刻,往往是一个人身心俱疲、毫无防备之际。
1910年11月3日的日记该是托尔斯泰最后留下的文字,其中提到他在发烧,妻子要来了。最后一句是:“而一切都是为着别人的幸福,同时,特别是为着我的幸福……”我想到了他的未完之作《光在黑暗中发亮》,从1890年至死,他找不到释放痛苦的缝隙。这部未完之作,就像一个走在路上的朝觐者,一方面在熄灭自己内心的恶,而不断涌入内心的景观又迫使这种说教显出它的浅陋,这是他最为矛盾的作品。也许,在那个风雪之夜,他在招展的雪片里,发现了雪片正是火的手套。那是挑战者的手套啊,他伸手去抓,火在掌纹里流着眼泪匿名,他感到了火对自己的讥嘲。
火在火的道路上转身,火从眼泪的折返里上路。道路本身就意味对解脱的追忆,对自由精神的探求。在阿斯塔波沃火车站,怀揣着六十九卢布、在八十二岁高龄时毅然离家出走。挣扎了十天,他终于回到了路上,他终于带着自己的魂回到了路上。而这恰恰是所有倒在路上之人的唯一共同点。
不同的是,那位磕长头的老者,魂在身体的每一次俯仰过程中,一点点播撒在路上了。
那才是他的生路。无始无终,所以他并不需要刻意到达。
我告诉朱林,我和作家祝勇、庞培在稻城县海子山一线考察一周后,缺氧伴随肌肉的疼痛,对事物的进入总是需要体力的透支才能获得。事物在漫漶,命名在暧昧之中挪移,道路突然缠在空中打了一个结,酥油花一般凝定,又渐渐归于冰的剔透。在难以入睡的高原之夜,我写了一首《海子山上的旧轮胎》——
该是一辆愤怒的汽车
不再忍受雪峰和尖石的无始无终
扔下道路和鞋子
寻着雪花登空而去了
狼毒草从胎圈蔓延而出
就像往事中正在溶解的
一把纤腰
以缺氧的唇红
来推测橡胶的乳香
通达天上的距离比找到出路更近
几只乌鸦自轮毂悠悠飞起
从云朵唤醒饥饿的大军
旋动的磨盘下
时间细如青稞
它们等着我倒地
想起那些同我走失的人和事
如能在此相遇
我定会照料她们一生
但她们早改头换面
自己只有一张口唇
怎容得下潮水一般的人民
那么——我就只有把你们供作我的母亲
实在不行的话,那就是花岗岩与
海子之间,一声爆胎的巨响
群鸦把黑暗卸在大地
星光就被抛入水底
走兽们举着安静的灯笼
与石头一起赶往他乡
月亮卡在垭口
我听见鱼上岸的脚步
朱林默默听完我的叙述,他塌陷在画室弥漫起来的藏香和浓烈的松节油气息深处,似在梦游。人体的轮廓把寂静底部的热力逼出来,就像我企图从他描述当中把那个老人皱纹的沉淀物扣出,放它到旷野。朱林对我说:“自此,我不但删去了这次出行的所有照片,而且我有些怕摸照相机了。不但觉得镜头吞噬的事物我消化不了,而且日益觉得镜头藏着一个无法愈合的深渊。老人的眼神烙在我的记忆里,我觉得自己拥有的一切也填不满他空洞而空荡的眼神。那是一个莽水不兴的渊薮。他知道自己会死,但还是上路了。在虔诚和坚韧的灵魂面前,我有无能为力的苍白感,就像一块石头渴望走出稻城的海子山。生命本来是可以慰藉的,而有些生命你只能敬畏,哪怕这个生命瞬间在你眼前消失。但形体消失了,也许他就回到了有光的路……”
我注意到身边那些架上的油画,有一幅画,展示的是一只朝觐者套着木掌的手,只有一只手,粗糙黑黢而苍老的手,以及手掌边缘矮下去的群山。而朝觐者的眼睛应该在朱林心中,包括那些皱纹里的黑金,让他发怵,也让他变矮,矮到尘土里。
秃鹫的雷声
让朱林受到更强冲击的遭遇,是一次油锤高举之下的“色达愤怒”。
“色达”在藏语里是“金马”的意思,暗示此地因有马头形金块而得名,也有人说是因为在地下埋藏着一匹“金马”,但至今没有说清楚金块出在哪里。在色达的山沟后来被人发现真有金砂,引来一些淘金者在这儿竖井架、搭滤槽,采砂淘金,对环境自然有破坏。在色达县城的十字路口,耸立着建于1989年的金马雕塑,已成为色达的标志性建筑。
去五明佛学院的路只有一条,离开县城二十余公里有一条山沟叫喇荣沟,从六个白塔挺立的地方拐弯翻过一座山,到达驰名藏区的佛地,就可看到西边的山顶,巨大的“坛城”之顶在阳光下发出神秘的金芒。
蓝天白云之手呵护的喇荣五明佛学院一派深红。
几千幢藏式建筑是红色的。上过红漆的木头僧房密密麻麻遍布山坳,在氧气稀薄的高地,耳膜发痒,宛如不真实的迷宫。身着红衣、红帽的喇嘛不徐不疾,在狭窄的土道攒动。红色经幡在山巅荡漾,有一种大醉的淋漓,圈圈层层波浪而上,在山坡迎风的垭口呼啸猎猎,逆风相激,如此盘旋升望高天,响成满世界的梵声。
色达之红是如此强烈、鲜明,就像医生翻找一个伤口里的宝石,深深浅浅、浓浓淡淡的红色在渐次展开,然后,凝聚最深的红突然以黑金的内敛神光熄灭。在这个红时空里,让我从视觉上完成了对宁玛“红教”的第一次感悟。
这是我对色达的印象。还是听听朱林的叙述——
1997年,我在位于五明佛学院的后山上,结识了天葬师邱彭。藏人缺乏对精确时间的记忆,记个大概就足够。据喇嘛说邱彭是1960年代初期出生的,但看上去他比实际年龄要老出十几岁。他约有一米七高,很强壮,也很沉默。他目光空洞,但遇到让他感到陌生的事情,他会停止手上的工作,身形缓慢地挺直,聚光凝神,眼睛里就有一种纵深不断下切的锐利。这种表情总让我联想起一个从列车窗口探出半个身子的人,全力追逐一棵在平原上狂奔的树,而全然忘记了另外一列火车正迎面驶来。
他和妻子、两个孩子住在山外的一栋小泥屋里。一来二去,邱彭觉得我为人不错,久而久之,就成了朋友。1999年夏天,我决定到色达去找找感觉。算起来,这已是第五次去看望邱彭,出发之前,我特意在成都将军街的医疗用品一条街买了一大包医用橡胶手套。
后山之巅的草甸与天光接壤,但中心光秃秃的,别说树,连草也没有,散布的几团青■丛点缀着这片沙碛斜坡。一栋孤独的小石头房子很适合邱彭。这里的天葬台是康区最大最著名的,虽对外开放,但一般不允许拍摄。那天中午,邱彭看见我来了,很高兴,点点头,深褐色的脸膛绽开了笑意。
我把一大包手套从背包里拿出来。
邱彭问:“什么东西?”
我说,用这个卫生嘛。
邱彭一伸手,将一大包手套狠狠掼到地上,掼到地上一块黑色的青石上,纸盒子发出破裂的声音。那是一块天葬石,比一个人的肩膀略宽,饱受人油浸淫,发出动物毛皮的青光。石头中部凹陷下去,那是被油锤砸出来的凹痕。橡胶手套的捆扎绳子断开了,手套在石间耷拉着,很像那些自然下垂的白手指。他受了侮辱,用藏语大声痛骂我,抽出腰刀向我比划,大步来回走动,靴子惊起了细微的尘埃。
橡胶手套撞击地面的声音在石头上漫开,好像搅动了远方大片乌墨的云。
那至少有几百只秃鹫,毫无声息地漫过来。它们飞动,白粪便染过的山河就如墨水吃入宣纸。
有些地方,呼唤秃鹫要“煨桑”。“桑”是藏语,为“清洗、消除、断除、驱除”之意,“桑”也引伸出了祭祀献供的含意,在藏地“煨桑”成了祭祀神灵的代词。邱彭只有在很特殊的时刻才煨桑,比如,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死人送来了。一般而言,他立在那里,高举双手,像一个V字,左右一转,他的身影就是桑烟。藏传佛教认为,桑烟就是铺五彩之路。
密乘教义认为神鹰是十方空行母的化身,在有些经书中,它们被称作 “夏萨康卓”,意思是食肉的空行母。秃鹫认识邱彭,它们只靠近他。如果附近有生人徘徊(这往往是送死者来的家属),它们会表示出不安,把邱彭靠得更紧。
秃鹫打开足有两米宽的翅膀,每一扇翅膀上均有八九根突兀的羽翎,峭拔如两排反飞的箭。越来越近了,就闷雷一般地响,破蒲扇一般地扇。秃鹫一般近一米高,特异的个体一般是“鹰王”,看起来直抵邱彭的腰肩,肉红的脖颈沾有天庭的血。“鹰王”站立一旁,大人物一样奔走巡视,举翅高叫,维持秩序。秃鹫列队,身披麻袋的古罗马军团那样列队,然后闪出一道裂口,邱彭走进乌云,乌云立即合围如初,把邱彭和那块散发黑光的天葬石淹没在羽翼与腥膻的空间。
准确点讲,那不是腥膻,因为混合着冷风、草甸、枯叶、尘土的气味,那只是天葬台的气味。
康区多雨,多诡异的暴雨。一会儿下雨了,秃鹫一动不动。在惊雷每一次炸响时分,它们也发出剪刀剪割镔铁皮的叫声。秃鹫耸起翅膀,是一个奇怪的M字,就像海子山的铺天石阵,用一种可以让时光老死的忍耐力,等待天光转暖。高举的M构成迷宫,立刻淹没邱彭。邱彭蹲在翅膀下避雨,一动不动。雨点打在天葬石上,比油锤的闷声要清脆得多。
一会儿,秃鹫队形的闪电在慢慢张开,露出锯齿。邱彭红着双手走出来,他身后的闪电在缓缓熄灭。秃鹫举翅,抖落雨水,轰轰轰……
那些升往天界的魂,走得已远了。
那天,刚巧有一个年轻女人被送上来了。她在学院里已经过了喇嘛的念经超度。喇嘛以浑厚的胸音念《颇瓦经》,有些老年喇嘛的声音好像不是出自胸臆,而是发自丹田,再从头顶钻出来一道锐气,他们口唇不怎么张合,但那熟铜之声能让听者天庭发痒。
有些死者被《颇瓦经》诵度后,头顶天灵盖会出现一个小洞。世俗说法是这人的灵魂已从小孔飞遁,离了躯体;佛家的说法则是,这人的神识已从小孔飞出,投胎转生去了。这种被“念力”开凿的言语通道,邱彭把刮过头皮后的头颅给我指认。
人是蜷缩着来自母体,因此人死后必须还原初始,原路返回,便于投胎转世。一般而言,死者送到天葬台早已僵硬,邱彭要用非常大的力气把弯曲的身体扳直,让他们平息下来,让胴体与石板合二为一。再用一根绳子拴住死者的脑袋,并拴在天葬石旁边的一根木桩上。那天,邱彭用刀割开口袋时,女人蜷缩的身体自然而然摊开了,刚好匍匐在石头的凹槽,邱彭显出了惊异的表情。当她身体上的腰带、衣裙等累赘被清理干净后,一具白蜡的胴体使天光坍塌。
人一死,身上所有的装饰物必须摘下,干干净净一丝不挂,好使灵魂无牵无挂归去,没有人间眷恋,早日进入轮回。
仅仅二三十分钟,这个熟睡中的新娘,被密不透风的翅膀接走了。
呆立在一旁的我,听到内心发出了一个声音,是不是那包橡胶手套摔在石头上的声音?我突然泪水滂沱,在雷声覆盖下这哭别人听不到,秃鹫更听不到。它们的听觉深埋在闪电和血肉当中。都几十岁的人了,我头一回这么痛快地哭。
邱彭没有理睬我,他返回鹫群径直做自己的事。我看见他的钢刀透过秃鹫的缝隙不停地起落,在细致地完成一座浮雕,偶尔溅起了火星。嘴喙的角质化光,比雨更亮。等不及了的秃鹫,叼起一条胳膊就跑,邱彭放下片刀拔腿去追,秃鹫群裂出一条通道,邱彭把胳膊抢回来,裂口合拢了。邱彭双手挥舞,向四周播撒。场面骤然激烈,大型的个体如同打桩机的大锤砸下来,鹫群一阵大乱,发出剪刀剪镔铁皮的叫声。我觉得,自己在这一瞬失去的东西,可能比大半生还要多。我所受过的教育,那些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奉献毕生万人欢呼名垂青史之类的意识形态,正在随雨水融进沙地。那么,把镜头对准邱彭以及他身后的神鹰和天空,炮制出来的“人文镜头”,还有意思么?糊在银盐颗粒像纸上的影像美轮美奂,与藏地上的生与死有关系吗?
可能毫无关系。
就像那包摔得四分五裂的橡胶手套。
上百只大乌鸦早已等得不耐烦了,沙哑的悲鸣混入风声,它们从缝隙里穿梭,身形迅捷,把鹫群煽动起小小的骚乱。有两只乌鸦竹箭似的直射邱彭腰部,叼走了一点碎屑。曾经在印度人群沛诺尔布所著、向红笳翻译的名著《禁忌:乌鸦的语言?》里读到过几十种乌鸦叫声的寓意,乌鸦不愧是藏地的怙主。
眼前一地狼藉,满地飞扬秃鹫的羽毛。山风吹来,羽毛飘然而去,随气流越飞越高,在追逐它们的主人。神鹰在天空盘旋,地上的邱彭在慢慢收拾油锤、刀子、铁钩。
邱彭很疲惫,顷刻就老了几岁。他用糌粑搓洗手上的血迹,但实在搓不干净,他略侧下身就用自己的热尿洗手,在衣服上擦干,然后开始吃午饭。死者家属恭敬地奉上干牛肉、暖瓶里装的酥油茶、糌粑以及半瓶大曲酒。邱彭一言不发,默默吃完。他的工钱是一个人二百元。实在太穷的收一百元,个别拿不出的就算了。当然,这个收入他一人吃不进去,还要与管理者五五分成。
他看了我一眼,然后就刚才的事向我道歉。我们还是朋友……
是的,朱林听到了雷声。我也感到了。2008年夏天,我来到色达,我看到了那一片绛红色的城池,那是秃鹫脖子的颜色啊。可是,我更倾向于这是邱彭的愤怒火焰。
上路就是趋光
一个人就这般飞起来了。
我对朱林说,照相机镜头固然是你之于世界的连通器,但你决定拿起画笔时,笔立如藏香,画笔就是敬献于藏地的一桌香案。对于大地而言,照相就是一种比喻——尽管比喻也有大师,但一幅真正的画作绝对是隐喻。在隐喻的地域没有大师,只有彰显隐喻的人子。不要过分夸大摄影的纪实功能。我们是根据摄影的引申义来寻找、确认现实意义的,因为摄影者在对现实取景过程中已经注入了新的意义。因此,我们看到的照片,已经不是现实的一幕了。这既是摄影的悖论,也是它的魅力。
我愿意再重复一次:对于大地而言,照相就是比喻。
他没有否认我的说法。他笑笑说,他已经不摸照相机了。他让我看近年完成的一幅五尺全开的油画:整幅画面都是灰色基调。群山撑起了画面的高度,在凹地里,一个人高举油锤,正在砸向青石上的两台相机。举锤人的右面立有一个写生板,上面恰好是整个画面的缩小;左面还有一台手提电脑,页面也是整个画面。甚至两台照相机的显示镜也是同一画面……这让我联想到一部悬念电影里的设置:无数面扇形排开的镜子相向而立,一个人立在正中,无数个“我”被镜子克隆,被镜子虚拟的深度推向了一条必须跳出自我否则就没有门的道路。
2005年后,朱林几乎没有再“上路”了,他选择了隐遁,这种隐遁里有尊重的默会。他想再体验一次那快速漏走的半生知识和意识形态,自此,他再也没有去见邱彭。
过往的体验,作为记忆的感觉让渡给淡淡的怀旧:“记得过楚玛尔河的时候,还没有桥,先要把汽车里的零件卸下,用黄油和塑料密封,再装上。开入河的时候,水会透进车体漫过腰际,水刺骨得冷,你感觉不是在开车,而是在开船。最担心的不是被水淹死,而是汽车在河中熄火。上岸后再去掉黄油,把卸下来的零件散放在草地上晒干,天很蓝,白云飘卷,你可以躺在草地上打个盹儿。现在楚玛尔河上已有一座大桥横跨,过去过河要用半天,现在只需两分钟。我怀念在河里开车的感觉。”
我们喝茶,那只杜鹃鸟又在苦叫,不知道是不是先前那一只。“思归,思归,归朱提;思归,思归,归朱提……”去而复返的杜鹃,你在叫什么呀?
“他一定知道自己会死在路上,可是他还是上路了。”
我们的话题突然转到了汶川大地震和玉树大地震。朱林参加了几次救灾,尽管都江堰的火葬场已经全速运转,依然无法处理太多的尸体。上千具尸体运到了成都,上千位死者家属在火葬场大哭。蜀犬吠日的阴霾,以更低的幅度构成了天地的回音墙;但在玉树地震之后,死者停放在一个操场上,几百名藏族家属目睹亲人和天空,流泪,没有声音……
生与死,就是从一个花园推开另外一个花园。老年的托尔斯泰明白面对不同信仰的抉择圭臬,唯有一种更高的理性促使我们择善而行。
朱林不由自主地会回到老人的木掌以及邱彭的愤怒:在那场强烈的光照下,我想象得出,群山躺下来,光晕在倒地老人的身体边缘麇集,老人正在回到大地深处,他把光一并带入到地下,他周围芳草萋萋。置身秃鹫中的邱彭,就是但丁在地狱与天堂交汇处,那光不仅仅来自天界,也是秃鹫的大翅卸下来的高光。朱林更愿意以一种更加常态的观察方式,并以最简洁、最朴实的表达来尽可能再现事物的原样和真实。在他的画作里,所谓纤毫毕露地目睹流光飞舞已经显得过于纤细了。大自然中的明丽高光,在朱林画笔下被降低,赋予了一种绛红的悲悯,难以高蹈,因而他的光显得低缓,显得木讷,显得滞重。逆光下的藏地,石头、草地、枝桠、老人、袈裟、庙宇逐渐成为了撕开天光的钝器,人与事的光,成为了强光世界上的一层绒毛。说实话,我在别的藏地油画里,没能找到这么多的光。
那种令你能被我看到的光,那种我看到以后被劝化的光,就像死那样正常。
当然了,还有一种秃鹫的红。
责编:晓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