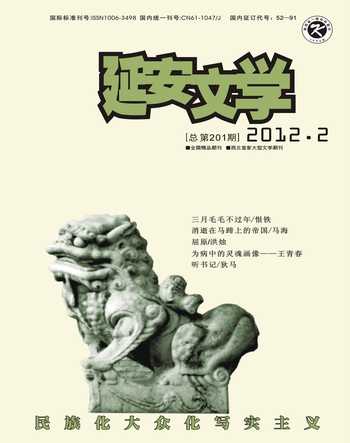抵达或者离开
廖淮光
太白村
在档案表、在信封上、
在求职书、在断行的诗歌里……
我无数次写下太白村;
现在,我越来越害怕写下这个诗意的名字了。
栽种“苎麻”而名的太白村,
完全可以想象收割苎麻时,村庄铺天盖地的白;
一想到那种白,与苎麻有关的白,
我的心就被千丝万缕的麻牵动着。
我害怕村庄这样的白;
我的父亲母亲正在那里老去,
他们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
我害怕有一天,他们的白与麻捆绑在一起。
炊 烟
空房子,
真的与天空失去联系了。
突然,我有种无法抑制的激动。
我多想把眺望远山的时间,找回来;
把焐暖一块石头的温暖,要回来。
我想高呼母亲万岁!
不停升腾的炊烟,让云朵低下头来,
我们小小的木格子楼,像爱的发动机。
黄昏陷落,又一枚锈蚀的螺钉,
完成了最后的楔入;我们,
在大地之上的家,越来越根深牢实。
对 面
就在对面,
一步,或者更短的距离;
只是暂时关闭了所有的灯盏,
只是与我开个玩笑,
只是想给我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
妈妈,这么久了,怎么还不显身?
我没有呼喊,可是已经哭了。
城市的灯火辉煌,烟花灿烂,
妈妈,隔着夜色,
我们彼此倾听着身后那些,
不属于自己的欢乐。
我们说着亲人,说着孩子,
说着工作,说着丰盛的年夜饭
说着祝福……我们唯独
没有说出:想你。
电 话
清早起床就接到母亲的电话,
老家下雪了,提醒我加衣服;
电话里,能听得到风地呼号,
隐隐感觉雪还在下。
母亲不识字,听力也不大好,
很少看电视,她总把故乡的天气,
当成我的天气;亲身体验,
热了,叫我别乱吃东西,
冷了,让我及时添衣。
我所在的城市从不下雪,
生活的地方都有空调;
但我从来不和母亲说起,
每一次都任母亲在电话那头,
不停地唠叨着,认真地应诺。
这样多好啊,仿佛我从未离开故乡,
仿佛我依然是个孩子;
更重要的是,千里之外,
我清楚地知道母亲是热了还是冷了。
抵达或者离开
从狗叫开始,孩子,
你肯定是出来迎接我的,
可是为什么?
我一走近,你却转身飞快地跑开。
我不是灰太狼,不是魔鬼,
孩子,我是你的亲人,
河对面的祠堂,有我们共同的祖先;
虽然这几年的漂泊,
我染上了城市的病痛
可是我们的骨子里流着相同的血。
孩子,你是太白村的传承和希望,
是我们共同的孩子,
可是我却不知道你的名字,
无法准确说出你的父母。
你风一样的跑开,带着整个村庄飘摇起来。
就这样,两位亲人,
在故乡,在自己的土地上,
擦肩,陌生,不相认。
重 逢
无论有没有人在,
门没有上锁,你可以自己进屋;
火塘里的火温暖,
水缸里有清早打的山泉水,
桌上有自制的手工茶,你可以自己沏上一杯。
见到你的时候,我不会太激动,
不会和你握手,更不会和你拥抱,
我知道你早迟会回来,即使是路过;
我会笑着问你:“吃过没有!”
然后往火塘里添两把柴,
俯身使劲吹几下;不好意思,
烟雾会熏到你,也会呛到我自己。
凳子上布满尘灰,
哪里来的,我也不知道;
你可以选择坐,或者不坐,我都不会介意;
我不会问你这些年在外面怎么样,
请你也别问我,如今生活好不好!
我们可以大碗喝酒,墙角最里面的那一罐,
酿起好多时日了,够我们喝两个晚上;
用什么下酒?你寻思有的,尽管点,
凉拌猪耳朵、油炸花生米、炒胡豆……
今晚,我们不醉不休。
一会儿,我们再去村口,
看看朝向远方的路;
在院里的稻草垛里,数一数天上的星星,
把童年的蚂蚱逮回来;
但千万要记得,再困也不能睡着了;
现在,不会再有人四处找我们了,
就算有,也绝对找不到这个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