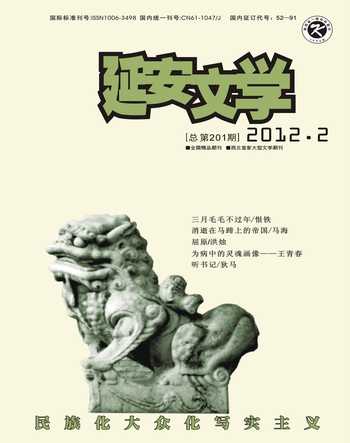听书记
狄马
听书,对现在的人来说已经是一个很陌生的词了。我们常说听歌、听报告、听音乐会,也说读书、买书、翻书,但没有说“听书”的。而在我的故乡陕北,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因为在这块陈迹四布的高原上,至今仍保存着全中国形态最完整的说唱艺术——陕北说书。陕北说书是一种古老的民间说唱艺术。有记载以来的艺人全是由盲人承当的,因而谈不到什么动作表演,功夫全在一把三弦和一张绣口上。既然表演的人全靠声音和讲的故事吸引人,听的人也就用不着眼睛,只需带一个小板凳,静静坐着欣赏就是了,因而叫“听书”。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观念的变化,有许多明眼人也加入到了说书的行列中,但在电影、电视、流行音乐、网络等娱乐方式的冲击下,说书的市场日渐萎缩。艺人们为了吸引观众,将原来的“坐场说书”改为“站场说书”,说唱时加入了许多动作和表情表演,这门古老的“听觉艺术”已慢慢地变成了“视觉艺术”。尽管这样,这门流传了几百年的说唱艺术还是无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一时一地的兴盛不过是“最后的辉煌”。遇节庆庙会,台前全是老婆老汉,从台上望去,都戴着白帽帽,白花花的一片。年轻人来了就停在后面,骑在摩托车上不下来,听几分钟,就一溜烟跑了。因而,听书越来越成为一种奢侈的享受。
2008年8月,我却在延安万花山下的一个农家小院里,完完整整地听了一本书。说书人叫熊竹英,是我请来为陕北传统音乐论坛在这里搞的年度聚会助兴的。书场就设在这个农家小院的窑洞前。夜幕刚刚降临,参会的网友都陆续到齐了。说书人从台上站起,四片瓦一打,三弦、二胡、笛子、刷板的伴奏就响了起来。开场说了个劝人孝敬的小段,观众的嘈杂声就安定下来了,随之就开始说今晚的正本《善士亭》。这是陕北说书里一部优秀的悲剧作品。讲的是唐乾德年间(艺人假托),河南洛阳郊外有个桃李庄,住着一户人家姓冯,名四奎,娶妻马家女,唤作秀兰。一天,四奎看见皇榜,知道皇上开了龙门大考,想上京求取功名,就拜别了妻子和小妹而去。秀兰独自去娘家拜寿,归途遇到大雨,栖息于善士亭中。正好一个叫李子霖的举子也来庙中避雨。一宿无话,天明各自登程而去。谁想冯四奎误将准考证遗落在家,回家后见秀兰湿衣湿衫,大起疑心,再加上妹妹撺掇,误以为妻子在破庙中与外男苟合,遂一纸休书将其休回娘家,他带着妹妹上京赶考,一去不返。
马秀兰回到娘家,父母因为“丢人败兴”拒绝接纳。苦难从此开始。她先是被代表家庭的丈夫抛弃,继而又被代表家族的父亲抛弃。没有谋生能力的马秀兰来到街上沿门乞讨,又被“三从四德”武装起来的道德民众抛弃。要不到饭的马秀兰只好重新回到她苦难的起点——善士亭,以刨食草根为生。儒家把不遵守忠孝伦理的人骂为“无父无君禽兽也”,马秀兰不想作“禽兽”,也无意反抗国家伦理,倒是比那些宣扬国家伦理的人更真诚地遵守它,但国家伦理还是无情地抛弃了她。她只好自甘为“禽兽”,与牛羊一道分食着大自然最初赐赠给人们的食品——草根。书说至此,听书人除了一声长叹,同时也应该感到庆幸。庆幸的是,山林里的草根树皮虽然没有营养,但总算没有收归皇家。因而善士亭附近的村民尽管道德热情很高,坚决不给马秀兰煮熟的食物,但他们不认为村庄附近的野草树木、河流山川也属于“善士亭”集体所有。否则,马秀兰只能活活饿死。
这就是我们通过《善士亭》看到的,一个人被国家伦理遗弃之后所面临的可怕后果,就像在西方社会被教皇宣布为“上帝的弃儿”一样。而令人沮丧的是,这种后果有时甚至大部分时候并不是他或她有意反抗的结果,像西方社会里那些公然向教廷宣战的斗士或异教徒一样。这种给一个人的一生带来毁灭性灾难的事件是建立在一种荒谬的误解基础上的,而误解的原因在于男女在一个家庭中完全不对等的地位,处于劣势的一方丝毫没有申诉的渠道,就像在封建时期皇帝和他的臣民一样。
作为一个女人,除了像男人一样要承受生存的负担之外,还得承受分娩的痛苦以及哺育后代的责任。冯四奎走的时候,马秀兰已有身孕,并给腹中的婴儿取了名字:男的叫天生,女的叫苦妹。秀兰被休以后,虽然营养不良,但还是按月产下一对双胞胎。这时,善士亭附近的村民显示了他们淳朴善良的一面。他们认为一个女人在如此匮乏的情况下还能顺利产下婴儿,说明她是得天神助。既然是得天神助,那么她一定是被冤枉的。关键的问题是教育人民。人民一旦知道什么是对的,就不能不去做。他们纷纷从家里拿来了鸡蛋、蔬菜以及奶茶等补品,帮助马秀兰度过了艰难的哺乳期。对于这桩雪中送炭的善举,我们还应感到庆幸,庆幸的是善士亭附近的村民只相信鬼神,相信古老的“天地良心”,不相信“拜金主义”。因而天生和苦妹得以长大成人,并通过废纸堆里捡到的《三字经》、《百家姓》等童蒙读物完成了初级教育。虽然没有上奥数、钢琴课、课外补习英语,但基本智力正常,发育完全,不差其他小孩分毫。
天生和苦妹长到四岁的时候,马秀兰遇到了一桩更加可怕的事。如果是一个男人,他遭到他的亲人、家族以及整个社会的放逐,不但得不到荣誉、身份和地位的认同,甚至连最基本的维持生命的食物都得不到,他要与牛羊一道分食草根树皮,作为一个陆地生命就已经到了苦难的尽头;但作为一个女人,这仍然不够。她身上还有另一项资源没有开发完尽,那就是性。在一个男女平权的社会里,性的占有要遵循两项原则:一是自愿;二是对等。但在男权垄断一切的社会里,性的需求和满足从来不考虑女人的意愿。尤其是对于像马秀兰这样完全失去伦理庇护的女人来说,几乎是可以人人得而交之。洛阳县令李老虎在一次出行中看上了马秀兰,要与她拜堂招亲,否则就要杀死她的一双儿女。情急之下,她只能应许了这桩强制的婚姻,而在洞房花烛夜,她用计放了已入虎口的天生和苦妹,而后用一把剪子刺瞎双眼,断了李老虎的淫念。李老虎派人将已成盲瞎的马秀兰抬回善士亭,又将天生和苦妹从高楼上扔下,企图斩草除根。幸得山东好汉孔龙、孔玉相救,带回山东老家卧虎庄教授武艺,直至成人。
冯四奎带着妹妹离开原籍,科举得第,被皇帝封为东台御史,又将妹妹嫁于西台御史李子霖,自己一直鳏居京城。出于对世上女人的绝望,一次借着酒兴他写下两句表达愤懑的诗,被妹夫李子霖看到,李于是对他讲述了自己多年以前在善士亭中遇见的贞洁女人。真相随之揭开。
这时我们看到,被一种极端道德绑架的人,即使看上去拥有绝对的主权,实际上也是牺牲品。冯四奎出于强烈的自尊和道德羞辱感休了马秀兰,可自己一直为嫉恨的火焰噬咬,灵魂不得安宁。最终为悔恨所伤,自刎在了马秀兰身旁。这是后话,不提。
现在我们看到李子霖向冯四奎讲述自己18年前在破庙中遇见的贞洁女人,如海的深冤露出了光明的一角。这时,台下所有的观众都长出了一口气。就在那一刻,我洞见了中国传统戏曲小说“大团圆”的本质——虽然这部作品奇迹般地是以悲剧收尾的。
大团圆,实在是适应中国民心需要的产物。文学不管是民间的,还是官方的,总的来说是要温暖人心的。中国人活在黑暗里,活在生命的死荫之地,被腐败的制度、苛刻的道德、充满诡诈和暴力的人际关系压得喘不过气来,好不容易死里逃生,听一会儿戏,看一会儿小说,他们当然不愿意“正视淋漓的鲜血”。他们要在书里,戏文里获得一种替代性满足。因而,大凡中国的戏曲和小说总是才子落难,佳人相随,父母坚决反对,但才子化悲痛为力量,发愤图强,最后高中状元,由皇帝钦点拜堂成亲。鲁迅先生讽刺说:“假使有之,也只在才子的能否中状元,而决不在婚姻制度的良否。”即使活着“团圆”不了,也不要紧。死后化成蝴蝶,化成神仙或鬼魂也要“团圆”,实在没有什么化的了,坟头上长出两根树枝,也要交相缠绕在一起。一部《红楼梦》虽然最后兰桂齐芳,贾府中兴,但终究不失为一部悲剧。后来的人因此很不满意。《红楼后梦》《红楼复梦》《红楼补梦》的作者便硬是要把晴雯和黛玉从坟墓里拉出来,与在任的宝钗“团圆”,妻妾各有定分,其乐融融。“奸臣害忠良”的套数更是俗滥。一般是奸臣当道,忠臣受诛,满门抄斩之时刮了一股大风,或者是义人暗中相救,用狸猫或自己的孩子换出忠臣的孑遗,日后练出盖世武功,或当大官,或领雄兵,奉旨诛杀奸臣,善恶各得报应。这当然是“瞒和骗”,但它实在是弱者的希望和亮光。
这场书头一天晚上没有说完,热心的听众仍急切地要知道马秀兰最终的结局。原定第二天上午的民歌研讨活动只好取消,临时改为《善士亭》的后半场演出。
虽然时节已是盛夏,但陕北的早晚还是有点冷,年龄大的网友第二天一早就穿上厚厚的衣服,揉着哭红的眼圈出来了。他们静静地坐在凳子上,等着说书人演绎马秀兰故事的最终结局。冯四奎听了李子霖的叙述,知道大错已经铸成。赶忙向皇帝告假,离了京城,直奔家乡洛阳而来。中间穿插了一段“乾德皇帝”微服私访,到了扬州被地痞流氓孙彪孙霸吊起殴打,幸得下山探父寻母的天生和苦妹相救,三人拈土为香,拜为兄妹,同归长安城。皇上知道他们是东台御史冯四奎的子女后,派兵丁护卫,兄妹二人快马加鞭,也直奔桃李庄而来。
这时,我们看到了整个故事最为悲情的一幕:冯四奎辗转来到善士亭,见一个盲眼的女人在煮食草根,周围堆着几根煮剩的柴火和野艾。这就是他18年未见面的妻子!冯四奎伤心欲绝,向她讲述了自己的万般悔恨,这个受尽人世辛酸的女人没有抱怨,没有指责,有的只是一身污名被洗之后的释然。18年来她等待的就是这一天,这是她活下去的唯一理由。可是什么理由能让她继续活下去?什么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生活能够重新点燃她对人世的信心?我想说的是,人能承受的苦难有他的极限。一旦过了某种极限,即使苦尽甘来,活着也没有了意义。总之,我们看见她静静地听完四奎的讲述,并向他表达了不变的爱,而后拔下结婚金簪,对准了自己的咽喉。可怜芳香三魂,幽冥七魄,竟直奔望乡台去了。冯四奎眼见芳花揉碎,玉山倾倒,也拔出腰间佩剑,刺向胸膛,随妻去了。一个男人用自己的生命偿还了他在陆地上制造的全部孽债。现在他一身轻省,躺在了妻子身边。随后赶来的天生和苦妹,秀兰的父亲马金龙和母亲马夫人肝肠寸断号啕不止:
天生哭得一声高,好比春风摆动杨柳梢。
苦妹哭得一声低,赛过七月天的连阴雨。
马金龙哭得一声长,好像三岁的娃娃离了亲娘。
马夫人哭得一声短,好比孤雁落沙滩。
书说到这里,时间已到了正午,陕北话说的“亮红晌午”就是这个时候。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人们的头顶,许多听众已经不堪烈日的毒晒,回房休息或打麻将去了,KTV包厢里不时传来张也的《走进新时代》。阳光用直射的方式为一场说书拣选着它最忠实的观众。这时,院子里只剩下零落的几排人。坐在前排的是我们几个组委会的服务人员,坐在后排的是二三十位来自绥德“四妹子合唱团”的成员,这次活动正是这些已经退休在家的妇女,用她们的谦卑和热诚向我们展示着“老陕北人”对生命的绵绵温情。她们中的大部分人是自始至终流着眼泪的。当讲到马秀兰和冯四奎双双辞世,善士亭的地面上躺倒一对义女忠男时,许多人已经泣不成声。我看见“合唱团”的刘巧民团长手里拿着纸巾,不停地拭泪,拭完后将纸巾递给了旁边用手背抹泪的姐妹,而周围的姐妹,也几乎是人人眼里闪着泪花。本村的一个老人,看上去有七十多岁,不好意思坐在网友中间,就一个人圪蹴在树底下,开始还能听见他的笑声,再后来就只看见一张老泪纵横的脸。
西方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兴起了一个美学流派,人称“接受美学”。这派美学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和审美价值是在阅读的过程中展现出来的,不是由作者单方面赋予的。读者的预测、期待和反应在很大程度上也参与了文本的创造。也就是说,一部好的作品实际上不是由作者独立完成的,而是由受众和作者共同完成的。在《善士亭》这场书中,我们看到观众的掌声和眼泪激发了说书人的想象力,使得他们在一种更加逼真的情境中完成对书中人物的塑造。一个敲梆子的女演员,坐在主说人的旁边,一字一句地完成着人物对话,而眼泪始终不干。这种情境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观众的情绪。
对于这个正午的书场,我还有一个想法。虽然阳光下的人数不多,用耶稣上十字架前对睡觉的门徒们说的话,就是“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隐喻。它象征了善良与爱在这个时代的真实处境:比起那些在外边打麻将的,KTV包厢里唱《好日子》的,泪洒书场的人总是少数,但善良与爱从来就是弱者的权力,一滴水、一把剑甚至一张印有老头像的纸片就能将它杀死。但从长远来看,正是这不多的人构成一种希望,他们比外边逍遥的人更有力量。因为善良与爱是生命的盐,它终将战胜恶,战胜仇恨,成为人们心灵的主宰。
忍耐就是我们的秘密武器。
责任编辑:杨建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