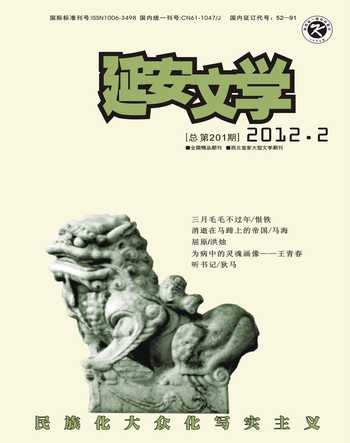钟山寺记
阿莹
记得王安石写过一篇著名的散文《石钟山记》,而我所要描述的这座石钟山,则是另一地景致了。
这座石钟山坐落在子长县安定镇的秀延河边上,几栋青砖砌成的寺院飘荡着久远的香雾,一座挺拔的七层青塔屹立在起伏的山脊上,似与远方延河畔的那座宝塔遥遥相望。虽说是仅仅只有百十米高的山丘,却形如扣地的大钟,可能就是因了这寺这塔这山的缘故,使得这道绵绵十几里的沟壑都笼罩在寺内石佛的气场里了。我们距寺院还有很远的距离,就感觉到天清气朗孤傲凛然,连空气都似乎愈发凝重起来。待走到寺院门前,你会发现这座寺院风水了得,背靠的是一道连绵不绝的小山脉,面对的是一条哗哗流淌的汾水河,衬以沟壑里满腾腾的绿树青草,行进到此会以为到了江南水乡。
这里的护寺人告诉我们,钟山寺始建于东晋时期,里边的石窟被很多文化人誉为“敦煌第二”。这让我们多少有些诧异,敦煌是建在一道绵绵的山崖上,成百上千的石窟一个挨着一个,里面目不暇接的石像与绘画让世界为之惊叹,而这里抬眼张望绝没有那样的规模啊。
但是走过精雕细琢的牌楼,越过几十道台阶,正殿石窟会有惊奇在等待着你。里面大约有三百多平方米,首先扑入眼帘的是大殿中央祭台上三位佛祖的立姿石像,这些石像体现了佛祖释迦牟尼修行的三个阶段,从左到右为过去佛、现在佛和将来佛。细细端详就会发现,这三尊石佛还存在着渐进的变化,首先那过去佛头上的发髻由头巾包裹形似火焰状,中间现在佛的顶髻已是修成正果的小发卷,而未来佛的发卷则极为规整细密,象征了佛陀超然的觉悟。那三尊佛祖的手势也充满禅意,由右手指向的“无畏印”,到左手前倾的“说法印”,再到双手下垂手心向上的“禅定印”,象征佛祖的修炼由智到悟再到无我的状态和过程。再看那身旁弟子们的神态,线条柔美,栩栩如生,眉眼间传递出摄人魂魄的生动,让人感到悲悯与慈祥。尤其是一尊犹如仕女的修行菩萨,虽说已断掉一只手臂却让人产生联想,飘逸的服饰衬出婀娜的身姿,恬静的脸庞露出淡淡的微笑,其行其态美丽得如同下凡的仙女。不过,大殿里雕塑得最为生动的是那十六尊高浮雕罗汉,或微笑或怒视或沉思或恍然,最拍案叫绝的是有尊罗汉已入禅态,耳朵却被一只小狮子咬住了,似痛得侧过头来,却仍用手托住小狮子不忍伤害了童真,让人不由地对古代雕塑家精湛的技艺钦佩不已。
大殿的中央是两根方形的石柱,都是在原石上凿成的,四周皆是手掌大的彩绘小佛像,这些小佛像据说是释迦牟尼的化身。其实稍加注意你会发现那石壁上的小佛像中间还隐藏着佛主修炼涅槃的故事,似乎所有的小佛像都围绕着释迦牟尼在盘旋飞舞,这让观者不由地感到神奇,继而因石佛透出的庄严而肃穆。我实在惊讶这些彩绘的佛像,虽然历经千年却依然鲜艳如初,显露出雍容妩媚的魅力。护寺人说有专家想分析颜料的成分,却几经周折而未果。
当我们走到石佛的身后,发现这间石窟虽说每个墙面都刻满浮雕,而靠山的墙面却只能见到几处模糊的轮廓,犹如流水把浮雕冲刷腐蚀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同处一窟怎么会状态这般不同呢?仔细琢磨才发现,这寺院地处的石钟山“前脸”,居然是厚厚阔阔的一整块青石,仿佛是侧盖在沙岩的山体上,古代工匠们极为精巧地将青石面凿成石窟,这也就是古籍记载的拓雕艺术。而穿透青石紧靠山体的沙岩却有渗透性,在经年累月的渗水侵蚀下,雕像便被冲刷得面目全非了。有趣的是在大佛前侧的石壁上,还刻有孔子和关公的浮雕像,据说是明清两代人所为,想来这精美的石窟建成后,后人们为着自身的精神需要,是在毁掉两块佛像后雕凿而成的。想想如此也好啊,儒释道三教合一,虽在坊间多有传说,但在一座大殿里同檐供奉,确实是不多见的,显示了中华文化的递进与包容,遗憾只是这两座神像的雕工与前者相比却不在一个等次上。
寺院有时候会创造一些难解的神秘和谶言。护寺人告诉我们,几年前在弟子阿难的头顶崩落过一块三吨重的石块,按正常推演这块石头怎么也要砸向阿难石像的,但展现在人们面前的雕像却毫发无损,石块显然在下落过程中偏离轨迹滚落到雕像基座旁边了。我恍然注意到,那过去佛的手形恰恰就是化解风险的“施无畏印”啊,所指方向就是石块坠落的方向,早年释迦牟尼不但用此法保护自身免遭杀戮,以后那手式便是保护佛界僧尼的法宝了。
我问那护寺人这石窟可留下古代雕塑家的信息?没曾想护寺人居然真在莲花座的后面,找到了古代雕塑家的名字:王信。似乎有朋友说过这是一个雕塑家族,他们沿着陕北子午岭开凿了一连串的佛窟。我默默地咀嚼着这位艺术家的名字,顿时感受到了这些雕塑艺术家卓越的才华和穿透历史的魅力。中国在很长的历史阶段皇权思想超然,人们对艺术创作几乎不屑一顾,无论多么宏伟的遗迹,几乎无法知晓是哪位艺术家的倾心之作,而在欧洲每一处艺术遗址,都在显著位置把设计者的尊姓大名昭然于众。但是,尽管历史没能给我们留下这位艺术家的其他信息,但这里精美绝伦的雕塑却向我们传递着一千多年前的审美情趣。那位王信雕塑家把对佛的认识,对艺术的理解倾注到他的钢錾铁铲磨石上,使得今天的人们无论置身窟里还是站在寺外,都可以与之进行艺术和哲学的对话,这也就实现了他艺术生命的不朽。进而,我惊奇地从门口石碑的开龛题记中看到这寺院原名为石菩萨堂,最初的主持为“张行者”。我无法考证北宋时期这所寺院开光时这位张行者的生辰,但我从其名字理解,这位张行者与人们熟悉的西天取经的“孙行者”大概都是奔波于险途的大德高僧。由于唐末以来这里战争连绵,是中原朝廷与北方马背民族刀刃之地,尸陈遍野血流飘杵是一定的了。张行者一定是为超度亡灵开龛立寺,也算是一位佛人的善良之举。这是我此次子长之行的最大收获,使得我们知晓了东晋年间在陕北这块烽火连天的土地上活跃着一位名为王信的雕塑家,他用铁制工具凿出了一个个能够给人们带来心理安慰的艺术形象,而一位名为张行者的北宋高僧则在这石钟山用他微薄的力量演奏了一曲曲悲悯的音乐,让无数流浪的灵魂得以安息。
然而这钟山石窟能够历经战火和动乱顽强地生存下来,一展华丽而又悲悯的风采,大概真是有些“灵气”的。护寺人煞有介事地说,文革是这千年古寺最大的劫难,曾有一帮人手握利斧想要砸毁这座寺院,但刚迈进寺院大门,石窟里竟然飞出一条胳膊粗的青蛇,高昂着愤怒的头颅,口吐着血红的信子,怒视进寺的来犯者,众人见此一哄而散。后来那些人又集合过来毁寺,途中却遇到一股山洪倾泻,就全被堵到秀延河对面的山坡上,只能站在那里望寺兴叹。其实,也正是有了这些传奇,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才能供给后人从容地欣赏。遗憾的是县志记载大殿两边曾有十五个石窟的,而今只开发出区区三个,其它的石窟似乎都隐藏在浓密的草丛里难见踪迹。但步出石窟门外,看到两株陕北极为罕见的菩提树居然从青石缝里生长出来,在阳光的映照下,绿波粼粼,犹如智慧的佛经真言在抖动,播向人间的都是慈悲之情啊。
走出寺院来到秀延河桥上,清粼粼的河水潺潺地向东流去,隐约可见宝塔飘动的影子。我想这秀延河水应该是最有灵性的,滋润四野八荒医治心灵创伤,也用持久的热情培育一个绿树葱茏的安定镇……
责任编辑:魏建国杨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