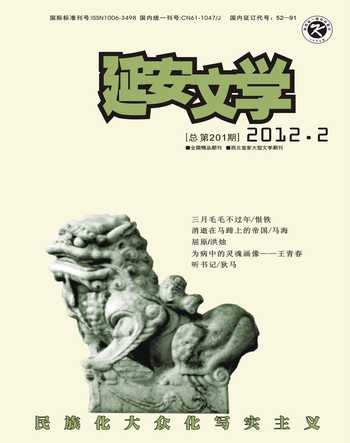白光闪
张全友
大清早,刘白光先生漫步在整洁的村庄街道上。他每天在天不亮的时候就起来,去街上锻炼。踢腿,扩胸,弯腰,捶背,还长长地深呼吸几口农村的新鲜空气。练着练着,刘白光先生心里就有了些想法儿。那会儿,他正好看到一块挂在一处临街门脸上头的牌匾。那是一处被村里人们俗称作“打锅儿”的麻将馆。早上,虽说还没有卸去外面的夹板护窗,可那门脸的上方,用红漆喷着的“及时行乐麻雀屋”几个美术大字,却是分外地扎眼。看着这几个字,刘白光先生就有些不舒服起来,心里泛嘀咕:及时行乐,我看就是一群坑害庄稼的麻雀而已。
刘白光早年在自己村的小学里当过两年代课老师,可惜,命运弄人,机会不是甚好,他没有赶上转那个正。后来,觉得几十块钱也实在养不了家,就不教了,彻底务了农。然而教书的时候烙下了一些口病,比如,说话的时候尾音有些重。你若问他:刘先生今年多大了?他答你:已经六十有三了。他还会伸出拇指和小指一晃,然后蜷起拇指和小指,再翻转伸出了食指中指和无名指来。这个动作虽说算不上多么漂亮,可至少让你觉得他和一般的农民不太一样,有一股子不伦不类的书卷酸气在里边。所以啊,刘家坳的上上下下,都还是乐意叫他刘白光先生。在农村,往前了推几年,六十三岁那也是个老人的岁数了。不是有句乡下流传的俗话这样说:活至六十三,不死鬼来拴。但是现在就不同,现在是新社会了,人的平均寿命逐年在攀升,不要说城里,就是在农村,活个八九十的也不算稀罕。就拿这个刘白光先生来说,六十几岁的人,耳不聋,眼不花的,四肢活泛,腰板笔直,走起路来脚下呼呼挂风,还依然务持着二十几亩庄稼。现在刘老先生老两口,不用自己的孩子来负担他们的生活,自给自足手里还有些余头。这样的日子过起来,自然也就有了底气,不用去看儿女们的脸子。人活到这个份上,能够有一个好的家庭局面,还赶上了这样好的时代,也就该知足了。
刘白光先生身下有两儿一女。老大那福是个汽车司机。现在的司机可是挣钱啊,一月包吃供烟还拿四千五的工资,肥得流油啊。这样,家里的女人孩子可就好活上了,想吃啥穿啥,就信马由缰地买回来。房子、家电,一应俱全的,不说幸福,那是他们身在福中不知福。可是让刘白光先生生气的是,这样活泛好过的日子,偏偏那福小两口儿不多摊揽儿女,膝下就养了一个女儿叫晓琳,十六岁了,一整天野鬼似地浪荡在县城里,书没有读成,上网蹦跶倒可以评个电视上所说的吉尼斯纪录。并且整天都和那些不三不四的小伙子们撕肩擦鬓地滚在一起。刘白光先生还听说孙女晓琳偷偷一个人去医院堕过胎。才十六岁的一个嫩娃子啊,头发染得不灰不黄一团乱麻似的,大冬天的肚脐眼子也要掉在外面,这算什么体统嘛?她妈妈是一整天都早出晚归地候在那间乌烟瘴气的麻将屋,整个无事人一样。刘白光先生就觉得老大的日子过得赖气,为此他还在老大那福的耳朵边上叨叨过,你出车再忙,那也得管着点家里老婆和孩子,要不然风罗雨散的,这算过得什么光景啊?那福却一脸无奈,话倒说的也随意,我这样不分白黑地在路上跑,顾不了那么多,吃西瓜拌辣椒,各随脾气,由她们去吧。老二那贵家里倒是消停安稳,男人领着一个小包工队在外边做短工,女人家里也种着十几亩地,还养猪养羊,两个孩子一儿一女都在村里读小学,学习也还好。一家人规规矩矩过着日子,刘白光先生对老二一家就放心不少。最担心的是女儿,近来正在闹着离婚呢。好好的日子不过,闹个什么劲离婚?刘白光先生不知道背后有什么缘故。他横竖也不理解现在的孩子们都是怎么去想的,人心不古了啊。
女儿叫那英,不是电视里会唱歌的那个那英,是刘那英。那英长得好,村里人都这么说。他们认为刘白光先生的女儿那英绝对不比电视里的那个那英差,她天生不像是村里人,是城里人的胚子,生长在这遥远的刘家坳里是有点可惜了。那英初中未读满就学起了手艺:理发。确切一点说是美容美发。后来她就在镇上开起了一间“玲珑美发屋”。这个时代人们头上的头发,已经不单单是剪短了就成的,特别是那些年轻人。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脑袋上的头发也就跟着沾了光。那英美发手艺学得精到,男人、女人和孩子,到了她的“玲珑美发屋”不过几分钟,出来后一概都成了焕然一新的洋脑袋。这样,那英的兜里也就鼓了起来,一年忙下来,也可以挣上个七万八万的。后来,那英和常常来她这里理发的一个小伙子好上了,恋爱谈了足足一年多,扯来扯去沸沸扬扬的,竟然把中间的那些枝蔓和风雨瞒过了家里。再后来,终于纸没有包住火,那英自己也不想再包了。刘白光老夫妻俩说,你把他领回来,领到家里让我们大家帮你瞧瞧。
那英觉得是应该这样,父母总归是一重天,迟早都是要面对的。
在一个热夏的午后,那英把那小伙子领到了家里。刘白光老两口儿嘴里有些抱怨地说,干嘛不上午回来,好为你们准备午饭。那英说,店里忙不是,也不是外人,别弄那麻烦事。
小伙子真是不赖,刘老夫妻俩看着就心里甜甜的,心想把闺女交给这样的后生,做父母的也算交待了。小伙子还有些腼腆,也许是初来乍到吧。手里拎了一大嘟噜水果什么的,往炕上一放,就什么话都不说了。即便说个一句两句,那也是刘老夫妻俩问一句答一句。刘白光先生就大概知道了些小伙子的生世。原来这孩子还是有点背景和来头的哩,他爸是镇里的副镇长,妈是一个小学的老师。一开始刘白光还在心里鼓捣了一气,觉得门不当户不对,这样可不好,自己这一个农村出身的闺女家,找了人家领导干部的子弟似乎是高攀了,会不会被人家瞧不起?这样后头过日子不就会吃亏的吗?可是过了一阵后,一家人都觉着这后生皮实得很,刘白光先生心里就又想:领导家庭怎么了,他们也不见得都是坏人,好人还是多么。女儿找下个皮实的男人还是可靠些,现在这社会,男人花里胡哨的多,能够遇上一个稳重的,可真是百里挑一,不易啊。于是,老两口就打心眼里愿意了这桩婚事。就在那个冬天里,也就是新年的那一天,那英和那小伙子结婚了。屈指算来,也快有四个年头了。刘老夫妻俩在这四年间似乎早觉出了不对劲,总觉得结婚后闺女那英和女婿有点皮不沾肉不疼,那英整天打理她的那间“玲珑美发屋”,小伙子在他的自来水公司按部就班地上班,不正常的是他们很少在镇上的新房里聚到一起住,因此老夫妻俩至今都没有抱上外孙。可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会闹到离婚的地步。
刘白光先生回想着:前天还是大前天呢?老大那福过来了。那天老大那福出车回来,从河北邢台买回了几袋子红薯,他还没忘记老爸老妈有这个喜欢吃异地产的红薯的嗜好,所以就给他们也扛来了一袋子。看着儿子发胖的腰身驮着红薯袋子一走一晃的样子,老夫妻俩的心里就疼上了,刘白光先生急忙上去扶了那袋红薯一把。那福气喘吁吁坐在了一方凳子上。那福说,英子的事下个礼拜法院就要判,这事总算要划上一个句号了。刘白光先生眼睁得像一对铜铃说,难道就再没有回转的余地?那福说,还回转什么?妹子自己愿意的事,走开了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刘白光先生老两口就唉声叹气上了,好端端的一对儿,怎么说散就要散了呢?
更为可气的是那些街坊邻居们,秋收结束,一整天都呆在街上没事干,东家长西家短地议论个来去。那议论就像一个筛子似的疏而不漏,只要能打起来个由头,你就会在劫难逃。那议论里难道还能少了他刘白光一家的事?不会少的。刘白光先生是最要面皮的,在刘家坳那也是体面过来的人,听着那些冷风似的议论,老人的心里冰凉啊。
刘白光先生觉得英子的事他们议论议论也就罢了,他们有使不完的劲儿,能磨嘴皮子只管叫他们磨去,女儿离婚的事也早不是什么秘密。可话题说着说着就给扩大了,话锋一转,扩到了那福那贵的身上。他们说,刘白光老汉的女儿那英不仅要离婚,他的大儿子那福在外边也有外遇了。你们想想,他可是个汽车司机啊,一个月下来几千块钱,家里能用得过来吗?一个常年刮野鬼的车豁子,不在外边养个二奶那才叫个怪。他们说,你们再看那福的媳妇,整天不着家,蹲到麻将馆里做什么?是打锅赌钱吗?不是,是踅摸着寻找新的对象哩。他们的女儿刘晓琳,听说在城里的一个娱乐城里做了小姐,一晚上七八个男人都过得去,那可是能耐啊。他们说,刘白光老汉的老二那贵你们知道吗?不知道吧?这样老实巴交的一个人,一次他领着那些做工的在镇上给人家砌围墙,工程才做了几天,他就和那家的女人搞上了。能耐吧?据说这些天,老二那贵两口子也开始闹上矛盾了,媳妇回了娘家,离婚那也是迟早的事。有人就应和了说,原来,他刘白光老汉一家子,正在犯着桃花痴这种怪病啊,规矩了多年的一家人,穷的时候还安稳本分,现在,日子好过了,有钱了,却扒拉过料碳寻灰哩。有的还发感慨,这似乎真是一种当下的传染病?饱暖思淫欲啊。
听着这些话,刘白光先生首先是脸涨得通红,紧接着他就感觉到了家庭的危机,这就和当下刮起的一股全球金融风暴一个样,来势凶猛啊,太让人害怕了。
那天老大那福来给他们送红薯时,刘白光先生就打定主意要问一下他。
刘白光先生说,你是怎么搞的吗?说着,心里的气就憋着涌上了脑门子。
那福有点懵,他说爸,你说什么怎么搞的?我怎么了?眼睛眨巴着两手就摊在了胸前。
刘白光先生问,人家都说你,你也……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
到底什么事?让你这么为难说出来。
你在外面到底有没有乱搞?
爸你把话说明白点,什么叫乱搞?
你在外面到底有没有二奶?
那福噗嗤笑了。我当什么事呢,一个破司机还养二奶?
到底有没有?
没有。
真的没有?
您还当真不信啊。
那天,刘白光先生就像他当年询问违纪的学生一样问过了老大那福,结果也就是那几句话。一开始他也认为自己的儿子不会是那种人。司机开车,那一定要全神贯注的,有时候一个整夜,十几个轮子都轰隆隆地磨蹭在高速路面上,他还哪里有心思去寻思女人啊。可是下来,他就进一步地作了些分析:虽说司机的工作有点脏和累,可总归是要去住店休息的,手里又有两个臭钱,即便没有养二奶,那也说不准你不去娱乐场所找一回小姐鬼混。现在那些大大小小的旅店,刘白光先生也早听说过,不怎么干净。想到这里,刘白光先生的心情糟糕透了。接下来,他又训斥了那福几句如何如何不顾家的话。刘白光先生都近乎是在数落他了,手指头抖抖地,指着那福的鼻梁骨。你瞧瞧晓琳,现在都成什么样儿了,难道你这个当爸的就没有责任?再看看你那婆姨……就你现在的那台面光景,我想起了,都为你脸烧。刘白光先生接着叹息,我是老了,不中用了,论个理儿,我和你妈这样年纪的人,那也是该享清闲的时候了,可是你看看你们这几个不孝子,离的离,散的散,哪个让我们安生一天了?这倒让我想起了当年,那些清贫的日子多好,安生好啊,哪怕再清贫的日子也好。刘白光先生说到激动处,稀泥捏成似地垂着个头,差点把老泪都落下来了。老婆子过来使劲推了他一把,眼角生出一对黑豆仁,剜着他,你就不能少叨叨几句?孩子不是刚出车回来,好意给你扛一袋子红薯过来,身上的汗还没落干,难道就为了讨你一顿训?
那天那福倒也温顺,始终低着个头,把老爷子的一席话从头听到尾。
临走那福就撂下一句话。那福说,我操!
刘白光先生最想不通的是老二那贵。想当年那贵还小,刘白光先生还在小学里教书。有一天,他大约是觉得身子不舒服,可能是着了点凉,起来晚了些,急忙赶到学校后,他才发现忘了吃几片药,还把昨天的教案落在了家里。那时候都快要上课了,回去拿已经不可能了。刘白光先生正在心里责怪着自己大意,办公室的门后头却蹭进来老二那贵。那贵说爸,这是你落下的教案,这是你的药,还有喝药的水。那贵一样一样探着胳膊把这些放到了桌子上,完后还仰起个脸看了他爸一下。那年那贵才七岁,个子低低的,瘦瘦的,读着一年级,书包还耷拉在小屁股下。这么小的一个人,就会替大人操心了,还这么孝道。刘白光先生就觉得这孩子是个家里的忠臣。从小看大七岁至老。就是到现在,刘白光先生的心里也没有起过一丝那贵不好的杂念。这样的孩子,长大成人后,过到了今天,家也成了,业也立了,老婆孩子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难道好日子不好过?非要去寻歪心思?非要斜斜摸摸地偷一个别人的女人在心里?不可能,老二绝对不会的,不管别人怎么说,他是怎么也不会相信老二是那种人。
可是怎么又能证明那贵就不是那种人呢?人之为人,都是一个样,眉眉脸脸的,又没有画着好人坏人的记号。还在当年教语文课的时候,刘白光先生关于形容人的品性的成语就教过学生许多,比如:心猿意马;比如:阴险狡诈;比如:脱胎换骨;比如:忘恩负义。那贵心猿意马?那贵阴险狡诈?那贵脱胎换骨?那贵忘恩负义?刘白光先生不相信这些成语会用到老二那贵的身上。老大和那英或许还能拣着用用,惟独老二,一个也不能用。
这些天,刘白光先生在家里坐卧不宁,他又不想到大街上去闲逛,他怕外面传着的那些闲话忽然又派生出些什么新内容来。已经够多了,他的心里实在再放不下一丁点那种叽里咕噜的垃圾闲话了。
刘白光先生决定找个时间去和老二那贵坐一坐。儿子不来看老子,兴许真是手头事情多,腾不开身子,这样的话老子也该主动去瞅瞅儿子。看看他最近在忙些什么?工程顺利不?身子板可还好?家里的人可还好?那些收回来的庄稼都规整妥当了没有?这些都是可以去照料的,不说是老人的责任吧,至少也是一种义务。可是几次过去了,那贵都不在。也不仅仅是那贵,媳妇孩子都不在。刘白光先生回头看着那把大铁锁,就像是一张黑黑的脸,死死地挂在门闩上,一言不发地截住了他去看老二那贵的道。
难道会是真的吗?
那英这面镜子,看来是在所难免必破无疑了。那福在外边有没有胡来?他的那个家,刘白光先生仿佛也早没有了信心。现在,最让刘白光先生想不通的是老二那贵了。假如那贵也是那个样,将是他最为痛心的一件事。危机!刘白光先生突然想到了这个时髦的词。他走在刘家坳的街上,缩头缩尾的,仿佛成了一只偷吃过粮食的老鼠,大街上那些三三两两的村里人,都成了要吃掉他的猫。就连一个若无其事的眼神,他都觉得那是在议论并嘲笑他。
刘白光先生感觉到自己的家庭真的要面临一场危机了。这就和当下因为雷曼兄弟的破产而引发的一场全球金融危机一个样。家国一个理儿。刘白光先生每天都关注CCTV的经济频道,他看着那些人头攒动的图像,都是脸上冷冰冰,心里闹哄哄的,不免心跳就会加快一些。雷曼兄弟,福贵兄弟,多么相似的称呼啊。
刘白光先生就又有点怀念起来当年。他翻着犄角旮旯地把当年那些尘封的事都晾在自己心里的晒场上,就像是选择一个阳光明媚的好日子,在翻晒陈年的粮食,还专拣几粒最好的丢到嘴里嚼着品尝。
刘白光先生想起了不做老师专事务农的那些年。老大那福学习不好,初中刚读一年,就辍学去学司机了。这小子心眼倒也灵活,他爱那一行。不到半年,他就能驾着轮子满路上飞了。回到家里,他妈看着满脸黑油的儿子,责怪他也不去料理自己的脸,给他端一盆水过来,就忙着包饺子去了。那会儿,那福精瘦精瘦的,老子娘的话他还是不敢不听。他的性子滑是滑了点,可也不至于像现在这个样,肥得像头猪,家都不去顾了。老二是连初中都没有读,刘白光先生心里好气,还咋咋呼呼地要揍他一顿。心想老大不读了,你也看他不读书,小小年纪能去做什么?家里难道连一个成才的也出不了?老二那贵的一席话,感动了刘白光先生,他把举着一根棍子的手慢慢放下来。那贵说,天生我材必有用。一个人不见得就走读书这么一条路,能成才的路多的是。我要去学泥瓦匠。既给家里省了钱,又不浪费时间。原来,除了那贵要学泥瓦匠意向的话,前半部分的内容,都原原本本是刘白光先生曾经教授给儿女的原话。那贵说,爸的话就是我的座右铭。刘白光先生哭笑不得。能说什么好呢?不料这个那贵还真的就学成了远近出名的泥瓦工,还成立了自己的包工队。这样,刘白光先生就为自己的教导在孩子们的身上得到闪光有了些自豪。后来,到了那英要去学理发,刘白光先生也干脆一言不发。人命在天,就由他们去吧。
可是现在,他们兜里都有钱了,怎么会都变成这样呢?刘白光先生觉得还是一个教育的问题。悔恨自己当年没有约束他们去读更多的书。他们现在对伦理纲常是什么都不懂。悔之晚矣!刘白光先生使劲砸着自己的脑壳。
老婆子,你说英子这事就没有挽回的可能了?他们可是结婚还不到四年的啊,这不是拿婚姻家庭开玩笑吗?
到了夜里,刘白光先生无心去看那些婆婆妈妈的电视剧。他侧过身子问老伴。你说老大到底有没有那种事?我怕是无风不起浪。这老二嘛,平时咱也看不出他像是那种人。这些日子,他们到底是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老伴显然也打不起精神来,长长叹了一口气。她的眼睛虽说瓷盯着那个荧光屏,心思却早不知飞在什么地方了。
要不咱们去请个先生看看?莫不是流年不顺?
你还信这个?乱弹琴。
刘白光先生责怪过老伴后,又自言自语地说,人老了连家里的狗都不稀罕你,老大那福还给扛袋子红薯过来,那两个货却连个人毛影子都摸不着。他们爱怎么地怎么地,不管了。
刘白光先生觉得被自己的儿女冷落了,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他听着机子里那些哭哭啼啼的剧情,想着自己一生拖儿育女的辛酸历程,不觉眼圈潮湿起来。
人嘛,有时候就应该看开些,儿女大了,不把你看在眼里,那也是很正常的事。他们也有七七八八要去处理,这就像是树大分枝一个样,自然规律不可逆转。刘白光先生在被窝犹自安慰着自己,这样一去想,倒真的轻松了不少。
可是第二天太阳升起来之后,昨个那些杂拉吧叽的肮脏影儿还是直往胸口上涌,而且来得比以前还要猛。儿女们都是自己的,谁不希望他们过得光鲜团圆?在刘家坳我刘白光好歹也是半个文化人,他们不在乎面皮,我还在乎。现在的问题是,他们要毁坏这个光鲜和团圆,把本来好好的一个家硬要撕得七零八落不成个样子,作为他们的老爸,难道就放任自流,坐视不理,无动于衷?不行,我要治治他们。
刘白光先生开始和老伴商量,他要找到一个能够扭转当下儿女们所遇到危机的办法。
他拿定了这个主意后,心情觉得好了许多。人总得要有个事做才行,不然那还活得有意义吗?尤其是现在,家里儿女出现了这么大的危机,能把这些危机给他们缓解了,根除了,身为父母,这可谓是一件最有意义的事,这也就像《士兵突击》里那小矮个子许三多说的,好好活着就是有意义,有意义就是好好活着。现在儿女们不好好活着,老往歪道上溜,这样可不行,得把他们拉回来。
刘白光先生在老伴面前慷慨陈词:当前,二十个国家的大领导们都聚到一起研究如何来救市,咱家老大老二和英子,都在被村里人戳脊梁骨,你说咱们该不该救救自己的这个家?
是应该,可怎么个救法?
不急,你让我好好想想再说。
刘白光先生闷头想了三天三夜,也没想出一个好法子。一开始,他想让老伴佯装喝农药,目的是以此来要挟儿女们就范,希望他们不要漠视了做父母的苦心劝慰。可刘白光先生很快就把这招给否定了。首先是这法子有点笨,太无能也太传统了,处理得好,作用也不会太理想,处理不好,反而会断送了老伴的性命。这样,不仅没帮孩子们破镜重圆,反而会破镜子破摔,效果适得其反。后来,刘白光先生还想用虚张声势离家出走这一招,来恐吓他们一下,假如他的突然失踪成为村里的一个新闻,在全村传开了,无疑会像一枚重磅炸弹,这样呢,他的那些儿女们就会不约而同地急忙赶回来,先找人,可能是最最要紧的事。收到的效果,也无非是来转移一下他们的注意力,淡化眼下的矛盾,达到一个非常时期面前,一家人能够体谅忍让的目的。但刘白光先生觉得这样也不好。离家出走,首先是亲戚家不能去,到了外面,这世界可是太大了。还是做代课老师的时候,只在市里培训过两个月的刘白光先生,至今连省城都没有去过,一下子要他扑到黑乎乎的大世界里去,无依无助孤苦伶仃的,老都老了,在外面病倒了可怎么办?这就好比是一粒石子儿,投到了黑咕隆咚的湖心里,恐怕是有去无回了。其次是,家里的儿女们还要为你劳精费神人力财力的,一定也要破费不少,误事不少,这是刘白光先生横竖都不忍心的事。
这可怎么办才好?刘白光先生陷入了苦思冥想的境地。
他在院子里用一把扫帚扫地,扫来扫去,地上已经很干净了,他还一直在扫。老伴说,你没事去帮我把那几只鸡喂一下吧。刘白光先生就端起来食盆子,去鸡圈里喂起了那些鸡。老伴又说,你呆了吗?鸡吃食你叫它们自己吃去,蹲在圈子里,你也要吃食吗?
刘白光先生起身走出了鸡圈子。怎么办呢?忽然,他看着老伴的眼子一亮,有了。
刘白光先生说过“有了”这句话后,脸上就绽开了一朵很灿烂的花。
他凑在老伴的耳朵边上,嘀嘀咕咕的。老伴扒拉开他说,又没有人在跟前,你鬼里鬼气的,像什么。
茅塞顿开,茅塞顿开啊。刘白光先生说。
原来刘白光先生想出一个以牙还牙以毒攻毒的好法子:老两口闹离婚,这事必然会在村里传得沸沸扬扬。然后,分居另过。这样一来,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成了一面镜子,让他们的儿女来照自己,从中吸取教训。老了也不得安生,为儿女操心操碎了啊。刘白光先生感慨万千。
这样能行?老伴有点疑惑。
你就瞧好吧。
第二天一早,刘白光先生的脸拉得很长,像一头驴脸的样子,并且眉头上还突然长起来一团黑云,就像五六月时节要下一场暴雨前的那种黑云。刘白光先生说,四十多年了,我早受够你了!
完毕刘白光先生就在地上转悠。老伴一开始还纳闷,这老东西今儿是怎么了?发什么神经?看他老这么转来转去地转,都快要把人给转晕了,老伴才似乎明白过来。哦,老头子这是在搞戏前排练呢。看他转到放着一只座钟的柜台前,不转了,立在那里,一言不发。那只座钟是他们结婚的时候购买下的,还真是一件见证他们数十年婚姻的最好信物。刘白光先生把这只罩着玻璃罩子的座钟轻轻端起来,他还用袖子擦了一下那上边敷着的灰尘。
四十年了,你这个老伙计陪伴着我们,家里别的东西,几乎都不见了,唯独你还分秒不差地陪到了今天。行啦,你也该去歇会儿啦。刘白光先生仿佛在做一次动情的演讲,又像是在致悼词。很快,他就脸凝得像一个疙瘩,两臂把那只钟举得高高的,使劲朝地板上摔去。
可怜的一只座钟,像个病入膏肓倒下去的人,死了。
你疯了吗?干啥要把它摔了?老伴上来就推了他一把,十分气恼地看着一地玻璃碎片。
四十多年了,我早受够你了!
刘白光先生想着刚才那句话,心想这是正宗的点心芝麻饼,嚼着很带劲,所以就又用了一回。他觉得戏要演,就得像那么回子事,唱念做打一起上,这样才逼真。他仿佛还有了破坏欲,就来到了一个摞放碗筷器皿的橱柜子前,使劲一划拉,稀里哗啦地摊了一地碎瓷片。老伴气得鼻孔冒烟说,你还真来劲呀你,这日子看来是过不成啦!随手揪起了一口大铁锅,朝着刘白光先生的后背就扔过来。刘白光先生早有准备,斜着躲过那口飞来的锅,就来到了院子里。这时候太阳还不是太高,他看到左邻右舍趴在墙头上看热闹的那些脑袋,就像一个个接在藤上的倭瓜。有几个平时关系要好些的还进到院子里。他们拉着刘白光先生的胳膊,说有什么过节您老两口儿不能慢慢调理?非要打打闹闹的?都这么大年纪了,叫年轻人笑话。刘白光先生借着有人拉他的劲儿,还回头踮着脚地嚷嚷着:四十多年啦——我刘白光早受够你啦——
刘白光先生被人拉到了街上,他的心里似乎真的充满了气愤和怨怒。有个看热闹的丢过来一句话,白光叔,日子好端端的,和婶子闹个什么劲?后边还有儿女呢,不能给他们脸上挂黑。
我烦!刘白光先生说,我都烦了四十多年了,再也憋不住了!
他想找一块石子儿,用脚去踢一下。可是新农村建设的街上都被水泥和砖块硬化了,根本没有他想要找的什么石子儿。一盏莫斯科式的路灯撞进他的眼里。这会儿他似乎把所有的气都撒在了这盏灯上,上去就给了它两脚。可是他低估了这盏灯的结实度,莫斯科路灯岿然不动,他的脚趾却嘎嘣了两下。
给你们脸上挂黑,我就是要给你们的脸上挂些黑,你们才会灵醒过来。
刘白光先生不去管街上的人们如何看他发神经,他想起了村子外面的那几间菜棚子。折回屋夹起了自己的铺盖卷儿,就朝村外的菜棚子走去。
刘白光先生老两口儿闹分居了,这消息沙尘暴似地刮过了刘家坳。这些天新农村建设在刘家坳又有了新进展,全村都要装闭路。其实呢,在刘家坳这里,外面的消息已经覆盖得够满了:年初南方的冰冻;5•12汶川大地震;嫦娥神七飞天;北京奥运会;全球金融危机。刘家坳家家早有了卫星接收器,现在又要搞闭路。刘家坳的人对这消息无动于衷,也不是这里的人冷漠,刘家坳村确实太远了,外面的动荡也好不安也罢,怎么会波及到这里呢?倒是刘白光先生老两口儿闹分居,这消息简直酷似一场沙尘暴,在刘家坳搅起了不小的波澜。这就得分析了:现在的村里人安逸极了,没什么忧愁在心上,秋收结束后,手里就没事做了。人,尤其是庄户人家,无论男人女人,手头上没个事心里就憋屈得慌。怎么办呢?生个事儿出来,自己去做,只有这样才不会乏味。刘白光先生一家子可能就是这样子。现在他们有事做了,整个村子的人也有了层出不穷的新消息来剔牙。不过他们也做进一步分析思考,这事情最好还是不要让自己给摊上,看看这刘白光一家,大儿子那个样,老二那个样,那英又是那个样,如今就连刘白光先生这样的乡土文化人,也和老伴儿分居了。这世界的事真的是太不好把握,太不可思议了。刘家坳村人就这样茶余饭后地议论着,不咸不淡的。据外围消息说,一些家里的主事人,自然也免不了要为自己的家庭防线设个卡,或者布张网,听说还真有不少人家网住了些大鱼或小虾。
消息是无孔不入的,刘氏兄妹怎么会听不到呢?事情过去的第三天,他们都以最快的速度,在不同的时间段里急忙赶回老巢打探消息的虚实。
屋里虽说就老母亲一人,可那气氛还和平时一个样随和。老妈一概回避儿女们的无聊追问,反而一再关心他们各自近来的情形。
那英第一个回到身边,那英说,离了,那家人都是牲口,公爹还打媳妇的主意,换谁谁不离?你们到底是怎么了?我爸他人呢?
老妈叹息,看来你是对的,有合适的,再找吧。
老大那福和老二那贵脚前脚后进了屋。
那福说,咱爸是不是脑子有毛病了?他显然对上次被刘白光先生的训斥还耿耿于怀。
爸那么精明的人,怎么会有毛病?那贵说,不会的。
老妈依然一一盘问着他们的那些事。老妈说,儿走千里母担忧啊,你们和妈照实说,再丑的事,出在儿的身上,妈都不会怪你们。
两兄弟对视着愣怔了一下,完毕哭丧着脸,一语不出。
老妈似乎已经知道了结果,说,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三兄妹一百个不理解面前老妈的情绪变化为何会如此复杂跳跃,各自都心里怪不踏实。
那贵说,妈,听说咱爸去菜棚子一个人住了,真有这码事吗?
他那是在演戏呢,不要去管他,住几天就会回来的。老妈还对刘白光先生无端摔坏那些东西的举动生着气呢。
你们都是有事做的人,回去做自己的事情去。
三兄妹对视。老二那贵说,去菜棚子看看爸?
老妈说,不必了,我知道他的脾气,没事。
老大说了,有什么大不了的,老爸这是牵咱们鼻子呢,害我们空跑一趟。
也确实是,现在谁还有时间玩这种猫腻游戏?现在是个竞争激烈到快要崩溃的时代,都在争分夺秒地争夺生存和发展空间。于是三兄妹各自悻悻然散去,事情也就到了这里。
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刘白光先生没有回来,这就有点怪了。
闹分居之后的刘白光先生,会突然觉得风光无限好。他似乎真的看到了一束白光,很耀眼地一闪。那是一个自由的世界。他心里想:有时候更为宽阔的天地,是偶然获得?还是被逼出来的?他现在不想回去了,回到老伴的身边难免会重蹈覆辙。过去的日子,在他的心里堵得满满当当,太稠了,不稀罕了。他却颇为珍惜起来眼下的这种安闲自在。这里没有新农村,没有最新消息,也不会被任何群居的喧闹所干扰。他品尝到了前所未有的宁静味道,他开始难于割舍并留恋这份宁静了。如果晚年能够一直这样过下去,那该多好啊。
一个月之后,初冬的凛冽日渐乍起,儿女们觉出了势态的严重。他们一拨拨一趟趟前来菜棚子规劝老爸回去和母亲团聚。都几十年的老夫老妻,有什么过节不能化解的?莫非真的是因为我们才……
刘白光先生用手势打住了他们的规劝,每次都说,明天吧,明天我就回去。
可是他至今却仍然独守在那里……
夕阳落下时,他会想起盛夏时节那些旺长的菜秧子。
责任编辑:高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