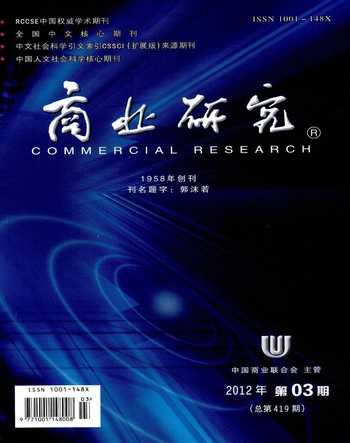大股东制衡机制与定向增发隧道效应研究
李传宪 何益闯
摘要: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后定向增发的现实情况,本文从大股东制衡的视角,以我国2008-2009年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了定向增发的隧道行为和大股东制衡机制对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折价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大股东有更大的动机和能力利用定向增发进行隧道行为,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大股东联合控制力、大股东间的制衡度在一定程度上会约束定向增发的隧道行为。
关键词:大股东制衡;定向增发;隧道行为
中图分类号:F273.4 文献标识码:B
一、引言
自2006年5月8日中国证监会颁布并实施《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来,定向增发(即非公开发行)逐渐成为了我国上市公司直接融资的主要方式和渠道。根据国泰安金融数据库统计,从2008年1月1日到2009年12月30日止,通过定向增发进行再融资的公司有212家,其中有15家公司进行了两次定向增发融资。然而,在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较为集中的市场环境下,第一大股东因持有较高比例的股份而能够参与公司的重大决策,甚至拥有实质性的控制权,这些控制权能让控制股东享有其他中小股东所没有的私有收益。因为控股股东常常采取资产转移、债务担保、关联交易、并购等方式将上市公司的资源从中小股东手中转移到自己所控股的企业中去,从而出现了控股股东掠夺中小股东利益的现象,亦称“隧道行为”(Shleifer等,1997)[1]。
从2004年股权分置改革开始,我国证劵市场逐步实现了“同股同质,同股同权”,此时大股东可以利用其对定向增发融资方式的控制权影响对上市公司实施“隧道效应”,如通过发布利空消息、串通机构对定向增发的价格进行操纵,或以劣质资产认购定向增发股票等方式获得额外资本利得,且在这种“一买一卖”的双重关联交易中,定向增发过程中的增发时机、增发价格、资产定价等环节都存在着“隧道效应”的可能。
然而,国外学者Bennedsen(2000)[2]认为股权制衡在一定程度上能抑制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的隧道行为,有利于提高公司业绩和价值,是一种良好的公司治理制度。基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投资者保护不足等现状,李增泉等(2004)[9]、陈信元等(2007)[10]的研究表明大股东在股权制衡的公司发生隧道行为的程度较低,市场价值更高。高雷等(2006)[11]通过对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和公司治理结构的PLS回归分析,证实了股权制衡对控股股东的掏空无显著影响。徐丽萍等(2006)[12]、赵文景(2005)[13]的研究,均表明股权制衡程度与公司业绩并无显著正相关关系。总而言之,在中国资本市场环境下,股权制衡是否能够发挥公司治理作用,有效约束大股东的隧道行为,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大股东的利益与公司股票价格的关联度大大增强,大股东所持股权的价值与公司股票的高低直接相关。因此,控股股东在参与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认购时,有很大的动机对其他中小股东权益进行侵害,控股股东持股数量越大,越有可能通过定向增发进行利益输送(隧道行为)。此时股权制衡程度对定向增发的影响程度如何,这是本文需解答的问题。本文拟选择我国2008-2009年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定向增发折价程度为被解释变量,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具体讨论定向增发过程中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大股东控制力,大股东制衡度对于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折价的影响,从而为后股权分置时期股东制衡和定向增发折价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证据。
二、文献回顾
(一) 定向增发和隧道行为
现代资本市场关于定向增发的研究均表明,定向增发过程存在着普遍的折价发行现象。现有文献主要从股权结构、信息不对称理论和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等方面,对定向增发的折价发行进行了解释。Wruck(1989)[3]认为定向增发是对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这将会改变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从而带来新的外部监督力量。此时公司管理层会有更大的动力去改善业绩,从而提升公司价值。因此,定向增发的折价发行是对增量股权监督成本的一种补偿。Hertzel等(1993)[4]的研究表明: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潜在投资者在对公司的情况进行预测或评估时需要一定的成本,而定向增发的折价则是对投资者这种搜寻信息成本的补偿。Maury等(2005)[5]认为定向增发折价是管理层对那些认购股票却不会参与或监督管理层的特定对象的补偿成本。管理层为了实现对公司的控制,减少委托人的监督力量,从而更愿意对那些消极投资者进行定向增发折价。
然而,部分学者认为定向增发的折价可能与利益输送行为(隧道效应)有关。国外学者Baek(2006)[6]以1989-2000年间韩国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定向增发中的隧道效应,其研究表明定向增发的价格决策受到财阀内大股东的掏空动机影响,当大股东持有财阀内认购方的股份比例高于其持有财阀内发行方的股份比例时,大股东的掏空动机更为强烈,因为大股东此时通过关联方的定向增发能获利更多。国内学者黄建中(2007)[14]认为董事会融资权过大,大股东可以利用定向增发中定价基准日的确定和增发价格折价率的选择等方式进行利益输送行为。方勇华(2008)[15]指出,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监管法律和审核机制不够完善,大股东很容易在定向增发过程中通过关联交易、资产占用等方式进行利益输送,从而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刘宇(2006)[16]以武钢股份定向增发为案例,重点分析了定向增发中各大相关利益体(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等)在定向增发前后的财富变化情况,结论表明定向增发将在一定程度上“牺牲”非流通股股东利益,而流通股股东利益损害的情况有所减弱。张鸣等(2009)[17]通过考察大股东控制下的定向增发折价行为,实证发现大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动机是影响上市公司进行定向增发的重要因素,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的折价水平和大股东认购比例共同决定了大股东是否从上市公司转移财富及其转移财富的多少。朱红军等(2008)[18]主要对“驰宏锌锗”定向增发事件进行案例研究,揭示了驰宏锌锗定向增发中大小股东间的利益协同行为的本质是利益输送行为。陈信元(2007)[10]基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的特征,对定向增发折价原因的实证结果表明,大股东会利用定向增发进行隧道行为,从而导致较高的折价程度。王志强等(2010)[19]的实证研究发现大股东在定向增发中会通过刻意打压定价基准日股价、提高折价幅度等手段进行利益输送,即隧道行为。
综上所述,在目前国内外的关于定向增发的规范研究文献中,学者们普遍对定向增发折价的原因及影响程度进行了讨论,且针对大股东认购定向增发股份中是否存在隧道效应提出了疑问,而中国的上市公司所面临的股权集中度较高,大股东能够有效的控制定向增发过程中的资产定价、增发时机、增发价格等。由于中小股东与大股东在定向增发中会有利益协同行为,加之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环境较为薄弱,因此大股东很容易通过定向增发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从而产生隧道效应。
(二) 股权制衡和隧道行为
在股权制衡研究方面,国外学者Pagano等(1998)[7]的研究认为理想的股权结构是多个大股东的同时存在,并表明大股东之间的相互监督可以内部化控制权私人收益。Gomes(2005)[8]也认为股权制衡是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拥有足够股份的第二大股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大股东的隧道行为,从而提高公司业绩,并且多个大股东之间互相约束和监督能够有效抑制大股东的隧道行为。Maury等(2005)[5]的实证分析,发现多个大股东并存与公司价值显著正相关。由此表明,国外研究普遍认为股权制衡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的作用。国内学者陈信元等(2004)[10]也认为股权制衡对公司价值和市场价值有正向影响,李增泉等(2004)[9]发现股权制衡公司的大股东掏空行为更少。只有少数学者如高雷等(2006)[11]人通过对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回归分析,证实了股权制衡与控股股东的掏空没有显著相关性。另外,徐丽萍等(2006)[12]和赵文景(2005)[13]的研究均表明股权制衡程度高的公司业绩比股权制度程度较低的公司业绩更差。考虑我国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和制度特征等,股权间的制衡是否能抑制定向增发的隧道行为,这仍需进一步细致的研究,以提供更直接的经验证据。
三、研究假设
由于上市公司在定向增发过程中,大股东可以利用其控制权对定向增发的增发时机和价格制定进行有效控制,故第一大股东有更强烈的动机利用定向增发进行隧道行为。本文参照Baek等(2006)[6]、陈信元(2007)[10]、唐跃军等(2006)[20]的研究方法和思路,选取定向增发的折价程度作为衡量定向增发隧道行为的主要变量,即定向增发的折价幅度越大,定向增发的隧道行为越严重。基于此可以假设:
假设1: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定向增发的折价幅度越大。
在中国的上市公司中,其他大股东(本文指第二至第五大股东)在持股比例上明显少于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不太热衷于定向增发的隧道行为,且出于长远利益,他们更愿意充当监督和制衡的角色。基于此可以假设:
假设2a: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第二至第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定向增发的折价幅度呈负相关关系。
假设2b: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第二至第五大股东中的部分或全部持股比例之和与定向增发的折价幅度呈负相关关系。
根据内部治理平衡和成本收益的考虑,如果第二至第五大股东认为监督制衡第一大股东的成本大于联合第一大股东的收益,那么在定向增发时,他们中的一部分甚至全部都可能和第一大股东一起进行隧道行为,从而侵害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但是,随着股权分置的改革,股票逐渐实现全流通,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而此时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能力会逐渐增强,且其他大股东可以依靠联合制衡能力对第一大股东实施监督和制衡。因此可以假设:
假设3: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第二至第五大股东的制衡度①与定向增发的折价幅度呈负相关关系。
四、 研究设计
(一) 研究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8年1月1日到2009年12月31日已完成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其相关数据主要来自国泰安CSMAR系列研究数据库和巨潮资讯网,同时根据上市公司公布的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 》及相关公告补充收集了部分数据资料。初步统计共收集了212个样本公司,但为了研究的需要,本文对研究的样本公司进行了筛选:(1) 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进行定向增发的样本,因为金融类上市公司与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经营范围不一样,共3家;(2) 剔除B股公司增发A股,A股公司增发H股以及H股公司增发A股的样本,共1家;(3)剔除财务数据和市场交易数据无法获得的样本;(4)剔除定向增发两次或两次以上的样本,共15家;(5)剔除在定向增发前后被ST,ST﹡的公司,共6家;(6)剔除存在其它异常或缺乏相关数据的公司。进行以上剔除后,本文总共选取了187家样本公司。
(二) 研究变量及其说明
主要解释变量如下:(1)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主要考察单个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对定向增发折价幅度和隧道行为的影响。(2)大股东控制力,主要用于考察第一大股东是否处于“一股独大”,以及其他股东中的部分或全部持股比例之和,即股权集中与股权制衡的不同对定向增发折价幅度和隧道行为的偏好程度。(3)大股东制衡度,用于考察第二至第五大股东中的部分或全部的联合制衡度对于定向增发“隧道效应”的影响程度。
鉴于定向增发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故引入以下变量为控制变量:(1)资本结构(LEV)。上市公司增发前一会计年度的财务杠杆系数,主要用于衡量公司风险,计算公式为总负债除以总资产。(2)成长性(OPE)。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利润率,用于考察公司的盈利能力对定向增发“隧道效应”的影响。(3)公司规模(LNTA)。上市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这是用于考察公司规模的代理变量,公司规模越大,信息披露就越全面。(4)增发规模(Fraction)。定向增发的股票数量与增发后股票总数量的比例,增发规模的大小会给外界传递大股东的经营信心,其代表着大股东或特定对象的认购比例,具体如表1。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将全部样本的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从中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平均持股比例较高(约为40.62%),显示出第一大股东对上市公司仍有较大的控制权,在所有定向增发的样本公司中约有31.02%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0%。平均而言,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仅依次为7.42%、3.25%、1.80%、1.37%,这表明第二至第五大股东与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数有明显差异,进而体现他们的监督制衡能力明显不足;同时,第二至第五大股东、第三至第五大股东、第四至第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之和(均值)也仅为13.84%、6.42%、3.16%,这说明即使第二至第五大股东之间联合,其对第一大股东的监督制衡能力也相当有限。此外,从各大股东间的制衡度均值比较可知,第二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第二和第三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第三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第二至第五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第三至第五大股东对第一和第二大股东、第四至第五大股东对前三大股东的制衡度依次为0.2504、03714、0.0833、0.4914、0.1700、0.0746,这进一步表明在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时,股权制衡的作用仍受到大股东的很大限制。
(二)多元回归分析
多元回归分析的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中可知各回归方程的D.W值均在2附近,这表明该模型基本不存在自相关问题。多元回归分析检验多重共线性的容忍度Tolerance值远大于0.1,方差膨胀因子VIF值远低于10(限于篇幅,没有列示各变量的Tolerance值和VIF值),这说明模型的各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从表3的模型1可以看出,定向增发的折价率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呈正相关关系,且模型2中哑变量DS1的回归结果亦支持假设1。这说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大,定向增发的折价幅度也越大,进而第一大股东更有动机通过定向增发对中小股东进行隧道行为。
在模型1中对各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回归结果说明,第三至第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定向增发的折价率显著负相关,而第二大股东与定向增发的折价率的相关性并不太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第二大股东与第一大股东有共同的利益出发点,两者趋于联合决策,共同对其他股东进行隧道行为,但该实证结果仍支持假设2a。在模型2中,对前五大股东中部分或全部持股比例之和的回归结果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定向增发折价率显著正相关,而第二至第五大股东中的部分或全部持股比例与定向增发折价率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该结果证实了假设2b。在对模型3的回归分析中发现,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各大股东间的制衡度基本上与定向增发折价率呈负相关关系,只有后两大股东对前三大股东的比值与定向增发折价率呈正相关关系,这可能是因为在中国的上市公司中,后两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太低,其制衡度完全不起作用,且出于制衡成本和附和控股股东的收益考虑,他们更倾向于支持第一大股东的行为,而不是充当监督和制衡的角色,所以该实证结果基本上支持假设3。
此外,相关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财务杠杆、主营业务利润率和定向增发规模与定向增发折价率的相关系数全部显著为正,而资公司规模与定向增发折价率的相关系数显著为负。这可能因为上市公司的财务杠杆越小,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越低,从而在定向增发过程中,大股东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从而选择较少的折价进行增发。由于主营业务利润率主要反映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盈利能力越差的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的股份就越大,定向增发的股份就越大,从而有更多的机会进行隧道行为。由于定向增发的规模会向市场传递一种投资的信号,增发规模越大,传递的投资信息越积极,从而大股东有更大的动机和能力进行定向增发隧道行为。根据公司法和信息不对称理论可知,上市公司规模越大,其信息的披露量越大,从而信息的不对称程度就越小,信息搜寻成本也就越小,从而可能降低定向增发的“隧道效应”。
六、研究结论与展望
本文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后定向增发的现实情况,从大股东制衡的视角,以我国2008-2009年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的187个观察值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了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定向增发的隧道行为以及大股东制衡机制对定向增发隧道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
第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的折价幅度呈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大股东与中小股东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大股东有充分的动机和能力在定向增发折价发行的过程中对中小股东进行隧道行为。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推进,第一大股东占绝对控股地位(持股数超过50%)的比例依然较大,一股独大的治理问题及如何建立制衡的股权结构仍需进一步的研究。
第二,实证结果表明大股东之间确实存在着互相监督与制衡,在定向增发的过程中,第二至第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和制衡度会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大股东的隧道行为,减少中小股东利益被掠夺的可能性。这主要是因为第二至第五大股东的联合制衡能力和收益有可能高于其个体对大股东的监督行为,但同时发现第二大股东在面对定向增发隧道行为时所表现的不确定性。股权制衡理论认为第二大股东是对第一大股东监督制衡的重要力量,而实证结果表明第二大股东与定向增发折价率并无显著相关关系,这说明第二大股东在定向增发中存在着与第一大股东联合进行隧道行为的可能性。然而,从模型3中对第四和第五大股东制衡度的实证结果可知,这两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有限,即使联合也无法发挥应有的制度制衡能力,他们反而更倾向于附和第一大股东,因为附和第一大股东所带来的收益可能大于被第一大股东掏空的成本。
第三,在后股权分置改革时期,大股东间的股权制衡会进一步抑制定向增发的隧道行为。因为股价的高低会进一步影响大股东自身的利益,而定向增发的折价发行幅度会影响股价的走势,从而在定向增发的隧道行为中,大股东间的监督和制衡作用会更积极。
本文的发现为股权分置后期研究上市公司大股东制衡机制与定向增发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证据。与前人研究相比,本文对制衡股东和定向增发折价的研究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证据,对相关资本市场的监管部门如何发挥大股东制衡作用以及加强对定向增发隧道行为的监督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未来可能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包括:不同性质的大股东制衡机制会如何影响定向增发的隧道行为?在大股东制衡机制中,第二大股东的具体性质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第二大股东到底是监督制衡能力大,还是与第一大股东联合的可能性更高?
注释:
① 本文中的制衡度定义为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间的比值。比值越高,表明大股东制衡度越高,从而其他股东的监督制衡能力越强;反之则表明监督制衡能力越弱。
参考文献:
[1] Johnson, S., Rafael La Porta, Lopez-De-Silanes, F. Shleifer, A. Tunneling[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0(90):22-27.
[2] Bennedsen, M., Wolfenzon, 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Closely Held Corporations[J].Th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0, 58:113-139.
[3] Wruck, Karen Hopper. Equity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and Firm Value: Evidence from Private Equity Financings[J].Th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89,23(1):3-28.
[4] Hertzel, Michael, Richard L.Smith. Market Discounts and Shareholder Gains for Placing Equity Privately[J].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93,48(2):459-485.
[5] Maury, B., Pajuste, A. Multiple large Shareholders and Firm Value[J].Journal of Banking&Finance, 2005(29):1813-1834.
[6] Baek, Jae-seung, Jun-koo Kang, Inmoo Lee. Business Groups and Tunneling: Evidence from Private Securities Offerings by Korean Chaebols[J].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6, 61(5):2415-2449.
[7] Pagano, M., Roell, A.The Choice of Stock Ownership Structure: Agent Costs, Monitoring and the Decision to Go Public[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8(113):187-225.
[8] Gomes, A.R., Novaes.W. Sharing of Control as a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 Working Papers, Penn CARESS, UCLA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9] 李增泉,孙铮,王志伟. “掏空”与所有权安排——来自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资金占用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04(12):3-13.
[10]陈信元,朱红军,何贤杰.利益输送、信息不对称与定向增发折价.中国会计学刊创刊会议论文集,2007.
[11]高雷,何少华,黄志忠.公司治理与掏空[J].经济学季刊,2006(4):1159-1178.
[12]徐莉萍,辛宇,陈工孟.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及其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J].经济研究,2006(1):90-100.
[13]赵景文,于增彪.股权制衡与公司经营业绩[J].会计研究,2005(12):59-64.
[14]黄建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定价机制研究[J].上海金融,2007(2):56-60.
[15]方勇华.定向增发的散户利益保护问题研究[J].时代金融,2008(6):45-46.
[16]刘宇.定向增发对相关利益体财富的影响分析[J].证劵市场导报,2006(4):12-16.
[17]张鸣,郭思永.大股东控制下的定向增发与财富转移——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09(5):78-86.
[18]朱红军,何贤杰,陈信元.定向增发“盛宴”背后的利益输送现象:理论根源与制度成因——基于驰宏锌锗的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08(6):136-148.
[19]王志强,张玮婷,林丽芳.上市公司定向增发中的利益输送行为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0(3):109-149.
[20]唐跃军,谢仍明. 大股东制衡机制与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来自1999-2003年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南开经济研究,2006(1):60-78.
(责任编辑:关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