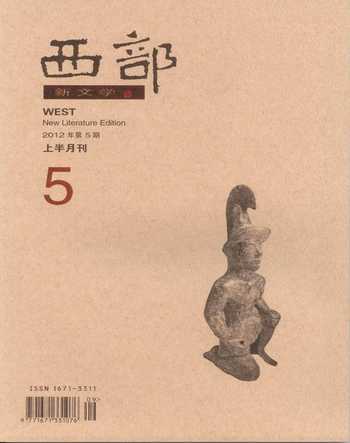饥饿散记
张炜
古老的故事如果没人倾听
一直揪紧的风筝也会断线
让春天的风筝牵上人奔跑
让人和风筝一起飞翔
人仍然不能忘记老故事
尽管它有时不让人愉快
榆树
老人最感激的不是她的亲人
不是任何人
也不是什么思想
更不是乡间艺术
她只把铭心刻骨的感谢
留在后院
后院的某个角落
那里有一棵半死的苍榆
如今因为将死而努力繁衍
刚刚成年或幼小的子孙
呼拉拉挤满半个院落
春风吹来
最小的重孙笑声朗朗
惊人的繁衍逼近了小屋
一夜间根须穿过墙基
老人一大早醒来
看着床前破土而出的叶芽
这是她拥有的幸福时刻
她在它面前蹲下
她像它这般幼小
经历的是饥饿的折磨
就像焦渴中盼一滴水
祖母在盼一粒粮食时死去
所有的亲人死去之后
她靠吞食泥土长大
她最懂得泥土的气味
特别是深部埋着姜石的褐土
当她长得更大更大
她开始吃草
她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羊
狂喜地奔向渠边青绿
她最迷戀槐叶和它的花朵
她与蜜蜂争夺花朵
几乎所有人都死了
所有的人都找不到墓地
她吃过了槐花又吃树皮
树皮屑末中掺了一点土
她越来越厌恶土的气味
记得祖母在世时抚摸那棵榆树
让孙女最后的时刻再来找它
她知道这样的时刻到了
她吃掉了它的叶子
她吃榆树的嫩茎
吃一点苍老的皮
她知道美味的树皮剥尽
它就会先于她而死
她用了许久时光才吃掉它的半边
然后剖开泥地
顺手把柔细的黑土抹到嘴里
再咀嚼多汁的树根
一生一世最难忘记的
就是榆树根的芬芳和甘甜
整个冬天她都嚼着树根
等待春天的嫩芽
槐花终于又开了
蜜蜂又来争夺了
她的嘴被蜜蜂蜇肿了
她知道自己活过来了
失传的酒
红薯根和高粱屑
一点植物的藤蔓和药材
一种奇形怪状的陶器
它们叠在一起就开始造酒
是为数不多的一些老人合计着
是他们每年秋天合计着造酒
这是真正的故乡美酒
浪子常常把它携入深山
一壶酒就能换来一个美人
一场豪饮就会化解世仇
这里再没有其他记忆
只有关于酒的传说
这里没有任何财富
只有美好难舍的沉醉
一切故事都是酒的故事
一切都用杯子陶碗葫芦量取
一个妇人安然入睡
在梦中自语和微笑
那是因为她忘却了日子
那是因为她饮过了酒
狐狸和黄鼬以及村中生灵
都带着熏人的酒气懒洋洋走过
春天的歌唱起来就不能停歇
春天是小村人齐开酒坛的季节
有人已经是第三天空腹饮酒
有人已经是长醉不醒
直到没有了粮食也没有了酒
没有了孩子也没有了老人
死寂的日子还在继续
平原上长出庄稼
庄稼旁全是坟墓
小村里再也没有了酒香
酿酒的老人全都走了
食土者
都预言唯有他能够生还
就把怀中的孩子托付给他
人们亲眼见他食过黄土和白土
还食过肥得流油的黑土
掘土掘这片无边的膏脂
它把逼人的甘味藏到种子里
它自己就有最深长的甘味
可惜只有一个人学会了品咂
他们看他掘开浮土和松土
挖出下面最黑最亮的部分
然后是悉心捏成长条
然后是从一端吃起
棉花
它曾经是美丽的花
未结出汁水丰盛的果实
可是它像母亲一样温暖
让人在寒冷中依偎
一个人在最恐惧的时刻
伸出双手揪住了它
它当时是一床被子
一个人大口吞食它
从早晨噬咬到黄昏
午夜的钟声刚刚敲过
这个人停止了咀嚼
永远的追赶
是人追赶影子还是影子追赶人
是人的影子还是陌生的阴影
那索索颤抖的是生命还是其他
为什么总有一条线连在心上
为什么总是揪得生疼
逃离之路漫长崎岖
人趴在地上永不再起
人用死亡回告了大地母亲
人用沉寂传达了最后一次抗议
可那影子还是追赶不休
直把人追到悬崖
人若止步它就缓缓爬来
它不是咬住人的喉咙
而是攫住人的腹部
然后再俘获整个生命
挖掘
她的目光垂落在哪里
你就在哪里剖开地幔
有什么循着矿脉游走
你的追逐已经力尽气竭
你交付的是全部希望
她回应的却是死亡的焦渴
你一次次撕破了自己
让鲜血和汗水一起淋漓
永恒的清泉悬在唇边
可是死亡才能让你餍足
于是你喜泪长流发出嘶喊
一刻不停走进无边的黑夜
在黑色幕布的另一边
挖掘的喘息吹落了云朵
这是一场生与死的接力
这是催逼死亡的焦灼
世上再没有更大的魔法
像它一样顽固与莫测
她的目光落在哪里
你就在哪里剖开和击打
人世间只有一种力量
只有死亡才能把你阻止
想
脑海深处右半部有根藤
它正慢慢干枯发白
它的颜色就像正午阳光下苍白的火
那阳光对一切不理不睬
阳光比山脉和水心肠更硬
发白的藤栽在思念和想象的火上
火窥视着阳光一刻不停地燃烧
水与土都烤成了焦饼
火还是炽烈急躁地蹿跳
这根藤永远不知道火的渴望
不知道火到底要什么
想念和思念才是一把火
绿色的藤把根脉扎错
烧啊烧啊烧啊烧啊
绿色的藤正在变白
白得像炭火上蜕下的屑末
白得像没有光泽的银子
离它有多远
从第一个黄昏到柳树那么远
远得像通往小城的泥路
像大山最高处的喊声
飘落到拥挤无风的巢穴旁
它像一只手臂那么长
长得真是遥不可及
长得像早晨和傍晚的目光
距离变得饥肠辘辘
坐上飞车也难以追逐
远行人不得不备下一块糕饼
它的颜色像太阳烤过的皮肤
像你那个夏天海上归来
像你含而不露的模样
此刻的食物能把距离缩为一寸
或者短到不能再短
你日夜吞食的是它的长度
而他正忙着给大海再添几滴泪珠
呼号驾着波涌抵达彼岸
你却一直站在黄昏的树下
这儿仍旧是一棵柳树
你第一次想要丈量的树
它在暮色中缓缓倒下
最后盯视着通往小城的泥路
最苦的叶子
问遍茫茫山冈和平原
我要寻访天下最苦的叶子
那肯定是一片有毒的叶子
它把威严和恐惧留下
谁不怕浮肿流血长眠不醒
谁就伸手采摘这片叶子
听说它曾毒死过一头犍牛
它长在海滨的一座沙冈下
那么就是它了我梦中的食物
我用最后的力量去获取它
牙齿让大地失去了绿色
世界已被贪婪的牙齿细细咬过
唯有那一树岗下的叶子
正迎着烈日发出残忍的微笑
它垂挂的是一张通往冥府的证件
干枯的四野一声不吭
它这会儿挨近我灼热痒痛的面庞
被我恶狠狠咬了一口
苦辣惊心的味道让人失去了比喻
最后时刻我才想起了孔雀胆
送别
送一个美男子到远方
远得没有尽头
他因为与生俱来的美
临行前也没有找到伴侣
最后现在他去的地方没有光
那里呈现彻底的阴性
他有一头浅黑色的柔发
每年里有八九个月吞食野草
草叶使他的眼变蓝了
使他多少像个异邦人
还有越来越高的颧骨
越来越大的巴掌
细细高高真像一棵高粱
十月的风把他吹折了
因为他是最高的草本植物
他该上路了随同别人
同行者成群结队
送别的人三三两两
留守者在大地上挖一个出口
每一锹土都让他们剧烈喘息
最后看一眼他没有血色的嘴唇
这里不曾被任何女性亲吻
出口和入口都敞开了
不知美男子是离开还是归去
反正是去远方
真正的远方
哭泣的柳树
它恳求他走过来
在焦干的荒漠上
它将赠他一串亮晶晶的泪珠
它在此地是唯一的树
而他是匆匆赶来的路人
一个比一个更孤单
一个比一个更贫穷
只不过一个独守了二十年
另一个奔跑了二十年
他真的朝它走来
然后一头扑到它的身上
他在低低呼叫
揪住细嫩的枝桠一阵猛啖
它浑身颤抖
它痛得哭了
化学
春天脱下了老式棉袄
春天听到了一个词叫化学
它们用石臼和碾子化掉了
又用铁锅和火化掉了
人们学着把谷糠和玉米芯掺好
学着加进红薯梗和水
然后一切都投入蒸笼
揭开笼屉赶走白汽就露出了化学
平原上的人都开始吞食化学
这怪异的名称真难下咽
他们一边照镜子一边诅咒化学
镜子里的脸又大又圆
哲学
从老辈起就不记得有这种奇怪东西
尽管也见过火轮船和三眼枪
就像第一次见到收音机和手电筒
这一回又遇到了哲学
老人惊得不敢抽烟
一听人讲哲学就掉了火镰
据说哲学这物件到处都有
它硬得像石头香得像米饭
一天到晚都不能离开
它好比是水和瓜干
好比是天上的太阳碗里的糊糊
都说瓜干是内因水是外因
火和锅子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
哪个村子不吵架谁不闹肚痛
真是矛盾无处不有无时不有
手心和手背就是正反两个方面
又对立又统一都在一只手上
加紧弄些瓜干就是主要矛盾
种韭菜收豆角都是次要矛盾
黑三月
不知几年前告别了这个月份的欢笑
最多的欣悦连接了最多的悲苦
翻腾的春水让人色变
赶不走的乌鸦一群群挤进院子
老人摸着泥碗上的裂纹
找到了走向归宿的去路
燕子一只也没有来
全村只剩下一条狗
月夜里只有一条狗的吠叫
它一声声催逼什么
三月里安静得让人心惊肉跳
三月里不该这么安静
三月里全是黑咕隆咚
三月里正等着掩埋什么
该掩埋的都掩埋了
用锹和手用泪和心
黄土与天空一样颜色
手与黄土一样颜色
三月里不该这么安静
月夜里只有一条狗的吠叫
浸泡
因为坚硬和苦涩无法下咽
一切都必得浸泡
随处可见陶缸与瓷盆
浸泡着树叶海草和皮革
把苦味和毒味浸掉了
把无味的岁月吞食了
有一块奇妙的老皮革浸了十八天
搓洗得洁净而柔软
它在刀下变成纤细的白肉丝
烹炒青黄不接的苦柳叶
海草在午夜水中泛出噼啪气泡
闪烁着海怪阴暗的眼睛
老人在梦中与海草对话
说明天要试着浸泡一下鹅卵石
我等你
你说要等我到那一天
那又是怎样的一天
那一天你能在太阳下站起
能在山壑里发出呐喊
现在你只能匍匐着看我
最珍贵的礼物只是微笑
你的手摸不到我
你的目光伸得很长很长
那一天我们都能站起
那一天你能够爱我
现在还不行现在
我們只能用目光深深地触摸
栏目责编:孙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