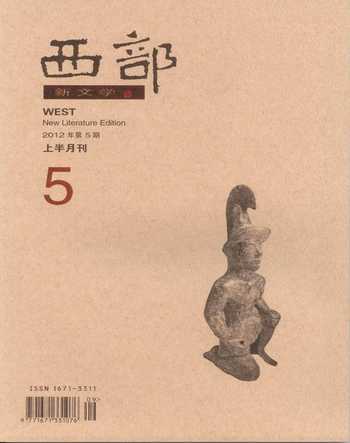晒晒黄沙梁的太阳
刘亮程
有一年
那年地震房子晃动了几次
村里人便都忘了
留麦种子
第二年土地长满荒草
我们去河那边的村庄找亲戚
回来时村里人全走光了
留下狗和空屋
我们一家家敲门
背着讨来的半袋种子
又一年离乡的人回来
一个个风尘仆仆地蹲在门口
他们都进不了家
他们把鑰匙丢在逃荒路上
那一年我们长大成人
向他们讲家里的事情
许多人哭了 他们都没想到
前几个秋天洒落的种子
在他们背井离乡后一下子发芽
遍山遍野长满粮食
人们远远闻五谷的香味往回赶
那一年
没有谁赶上收获季节
村里人只把自己
从异乡收回
老皇渠
我们走后剩下的人
将黄土路向北挪动了半里
腾出些地方盖房子种地
还是那几样作物
一茬一茬从老地方长出
人们一年年走过去
水从老皇渠淌来环田绕户
一些作物在几天前干渴而死
另一些活了下来
这场水后土地还要重新龟裂
人们依旧吃去年夏天的麦子
活到今天依旧有力气结婚
造屋生养孩子
老皇渠浸满枯死作物的根须
我们走后不知道粮食
又收获过几次
总是有人
等不到这一季的麦子长熟
五谷青青时他们匆忙离去
背影飘摇如叶
让剩下的人感到一种作物熟了
却不知这种作物熟在哪里
梦里我们常听见熟落的谷粒
敲远方某一块土地
因此总有人悄然离开村庄
像我们一样流落异域
剩下的人依旧看粮食
从老地方长出
依旧饮老皇渠水
渐渐吃胖又渐渐憔悴下去
这粮食
收获一百次还跟没收获过一样
一生的麦地
有人走过你一生的麦地
面影模糊似你曾见过的某人
又像不是早年的矮草棚里
一条白狗含含糊糊
梦见你的脊背爬满绿虫
醒来它的狗皮不见了
大片黄熟的麦子洒落在地
没有人收割
生命是越摊越薄的麦垛
生命是一次解散
有人走过你的一生没遇到你
老鼠偷食你剩下的日子
一群红蚂蚁 打算用五年时间
搬空你后墙根的沙土
你得走了村里有许多人卧病不起
许多人开始感到家不在这里
他们被自己的狗咬伤
在麦子快长熟时发现
种子错洒在别人地里
自己的那片荒在野外
一个早晨你醒来
四周全成空房子
人们在远迁的另一个村庄
注销你的姓名地址
而你还惦念着他们
扔下一生的麦地去远方寻问
年代那头的破墙下面
一个很像你的人
正结算你一生的收成
你要顺路去看看离他不远
另一些人表情麻木
大捆大捆的麦子扔进火堆
寂静家园
我看见你们走过家门
不知几更了 我看见你们
在稀稀的星光下边走边朝后望
大哥我跟在你们身后
一个人回到家中
站在寂静的院子里
望着我们的家门
在夜色里静静敞开
房子黑黑的我不敢进去
大哥我隔着矮院墙喊你们
我费了很大劲喊不出一点声音
你们走在不远的星光下
偶尔回头朝家里望望
我喊急了跑出院子
拼命向你们打手势
你们中间的一个看见了
转身朝家里跑来
院子里忽然响动起来
你们跑到院门口时
夜色比刚才暗了
大哥我好像听见你问我
家里出什么事了
我的嘴在黑暗中大张了几下
仍旧没一点声音
这时夜色更显得暗了
我看见你们在院门外不安地走动
身影模糊不清
我一下子害怕起来
转身跑进漆黑的家中
顶好房门
在土炕的一个角上悄悄睡下
过了好一会儿我听见你们
走路和说话的声音
离家越来越远
太阳偏西
谁收起农具
好像早早干完一辈子的事情
回到家里
谁这时候锁门出去
午后的光景仿佛
谁的后半世
谁最后被远方隐约的田埂拦住
夕阳斜照的庄稼地里
一个人猛然站起
高出庄稼半截子
谁蹲久了也来这么一下
走路和劳动的人
已经没多少力气
谁还要再干一阵子
谁知道自己要种多少年地
收成才能够吃一辈子
谁望着满眼葱郁的青禾
发觉先长老的竟是自己
天黑透了谁收工回去
木桌上简单的晚饭凉如往事
一样农活死死缠住谁
谁在以往的坦途中慢慢
感觉到时间坡度
走过千次的坎儿竟一次也
走不过去日子好好的
衣食足足的谁不行了
满坡满梁的黄花为谁
开遍四季不结一粒籽
离村庄很远的麦地
总在寂寞中熬黄叶子
该熟的时候它们自然就熟了
谁睡在家里推算收获日期
我们黄土高筑的村庄是
另一片作物
此刻静静生长影子
水一样的光阴环田绕户
遥远的黄沙梁
在遥远的黄沙梁
睡一百年也不会 有人喊醒你
鸡鸣是寂静的一部分
马在马的梦中奔跑
牛群骨架松散走在风中
等你的人在约好年成
一季一季等来三十岁的自己
等来五十岁的自己
道路尽头一片荒芜
有时你睁开眼睛 天还没亮
或许天亮过多少地
又重新黑了 炕头等你的鞋
被梦游人穿走经历曲折异常
他在另一个村庄被狗咬醒
名字和家产全忘在异乡
而你睡醒的梁上
一棵树梦见它百年前的落叶
还在风中飘荡漫天黄沙向谁飞扬
离家多年的人把一生的路走黑
回到村庄内心的阴暗深似粮仓
在遥远的黄沙梁
人们走着走着便睡着了
活着活着便远离了家乡
房子一间间空在路旁多少年
家还是从前模样
你一个人从梦中回来
看见田野收拾干净草高高垛起
播种和收获都已经结束
爱你的人睡在另一个人身旁
儿女一炕从村南到村北
只有你寂寥的心被风刮响
梦里用旧的一把锨扛在肩上
没意思地游逛
像件布衣被忘在另一世
给你梦想的地方
给你留下墓地的遥远村庄
有人一夜一夜扫起遍地月光
堆成山一样高过沙梁
又有人吃饱了没事
头枕土块在长夜中冥想
一颗扁瓜熟透在肩上
草莽中的一颗瓜被人遗忘
才熟透彻也跟没熟过一样
在遥远的黄沙梁睡着
你的寂寞便变成
无边永远的寂靜了
晒晒黄沙梁的太阳
一个人
在黄沙梁出生长大
种几十年地
最后老死埋在沙梁上
这是很平常的
也没什么不好
一个人
即使离开黄沙梁
在外面享够了福
老了他也想回来
傍晚时靠着土墙
卷一根莫合烟
晒晒黄沙梁的太阳
一个人
要是真的离开了黄沙梁
可能想法就会不一样
隔世情语
多少年后我自己就是一座村庄了
几十栋空房子为你
腾空的几十年岁月耸立荒野
一生中最富有的那些年
最穷困的那些年都过去了
流水返回高处风雨停歇
生命晚期的我
住在暮色很深的村西头
一个孤独的守望者
你的到来使我
寂静一生中尘土又起
仿佛一个巨大商队
正经过我将荒弃的一世
年轻时我梦想
在你柔美一生中
种满麦子我一个人的麦地
无边无际一生中每一天
我都提镰走向你
多少年我拿起来又放下
多少大事就像一株草
最后把开花的愿望枯回根部
多少年后注定有一次无言相遇
荒野朝天月光铺地
久远的歌声响起青春回来
身体娇小的你靠在我空茫一生的
最后角落像一句隔世情语
多少年我珍藏的东西一一变质
多少年荒草淹没世路你去了哪里
我等来衰老的自己孤守家园
多少年岁月是一片
无法逾越的苍茫地域
离你很近时我会恍然觉出
我们各自在各自一生里
一生和一生之间相距百年千里
而在我多少年的梦中
你激情纷呈的岁月正向我涌卷而来
将我沧桑的一世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