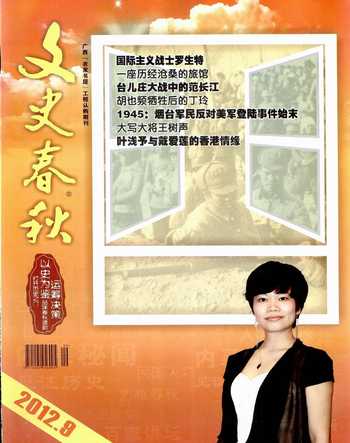胡也频牺牲后的丁玲
滕晓梅
携手文坛与“东方旅社事件”
1924年,丁玲在北平偶然结识了时任《民众文艺周刊》编辑的胡也频。然而,这一般性的相识却成了他们日后的情感之缘。
1926年夏,丁玲返回故乡湖南常德。这天,对丁玲心仪已久的胡也频,专程赴常德叩开了丁玲家的大门。与母亲同住一起的丁玲非常惊讶地看着这个“只见过两三次面的、萍水相逢、印象不深的人”。此后,胡也频便与丁玲走近了。丁玲了解到胡也频曾经在天津大沽海军预备学校有过一段军人生涯,后来海校停办,他走上了一条与军人职业反差很大的文学道路。丁玲后来回忆,那段时间“他一天到晚,似乎充满了幸福的感觉,无所要求,心满意足,像占有整个世界一样那么快乐”。不久,丁、胡二人结伴前往北平,度过了一段犹如“漂泊者”般的自由文人生活。这时的丁玲因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莎菲女士的日记》而蜚声文坛。
当时,中国文坛中心已由北平南移上海,“五四”时期的学界耆宿和文坛骁将虽然仍有一部分蛰居文化古都北平,但似乎已风韵不再。丁玲、胡也频不能忍受北平的沉闷,希望寻求一片新的天地。后来,在教丁玲日语的共产党员冯雪峰的影响下,他们于1928年春天又携手前往上海。经沈从文推荐,胡也频在“现代评论派”彭学沛任主编的《中央日报》负责编副刊。副刊名为《红与黑》,撰稿人有叶圣陶、沈从文、戴望舒等,丁玲亦忝列其中。
有了固定的编辑费和稿费,丁玲与胡也频的生活也相对稳定。但仅过3个月,这样的生活即有了变数。用丁玲的话说,“逐渐懂得要从政治上看问题,处理问题,这个副刊是不应连续编下去的。这样,也频便辞掉了这待遇优厚的工作”。之后,丁玲便与胡也频、沈从文一起办了红黑出版处与《红黑》月刊。据丁玲介绍“红黑出版处维持半年多,出版过六七期月刊、七八本书。沈从文和我都做了一些工作,但所有事务主要是也频一个人承担”。红黑出版处后来因经营状况不佳倒闭,丁玲、胡也频在经济上承受了很大压力。为了还债和谋生,胡也频经人介绍只身前往山东济南省立高中教书。一天,丁玲抵济南看望胡也频。这次见面,丁玲后来曾如此回忆:“……等我到济南去时,也频完全变了一个人。我简直不了解为什么他被那么多的同学拥戴着。天一亮,他的房子里就有人等着他起床,到深夜还有人不让他睡觉。他是济南高中学校里最激烈的人物,他成天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唯物史观、宣传鲁迅与雪峰翻译的那些文艺理论,宣传普罗文学。我看见那样年轻的他,被群众所包围、所信仰,而他却是那样的稳重、自信、坚定,侃侃而谈。”
由此不难读出丁玲对胡也频的欣赏和为之骄傲的情愫。但在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视线中,胡也频的文学活动已演变成了政治活动。胡也频及同事楚图南等因此遭到通缉,被迫返回上海。
当时丁玲虽然在文坛上已很知名,但她对人生仍有虚无主义倾向,用她自己的话说:“那个时候,也频也好,我也好,我们仍感觉到苦闷。希望革命,可是我们还有踌躇,总以为自己自由地写作比跑到一个集体里面去更好一些。我们并没有想要参加什么。回到上海,我们只是换了一个地方,仍然寂寞地在写文章。”
1930年初春的一天,“一个不认识的客人来叩我的门了。客人是一个个子不高,有点老成,又常常露出一些机智的一个很容易亲近的年轻人。这个人就是潘汉年同志”。这是丁玲所回忆与潘汉年第一次见面的情况。这时的潘汉年已是中共中央文委书记。正是这次见面,潘汉年向丁玲、胡也频介绍了成立不久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及发起人鲁迅、冯雪峰、柔石、夏衍、蒋光慈、钱杏邨等情况,并在征得他们同意后正式介绍丁玲、胡也频加入了“左联”。之后丁玲曾以《决定一生的谈话》为题对此作了回忆。不久,胡也频被选为“左联”执委并负责工农通讯委员会。他对新的工作充满着热情。丁玲称“也频就是这样一个人,当他了解了革命真理的时候,他是不会踌躇退缩的。因为他不是一个私心很重的人,动辄要权衡个人得失。他日常不爱多说话,不善诙谐,不会讽刺,他讨厌用玩世不恭来表现自己的聪明。但他却是扎实的、坚强的、稳重可靠的。”原创造社成员郑伯奇对胡也频亦有较深印象。他说:“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是在‘左联的一次会议上。听人说他曾上过海军学校,但却没有一点点赳赳武夫的气象,他看上去年纪很轻,像一个英俊的大学生。他满腔热情地叙说自己的经历。他爽直、虚心、精干、英迈,给人留下非常良好的印象。”
1930年11月,胡也频与柔石、冯铿一起被“左联”推选为出席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代表。继之,他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控制了中央领导权,由此引起中共党内众多的反对和抵制。当时,为了应对四中全会后的政治局面,一些王明的反对派正酝酿召开一次会议,其组织者有何孟雄、林育南、李伟森、罗章龙等。会议地点即在东方旅社。李伟森时在中央宣传部工作,他专门通知了胡也频、柔石等人也参加会议。
东方旅社坐落在公共租界最繁忙地段汉口路666号,为4层欧式建筑。那里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会议在当天晚上举行。出乎意料的是,当时东方旅社已处于工部局和上海市警察局的联合监视之下。会议开始不久,早已埋伏于此的工部局巡捕和上海市警察局警察持枪冲进房间,胡也频及与会者全遭逮捕。突然搜查行动在天津路上的中山旅社和华德路小学同时进行。行动持续了一整夜,至凌晨共有36名共产党人被捕。这便是震惊一时的“东方旅社事件”。事后始知,整个事件系叛徒告密所致。
胡也频在狱中曾数次秘密托人带信给丁玲,称他的口供是随朋友去看朋友,并要丁玲转告组织,他决不会投降。他要丁玲设法多寄些稿纸给他,他在狱中仍要坚持写作。胡也频与柔石、冯铿等人的被捕,是“左联”所面临的最重要的突发性事件。当时负责“左联”工作的冯乃超、冯雪峰等人通过多种关系打探消息,设法营救。
丁玲也频繁奔走,甚至找到蔡元培、邵力子、陈立夫。但因这一事件影响较大,国民党当局视为重大案情,蒋介石亲自过问,故而营救工作非常困难,几乎难有进展。1931年2月7日,胡也频与其他22位“东方旅社事件”中被捕的共产党人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杀害。胡也频身中3枪,时年28岁。
放弃前往苏区与主编《北斗》杂志
胡也频的被捕与牺牲,对丁玲来说是“经历了一番天坍地陷般的沉重打击”。她一下子变得非常消沉与落寞。之后她自己曾如此坦露:“在双龙路附近的一家三层楼的正房里,只剩我一个人,孤独地冥想着流逝了的过去,茫茫地望着天边的未来。天是灰沉沉的,四周是棺木一般的墙壁,世界怎么这样寂静,只有自己叹息的回声振颤着我的脆弱的灵魂……”“我坐着,痴痴的;躺着,闷闷的;在马路上走着,心象被狂风卷起的落叶又被抛下。我写过一篇小说《从夜晚到天亮》,那是我自己这段生活的写照。”
为了调整心情,丁玲在沈从文的陪同下返回常德娘家小住。胡也频的牺牲,丁玲一直瞒着她的母亲,但她又不时地要面对母亲的询问,以致难以掩饰心中之痛。她怕在家住久了会让母亲生疑,于是又匆匆返回上海。
在一个华灯初上的晚上,潘汉年与“左联”负责人冯雪峰来到丁玲的住处看望她。丁玲对他们说:“怎么能离开这旧的一切,闯进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与旧的全无瓜葛的新天地。我需要做新的事,需要忙碌,需要同过去一切有牵连的事一刀两断。”
潘汉年说:“那太容易了,明天你就跟我走。”
丁玲坦言直说:“我想到江西区,到苏区去,到也频原打算去的地方。”她特别强调,她是搞创作的,只有到苏区才能体验到火热的生活,才能写出革命的作品。
潘汉年、冯雪峰都很理解丁玲的要求,他们认为换一个环境可能对丁玲会更好,于是答应一定设法将她送到江西苏区。那天晚上送走他们后,丁玲充满希望地等待着消息。
但丁玲的愿望却未能实现。
一天,潘汉年代表组织找丁玲谈话。他说,党中央宣传部对丁玲的去留专门进行了研究,要求她继续留在上海,有个重要的任务交给她。
丁玲对不能去苏区感到非常遗憾,显得有些情绪化。在潘汉年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劝说下,丁玲最终有所触动,询问有什么工作要她去做。
潘汉年说,“左联”近期将出版一份杂志作为机关刊物。以往“左联”的刊物,如《萌芽》、《拓荒者》、《文化斗争》、《巴尔底山》等均遭到当局查封,仅有的《前哨》已改为《文学导报》,因刊物内容的定位,只能秘密刊发。新刊物已定名叫《北斗》,组织决定由丁玲来主编。
经过认真考虑,丁玲终于放弃到苏区的打算,服从组织的安排,开始主编《北斗》。“左联”同时又派姚蓬子、沈起予协助她做编务。因此,丁玲、姚蓬子、沈起予当时被称为《北斗》的“三驾马车”。为了给创刊号配插图,丁玲曾专门到鲁迅寓所选画。鲁迅推荐了一幅凯绥·珂勒惠支的木刻画《牺牲》,此画后刊登在《北斗》创刊号上。《北斗》于1931年9月20日出版面世,封面为淡黄色基调,衬有一幅天体图,北极星清晰可见,并有“北斗”两个醒目大字。后来丁玲曾说:“《北斗》一开始的确比较‘灰色,写文章的包括有谢冰心、陈衡哲、凌叔华、沈从文等。但是出两三期后,也就慢慢地‘红起来了,国民党也注意了。”当时瞿秋白、鲁迅都为《北斗》写文章。值得一提的是瞿秋白的杂文就是从《北斗》开始的,而艾青的诗歌处女作也是在《北斗》发表的。
这时候的丁玲除了主编《北斗》外,还经常到学校讲演,以唤醒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同时,她还参加“左联”组织的游行集会以及上街张贴标语等活动。丁玲穿着皮大衣、高跟鞋,打扮成贵妇人,为贴标语的同志放哨掩护。经过大时代的风雨洗礼,丁玲的思想产生了飞跃,也从之前的消沉情绪中振奋了起来。她主动提出申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3月的一天,丁玲的入党仪式在南京路大三元饭店秘密举行。后来丁玲回忆说:“瞿秋白代表中宣部来主持,还有文委负责人潘梓年。和我同时宣誓的有田汉、叶以群、刘风斯等。我在宣誓时讲:‘我只是一个同路人的作家是不满足的,我要当一颗革命的螺丝钉。那时‘左联不设党支部,盟员也不能参加街道支部,因此我一入党就是‘左联党团成员。1932年下半年,钱杏邨不当党团书记了,‘左联的党团书记就由我来担任。”
《北斗》终于因为变成了“红色”而在出版8期后,于1932年4月被国民党查封了。这时的丁玲既是左翼著名女作家,又是“左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她的名字在社会上已有很大影响,自然目标也比较大。
扑朔迷离的“绑架案”与冯雪峰的秘密安排
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法租界寓所中突然被绑架,失踪,生死不明。一时间舆论哗然,上海滩被搅得沸沸扬扬。各种传说、猜测甚至演义纷纷出笼,致使这一事件更云遮雾障。后来丁玲自己写有《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长文,详细介绍了这一事件的经过,匡正了很多是是非非的流传。据此,我们可以相对清晰地了解这一事件的轮廓。
自胡也频牺牲后,丁玲在生活中一直显得较为寂寞。这时,一个人进入了她的视线。他就是冯达,左翼社会科学联盟盟员、年轻的共产党员。不久,他们就住到了一起。之后,冯达调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真话报》工作。出事当天,冯达前去看望《真话报》的两个通讯员,而丁玲又要参加正风文学院一个文艺小组的会议。他们相约,如果12点以前一人不回,另一人必须立刻离开,并且设法通知组织和有关同志。
11点半时,丁玲到家,但冯达却未回来。丁玲预感到可能出事了,她准备等到12点,如冯达不归,她就离开。不料这时《真话报》总编辑潘梓年跨门而入。后来丁玲回忆说:
“……我把情况告诉了他。他这个人向来是从从容容、不慌不忙的,他拿起桌上的一份《社会新闻》,坐在对着门放置的一个长沙发上。我坐在床头急于要按规定及时离开,但看见潘梓年那样稳定、沉着,我有点不好意思再催。不一会,突然听到楼梯上响着杂乱的步履声,我立刻意识到:不好了。门‘砰地一声被推开了,3个陌生人同时挤了进来。我明白了,潘梓年也明白了。我们都静静地不说话。”
“过了五六分钟又进来了3个人……我只注意一个人,那就是冯达。他一看见我和潘梓年,猛地一惊,然后就低下头,好像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潘梓年。他木然地、无神地往床头一坐,我立刻就站起来走到立柜边去了。我瞪着他,他呆若木鸡,我心里想:难道是他出卖了我们?”
这3个陌生人都是国民党特务,为首的叫马绍武,一进门他就命令将丁玲和潘梓年抓起来。
丁玲带着疑惑与潘梓年一道被特务押上车。因为丁玲住的地方在法租界,国民党特务还不敢明目张胆地捕人。他们采取绑架的办法,将人塞进汽车便疾驶而去。第二天,丁玲、潘梓年以及冯达便被押解南京软禁起来。
之后,冯达出卖丁玲则成了“丁玲绑架案”起因的惟一解释。丁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鄙视冯达,痛恨冯达,甚至用最刻薄的语言咒骂他。但“冯达只是赌咒、自己骂自己,他承认犯了罪,连累了别人,是一个不可饶恕的人,但他死不承认自首。他分辩自己没有一点点要自首的念头。他恨自己太愚蠢,轻信了敌人的谎言。”
后来,丁玲终于相信了冯达的话,并了解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那天冯达去看望两个记者的时候,被守候的特务扭住了。在盘问过程中,他竭力分辩,也无法脱身。特务便对冯达说:“你既是一个普通人,就应该有妻室、有家,只要到你家看看,证明你不是共产党,与共产党也没有关系,就放你。”冯达此前已与丁玲约好,如12点不回来,丁玲就离开。因此在过了12点之后,冯达认为丁玲肯定已离家避走,而且认为家里也没有什么东西,不会出事,因此就说出了住址。他没想到丁玲这时还在家里,而且潘梓年也在现场。
丁玲在南京历经了3年多的囚禁生活。这3年,对她来说真可谓一言难尽。特务的威逼利诱,叛徒的轮番游说,卑鄙的谣言蜂起,同志的误会冷语,身心的严重摧残……成为她这3年生活的全部内容。她孤独难捱,有口难言,甚至产生绝望的情绪。当时曾面对面直接劝降丁玲的即有国民党调查科长徐恩曾、叛徒顾顺章以及国民党文化官员张道藩等人。但丁玲始终未为所动。她知道,这个头一旦低下来,整个人生则将随之毁灭。
国民党对丁玲的策略是不杀、不放。她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环境中,维持着基本的生存状态,但却失去了自由。
为了营救丁玲,“左联”在《中国论坛》上发表《为丁、潘被捕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宣言》。《宣言》称“丁玲是中国特殊的女作家,是新革命文艺最优美的代表者”。上海文化界随即亦发表《文化界为营救丁、潘宣言》,作为呼应。此后,蔡元培、胡愈之、洪深、邹韬奋、陈望道、柳亚子等36位文化界名流联名致电南京政府,“敢为呼吁,请查明释放或移交法庭办理”。为达此目的,文化界还专门成立了仍由蔡元培领衔的“丁潘营救会”。由于国民党当局矢口否认逮捕丁玲,营救工作因此十分艰难。
丁玲一直过着与世隔绝的软禁生活,外界很难知道她的真实情况。不久,即传出丁玲被迫害致死的消息。鲁迅闻此,于悲忿中写下了一首《悼丁玲》:
“如磐夜气压重楼,
剪柳春风导九秋。
瑶瑟凝尘清怨绝,
可怜无女耀高丘。”
鲁迅将这首诗交给曹聚仁,在其主编的《涛声》上发表。茅盾在听到丁玲被害的传闻后,特地赶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女作家丁玲》。这是茅盾继《徐志摩》之后的又一篇作家论。其中称:“在‘左联的干部中,她是一个重要的而且最有希望的作家。她的被绑(或已经被害),不用说是中国‘左翼文坛一个严重的损失”,“全中国的革命青年一定知道对于白色恐怖有力的回答就是踏着被害者的血迹向前!丁玲女士自己就是这样反抗白色恐怖的斗争者”。这篇文章当时公开发表在伊罗生主编的《中国论坛》上。
所幸的是丁玲并未死,国民党对她采取的是“不杀、不审、不放”的所谓“绵中裹铁”的卑鄙手段。而持续3年的这种生活究竟给丁玲带来了什么?丁玲后来回忆说:“刚到南京的时候,好几个人看守我呀!我真是苦闷。我以为我会死。院子里有好些小石头,石头缝之间长着青苔。我就想,有一天,我会葬在那里。”
直到1936年,国民党特务对丁玲的监视、控制有所放松。于是丁玲便酝酿逃离南京的计划。这时从陕北返回上海领导进步文化工作的冯雪峰特地安排张天翼赴南京与丁玲接触,并相机帮助丁玲逃离南京。正是在张天翼的具体策划下,丁玲终于在这年6月逃离了遭软禁3年之久的南京,秘密潜回上海。而在上海的胡风已事先为她租好了一处公寓。
3天后,冯雪峰前来看望她,安慰她,同时鼓励她要坚强起来面对未来。
丁玲向冯雪峰提出要求前往陕北苏区的愿望。冯雪峰随即电告中共中央,在得到获准前往的电令后,他立刻通知丁玲做好准备。
等待的日子里,丁玲既兴奋又焦急。
这天,冯雪峰又来看丁玲,并带来了宋庆龄托他转交的350元钱。冯雪峰对丁玲说:“孙夫人听说你出来了,要去西北,很关心你。这笔钱是她托我专门送给你的。”
丁玲十分意外,同时又非常感动。后来她说:“3年多来,敌人对我制造了许多无耻下流的谣言,用软刀子杀我。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受了谣言的影响,也曾用怀疑的眼光审视我。这时孙夫人赠我的350元所代表的对我政治上的信任,却比泰山还重,是千万两黄金难买的无价之宝,怎能不引起我由衷的感激之情。”
1936年9月,在冯雪峰的悄然安排下,丁玲离开上海,踏上了前往陕北的征程。“左联”特意派了聂绀弩改名换姓陪她同行。经2个月的辗转跋涉,离开牢笼的丁玲终于抵达当时陕北苏区首府保安,翱翔于一个崭新的天地……
——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