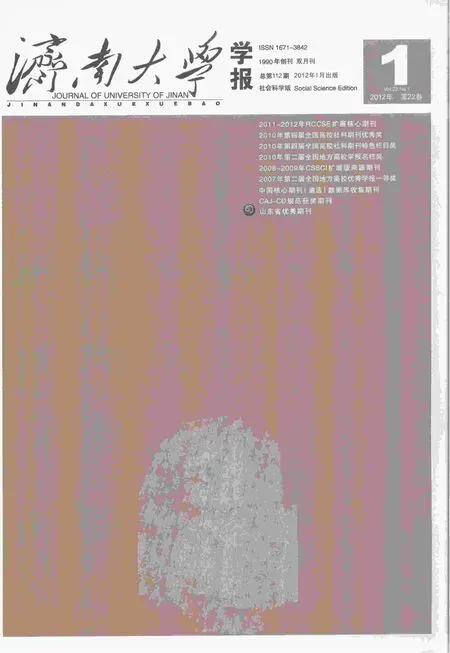晚明狂草到清代碑学书法之审美变迁研究
兰浩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哲学系,福建厦门 361005)
晚明狂草到清代碑学书法之审美变迁研究
兰浩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哲学系,福建厦门 361005)
晚明到清末社会剧烈变动,书法风格变迁明显:从晚明行草的狂放到清前期赵董的柔媚、馆阁体的板滞僵化,到清朝中后期碑学复古。晚明狂草书风形成主要受思想解放思潮影响,清代赵董书风和馆阁体与政治专制影响关系密切,清代中后期碑学大兴是帖学式微的产物。晚明到清末书法审美的变迁原因有不少相同之处,也有一些差异。晚明到清末书法风格变迁植根于社会与文化发展变化,与时代思想、书家个性、社会变动等相契合。
晚明狂草;赵董书风;馆阁体;清代碑学
一、晚明思想解放与狂草书风
明代中晚期,随着市民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思想解放高潮。在哲学思想方面,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心学、高举良知说,发展和替代程朱理学。随后李贽在此基础上发扬了离经叛道的怀疑和否定精神,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提出“童心”说,对文艺思想的发展影响深远。徐渭就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出现的书法大家,他认为书法及一切艺术是为了寄兴,表达个人的主体意识要有“真我面貌”,“时时露己笔意,始称高手”[1](P25)。他的书法以行草见长,笔墨纵横散乱,章法变化莫测,满纸烟云,一派狂放不拘的气魄。时人称为“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堪比西方艺术史上的梵高。徐渭书法给明末清初书法家以重大启示,书法要冲出传统的牢笼,获取一颗自由的心灵。之后出现了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等一大批风格奇异的书法大家。他们以狂放的行草书成就最为突出,风格诡异多元,或恣肆纵横,或高古遒媚,或奇崛陡峭,或热烈奔放,相对明初和中期书风是极大的创新。
明代中期书法以吴门书风为代表,代表性书法家有祝允明、文徵明、陈淳和王宠等。这一时期,书法逐渐摆脱了台阁体的统治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书法活动中心也由皇宫官僚集中的北京转向商业经济繁荣的江浙。吴门书派产生于繁荣和平的苏州,是当时政治上相对自由、经济活跃、文化发展的结果。吴门书风扫去明初台阁体的庸俗板滞,以一种典型的文人书卷气,即深厚的文化修养与疏放的艺术个性适应当时市民趣味的审美需求。从代表性吴门四家祝允明、文徵明、陈淳和王宠来看,书风基本上不脱离雅致、疏放、散逸。比如文徵明行草在总体风格上以其清雅、纯正、醇和的品格,表现了文人“士气”与隐逸之风,以其适度的把握,使这种高雅的书法趣味转为平易近人,适应了当时市民审美情趣的需要。王宠书法也是以清新、旷达表达特有的雅逸,不染尘俗,以韵致而得名。在明际书风竞尚柔媚的风气中,试图以一种刚健的风骨和雄肆的气概力矫时弊是当时一大批士大夫的共识。书风变革从徐渭到张瑞图、王铎等,堪称书法史上重大的变革期。从书法形式到审美风格都有重大的突破,八尺到丈二的作品在这些书法家手中如云烟变幻、飞瀑倾泻,气势逼人,史无前例。如徐渭狂草,面孔之奇异,用笔大胆奔放,绝去傍依,结体的变幻莫测,章法满纸烟云,点划狼藉不堪,表达内心的狂躁、激热、愤懑等情感,充满天才的想象和架构。之后的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等群星灿烂,将晚明狂放书风尽情演绎。他们书风虽各有千秋,但共同处为草书成就突出,情感表达极为狂放。张瑞图书法以偏侧之锋大翻大折,横向取势,用笔以方峻峭利取胜,章法行距疏朗字距致密,迥异前人,独创性强,气势滔滔不绝,体现了对传统书风的反叛,表达其激热的情怀;黄道周书风取法锺、王、索靖,崇尚遒媚加以浑深,绝去明中叶书风的纤糜之习;倪元璐书法则以浑深加以遒媚,用笔苍劲浑厚,飞扬恣肆中内含骨力,结体奇险多变,展示其倔强狂躁性格;王铎书法是晚明清初书法的集大成者,在用笔、章法、意境上均有极突出的发展创造,他独宗羲、献,推崇古法,广泛吸取前贤,尤重发展米芾侧势,章法跌宕多姿,轴线摆动激烈,在用笔、形式、气韵上极大发展,将学习传统法度与任情恣性的自由高度结合,是晚明狂放行草书法的杰出代表;傅山的书法也是以狂放的草书为最高成就,秉承晚明以来摆脱技法规制束缚、注重个性宣泄的特征,书法崇尚丑拙,反对甜媚,其草书恣意挥洒,气势澎湃,从点画到章法都不受任何成法制约,大笔浓墨,纵横牵绕,表达其癫狂不羁的人格特征。
书风发展到晚明,狂放书风何以凸显?明末社会的复杂多变是狂放书风形成的直接原因:思想上受明末王阳明心学、李贽、禅宗和泰州学派等影响,经济上因晚明商业经济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形成,个性解放思想逐渐兴起,政治上则与明末政治逐渐腐败,国力衰退引起士人心理阵痛表现,以及清初异族入主中原,山河变色带来的文人士子的心灵沉痛等相关。徐渭所处时代,新儒学经历一个以王权为中心向以民间教化为中心的位移过程。王学风靡的高峰时期,心学前辈王畿、季本和唐顺之对他影响最大;黄道周则是与当时的刘宗周齐名的大儒,在思想上倾向于用朱学纠正王学后偏离道德主体和空疏放纵的流弊,而与之关系密切的倪元璐和王铎都极为推崇黄道周的人格风范。满族入主中原,明朝灭亡带来的士人的心理剧变在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等书家作品中均有明显表现。黄道周、倪元璐在明亡后以身殉国即是儒家思想的舍身为君;王铎在明亡后的出仕清廷,把他自己推上了封建政治的审判台,“忠臣不事二主”是封建政治伦理纲常,“舍生取义”是孔孟教义中的要旨,王铎背叛了这一规矩信条,在他本来悲剧的命运上又蒙上浓重的暗影,相对黄道周、倪元璐的殉国,王铎的苟活为时人所鄙,他借书法充分表达身背“贰臣”之大耻引起的心理痛楚,坎坷的身世、命运又促成了其书法技艺的高超成就;傅山是明清鼎革的遗民,政治上坚决不与清合作,性格孤傲耿介,书风上标举“丑”“拙”“直率”,鄙薄奴书,媚态,俗态,这种书风审美取向,与明朝灭亡,士人沉痛和反思的结果关联紧密,同时也与传统儒家刚健有为之气的激发等分不开。“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2](P170),徐渭到傅山等狂草书风形成与各自不同的个性、身世、时代密切相关。明末狂草书风的多姿多彩,正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天崩地裂。
二、清代前中期赵董书风的糜弱与馆阁体的板滞
清代前中期,明代书风不同程度地得以继承和延续。康熙喜欢董其昌书法,致使董书盛极一时;清中期乾隆皇帝对赵孟頫书法风格的赞赏和提倡,以及符合科举考试要求所形成的“馆阁体”书风,成为清代前期主流书法审美风尚;属于晚明变革书法潮流的王铎、傅山等以不同身份进入清代,并在文化领域发挥一定作用,作为晚明书坛的活跃人物,他们各自的书法风格也在继续发展、完善。然而这种带有自由和叛逆色彩的狂放书风,与清初政权迫在眉睫的稳定统治及恢复秩序的政治需要显然是很不和谐的,随着清政权的逐步稳固及其对思想文化控制的日益严厉,到康熙之后,这种生机勃勃、富有冲击力的风格很快就消失了。在清代满族入主中原的铁蹄下,书法艺术也受到极大影响。清前期赵董书风兴盛以及晚明狂放书风的消失,不难找到审美心理、社会气候根源:董书和赵书,取法风格稍有区别,董书受禅宗影响,平淡雅逸是其主要风格;赵书取法魏晋,平和优雅,古妙韵深。二者具有媚妍清丽等审美共性,符合入主中原、需求政治稳定、粉饰太平的审美需要。赵董书风的广受推崇,也迎合了当时的社会气候和皇家身份,成为政治利用和助成教化的工具。
康熙喜爱书法,曾以擅长书法、专学董其昌的沈荃为师,康熙一朝,大臣中擅长书法者,尤其是模仿董其昌书法者,多受到皇帝宠爱和重用。因此清朝前期书风基本上笼罩在董的影响下。学董书在科举中被录取的机会较大,在仕途上的际遇也比他人更为顺畅,书法成为赤裸裸的应试工具。清代前期在书坛上享有盛名者基本上都是来自南方江浙一带董书的“追星族”。康熙身边的众多大臣如高士奇、査昇、陈邦彦、姜宸英等书法风格大致均不落秀美精致、飘逸秀雅一路。康熙时期书坛几乎举世学董,造成书风的糜弱和单一,时人多有抨击:
华亭书法轻薄,摹仿顿失古意。[3](P62)
自思白以至于今,又成一种董家恶习。一巨子出,千临百摹,遂成宿习,唯豪杰之士,乃能脱尽耳。
学者不求其骨格所在,但袭其形貌,所以愈秀愈俗。[4](P64)
这样的批评是中肯的,在当时清代高压政治环境下,豪杰之士的书法必如王铎、傅山等人的命运一样遭受冷落。康熙一朝崇董,到清代中期乾隆时期发生一些变化,弘历开始推崇赵孟頫书法,身边也形成了一个书家群体,如张照、刘墉、梁同书、王文治、翁方纲、铁保等。弘历书法点画圆润,结体婉转流畅,继承赵书。在乾隆影响下香光告退,赵孟頫书法又大为世贵。从董书到赵书,书法风格基本上还是沿柔媚平和的特点发展。此期虽然一些书家意识到赵书的不足,兼学颜真卿,米芾,李邕,使得书风在赵书上有一些变化。如张照在学习颜真卿和米芾的书法方面花了很大功夫,基本上摆脱了董其昌的风格,着力汲取了颜书厚重和米芾的跳宕纵肆,遂与董书拉开一些距离。刘墉、翁方纲学习颜书,梁献学习李邕,但这毕竟是在清代帖学后期走入僵化后的有限改变,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帖学衰疲大局。书学界历来对康熙、乾隆青睐赵孟頫、董其昌书法多有微词,细心推想,二帝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吧,中国传统文化严于“华夷之辨”,有浓厚的汉族本位主义情结,满清入关,强烈感受到这一传统思想的排斥和抵抗,清帝选择雍容文弱的赵、董体现为一种策略,是否与其统治中怀柔之术相符合?
乾嘉以后帖学书法逐渐流于单调和僵化,特别是科举考试与官场中使用的“馆阁体”书风的影响,使学习法帖越来越被方整、光洁、均匀的教条所束缚。清代馆阁体书法承袭宋代院体、明代台阁体,作为读书人干禄求仕的工具本领。馆阁体书法的普及程度、对书法艺术的影响明显超过其他朝代。顺应皇帝爱好,馆阁体书法往往左右一个时期的书法取向。如顺治帝喜欢欧阳询楷书,文人士子则习欧成风;康熙玄烨对董书推崇,学习董书成为干禄求仕的捷径;道光年间,“欧底赵面”之字风靡一时;乾嘉文人士子大都习唐碑欧、颜或柳,与时风赵体相和,书风饱满圆润、匀称流畅则为时重,形成流行的“颜体赵面”或“欧底赵面”,风气所致,字体一概“乌,方,光”,应规入矩,了无生趣,以致千人一面、万手雷同。在印刷技术不发达的清代,馆阁体固然有其实用价值,但过分的整齐单调雷同,则与作为艺术形式的书风背道而驰。科举应试以工整的书风决定考生命运压制了艺术的创造力。
无论赵董还是欧、颜馆阁体,清代中前期书风主要受政治影响而形成柔媚、板滞的特征。这种书风审美倾向并非基于人性和艺术的客观规律,而是在政治控制下某种畸形、变质的艺术样态。清代满人部族政权的高压下,书风的审美倾向走向柔弱、平和、僵化乏创造、刚健之气,馆阁体与清代效法赵、董貌异神合:帖学流于糜弱,馆阁失于板滞,顺应了帝王的指挥棒,书风唯唯诺诺、谨小慎微。
三、清代中后期复古碑学兴起
清代中前期以赵董为代表的帖学书风日益走向衰疲,到后期开始改变,碑学兴起成为突出的书法现象。碑学书法创作实践主要包括篆隶复古和推崇北魏楷书以及推碑入行草的尝试和实践。从审美取法上,碑学最显著的价值取向是“复古”,即学比二王帖学更古老的秦篆、汉魏书法,乃至金文小篆等碑版刻石,汲取碑版的古拙雄奇、新理异态,从而扭转赵董柔媚和馆阁体僵化时弊、振奋颓废书风。从阮元著述《南帖北碑论》和《南北书派论》,到包世臣《艺舟双楫》,最后康有为《广艺舟双楫》集其大成,碑学从理论上得以发展完备。
清代大兴文字狱,文人士子转入实学考据,金石学得以大盛。出土大量古代金石文字不仅具备学术考古价值,其书法的古朴、率意等风格为书法界所重,形成篆隶复古和学习北魏书风的潮流。越来越多的书法家以金石文字为学书的取法来源,向帖学发起挑战。篆隶古体在乾隆嘉庆年间得以兴盛,邓石如、伊秉绶以篆隶新奇面目赢得大名。好古之风一时成为风尚,书法审美走向新的变化。乾嘉以来,经过阮元的号召提倡和包世臣具体入微的探索推动,碑学理论深入人心;实践上有邓石如、何绍基、张裕钊、赵之谦等人的施展,书坛开始利用碑石临摹寻找和强化个人风格的尝试。碑学运动在清代后期蓬勃发展,审美风尚与前期帖学拉开极大距离。阮元著作《南北书派论》、《南帖北碑论》,对北朝书法做了高度评价和鼓吹。阮元对宋朝以来书坛尊帖成风、竞逐姿媚、笔致纤弱十分不满,为此他详细考证南北书派分流历史,明确表示鄙南崇北的思想倾向,对南派以“二王”为代表的帖学书法表示轻视。阮元指出北派书法传承有绪,“古人遗法犹多存者”。而南派为变体,即使是《瘗鹤铭》这样的石刻,与北朝相比也是“妍态多而古法少”。在阮元看来,元、明以来书家皆为《淳化阁帖》所蔽,见识陋狭。清代各种汇帖辗转翻摹,笔法全失,严重影响取法。而对于北派书法,阮元给予由衷的赞美和较高评价:
北朝族望质朴……然其笔法劲正遒秀,往往画石出锋,犹如汉隶。[4](P630)
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4](P632)
要扭转帖学糜弱和雷同之风,只有重振北碑古法,他说:
所望颖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守欧、褚之旧规,寻魏、齐之坠业,庶几汉、魏古法不为俗书所掩,不亦煒欤。[4](P634-635)
可以看出,推崇北派书法即是推崇汉、魏“古法”,摈弃柔媚俗书。审美趣味的直接取向就是重视北碑,扭转帖学积弊。阮元的书法美学观点为稍后的包世臣所发展。包世臣将碑学主张发扬、完善,进一步分析了北碑的风格渊源,总结出北碑的一些特点,如“极意波发,力求跌宕”,“茂密雄强”,“画势甚长,雍容宽绰”,“出之自在,故多变态”等等。北碑的美学风格如雄奇、恣肆、古拙生涩被深度阐发。包世臣还从笔法角度肯定北碑的价值,对北朝书法大加赞扬,他说:
北朝人书,落笔峻而结体庄和,行墨涩而取势排宕。万毫齐力故能峻;五指齐力故能涩。分隶相通之故,原不关乎迹象,长史之观于担夫争道,东坡之喻以上水撑船,皆悟到此间也。[4](P653)
包世臣还提出一系列用笔方法“五指齐力”“笔毫平铺”、“用逆势用曲”、“中实气满”等原则,在创作技法和审美标准上突破和挑战帖学法则。从北碑风格和用笔法则的阐扬,包世臣的书学审美标准与传统帖学拉开距离,影响了一大批碑学书法家的创作,碑学理论也进一步丰满。后期康有为著作《广艺舟双楫》,更是将碑学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康有为推崇北碑,贬抑帖学和唐碑,崇尚变,主张复古。他认为上古、秦汉、魏晋书法才是完美的,唐以后则每况愈下。康有为大力推崇北碑,认为:
古今之中,唯南碑与魏为可宗,可宗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
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异态。[5](P135-136)
北碑书法在康有为那里,可谓十全十美。从这里看出他所推崇北碑的美学风格:雄强、浑朴、古健、率意等,即是以阳刚古拙之美对抗帖学的柔弱。在对碑的品评中,《爨龙颜碑》、《灵庙碑》、《石门铭》被列为最高等级的“神品”,是以能否体现“体庄茂而宕以逸气,力沉着而出以涩笔”的壮美特质作为标准的。康有为写作此书尊魏卑唐,舍弃年代较近的唐人法帖摹本,效法久远的魏碑、隋碑。倡导碑学、推崇壮美,不是要回归古代,真正目的是借古开新。梁启超归纳清代的文化思潮即是以“复古”为旨趣:“综观二百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6](P7)康有为的复古当有两层含义,一,欲拯救今日之弊,必须返归古代求药方。其二,古为今天所用,汲取传统以改变当下未来。这不仅是光大书道,也是拯救颓危时局之出路。康有为写作此书之际,正是上书变法受阻,他在寻找拯救中国道路之时遇到阻扰因而内心郁结。推崇壮美的北碑书风,既是扭转帖学弊病,也即痛恨清政府腐败懦弱以期变法图强的心理反映。含沙射影,用心良苦,借书法以言政治,这与他的托古改制、政治变法思想相契合。可见清代碑学大兴,其审美风格的追求,既有书法艺术发展内在的机理,同时也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
四、晚明到清末书法风格审美变迁之简要分析
书风审美总是植根于社会与文化之中,绝不是孤立的存在。晚明书风到清末书风变迁,既有书法艺术发展的自身规律,也植根于一定社会历史文化。晚明狂放书法是对中期台阁体和吴门书风平和典雅的矫正,而清代后期碑学针对赵董柔媚和僵化的馆阁体书风;晚明狂草书法形成与明末心学影响、个性解放思潮、政治腐败、社会衰退、满族入侵等密不可分,而清代碑学则与清政府落后、西方列强侵略、渴求变法图强等分不开,二者书风变革均处于社会激烈动荡之际;同为矫正时弊,康有为、沈曾植等选择北碑的古健雄肆,徐渭、张瑞图、王铎等则以狂放草书作为感情的抒发和寄托。可见社会和平时期,书风多为典雅平和,而社会变动之时,书风往往向纵肆、雄强或古拙等风格发展;清代碑学推崇古法,明代狂草黄道周、王铎、傅山也有遵循古法的大量书法理论和实践,“复古以开新”的文化理念,在社会动荡变革的年代往往成为有效方式和有力武器。
明代书风与清代书风变迁也有明显不同之处,比如吴门书风的平和艳丽典雅,与明代苏州一带的社会和平、经济繁荣的背景相称,而清代赵董书风的柔媚、馆阁体的僵化却受清代专制政治的左右和影响;晚明狂草书法群星灿烂,生机蓬勃,在中国书法史上影响较大,清代碑学虽然开创了新的取法对象,但理论建构并不成熟,例如康有为的碑学理论因为主观偏激倾向而受到不少批评。清代后期并没有产生像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等卓越、影响深远的书法大家。清代碑学需要学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探索。
艺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审美理想对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历代封建文人在书法艺术中畅情达性,抒发性灵,书法成为文人的“心象”。作为“有意味的形式”,书法艺术总是积淀着社会时代内容,承载社会意义。“艺术处于开放的文化关系之中。一部艺术作品,不论它如何自律,怎样拒绝或漠视社会现实环境,它总有其大量的文化意义,总深深植根于社会历史与文化之中”。[7](P22)明清书法艺术风格的不同,又反衬两个朝代政治、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一些差异。钱穆先生对比明清政治制度时,曾指出清朝是“部族政权”的私心,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清代比明代更独裁”,“若说考试制度是一种愚民政策,清代是当之无愧的”[8](P134,142)。李泽厚先生认为清代“从社会氛围、思想状貌、观念心理到文艺各个领域,都相当清楚地反射出这种倒退性的严重变易。与明代那种突破传统的解放潮流相反,清代盛极一时的是全面的复古主义、禁欲主义、伪古典主义”[9](P330)。二位学者一致指出清代相比明代的落后、保守、倒退性。结合明清书法艺术变迁的历史,他们的观点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印证:明代中期吴门书法的平和典雅,反映了当时商业市民经济的富足安和,而清代初期赵董书法的柔弱和馆阁体的奴性十足,则是严酷专制下的产物;从明末狂草书法,我们可以感受到士人内心世界的志气满怀、生机蓬勃和明末心学兴起、个性解放思潮的文化气象,而清代碑学“复古以求开新”,则是士人面临社会严重危机之际,渴求变法图强的社会心理隐射。晚明到清末书法艺术的发展规律与政治状况、历史文化有一定程度的深层契合。
[1]由智超.中国书法家全集·王铎[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
[4]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
[5]康有为.广艺舟双楫[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
[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7]丁亚平.艺术文化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8]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9]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J292.26
A
1671-3842(2012)01-0034-05
2011-10-21
兰浩(1973-),男,湖北黄冈人,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艺术美学。
责任编辑:陈东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