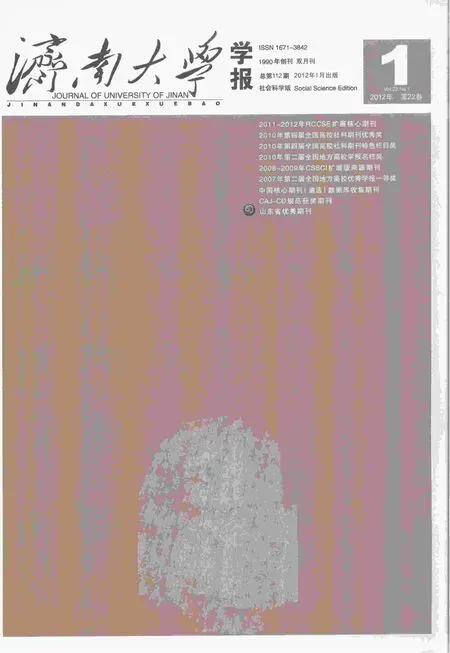论词学家刘扬忠——当代词学家系列研究之二
崔海正
(济南大学 文学院,山东济南 250022)
论词学家刘扬忠
——当代词学家系列研究之二
崔海正
(济南大学 文学院,山东济南 250022)
刘扬忠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著名词学家之一。其词学研究之路大体经历了起始——成熟——高峰——后高峰探索等几个阶段。其研究个性暂可归结为:(一)理论之倡扬与学术史之关注为其高扬的旗帜; (二)专攻而兼取;(三)研究与创作联姻;(四)“气”为统帅。
当代;词学家;刘扬忠
刘扬忠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亦即所谓新时期国内著名词学家之一。其为南方人士,然性偏豪爽,身材魁梧,时而诗酒慷慨,给人以“不似南人”之印象。他不但写有《稼轩词与酒》等妙文①见《文学评论》1992年第1期。,还推出《诗与酒》之大著②《诗与酒》,台北: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该著以酒为切入点,以此等“美禄”与古代诗家词客的历时性情缘为红线,相当精彩地表现出独特而斑斓的中国文人的心灵心态史。所以,刘氏并非一般所谓“酒狂”或“酒徒”,他对酒文化有着清醒的认知。不过,据笔者闻见,于意兴飞扬之际,其不免又常有“微醺”之态,或略失故常,或歌叹起舞,这反倒令人有“文士当如此”之美感。此且不论。鲁迅先生在《花边文学·北人与南人》一文中曾言:“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贵……南人北相者,不消说是机灵而又能厚重。昔人所谓‘贵’……在现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业了。”[1](P908)那么,刘扬忠如何兼顾南、北人情之两长,在词学研究这一“有益的事业”之路上不顾鞍马劳顿、渐行渐远呢?这正是下文将要探讨的议题。
一
刘氏已过耳顺之年,不说著作等身,亦可开列一个长长的书单了。截至目前,他已出版有关著作22种(含专著13种,合著5种,主编4种),发表论文40余篇,此外还有尚未编集梓行的各类文字如序跋和相当数量的诗词创作等。据已有成果看,他已经在词学领域将自己的事业“做大做强”了。
应该说明,《周邦彦传论》并非他的第一部著作,但其事业的“起始”却是对清真词的尝试。他于20世纪70年代末作为“文革”后首届研究生跻身吴门,时已过而立之年。虽早已对古代诗词有所爱好,但尚不知专业研究的真谛何在,以至当吴世昌先生征询其具体研究方向时,竟无言以对。《论周邦彦及其清真词》是在导师耳提面命、图书馆里馒头加开水的“急切”、硕士论文的“逼迫”之下确定选题并初战告捷的。[2](P408-410)因而,该文不仅有“为学位”的所谓“功利性”目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第一桶金”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作为一项事业,它似乎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制定出的一个宏伟蓝图的“必然的”第一步。但尽管如此,它在当时情势下却具有重要学术意义。本来,周邦彦是北宋末期具有领袖资格的大词人,其人品大节并无多少可訾议之处,但历来囿于某些传统说法,亦缺乏深细的综合研究,争议颇多。尤其建国之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受机械、片面甚至谬误的所谓“理论”之桎梏,更斥其为腐朽的“御用文人”,其词乃是“形式主义”的糟粕等等,给以全盘否定。而初出茅庐的刘扬忠,却对周氏为人为词进行了全面认真的检讨,反拨偏见,正其误读,“让他回到其应有的恰当位置”[3](P62)上。要知道,那是在浩劫甫过、官方正大倡“拨乱反正”,而学人还在四处张望、欲言又吞、犹抱琵琶的氛围之中,在学术艺苑春信始递、由一片荒凄到“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文化背景之下,难怪有关文章要被编辑们“柔性封杀”了,学位论文更不能全文发表或出版(部分内容后曾在《文学遗产》刊载),迟至十年后才加以修订并以今名面世,这或许使他失去了一个更早“成名”的机会。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起点较高的开端。下一步该如何走,他必须谨慎。刚刚完成学业,尽管留在社科院导师身边工作,以后毕竟要“自寻出路”。其实,他这时已对宋词研究的基本状况有了大概了解,又有了研讨清真词的初步经验,但他觉得还是先从“个案”入手为宜。而在宋代词家中,他最心仪稼轩。这不仅因其气质与稼轩为近,更因为并非有意作词人的辛稼轩的英雄情怀及其词作的高度艺术成就征服了他。于是,他决定搞一个稼轩词的译注本,扎扎实实地对这位词坛豪杰加深认识,以之为此后的事业打开通路,这便是他独立操作的首部著作、1983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推出的《稼轩词百首译析》。对于此著,刘扬忠很想“按自己的方式把稼轩词作为宋词中的一个特殊范本”介绍给读者。就像公认的那样,他很清楚古诗词今译“是一件吃力不讨好之事”,但考虑到辛词的具体情况和通俗读本的受众,他还是以“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办法”这样做了,虽“不能算是标准的翻译”,作为“读懂原作的辅助手段”的目的是达到了。实际上,只要我们浏览一下这些新诗形式的译词,不仅基本上都能扣合原意,而且也是蛮有诗味的;在选词上,也一反向来只“强调其慷慨豪放的一面”,又酌情“选了数量不少的婉约之作,还有意选了一些爱情词和农村词,力求让读者对这位古人获得近乎完整准确的印象”;再加上以尽可能浅显而又较为详细的注释和讲解,阐发出了“稼轩词中的精华”[4](《前言》P1-3),故使其成为20世纪80年代初颇受读者欢迎的一个极具特点的宋词选本。该著虽非所谓“理论性”的,但却成为进一步研讨稼轩及宋代词学的坚实铺垫与必要过渡。
但是,不应该忘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类似30年代而更加普遍和深入,外来学术观念与方法(主要是西方)潮水般涌入渐次开启的国门,几年间真所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泥沙俱下。包括词学界在内的整个古代文学领域,或许由于“包袱”过于沉重等多种原因,在面对这一挑战时显得尤为滞后。而不惑之年的刘扬忠,以其南人特有的机敏与冷静,一再呼吁容“故”纳“新”。对这位雄心勃勃、豪气颇浓的中年学者而言,一方面要在“弄潮”中把握准航向,不断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充实其知识结构;一方面要在宋词研究领地中权衡个人的位置,将事业再推上一个台阶。然而,宋词学苑“风景”眼花缭乱,进口“洋货色”应接不暇,究竟如何再试身手呢?终于,他还是选择了“亮点切入”,进一步解剖词坛上的另类人物辛稼轩(尽管是“邀约”撰稿)——此后证明这是一个极佳的契合点。已如前述,这不仅因其对稼轩无比崇敬,且于几年前就出版了《稼轩词百首译析》;同时也要注意到,他在思考稼轩词研究的“薄弱环节”及“如何对待新方法”时,也曾想到可探讨其词的“特殊美学价值”以及不妨运用“心理分析方法”的合理之处来窥视宋代词人的“创作心态”与“创作动机”的问题。[5](P91-153)似乎可以说,这种种“合力”孕育并催生了《辛弃疾词心探微》(以下简称《词心探微》)的问世。在这部著作中,他毅然抛弃了以往研究中机械反映论和单一社会学的模式化论证,把对稼轩词的审视角度转移到创作主体亦即“词心”上来,换句话说,即揭示稼轩在词中传达了“什么样的主体意识和特定情感”,以及他“为何”及“怎样”来传达这一切。正如王兆鹏教授在评论此著时所言,它光大传统的“心解”之法并借助心理学的理论来阐释“词人的心态和作品的构成”,标志着词学研究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作家个体研究的‘诗——史范式’向‘诗——心范式’的转换”,给学界以极大的“启发性和示范性”。[6]当然,这一成功的运作是方法的改辙,更是观念的革新。
然而,就在《词心探微》落笔之后,另一个早已酝酿于胸中的议题也常常浮现在眼前,这就是:既然志趣和职业已确定在宋词(及词学)研究,那就应该、也必须对宋词苑囿进行一番全面的勘察与“检阅”,这是研治稼轩的需要,也是未来事业的需要。更何况,此前已有对某些诗人词家的个案试笔和几年间对宋词研究资料及有关知识的积累。天赐良缘:1986年,天津教育出版社拟推出“学术研究指南”丛书,刘扬忠受命撰写宋词,题名为《宋词研究之路》(以下简称《研究之路》)。他颇为自信地宣称:自己虽属特殊的一代,但“并不是过时的一代,而是承担着承前与启后双重任务的一代”,“一代必须有一代的学术”。[5](《引言》P2)没有辜负众望,他对宋词研究状况的概括与评介,对研究者必备素质之表述,不知沾溉了此后多少学子!但也应该说,此著为读者而作,却也是为他自己而写,因为他需要站在那个时代的高度,对为之献身的事业了然于心,从而正视现实,并一展宏图。
可以说,《研究之路》的最大贡献是在回顾并总结了宋词研究的历史沿革之后,承续着现代词学学科主要奠基人之一龙榆生先生的脚步,又吸纳诸贤有关之说,审时度势,建构了一个全新的由若干层次和科目组成的“宋词研究体系”,并对之进行了精要的论证。他回答了人们期待视野中的宋词研究应有的“具体内容”、要达到什么“目的”以及“工作范围”等需待回答的基本而又重要的问题。尤其是,这个体系是开放的,它通向宋代文学与文化,通向整个中国词学以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华文化,并为当代文化建设提供借鉴。[5](P18-21)尽管今天看来,该体系的某些地方或可调整增益,但它无疑是当代学者自觉地、有意识地为宋词研究体系而创设的逻辑分明的比较科学的实施方案,是新型词学中体系建构的历史性突破;其所透发出的理论眼光和学术胆识,在经济社会与学术文化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已远远超出了它的实用性价值,而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研究者以及宋词本身应有的“尊严”。因而,谓其在中国词学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或者说是里程碑意义,当不是夸张之辞。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他初涉学海并不太久,除了完成其它论著的撰写任务之外,此书又与《词心探微》几乎同时杀青面世,这不仅可见当年拼搏之苦(乐),也以此二书为标帜,昭告了他的词学研究迅即进入到成熟的阶段,这是特殊年代、特殊经历、特殊挑战与机遇相撞击而成就的一幕特殊而精彩的演出!
该筹划并实施一个更宏伟的计划了!尤其在完成了对宋词研究园地的勘探、体系设计并重构稼轩模式之后。果然,经过大约十载的沉淀、构想与辛勤编织,在20世纪即将拉上大幕之前,他又把一部四十余万字的《唐宋词流派史》(以下简称《流派史》)摆在了人们面前,从而把自己的唐宋词研究推向了峰巅。
如果说之前的几部著作因各种情况导致其写作契机多少还有点“被动”的话,这一次却是主动出击,即作为一项课题向国家社科规划办申报并获得批准。关于这部著作的写作动因,照他的话说,一是多年来他在不断地思索宋词(及词学)研究中种种尚未解决的基本问题,其中的“流派”问题就特别纠结其“词心”,亟需重新梳理与科学论证;二是有意承继导师吴先生的未竟之志。20世纪80年代初,吴先生连续撰文力破“很不全面,不准确”的豪、婉二派说,引发了词学界一场激烈的争论。然吴先生遽归道山,未及建构唐宋词流派理论体系。但既然此课题已被提上日程,于是萌生承其遗愿并为学界开一新面的念头。[7](《自序》P2-4)或可补充的一点是,在他已经具备了“登顶”的条件与能力之时,其实也很想对整个唐宋词的纵向流程,按照自己的独特方式、从理论到实践来一个全局性把握,将峰峦迭出、百卉竞艳的绮丽美景尽收眼底,从而领略“险峰”的无限风光:这也许是更深一层的内在驱动力。
愿望得以实现,此著反响热烈,评论众多。因学界对之已很熟悉,此不多赘。简要地说,他打破了长久以来豪、婉二分的旧框,提出了一整套词派建构的理论思路;运用现代文艺学的科学原理和方法,清晰地勾画出唐宋词中三大类、十四个主要流派生成、衍变的过程及其规律,透视了特定文化背景下审美思潮的运行轨迹;继杨海明《唐宋词史》之后,创造性地结撰出一部以流派演变为主干的新型唐宋词史。他在“知天命”的“年谱”上奏出了强者之音,为其钟爱的词学事业的蓝图画上了一道靓丽的重彩!
生活与学术在继续,他还有更长远的目光和更加诱人的目标。受导师吴先生及其他先辈治学思路之启发,积多年研究实践之体悟,他感到要使唐宋词及整个词学研究这生命之花木常青常开,还必须打破“本位主义”,走出这片狭小的园林,以更为宽广的视野和深锐的穿透力,来观照、剖视它们的枝枝叶叶和每一条根系,及时输送养料,否则它们会逐渐枯凋,花径也不再为“客”而扫。为此,他多次说过不能只是就词论词,一再强调“打通”。所谓“打通”,主要是指词学与相邻学科、文体之间的打通,以及与当下社会的打通。这是因为,世间万物原本就存在着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的各种各样的联系,以意识形态呈现的各门学问,尤其是文史哲之间(更别说文学各门类之间)亦是如此。作为特擅摅写心灵奥秘与内在情愫的词体,在某种意义上与社会生活和人的各种行为之间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同时,习惯于困守、徘徊自家小院,甚至对某些特异花卉也会熟视无睹,倒是那些“眼观六路”者往往能够发现之。前辈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钱钟书、俞平伯等,并非专治词学,但因淹博文史,亦通词道,其不少高见卓识至今仍被我们引用或奉为经典,即是明证。当然,“走出去”并非“不回来”,不是研究主体的完全“转行”和词学研究的“消失”,而是使研究者在某种“通识”视域内,更有兴味地观赏并探究这个“花花世界”,从而提出新见新说。而鉴于词体与诗歌的特殊关系,刘扬忠早些时候就已把研究触角向诗学领域作了试探性延伸。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除了专著《诗与酒》外,他还写了《皮日休简论》、《关于曾巩诗歌的评价问题》、《迹浅而意深,言近而旨远——评俞平伯对古代诗歌的研究》、《胡适古典诗学的成就与偏失》等文章①分别见《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一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曾巩研究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文学遗产》1986年第2期;《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显示出主攻词学、兼治诗学的学术路数。同时,他也参加了《彩色插图中国文学史》、《唐代文学史》、《中华文学通史·宋辽金卷》的写作,进一步向文学史领域开疆拓土。到新旧世纪之交及稍后几年间,经过百年学术反思,则更加坚定了这一学术方向。他与董乃斌、陈伯海先生共同主编了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学史》而担纲第三卷《各类文学专史的形成与繁荣》(以下简称《文学史学史》),并为领衔撰稿人描述与论证了诗史、词史、散曲史发展概况及韵文通史之得失;随之又主持了《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宋代卷》(以下简称《文学通论·宋代卷》)的编写。该著注意吸纳前沿研究成果,在体例上也一反旧规,从而较为全面精当地展示出宋代文学的方方面面。那么,走出唐宋词及词学,向诗学及文学史领域逐步“蚕食”扩张之后,再回头观览那个对象,有什么效应或者说在实践上是否有异样的感受呢?回答是肯定的。且不必说他在唐宋词之外又关注金代山西、河朔词人群体及清初广陵词人群体②参见《金代山西词人群》,《晋阳学刊》2003年第4期;《金代河朔词人群体述论》,《学术研究》2005年第4期;《清初广陵词人群体考论》,《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7期。,也不必说在已有的几部论著特别是《流派史》中即已表露出的较为宽阔的文学史意识(如对柳永及柳派、稼轩及辛派的论述等),以及《文学史学史》中所展现的更为宏通的史识视野(如对清人周济“词亦有史”及胡适关于词的文学史意义的评判等等),也许只举几个小例便可见其端倪:比如谈陆游词,便取“诗词比较”角度,说“与他的诗歌有所不同的是,他的主导词风时时偏于低垂幽怨或清旷飘逸,不似诗歌那么激昂奋发、慷慨豪壮”[8](P8);在《文学通论·宋代卷》之《绪论》中说,如果严格一点,“完整意义上的宋代文学研究是从南宋初年开始”的话,则王灼的词学著作《碧鸡漫志》便是标志之一;在《关于20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中,断定“新词学是本世纪开头30多年新文化思潮冲击旧词学,使之发生裂变的产物,而决不是传统词学的传宗接代式的延伸或复制”[9]。也许这些并不是什么惊人之论,但见微知著,却可以说打通已初显成效。此一阶段姑且称之为“后高峰探索阶段”,当然,它还在行进之中。
目前,他正在撰写《中国词学学术史》,并主持中国社科院重大项目《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的建构》。后者将以文学史上一批著名作家为中心,勾勒传统人格与民族精神的形成历程,直通当代。有理由相信,他会在这段路程上绘制出灿然醒目的标记。
由上述,刘扬忠的词学研究之路可大致归结为:起始——成熟——高峰——后高峰探索几个阶段,它们密切连续又时而交错。不过,应该说明的是,他似乎不单单想做唐宋词专家或词学家,如是,则除此之外,又兼为古代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那又有什么不可!
二
在大体勾画了刘扬忠词学研究路径的基本轨迹之后,有必要揭明其独具的个性风采,这当是题中应有之义。
众所周知,科学研究的最大忌讳是“随人后”,低层次重复。然而,创新又谈何容易!它需要才识,更需要勇气;它需要丰厚的学术积累,更需要驾驭与透悟研究对象的能力;它需要激情,更需要冷峻的思考和深长的眼光;它需要强烈的意愿,更需要通脱的观念和适宜的工具与方法,等等。对刘扬忠而言,在完善这一切素质的过程中,理论之倡扬与学术史之关注成为其高扬的旗帜。这一点,在当代词学家中显得十分突出。他呼吁词学理论的建设与突破,几乎贯穿于所有的论著之中,还专门写过《研究者要重视理论》等系列文章,阐明要想在“若干规律问题研究等等方面取得突破,则断非理论指导不可”、研究“不但要出材料,而且更要出思想”的道理①分别见《研究者要重视理论》,《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实学”基础与理论修养》,《文学遗产》1999年第2期。,且反省自己于此颇有欠缺,企盼同行强化理论意识。因为理论与学术史特为“近亲”,而词学史在词学研究中又是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故而常将二者并提。如谓“要改变词学研究相对落后的现状,找到学科发展的突破口和新起点,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通过总结和撰写词学学术史,来实现理论的升华和超越”[10];又如《关键在于理论的建构和超越》一文,副题即是《关于词学学术史的初步反思》,文中回顾了千年词学史的足迹之后结论道:“鉴于旧词学研究体系和理论建构比较薄弱,我认为,当代词学研究要打开新局面,关键在于理论上的突破和飞跃”,研究“要自具手眼,不是凭天资敏悟,而是靠理论学习与积累。”[11]而在为笔者主编的五分册《中国历代词研究史稿》所写的《序言》中,除简述词学史概况并指出该著某些不足外,还特别鼓励、揄扬,称其“填补了词学研究史上的这个明显空白”[12](P2-3)。这些苦口婆心之言,实在意味悠长。
不仅倡导,他更重身体力行。较早出版的《研究之路》,就是一部词学学术史性质的专著。其中,本着“论发胸臆,文成手中”(王充《论衡·佚文》)之理,列专章详谈了宋词研究者的专业素养诸问题,指出要搞好研究,除“充分占有材料”外,“还需正确的理论和方法”。[5](P114)其实,在更早写作学位论文即上面提到的《周邦彦传论》时,便以历史的、辩证的、美学的新观点和新方法,完成了一篇出色的翻案文章,而这也正凸现了他敢于摆脱旧观念以立新说的理论勇气,尽管其文今天看来尚有稚嫩之处。在面对稼轩时,经过慎重思考,“发现了从熟课题里出新观点的可能性”[12](P3),于是告别习以为常的纯客观的反映论老路,立足于主体性原则及抒情词的本体特质,并“借鉴了一点西方的批评方法”[12](P6),初步完成了词学乃至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新旧范式的转换。其后,在关于唐宋词流派的研究中,他参酌有关论说,洞察词史实际,又创建了自己的流派学理论体系,并爬梳烛照,挖掘出一些重要的词派或群体。同时,他还与其他学者一起,展开对文学史研究的再研究,并最终提炼出构筑文学史学这一新学科的理论框架。其间,对文学史料之把握,对文学史观由循环论经进化论、阶级论到多元化观念之清理,对文学史学科及他主持的文学专史的历史行程之描述,换言之,史的反思与建构,都离不开理论的导引。上列种种推陈出新之举,无一不显示出这来自实践又反作用于实践的理论利器的强大威力。此其一。
其二,专攻而兼取。刘扬忠治学受导师吴世昌先生影响甚大,还在选定研究方向之始,吴先生就提醒过他,词的“娘家”是诗,要搞清词学、词史上的问题,必须溯源于诗史。因此,研治词学、词史,而又兼顾诗学、诗史,并注重在一定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下研究文学,也成为其治学的一大特色。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他除了取得若干重要的词学研究成果之外,还发表、出版过部分诗学论著,并参加过多部文学史的编写。关于此之基本情况,上文在论其研究道路的第四阶段即所谓“打通”的问题时已有述及,这里,拟就某些方面再稍作补说。实际上,“专攻”与“兼治”是个老话题,也是个大问题,道理却不难明白,主要还在于观念与所寻路径以及如何去实现这一诉求。如前所说,由唐宋词出发,延及词学与词史的其他领域,再由此扩充至诗学、诗史甚至整个文学史乃至文化史等更宽广的“大观园”,然后重新观察那“故国故土”之时,往往会有新的发现。因为由“此境”入“彼境”,再由“彼境”反观“此境”,犹如爬上一座山头,再攀上更高更险的山峰来俯视原先的山景,由于角度、视界之变化,其审美信息与审美判断自会有所不同。或者说,这是一种由内而外、再由外而内的双向运动,比总是呆在自己内部的“小国”里徘徊更有兴味。刘扬忠的词学研究循此路数,确实有所收获。但如果你对词与诗、词学与诗学的关系另有理解,一生只专注于词学,亦并非无所成就。不过也应该说,真正的“专”是建立在“博”的基础上的,况且,我们的研究对象也是很“博”的。于此,严迪昌先生的一段话很值得参考,他说:“宋代词人与唐代诗人不同,往往多才兼能,两宋以后此特点则成为普遍现象。诗文词无不兼能,有的还是小说家、剧曲家以至书画大家,或者则为学者史家。要整体把握他们各自的心态,把握他们共时性群体生态,或叫原生态,以及作品表现形态,是必须有个宽博的研究视野空间的。不要把‘专’变成‘狹’。”[9]有人以为被公认十分广博的钱钟书先生似乎不懂词学,刘扬忠专门写了《钱钟书与词学》的文章,指明钱先生不仅是词学内行,而且多有发明。[13]当然,要做到“博”极为不易,世界上的学问五花八门,尤其中国历史悠久,典籍浩瀚,即使天才、大学问家,也不可能样样精通。刘扬忠也曾说过,我们这辈人“运气”不太好,受各种情况制约,已难以产生人们理想中的所谓“大师级”学者了,大多数人难免学有所偏,才有所偏。只不过,学人可根据自己的主客观条件以及所从事的事业之基本范围尽量努力而已——但愿不要在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后“了无印象”。如是,则刘扬忠主攻而兼取的路子或许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借鉴。
研究与创作之联姻,也是其学术性格的一道风景。刘扬忠幼承家学,很早就对古代文学特别是唐宋诗词产生了浓厚兴趣。还在中学时代,即已开始了旧体诗的习作。三十岁后负笈京华,又学会了填词。师长的教导加上自己坚持不断地写作磨练,其诗词创作渐趋成熟,并达到较高的水平。目前他已创作诗词数百首,仅公开发表的就有三百余首。长期的创作与研究实践使他深信,要在词学研究上有所作为,学会创作是一个重要因素。他自己尝到了甜头,又大声疾呼两者之结合。事实上,在多年前出版的《研究之路》一书中,他就专门谈了“宋词研究者有无必要学会填词的问题”——尽管当时还可能有点“不合时宜”。由于文字较长,此可简要转述。他认为,研究者学会作词,是一项极为必要的专业训练,它至少有两重意义:一是工具意义。因为从语言形式的角度看,作为研究对象的词自有一套特殊的规则与要求,而这单凭读作品和机械记忆难以完全熟悉此中关捩,最好以填词实践获取具体之印象。二是认识意义。即通过深谙创作甘苦获得直接认知,以便更深切地体察它那除时代背景与情感内容之外尤为“难点”的艺术性方面的奥妙。[5](P126-132)总之,创作能帮助人们更好地掌握词体特有的语言信息符号,在鉴析词作、论述某些更高层次的问题时,能够得心应手,不至于说外行话,历代学者的经验也证明这是一个有效的途径。此后,在不少座谈发言和文章如《建立理论、文献、创作三结合的古代文学博士培养机制》①见《陕西师大学报》2003年第1期。一文中,仍坚持自己的基本看法,并且又进一步建议:为了让学生(包括本、硕、博)真正读懂自己的研究对象,必须教会他们写作旧体诗词(甚至文言文)。因为在我国传统的教育体系中,学问和创作从来就没有分过家。如所谓“诗学”,其主干部分即是创作。今天的研究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创作一项理应包括在内,等等。不能不承认,有的研究者对词的文体形式、内在结构甚至专业术语不够熟悉,或者基本了解而不能运用,在进行理论阐释与艺术评判时往往缺乏针对性,凿空泛论,乃至出现谬误和常识性硬伤,原因很多,缺乏创作实践也是主因之一。更何况,词为倚声文学,虽其乐亡,但其遗留的艺术形式、与乐理之关系以及历史的嬗替演变等,也是词学研究面临的一大课题。同时,研究者写点诗词,对涵养自己的情操、气度等亦大有益处,久而久之,随着“软实力”之增强,也会成为提高研究水平的一大助力。然于创作一道,早些年学界或有人偶尔为之,或在有意无意间将写诗填词之得渗入自己的研究中,但像他这样,不但大量创作诗词,而且摇旗呐喊与研究相结合,并不多见。近年学写诗词似已成热潮,各地诗词报刊如雨后笋起,发表作品难以数计。不仅中老年人,许多青年人也争相加入此一行列。当然,创作与研究毕竟还各有侧重,但此风已吹向学界,有人已欣然操觚,有人已忙于张罗诗教进校园活动。因而,说刘扬忠领此风气之先,是从理论到实践而“大肆作俑”者,起码是较早的鼓吹者,也许不是无根游谈。
刘扬忠自认其词学研究成果得益于他的诗词创作者多,此乃肺腑之言。在他的理论性著作如《词心探微》与《流派史》中,时见通过创作锻炼得来的“硬”功夫,对词人、词作的艺术旨趣及词意指向往往独具只眼,虽有“别解”而能准确到位,并升华为理论,抽绎出规律性的东西。比如由稼轩《兰陵王·恨之极》概括出关于其梦境词的“某些普遍道理”;由《汉宫春·立春日》得出“辛词中其他有感情寄托信息而不可以句解字求者,皆应如是观”的结论[12](P108-118;P131-132);由对东坡“挑战”柳永所创《戚氏》词调之疏解,“引申出两点对苏词的认识”[7](P241-247),如此等等,这就难怪他学会填词之后,脑子里涌现的多是识得个中甘苦后酝酿而成的有意义的论题了。也正因如此,这些论著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注评鉴析类著作中,对每一具体作品之解读,也常是另有会心,此亦顺便举两个小例。比如《晏殊词新释辑评》中释其《撼庭秋》(别来音信千里)令词(原词不录,下同),他说此调“始见于晏殊《珠玉词》,但其中仅有此一首,故《词律》卷五、《词谱》卷七俱列此首为标准之作。这是双调小令,四十八字,上片五句三仄韵,下片六句两仄韵。多为四字句。本篇抒写相思念远之苦情,而以‘此情难寄’为中心环节,所有的情节描写和意境创造,都是围绕这个中心展开,都是为了表明寄情之‘难’的”。以下再分别就上下片及过片等处句句详析,最后以之与小晏词比较作结。[14](P73-74)又如《周邦彦词选评》中评赏清真绝笔之作《西平乐》(稚柳苏晴)长调词说:“由于作者年老力衰,心境恶劣,故在词的形式上大不如前讲究:结构章法不像他的大部分词作那样精巧谨严,甚至音律也比较宽散,137字的长调,只有稀疏的七个韵脚,颇有点以散文为词的味道。这首词就像一个路标,记载着周邦彦本人随着生命的途程快到终点,其文艺创作灵感的火花也来了最后一次闪烁。”[15](P150-152)你看,一般论者弄笔,多按习惯释其背景,解其内容、艺术等,而他除此之外,还特别介绍调式、作法、声情关系等艺术要素,从而使读者得到更全面的审美享受,而这恰恰是没有创作经验的人最容易“忽略”的重要之点。同时,在赏鉴中对古今论者之说多有商兑,不是人云亦云,其见解多半令人信服,这也与创作经验的积累有关(其例甚多,为避文繁此处不再举示,读者自可翻览)。这些都表明,面对特殊的研究对象,出之以特殊的操作方式,可使研究与创作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近两年我本人亦学写点诗词,确感写好之不易,由此更实实在在觉悟到唐宋诗词之美,尤其对名家名篇更感钦佩;而省察以往之研究与教学,实为一缺失。当然,凡事不可过于绝对,不善写诗填词者也能凭藉敏锐的艺术感悟发为宏论,而研究家也不能事事经历,有些事则不能或不可经历,但可以经历者,如治词学而能填词,于研究有近乎“零距离”的切身感受,肯定会更好,而这也并非要求研究者都去当诗人、作家。
其四,“气”为统帅。刘扬忠为文为词,总使人感到有一股“气”在。“气”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概念,指构成万物之物质。孟子有“知言”“养气”说,大致是指通过人格道德修炼,培养出一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从而具有辨别言辞之能力(《孟子·公孙丑上》),后之所谓“气盛言宜”、“辞根于气”等,盖由此而来。曹丕又提出文气说,并以之评价作家,“文以气为主”云云,大意是说作品之气貌或风格与作家之气质、个性有关(《典论·论文》)。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尤其《体性》、《风骨》篇亦多涉及到气和文气。这些问题,大而复杂,且理解尚有歧义。此处所谓文气,照简单而通俗的说法,是指行文富于气势,具有生气灌注的感发之力。刘扬忠为文往往豪宕清峻、畅爽显豁,当为“气”之体现。此可摘引几小段文字,比如:“在许多研究者笔下,原本众芳争艳、风格流派纷呈的唐宋词大花园不见了,只剩下‘豪放’、‘婉约’两朵孤零零的花儿;群峰簇簇、山脉交错的唐宋词山国隐没了,只剩下‘豪放’、‘婉约’两座(或最多两列)山峰;涵汇万状、众水奔流的唐宋词海洋消失了,只剩下一清一浊的‘豪放’、‘婉约’两条河流!试问:这难道是唐宋词流派史的原貌吗?”再如:“任意扩大‘婉约’的含义,拿它来硬套全部柔美词,将千姿百态的各有特色的词人们笼统地纳入一个几百年一以贯之的‘流派’,岂不使词学研究简单化、狭隘化?”又如:“以‘豪放’概括苏轼词风,本就不确切,如果还要拿他来代表那些个性、风格与之相异的‘豪放’作家,就更离实情远甚矣!”[7](P4;P12;P14)这类文字如戛玉敲金,而又浩荡其势,简直咄咄逼人,但又不是不讲道理!似此者其论著中甚夥。不但为文,为词亦多以势壮为美。他喜欢也较有条件观览自然与人文胜迹、民情风俗,发而为词,往往真情充盈、鼓荡人心。不用说咏怀稼轩之若干篇章如《鹊踏枝》(题济南稼轩祠)、《水龙吟》(当年沧海横流)(词坛健鹘摩天)(廿年书卷相亲)等“填词多带稼轩气”,即使其他题材甚至闲情游戏亦有此风采,如《沁园春》(十载重来)下片:
荒唐,何物宣扬,谓宝岛居然另一邦?叹一春选战,族群撕裂;黎民忧郁,政客披猖。夜色苍茫,孤舟摇荡,颠倒难为雾里航。西回首,望神州万里,灯塔辉煌。
游台北街市而抒发政治情怀,直斥“台独”,期盼一统,大气凛然!而《八声甘州》(对茫茫雪野泛银光)写哈尔滨学滑雪,“竟几番颠扑,遍体汗如浆”,却“鼓雄情、偃而重起,气渐生、胸胆再开张。归途爽,轻舒铁杖,眉宇轩昂”。因此,尽管有些词作在艺术上尚可斟酌,但气盛却是共同之点。这“气”乃性格之显现,是禀赋,也是后天培育,包括先师吴先生诫其“言真行直,慎莫逐、波涛明灭。潜志读书常不寐,更刚肠嫉恶殊难得”之遗训(《金缕曲·哭先师吴世昌先生》)等。履正道,寓正气,才能有胆,为文为词才不至于拘束、畏缩,敢破能立。上文曾说他对论者之说时有驳辩,此可补举一例:如在解读稼轩《念奴娇》(书东流村壁)词说明应如何对待这类虽属怀人恋旧、却又在有意无意间渗入了一定的身世家国之感的作品时,首先据词序及正文,断定此词并不为寄托政治情感而写,接着便说他既不同意梁启超氏之说,也不赞成权威选家之解,对于梁氏另一说,也认为要作具体分析。最后,通过自己释说得出了更通达的结论。[12](P143-145)一般人也许觉得不便如此下笔,事实上,这除了才识之外,也与胆气有关。要之,有此大气魄,才使人感到其所论所说理清辞畅,能纵能收,痛快淋漓。
上文分述其研究性格,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实际上它们是交互联系在一起的。而除此之外,也还有其它方面,比如他对继承、汲取前辈治学经验就非常重视,还为此写过好几篇文章,鉴于文中已有涉及,不再单列。
行文至此按说该结束了,但笔者还想“画蛇添足”。总体言之,刘氏为人为词所涉之各个侧面相融相依,由此才会产生“活性效应”,并进而构成比较完整的学术形象。同时,本文似乎只是“好话说尽”,或以为有“护短”之嫌。俗谓人无完人,而为文也不会完美无瑕,刘扬忠绝不例外。只不过此文之旨乃试图为当代卓有成就的词学家做一份并非是最终的小结,以为同好及后来者提供某种“正面”启迪,至其所谓不足,可另择机会讨论。现在,刘扬忠尚未显“老”态,且仍在跋涉。前几年游武当山,他在一首调寄《绿头鸭》的词中曾经说:“念人生、风波频履,一似今日跻攀。举双眸、遥瞻金顶,鼓雄情、更上危巅。”是的,就其个人的研究经历而言,他已攀上了一座峰顶,而相对于词学事业本身及其神往的“兼治、打通”的更大目标,他前面还有金灿灿的“大世界”。但愿他在诗词事业的“洞天福地”里,伴着酒香“仙”气,再登光芒四射的“金顶”!
[1]鲁迅全集:第二卷[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
[2]张若兰.刘扬忠访谈录[G]//宋代文学研究年鉴(2006-2007).武汉:武汉出版社,2009.
[3]刘扬忠.周邦彦传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4]刘扬忠.稼轩词百首译析[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83.
[5]刘扬忠.宋词研究之路[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
[6]王兆鹏.“诗—史范式”向“诗—心范式”的转换——从《辛弃疾词心探微 》看古典文学研究的新变[J].漳州师院学报,1998,(1).
[7]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8]刘扬忠.陆游诗词选评[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
[9]严迪昌,刘扬忠,钟振振,等.传承、建构、展望——关于20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J].文学遗产,1999,(3).
[10]刘扬忠.二十世纪中国词学学术史论纲(上篇)[J].暨南学报,2000,(1).
[11]刘扬忠.关键在于理论的建构和超越——关于词学学术史的初步反思[J].文学评论,1995,(4).
[12]刘扬忠.辛弃疾词心探微[M].济南:齐鲁书社,1990.
[13]刘扬忠.钱钟书与词学[J].文学评论,2005,(1).
[14]刘扬忠.晏殊词新释辑评[M].北京:中国书店,2003.
[15]刘扬忠.周邦彦词选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Liu Yangzhong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famous etymologists since 1980 s.His etymology research goes through the phases as start,maturity,summit and postsummit.His research features can be temporarily summed up as:(1)the combination of advocating theory and concerning academic history;(2)specialization and compatibility;(3)the connection between research and creation;(4)“gas”acts as the commander in chief.
On the Etymologist Liu Yang Zhong:The Serial Study on Contemporary Etymologists(series two)
CUI Hai-zheng
(School of Literature,University of Jinan,Jinan 250022,China)
I206
A
1671-3842(2012)01-0001-08
2011-11-03
崔海正(1947-),男,山东茌平人,教授,主要从事宋代文学及中国词学研究。
责任编辑:张东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