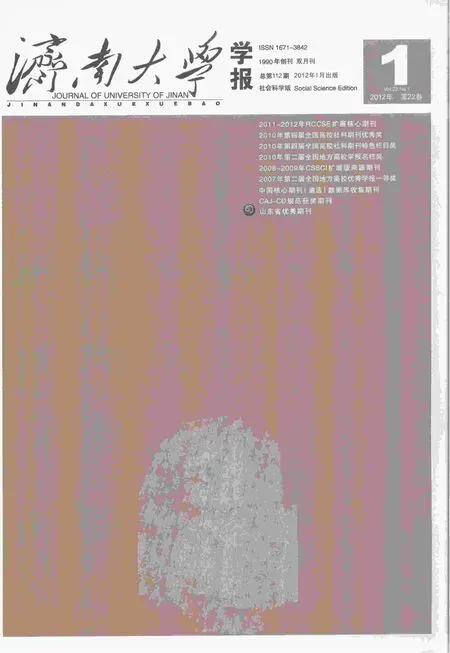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女性观念
刘铁群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桂林 541004)
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女性观念
刘铁群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桂林 541004)
鸳鸯蝴蝶派作家对女性问题的言说往往纠缠着层层交错的矛盾与冲突,这主要体现在人物形象与作者创作意图之间的矛盾以及小说的情节、内涵与作者、编者观念之间的冲突。鸳鸯蝴蝶派作家女性观念的复杂性与他们职业作家和传统文人的双重身份密切相关。传统文人的身份使他们难以摆脱陈旧观念的束缚,而职业作家的身份使他们必须以满足市民读者的消费需求为创作宗旨,必须让作品尽量贴近市民生活。这必然会使他们冲破很多陈旧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写出时代转型时期的女性,写出她们在礼教逼压下的反抗与挣扎,写出她们对自尊、独立以及婚恋自由的追求。从对创作过程的影响来说,传统文人这一身份的影响主要处于表层,而职业作家这一身份的影响则主要处于深层,因此,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女性观念虽然新旧杂陈,但其正面影响明显大于负面影响。
鸳鸯蝴蝶派;女性观念;职业作家;传统文人
鸳鸯蝴蝶派作家创作了大量的以婚姻恋爱为题材的小说,这些小说对女性问题的言说往往纠缠着层层交错的矛盾与冲突。这些矛盾与冲突正体现了鸳鸯蝴蝶派作家复杂的女性观念。
很多鸳鸯蝴蝶派作家在塑造女性形象时都明显地流露出自己的创作意图,然而,他们笔下的女性形象却常常偏离了作家的创作意图,她们就像不听导演指挥的演员,偏离了导演为他们设计的性格发展方向。秋梦的《孝女佩衡传》(《礼拜六》第28期)仅从标题就可以看出作者是想写一位孝女,小说中也多次表现出对孝的赞美。然而,这篇小说所塑造的女主人公佩衡已经远远超出了孝女的形象。佩衡家境贫寒,为了让母亲和弟弟活下去,她卖身给某中将做妾。佩衡卖身救母的行为的确是孝的表现,但佩衡的孝并非愚孝。卖身之后,她也没有放弃对人格独立的追求。在为人妾期间,她在有限的范围内尽最大的努力维护自己的尊严,同时读书习画,为恢复自由身做准备。她对弟弟说:“我甘为侍姬,以母与若耳。我鬻身时得两千金,今当以卖画所入如数偿之。还我自由。”佩衡以卖画积攒七千金后毅然离开中将家,并给中将留信说明出走原因:“佩衡夙念不欲为人姬妾……母弟无以存活,出此下策。一年来藉中将声誉,货画所入积蓄七千金。前负二千金,谨如数奉缴,余资则用以自存,已结庵野外,皈依佛门,长为世外人矣。”显然,佩衡的形象中除了孝之外还有勇敢、坚强、自尊的品格和追求独立的精神。这些品格和精神使她与传统的模式化的孝女形象区别开来,这才是她真正的魅力所在。但作者在小说的结尾借中将之口再次赞美和提升佩衡孝的可贵:“此孝女也。相处十年,竟失诸皮相。我过矣,我过矣。”包天笑的小说《一缕麻》(《小说时报》第2期)中某女士的形象也同样偏离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包天笑欲塑造一个贞洁守礼的女性,但在小说的前半部分,某女士是一个颇有叛逆色彩的形象。丽若天人,冰雪聪明的某女士“幼缔姻于其父同寅之某氏,某氏子臃肿痴呆”。女士不满包办婚姻,对父亲说:“今吾国婚姻野蛮,任执一人而可偶之。究竟此毕生之局,又乌能忍而终古,则离婚之说,儿殊不欲厚非之。”女士不顾忌有婚约在身,与邻居某生两情相悦,互为知己。虽然女士为不怫老父之心履行婚约,但在成婚之前她与邻居某生相约婚后继续交往,书信传情。她大胆地说:“我辈有书信自由权,宁不能藉青鸟之力耶?”她这些言行显然违背了传统礼教对女性贞洁的要求。在小说的后半部,女士身上的叛逆色彩消退了,但这种变化并不能简单地用贞洁二字来概括。成婚第二日,女士“觉喉中有物,梗然不便于饮,视之,则白腐绕喉矣,大咳。时吴中盛疫疠,死者踵相接”。女士得此病,举家惶惶,妪婢辈举不敢入新妇房,然痴郎乃不避,凡汤药之所需,均亲自料理。女士“心感其诚,于是厌薄之心亦消淡”。在女士昏迷不省人事之际,痴郎也染病不起。女士病愈醒来,发根有麻丝一缕。女士悲痛,“于是一易向者厌薄之心而为感恩知己之泪,盖郎固不痴,其至诚种子也”。此后邻居某生屡次传书问候,但女士终不复信。从表面看来,女士似乎回归传统,变成了符合传统伦理规范的贞洁女子。但女士的转变并不是被传统伦理道德束缚的结果,而是被痴郎的真情感动的结果。因此,不管是小说前半部还是后半部,在女士心中占最大份量的都是真情。不管是叛逆还是贞洁,都是女士根据真情做出的自我选择,也可以说是她追求真情的结果。她的爱情观念是真情至上而非伦理至上。她身上所表现出的一些可贵的精神品格并非贞洁二字可以涵盖。但作者却极力强调女士的贞洁,并从贞洁的层面肯定这个形象。他在小说中以赞美的口气感叹:“至今人传某女士之贞洁,比之金石冰雪云。”民国时期轰动文坛的长篇小说《玉梨魂》与上述两篇小说也有相似之处。《玉梨魂》讲述了年轻寡妇白梨影和书生何梦霞之间的爱情悲剧。在小说中,作者徐枕亚极力突出白梨影的温婉贤淑、善解人意、重情守礼、品质高洁。然而小说中的很多细节都让我们对白梨影的形象产生怀疑。细读文本可以发现,在白梨影与何梦霞的爱情关系中,白梨影一直占主动地位并且颇有心计。在小说中,白梨影虽然经常把礼教挂在嘴边,让何梦霞收敛对自己的爱意,但实际上推动两人感情向前发展的正是白梨影。小说第四章《诗媒》中,白梨影趁何梦霞不在偷偷去了他房间,拿走诗稿,遗花相送。遗花的举动让何梦霞浮想联翩:“其遗此花也,有意耶?抑无意耶?”结果主动向白梨影表白爱意。明明是白梨影对何梦霞动了心并以“遗花”的行为引诱何梦霞先表露心迹。在得到回应,达到目的后白梨影心中是“且惊且喜”,但她却故意做出一副被动的样子。显然,这一切都是白梨影精心设计的,她这样做的目的是既想得到何梦霞的痴情和尊敬,又想保留清心寡欲、维护教义的美名,以免遭受他人的耻笑。这是一个聪明、勇敢、渴望爱情的寡妇在封建礼教束缚下的有效的反抗途径。对于两人的爱情归宿,评论者向来认为是“发乎情而止乎礼”。然而,白梨影让小姑筠倩代替自己嫁给何梦霞仅仅是为了“止乎礼”吗?筠倩接受了新式教育,追求婚姻恋爱自由。聪明的白梨影当然知道筠倩嫁给何梦霞不会幸福,她所说的“保全梦霞之幸福,然为筠倩计,得婿如此,亦可无恨”不过是一个掩饰私欲的借口。白梨影李代桃僵的办法与其说是“为筠倩计”,不如说是为了自己的私欲,是为了躲避名誉受损,也是为了把何梦霞“名正言顺”地留在身边。为了促成此事,白梨影使用计谋让何梦霞好友石痴前来说媒。崔父认为这是一桩理想的亲事,但也没有立即许诺,而是表示“容往商之”。当崔父对白梨影提及筠倩的婚事时,策划此事的白梨影装作不知情,高兴地对崔父说:“筠姑得配梦霞,洵成佳偶,况有阿翁作主,儿亦深望此事之成就。得此佳婿,筠姑亦乌有不愿意者?儿当即以好消息报告,且将为筠姑贺喜也。”然而,白梨影向筠倩转告此事时却将崔父“容往商之”的态度偷换成了不得不接受的命令:“筠儿今已有婿,温郎不日将下玉镜台矣,冰人来,直允之,不由儿不愿意也。”而且她还把在崔父面前表现出的喜悦转换成对筠倩的同情和不平:“余闻言甚骇,乃婉语翁曰‘此事翁勿孟浪,一时选择不慎,毕生之哀乐系之,容儿商诸姑,然后再定去取。’余窃为姑不平。”白梨影的精心策划、巧言善辩使筠倩痛苦地接受了婚事而对促成这门婚事的主谋白梨影没有一丝怨恨。显然,白梨影费尽心机促成了这门婚事并不能用“止乎礼”来解释。如果她仅仅追求“止乎礼”,没有必要如此机关算尽,没有必要毁掉筠倩的幸福。白梨影的这些努力表明她在无望与何梦霞长相厮守之后仍然为两人的爱情寻找归宿,这是一个渴望爱情的寡妇无路可走时的反抗和挣扎,当然这是一种扭曲的反抗和挣扎,它不仅以牺牲其他女人的幸福为代价,而且也使自己无法走出痛苦、自责和内疚,导致她最后选择了死亡。因此白梨影在表面看来是一个“发乎情而止乎礼”的寡妇,但在精神深处,她是一个在封建礼教逼压下积极反抗、苦苦挣扎的女子。在《孝女佩衡传》、《一缕麻》和《玉梨魂》这几部小说中,作者都极力突出女性身上的传统美德,如孝顺、贞节、守礼等,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想塑造一个符合男权社会审美标准的女性形象。这说明鸳鸯蝴蝶派作家在女性观念上显示出守旧的倾向。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都偏离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她们身上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自尊、独立、崇尚真情、反抗礼教等可贵的品质。这又说明作家在女性观念上也有进步的倾向。
鸳鸯蝴蝶派作家女性观念的复杂性还体现在鸳鸯蝴蝶派小说所讲述的故事与作者、编者观念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鸳鸯蝴蝶派作家常常在小说的结尾以旁观者的姿态对小说中的故事做出阐释或评价,一些鸳鸯蝴蝶派杂志的编辑也喜欢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或篇末附上一段编者的话,对小说的内容发表议论。然而,如果仔细阅读文本就会发现,这些小说所传达出的信息往往与作者的阐释、评价或编者的议论并不吻合,甚至相互冲突。涉及到女性问题,这种冲突尤为明显。知先的《爱河水》(《礼拜六》第28期)写梅丽和查理在结婚之始伉俪甚笃。但查理性格暴躁,酗酒无度,无日不烂醉,所得俸给,偿酒债且不足。梅丽对其渐生厌恶,一年后夫妇间几如仇敌。梅丽的表兄亨达医生给梅丽一瓶治夫妇反目病的药水,并叮嘱梅丽:“此水效力极大,尔于查理归时,俟其入门,即取而饮之。勿下咽,亦勿启口,至查理酒醒后,乃出而哇之,否则无效。”梅丽如法饮之,果然奇效,夫妻和好。然而梅丽所饮之药水实际上是自来水。亨达对梅丽说:“吾今明以告尔:尔夫妇之所以不和者,由于不能忍耐耳。今尔既饮此一口水,欲争不得;彼以唇枪来,尔不能以舌剑往矣。彼见尔柔顺如绵羊,自然心平气和,将自悔所为之不是矣。”小说中的查理恶习不改,无理取闹,梅丽本来就有苦难言,表兄却劝她忍耐,努力做到“柔顺如绵羊”。梅丽所服用的“爱河水”实际上是男权社会中女人的苦水。服用“爱河水”就是以忍耐和顺从来获得丈夫的欢心,就是以压抑自我来维持家庭的平静,就是以失去主体性来换取男性的认可。小说以一个看似轻松有趣的故事客观地写出了丈夫的任性、专横与霸道,也写出了女性的悲剧,耐人寻味,引人深思。但是作者却在结尾加了一个偏袒男性、声讨女性的“著者曰”:“今之女界心醉平等,往往视其夫如奴隶,一言不和,即狮声乱喊,因之而反目者比比。一读此篇,当恍然自知其失矣。”是龙的《闺中人语》(《礼拜六》第11期)写丈夫移情别恋,爱上小凤。妻子不满,丈夫却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解:“我之爱若,乃别有所取,卿不知乎?人言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嫖,嫖不如偷,偷得着不如偷弗着,卿试思之,此言何味哉?凡为男子,莫不乐人之温存体贴,殷勤小心。此技实为婢妾辈所优为,而为我爱卿所不屑。至于脉脉含情,心心相印,若离若合,可接而不可近者,人必尤为之颠倒。卿其易地思之,当知我言非不确也。”妻子欲学小凤以得丈夫欢心,但却没做到,又被丈夫埋怨。小说写出了丈夫自私自利、用情不专、强词夺理的无赖行径,也写出了身为妻子面对丈夫移情别恋的无奈和悲哀。但在篇末作者却以“记者曰”的方式跳到故事之外写下这样一段指责女性的文字:“今我国女子,竭力步武西方美人,苛责其夫,役使其夫。独于彼妇对于藁砧之柔情软语,殷勤体贴,不使心上人有一丝毫不快意者,默然无动于衷。如此而欲求一双两好,笑态盈盈,无或嗔无或怒,无或一反目,不其难哉?余述此,余概有遗憾焉。”梅郎的《妻财误我》(《礼拜六》第38期)写贫穷的沈郎为了财与色娶活泼不羁的富家女素素为妻,素素无贤妇淑女之态,喜欢抛头露面。沈郎无法管束素素,受到朋友讥笑。他以留学为由骗取妻子的钱财,另觅新欢,与印霞订婚。然而素素知道了真相。在结婚之日,出现在沈郎面前的新妇不是印霞而是素素,沈郎惊慌色变,浑身战栗,不敢仰视。小说中的沈郎贪财、虚伪、无赖、卑琐。素素的形象却颇为可爱,她有经济的独立,有行动的自由,不愿做一切以丈夫为中心的失去自我的传统贤妇。出嫁前,她对母亲说:“苟他日往沈家者将身不越闺门一步耶?然则儿宁以丫角终,不愿有夫婿也。”沈郎反对素素抛头露面,她反驳道:“吾未嫁时,吾之性情业已如此……”“尔既爱我,不以我为非,是亦足矣!吾又何必强自敛抑,求悦于若辈?”在看穿沈郎本性时,素素愤怒地指出:“尔实非爱吾者,尔之乞婚,非婚我,乃婚金耳。”在沈郎移情别恋之后,素素也没把自己变成自怨自艾的怨妇,她揭穿真相并指出沈郎的卑劣行为,让沈郎在婚礼上当众出丑。素素身上已经表现出了女性自我意识的朦胧觉醒,这是难能可贵的。然而主编王钝根却在小说的结尾以“钝根曰”的方式感叹素素的不贤,表达对女界的失望,并为男性抱不平:“梅郎作此篇,不知其胸中有几许块垒,抑何形容尽致,至于如此耶?夫中国女子,素不受教育,不知孝弟廉耻为何物,求其少秉良赋,长为贤妇者,百不得一。于是懦夫匍匐裙下,窃窃祝妻速死;暴夫攘臂挥拳,悻然斥妻为不淑。呜呼,何其妄哉?汝何人,乃欲得百不得一之贤妇耶?汝欲得贤妇,必俟中国人尽得贤妇而后可;欲中国人尽得贤妇,必俟数十年后真实无妄之女学普及而后可。梅郎独归咎于妻财,尤非探本之论也。虽然,此篇之作,所以力挽贪财好色之徒,使勿堕于九幽地狱者,其功德自不可没。”《爱河水》、《闺中人语》和《妻财误我》这几部小说的结尾所附加的作者和编者对小说的阐释、评价或议论都有指责女性、偏袒男性的倾向,他们都强调女性的贤惠、温顺、忍让、无我是夫妻和睦、家庭和乐的重要前提,这显然表现出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陈旧的传统性别观念。然而小说文本所传达出的信息却与这些阐释、评价或议论恰恰相反,《爱河水》和《闺中人语》写出了男性的霸道、无理和女性的悲哀、无奈,显示出对女性的同情。《妻财误我》则生动地塑造了一个令人厌恶的、虚伪的男性形象和一个可爱的、有叛逆色彩的女性形象。这些都表现出女性观念的进步。
上述两类小说都反映了鸳鸯蝴蝶派作家女性观念的复杂性。鸳鸯蝴蝶派作家女性观念的复杂性与鸳鸯蝴蝶派作家文化身份的复杂性密切相关。鸳鸯蝴蝶派作家大多是在科举制度废除,传统文人由士而仕的官道彻底断绝之后进入上海的文学市场,寻求新的谋生之路,成为卖文为生的职业作家。近代上海经济的发展、报刊杂志的繁荣、市民文化消费需求的升温为他们参与大众文化事业提供了有利条件。他们也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使自己在市民社会中获得名与利。在上海这座近代城市,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成就有着直接的联系。在金钱面前,原来受到尊敬的高贵的血统以及令人羡慕的功名仕途等都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光环。这里流行的是独立的个人奋斗的人格。要想在这座城市立足,就必须寻找机会,以自己的才智去赚更多的钱。在这样的环境中,摆脱了传统谋生方式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作为独立的个体劳动者也都尽一切努力去为自己争取一份较好的生活。恽铁樵和陆士谔都是一边办刊物、写小说,一边开门诊;毕倚虹一边写文章一边替人打官司,还请朋友同行代拉生意。这种兼职和争取多渠道谋生的现象在鸳鸯蝴蝶派作家中很普遍。鸳鸯蝴蝶派的重要作家在写作和编辑报刊之外几乎都兼任过教师,有部分作家还曾卖字、当职员、从商、办实业。在民国初年,上海的各类报刊杂志上,经常可以看到鸳鸯蝴蝶派作家明码标价的卖字广告。周瘦鹃、郑逸梅、范烟桥、程小青等都曾供职于上海的各类影戏公司。张舍我曾在英美烟草公司、金星保险公司和一家外国人办的人寿保险公司任职员。张碧梧曾在先施公司、永安公司任职员,并且曾为上海各印刷厂绘制月份牌。王钝根曾一度倾向实业,1915年3月,他设立明记公司,经营铁业。后加入了陈蝶仙的家庭工业社股份联合公司,并担任公司的“监察人”。徐卓呆曾拟筑一生圹于虎埠山麓,没有付诸实践,后来卖起自制的酱油,自称“卖油郎”。相比之下,从事实业取得最显著成绩的鸳鸯蝴蝶派作家是当时被友人戏称为中国的“大小仲马”的陈蝶仙(天虚我生)和陈小蝶父子,他们因做家庭工业社之大股东获红利甚巨,“乃营华屋,出入乘汽车,俨然富家翁矣”[1]。鸳鸯蝴蝶派作家的这些行为表明,他们在谋生的过程中并不羞于言利,有时已经放下了传统士大夫的矜持和顾虑,就像普通的市民一样勤勤恳恳、付出劳动、收取报酬。然而,鸳鸯蝴蝶派作家毕竟不是真正由近代上海都市文明培养起来的都市儿女。他们多数来自苏州或来自一个类似于苏州的江南古城,他们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由那个“苏州”式的江南古城所塑造成的气质、情趣、爱好以及思维习惯和价值观念。因此,他们虽然在上海的文学市场中谋生存,并且在上海的市民社会中获得了名与利,但他们并没有在精神上真正认同上海,更没有成为真正的“上海人”。他们一只脚踏进了上海,另一只脚却留在了苏州。上海是他们赖以存活的谋生之地,苏州则是他们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他们在谋生的过程中显示出了勤劳、务实、趋利的市民本色,在生活中却追求、向往闲适、优雅、浪漫、脱俗的士大夫作风。无论独处还是群居,他们都竭力地营造一种艺术化的生活情调,不愿意将自己等同于一个俗人。郑逸梅曾以颇为谦虚的口气说:“我这个人,虽不敢谈到风雅,但却自认没有俗骨。”[2]天虚我生在临死前没有忘记强调自己是个名士,他对女儿说:“吾生平为名士,中途不幸溷堕工商界,遂为名人,今还吾干净,仍为名士去矣。”[3]
显然,鸳鸯蝴蝶派作家并不是在具备了现代市民心态的前提下主动选择市民社会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而是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身不由己地滑入了市民社会。他们虽然已经在市民社会中安置自己的人生,成了市民中的一员,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持着传统文人的心态和情趣。进入书局报馆,他们是个卖文为生的职业作家。回到家里,回到内心世界,他们仍然是优雅的士大夫。这就使鸳鸯蝴蝶派作家具有了职业作家和传统文人的双重身份,而他们的双重身份都会给创作带来直接影响。正是这种影响使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女性观念呈现出复杂的局面。传统文人的身份使鸳鸯蝴蝶派作家难以摆脱陈旧观念的束缚;而职业作家的身份则使鸳鸯蝴蝶派作家必须以满足广大市民读者的消费需求为创作宗旨和编辑方针,必须让他们的作品尽量贴近市民生活,这必然会使他们冲破很多陈旧的观念。具体地说,在塑造女性形象时,传统文人的身份会限制鸳鸯蝴蝶派作家对女性形象的想象与渴望,使他们流露出对符合父权制性别体系所规定的女性美德的赞美。但职业作家的身份又使他们在描写女性的行为、语言、心理时尽量贴近市民生活,这种努力能够使他们笔下的人物根据自然合理的逻辑自己活动起来,摆脱作者的控制。因此鸳鸯蝴蝶派作家在某种程度上写出了时代转型时期的女性,写出了她们在礼教逼压下的反抗与挣扎,也写出了她们对自尊、独立以及婚恋自由的追求。这些女性形象已经远远超出了作家的创作意图。另外,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鸳鸯蝴蝶派作家面向市民、贴近生活的创作倾向往往使他们职业作家的身份起到了主要作用,不少鸳鸯蝴蝶派小说客观地描写了夫妻之间的不平等,反映了男性的无理、霸道和女性的悲哀、无奈。然而,当作家结束对故事的讲述,在结尾以旁观姿态审视自己的作品,或编者以旁观姿态对作品进行评价、阐释时,传统文人的身份又浮出水面,因此他们在小说结尾添加的“著者曰”或“编者曰”中又发出了指责女性、偏袒男性的声音。这种声音常常与小说的情节和内涵相矛盾。
职业作家和传统文人这两种身份的影响使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女性观念呈现出层层交错的矛盾和冲突,但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说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女性观念是半新半旧的。因为鸳鸯蝴蝶派作家的这两种身份对创作的影响并不是对等的。总体来说,传统文人这一身份对创作的影响大多处于表层,主要体现在作者明显的创作意图和作者、编者在小说结尾对小说的评价、阐释。而职业作家这一身份对创作的影响则大多处于深层,主要体现在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对故事情节的讲述。比较而言,后者的影响更大。因为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兴趣的往往是生动的形象或贴近生活的故事情节,而不是“著者曰”、“编者曰”或作者创作意图中明显流露出的道德说教。梅兰芳曾把包天笑的《一缕麻》改编成京剧上演,相当轰动。梅兰芳在《缀玉轩回忆录》中谈到这部作品对观众的影响时称赞这部作品“感动了一些家长应允子女要求,解除封建婚约”[4]。徐枕亚的《玉梨魂》发表之后也激起了青年男女对婚恋自由的渴望。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的女儿刘沅颖在读了《玉梨魂》之后对徐枕亚本人顿萌爱慕之心。她主动给徐枕亚写信表明心迹,并冲破了父亲的阻挠与徐枕亚结为夫妻。可见,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女性观念虽然新旧杂陈,但其正面影响还是明显大于负面影响。
[1]王钝根.本旬刊作者及诸大名家小史[J].社会之花,1924,1 (3).
[2]郑逸梅.自说自话[J].永安月刊,1949,(116).
[3]纸帐铜瓶室主.说林凋谢録(一)[J].永安月刊,1943,(50).
[4]梅兰芳.缀玉轩回忆录[J].大众月刊,1943,(2).
The complexity of feminie concept of YUANYANGHUDIE author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identity as professional author and traditional literati.As a traditional literati,they are hard to escape the stereotypes.As a professional author,they have to meet the demands of readers and approach their common lives.This forces the authors to break the stereotype and describe the new feminie images.The authors have to describe the women’s struggle against feudal ethics,their pursuit to self-esteem,independence and long to free love.The identity of traditional literati influences the creating procedure superficially while the identity of professional author influences it significantly.Hence,the positive side of feminie concept of YUANYANGHUDIE authors overwhelms the negative side.
The Feminie Concept of YUANYANGHUDIE Authors
LIU Tie-qu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 541004,China)
I206.5
A
1671-3842(2012)01-0009-05
2011-10-25
刘铁群(1973-),女,湖南攸县人,教授,博士,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小说、女性文学、通俗文学。
责任编辑:张东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