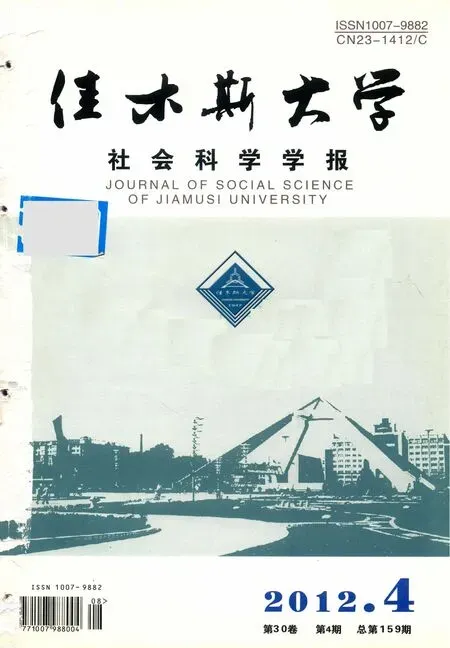沈志远与中国第一部马列主义哲学辞典①
王延华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北京100091)
沈志远与中国第一部马列主义哲学辞典①
王延华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北京100091)
沈志远于1933年编著的《新哲学辞典》是我国首部由国人自主撰写的马列主义专科辞典,该辞书的公开问世,为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和范畴的规范化和系统化做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但由于受时局所限,该书在上个世纪30年代出版以来,并未引起学界及广大读者的广泛关注。本文试图对沈氏辞书《新哲学辞典》的内容和特点加以概述,以期对这部我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首部马列哲学辞书予以公允评析。
沈志远;新哲学辞典;哲学语汇
沈志远是中国现代颇具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在他一生的学术耕耘和社会实践中,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于1933年根据苏俄资料所编著的《新哲学辞典》,是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一部较早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科辞典,这部辞典为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和范畴的规范化和系统化做了最初的铺垫,同时它也与其后出版的《辩证法唯物论辞典》(米定·易希金柯编著,平生、执之、乃刚、麦园合译)、《最新哲学辞典》(M·罗曾塔尔,H·右金主编,胡明译),三部辞典共同为中国现代哲学定位在苏俄哲学语汇上,发挥了特殊的推动作用。
一、沈志远其人
沈志远(1902-1965),原名沈会春,曾用名沈观澜、沈任重、王剑秋,浙江萧山昭东长巷村人。1925年经侯绍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2月,受中共上海党组织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劳动大学学习,期间主修课程是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等。1929年6月毕业后在莫斯科中国问题研究所攻读研究生。在读研期间,沈志远曾在共产国际东方部中文书刊编译处任编译工作,并参加了《列宁选集》(六卷本)的中文翻译与出版。1931年底沈志远学成归国。此后,他先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化运动,后应李达同志邀请,前往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经济系任教。这一期间,沈志远在国统区的白色恐怖下,译、著兼攻,奋力笔耕,先后发表、出版了近200万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著译,成为卓有建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传播者,徐铸成在评述沈志远早期的众多哲学著译时写到:是“当时知识界特别是青年人喜爱的精神食粮……在一代人中,至少是起过启蒙作用的”[1](P92)。建国初期,毛泽东曾在怀仁堂一次晚会上当面称赞沈志远为“人民的哲学家”。[1](P90)
作为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传播者,沈志远的著、译影响广泛,其中,他撰述的《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一书,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一本很有分量的马列主义哲学普及读物。该书自1936年公开问世以来,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广大进步青年的好评。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截止到1951年,该书被再版了15次之多,从中颇可见出该书在当时的受欢迎程度。他翻译出版的米丁《辩证唯物法与历史唯物论》一书,在当时被视为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它对马列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在中国的系统传播,作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罗瑞卿曾深有所感地评价该书说:“读几本哲学书,根据我个人的经验,首推沈志远所译之《辩证唯物法与历史唯物论》比较通俗易懂容易读”。[2](P309)
但有必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沈氏的众多哲学著译中,还有一部在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有着独特历史贡献的哲学著作,这即是沈氏于1933年编著的《新哲学辞典》,该辞书作为我国首部由国人自主撰写的马列主义专科辞典(截止到目前,我国尚未发现有比这部辞典更早的马列主义哲学辞书),它不仅为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和范畴的规范化和系统化做了最初的铺垫,同时它也一定意义上呈现了中国现代哲学由西方哲学向苏俄哲学语汇的逻辑转向,它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时代思潮产生整体化影响后,所附带的学术话语的系统性更新,从这个层面上讲,《新哲学辞典》是具有启蒙意义的。
二、中国首部马列主义哲学辞典:《新哲学辞典》
《新哲学辞典》是沈志远自1931年底从苏联回国后的一部力作。该辞书由北京笔耕堂书店于1933年9月15日出版发行。这部近300页的小型辞书,收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术语、概念、原理及外国哲学人物、学派等词目329条,词目按汉字的笔画排序,每个词头均标有英文括注,释义详尽,有一定深度,涉及的重要引文,也都注明了出处。书后附有中外名词检索和英汉索引,以便于读者查核。总体来看,作为我国首部由国人自主撰写的马哲工具书,该辞书具有以下几大特色:
首先,从该辞书的整体行文来看,体现出了鲜明的马列主义哲学立场;从该辞书整体的行文上看,《新哲学辞典》全书以叙述解释为主,通常先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某一哲学范畴作宏观解析,随后微观地以马恩经典作家或苏俄学者的论语加以引证,有理有据,论述详尽。据笔者统计,在该辞书329条词目中曾直接引用马克思著语4次,恩格斯著语17次,列宁著语15次,普列汉诺夫著语7次,从中颇可见出著者鲜明的马列主义立场。以“时间”范畴为例,沈氏先从唯心论与唯物论两大派别对这一范畴的不同认识入手,写道:“时间,存在的基本形式之一……,从彻底的唯心论观点上看,时间是观念上的东西,时间是思想底产物。恰恰相反,唯物论认为时间是‘存在的基本形式’,因为唯物史观既然承认客观现实之存在,动的物质之存在,同时他就必然地承认时间与空间之客观的实际性。”随后,沈氏用恩格斯和列宁的著语来对上述观点加以引证,补充道,恩格斯曾着重地指出来说,“离开时间的存在,是与离开空间的存在同样地不可思议”。伊利契说的好,“人类的时空概念底变化性,不能推翻时空两者之客观的实际性,正如关于物质结构及其运动形式的科学知识之变化性,不能推翻外界之客观的实际性是一样的。”[3](P136)可见,《新哲学辞典》全书皆在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析哲学专业术语,并以此来重点阐述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等方面的基本内容,行文间马列主义的立场明显。
其次,从该辞书的收词情况来看,体现出了浓郁的苏俄哲学语汇特色;沈志远曾在苏联留学五年,其辞典是根据苏联哲学词典和哲学著作资料而编,是一部体现了浓郁苏俄语汇的哲学辞书。对此,笔者特就《新哲学辞典》与同一时期的几部苏联辞典的中译本进行了比对,包括《辩证法唯物论辞典》(米定·易希金柯编著,平生、执之、乃刚、麦园合译)、《简明哲学辞典》(M·洛静泰尔,犹琴合著,孙冶方译)和《最新哲学辞典》(M·罗曾塔尔,H·右金主编,胡明译)。经比对发现,沈氏辞典与米定·易希金柯编著的《唯物论辩证法辞典》一书相似度颇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沈氏辞典收录的329个词条中,有238个词条是与易氏辞典重合的,重合比率占沈氏辞书词条总数的72.3%;其次,在这重合收录的238个词条的阐释上,两部辞典间参阅、效仿的痕迹也较为明显。以“二元论”范畴为例,沈、易二氏辞典对此词的解释分别如下:
二元论(Dualism)是哲学学派之一,他以二个相反的基本原素为出发点,他把这二个基本原素,看作独立的实质或实体(Substance);就一般所指的说,这二种基本原素就是心灵(或精神,或观念)与物质。二元论之最明显的实例,便是笛卡尔(Descartes)底哲学,笛氏认定物质与精神是二种并立存在的实体。康德底划分宇宙为“可认识的现象世界”与“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Ding-an-sicb)”,也是二元论之一例。[3](P11)
二元论(Dualism,Dualisme,Dualismus)以二种独立而相反的基本原素为出发点的哲学体系,称为二元论。二元论的原著例子是笛卡尔的哲学,他把物质和精神,认为并存的实体。康德把这世界分为认识的现象世界和不可知论的“物自体”世界,这也是二元论。[4](P2)
再来看一个带有浓厚西方哲学特质的词条“先天”,沈、易两部辞典对该词的解释也颇为相似:
先天(A priori)即在经验以前而与经验无关之谓。康德称思维之诸基本形式(如空间、时间、原因、必然等)为先天的。他认为这些思维底基本范畴,都是在经验以前就存在于思维中的,他们都是一切经验之必要的条件。在这一见解上,暴露了康德底主观唯心论思想。[2](P51)
先天的(A priori)即在经验之前,不依据于经验的意思。康德把思维的基本形式(时间、空间、因果性等)称为先天的;他以为这些思维形式,是在经验以前就存在于思维本身里面,它们是一切经验的必要条件。康德的主观观念论,明显的这一点上表现出来。[4](P60)
可见,针对上述词条的解释,无论是在概念的界定还是例证上,两部辞书的阐释都如出一辙,相对而言,沈氏辞书仅是在易氏词条原义的基础上做了细微的词汇上的转换和语句上的调整,行文间效仿的痕迹明显。另据,两部辞书的出版时间来加以推测,易氏辞典是苏联学术界清算机械论及孟什维克观念后的第一部辞典,也即是斯大林权威取得胜利之后的第一部辞典,而此时正逢沈志远在苏联留学,而沈氏个人纯熟的俄文功底又为其阅读苏俄原著提供了语言上的便利,故可大胆推断,沈氏辞书的撰写应是参阅了以易氏《辩证法唯物论辞典》为主的部分苏俄原著,其辞书则一定程度上呈现了苏俄哲学的原貌。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尽管沈氏辞书在撰写的过程中参阅了部分苏俄原著,但该辞书却绝非易氏辞典的中译本,相反,沈氏辞书在原版易氏辞典的基础上也做了一定量的修补,如除两部辞书重合收录的238个词条外,沈氏辞典还新增收录了一些新兴哲学术语和马哲史词目,像幻想观、一致或统一体、安那克西门、伽狄逊等等。而针对部分重合收录的词条解释,沈氏也做了一定的改动,以“本能”范畴为例,沈氏除了参阅易氏对该概念的界定外,还增添了对本能特点的介绍等等。
再次,从该辞书的体系建构上看,体现出了苏俄哲学体系简约化、明晰化特色;由于苏联哲学把哲学范围缩小到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并以此为轴心来建构哲学体系,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等进入辩证唯物主义之中,政治哲学、宗教、美学、伦理学等则进入历史唯物主义之中,因此使苏俄哲学呈现出了一种即简约又非常整一的逻辑体系。而从《新哲学辞典》一书的体系架构来看,该辞书的选词也较具代表性,即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经典性命题为主线,同时兼收少量外国哲学人物、学说、学派等词目,而像哲学体系中相当一些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关系较远的专业术语,如美学、伦理学、宗教学等词目因被归入到上层建筑层面里,而在该辞书中被直接略去,从而使该辞书从整体上看,也呈现出了苏俄哲学简约化、明晰化的体系特色。
最后,从该辞书的词条释义上看,较为稳妥、通俗;从该辞书的词目释义上看,《新哲学辞典》一书观点明确,立场鲜明,词目释义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且有一定的理论深度。而在遇到个别晦涩、生僻的词目时,著者还会附上一些简明、通俗的小例子,从一些平实的日常用语中引申出对高深哲学范畴的解释,于细微之处引见大道理。如在对词目“三段论法”的解释上,沈氏先就三段论法做了一般性的论述,写道:三段论法(Syllogism)或作推理式,即由大前提、小前提与结论三段所构成之推理方式。在前二题中,含有共同之概念,而用此概念为介,结合两前提以成一断案或结论者,谓之三段论。随后附上了“某甲是动物”的小例子来帮助读者对于这一范畴的消化理解,沈氏写道:例如人是动物,某甲是人,故某甲是动物。此处,大前提为“人是动物”,小前提是“某甲是人”,而断案则为“某甲是动物”。总之,《新哲学辞典》是一部语言简明通俗、 容深刻的哲学参考书,它不仅收入马哲方面的基本词目,而且释文比较稳妥、详尽,对人们初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哲学有一定的帮助。
但是,该书中也有不少的错误和不足,首先,在对词目的阐释上,存在释义不够精准和僻陋的地方。如在对“矛盾”的阐释中,只突出了对立面的斗争,不讲求对立面的统一,不承认对立面间的转化,而在对“我”范畴的理解上,将“我”简单解释为人的意识、思维或精神,而忽略了作为物质实体“我”的存在,将“变化”理解为become,只强调了事物的质变,而忽略事物数量、形态方面“量”的变化等等,都有待进一步的修订和完善。其次,由于著者撰写形式的不统一,使辞书中有的注释文字冗长、繁琐,有的则过于简洁、精炼。像该辞书中的词目“唯物论”、“生产力”等都有高达1900字的说明,而像“错综或组合”、“叠语或同语重复”等词目则仅有15个字左右,字数相差悬殊,篇幅长短不一。
当然,书中还存在着个别英文括注拼写上的错误等等。书中的某些缺点带有时代的特征,我们不能过于苛求作者。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看,该辞典作为国内最早的一部由国人自主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辞典,仍是不失为一部学习马列主义思想较好的入门书。
三、《新哲学辞典》:呈现了中国现代哲学由西方哲学向苏俄哲学语汇的逻辑转向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一部适实的哲学辞书则是它所处的哲学时代的合理概括和提升。从哲学语汇的视角看,《新哲学辞典》作为国内首部由国人自主撰写的马哲工具书,它一定程度上呈现了中国现代哲学由以日语新词为导向的西方哲学语汇向以苏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导向的苏俄语汇的逻辑转向,它反映了中国现代哲学从清末到建国初期间的哲学话语语系的变革与重组,从这个层面上讲,《新哲学辞典》是一部有着特殊历史意义的哲学辞书。
中国现代哲学语汇自鸦片战争后可分作两个阶段,其一是西化阶段(1840-1930年),即西方哲学语汇全面进入中国后,并形成自己语汇的定型阶段。主要表现为,清末制度变革中严复译语的出现和随后的日语新词的盛行,而在新兴的日语新词和严译语汇的较量中,日语新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并由此确立了以日语新词为导向的西方哲学语汇的基本定型。中国现代哲学定位在西方语汇之上的哲学体系以辞典的形式呈现了一次系统总结,其代表性成果是樊炳清的《哲学辞典》(1926年)[5](P47)。其二是苏化阶段(1930-1950年),即十月革命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逐步以苏式马克思主义形态被国人所接受阶段。苏式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语系即在于,它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并以此为整个哲学核心,重构了中国现代哲学语汇的核心及其关联语汇。苏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盛行,一方面对以中西对话为主导话语形式的中国现代哲学语汇进行了一次重组,并与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的其他哲学语汇(包括西方哲学)划定了明晰的界线,同时,它也为中国现代哲学语汇的重建划定了基本的范围和方向,即将中国现代哲学定型在以苏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导向的苏俄哲学语汇上。中国现代哲学定型在苏俄语汇之上并以辞典形式呈现出来的最早著作,即是沈志远于1933年编著的《新哲学辞典》。
可以说,中国现代哲学在西方语汇主导下的演变,较为集中地显现在了樊炳清编著的《哲学辞典》里,而中国现代哲学向苏俄语汇主导下的转折,则集中地体现在了沈氏的《新哲学辞典》里,前者达到了西方哲学语汇的尖峰,而后者则划出了由西方哲学向苏俄哲学语汇转向的拐点。但我们也应看到,尽管樊氏辞典将西方哲学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呈现了出来,但它却未能为当代中国提供一个用于快速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有效理论工具,即在这多样而丰富的哲学体系中,哪一类哲学是能用于指导我国实践的,是我们应当仿学和效法的。而以《新哲学辞典》为拐点的苏俄哲学语汇却以其简约性、明晰性,让国人即刻意识到它是什么,有什么用。这对于急于寻得有效的理论工具,并以此工具来快速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国人来说,苏俄哲学显然展现出了更大的理论魅力。而从这个层面上说,《新哲学辞典》作为中国现代哲学由西方哲学向苏俄哲学语汇转向的承转之作,其意义亦是不容忽视的。
[1]沈骥如.沈志远传略[J].晋阳学刊,1983,(3).
[2]李其驹,王炯华,张耀先.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3]沈志远.新哲学辞典[M].北京:笔耕堂书店,1933.
[4]米定·易希金柯.辩证法唯物论辞典[M].平生,执之,乃刚,麦园,译.北京:读书出版社,1949.
[5]张法.中国现代哲学语汇从古代汉语型到现代汉语型的演化[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1).
SHEN Zhi-Yuan and the Chinese First Marxist-Leninist Philosophy Dictionary
WANG Yan-hua
(Postgraduate office of the CPC Central Party School,Beijing 100091,China)
SHEN Zhi-Yuan’s composing“ The New Philosophical Dictionary”which published in 1933 is the fist Marxism-Leninism specialist dictionary which was compiled by the chinese.The public distribution of this dictionary,is benefit for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systematization of early Marxism philosophical concepts and categories in China.However,due to the limited current situation,the book have not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academics and readers since the book was published in the 30 years of last century.The paper try to expatiate the cont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HEN Zhi-Yuan’s dictionary,in order to impartially comment the fist Marxism-Leninism specialist dictionaryof the Marxism development history in China.
SHEN Zhi-yuan;Philosophical Dictionary;phiosophical vocabulary
B0-0
A
1007-9882(2012)04-0031-03
2012-06-20
王延华(1982-),女,吉林桦甸人,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陈如松]
——基于《广辞苑》从有无对应动词形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