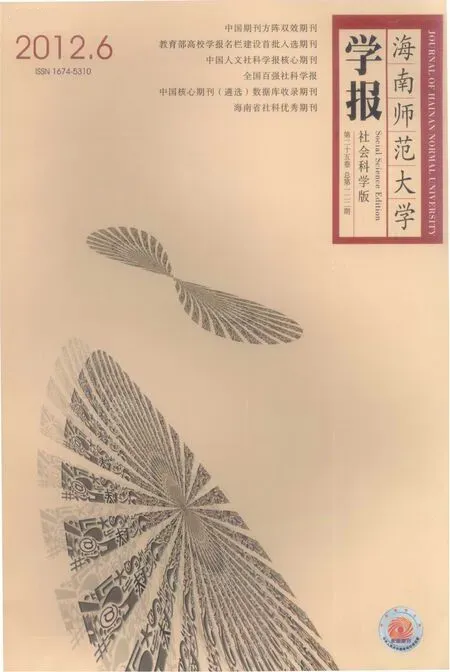政治权力场域与民国左翼“自由撰稿人”作家
张 霞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南充 637002)
政治权力场域与民国左翼“自由撰稿人”作家
张 霞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南充 637002)
政治权力场域中的各种力量与关系,如获得统治地位的权力结构、在朝在野的政党之间的权力争夺、以及其他非主导性的权力结构等,是制约现代作家尤其是左翼“自由撰稿人”作家的重要因素。政治权力场域的控制,让左翼“自由撰稿人”作家队伍逐渐分化,既有投机性的,也有机智应对政治权力场域、坚持左翼知识分子立场的。
政治权力;场域;左翼;“自由撰稿人”作家;制约 ;应对
一
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与发展,自始至终都负载着中国人民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想诉求。在民国时期文学30余年的历史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总是难解难分,政治权力场域成为影响和制约文学发展的重要力量。民国时期的政治权力场域一直处于风云变幻之中。从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权频繁更迭,到20年代后期开始的国共两党的朝野对立,再到日伪政府的出现,直至最后共产党的胜利和建国,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较量此起彼伏,从未停止。正如布迪厄所说:“权力场是各种因素和机制之间的力量关系空间,这些因素和机制的共同点是拥有在不同场(尤其是经济场或文化场)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必要资本。权力场是不同权力(或各种资本)的持有者之间的斗争场所。”[1]263-264在政治权力场域的多元结构中,获得统治地位的权力结构始终和其他权力结构处于对抗和竞争的关系之中。对于前者来说,如果不能有效地掌握和行使国家权力,就很容易被其他权力结构颠覆。在阿尔都塞看来,国家权力的实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并在两种国家机器中进行:一种是强制性和镇压性国家机器,另一种则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前者包括政府、行政机构、警察、法庭和监狱等等,它们通过暴力或强制方式发挥其功能。后者包括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工会、传媒(出版、广播、电视等)以及诸多文化方面(如文学、艺术、体育等)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后者统统以意识形态方式发挥作用。①引自孟登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外国文学》2004年第1期。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种形式,关系到国家权力的维护问题,因而无可避免地要受到政治权力场域的影响和限制。为了掌控文学这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作为政治权力场域中长时期的主导力量的国民党当局,主要是依靠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即通过政府文化管理机构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来约束和规范文学的生产和流通。
1914年,袁世凯政府颁布《出版法》,对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严加控制。袁世凯政府倒台后,国内军阀混战、政权更迭频仍,统治阶级对思想言论的控制相对松懈。这时的政治权力场域对文学的干预较少,现代文学因此在第一个10年中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国民党统治时期,政府频频出台政策法规并成立专门机构干预图书杂志的出版发行,文学的生长空间逐步恶化。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著作权法》。1930年颁布《出版法》,加强了对文化出版的登记、审查和限制,并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1932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增订1929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制定的《宣传品审查条例》为《宣传品审查标准》,把宣传分为“适当的宣传”、“谬误的宣传”、“反动的宣传”,其中把“宣传共产主义及鼓动阶级斗争者”、“宣传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及其他主义,而有危害党国之言论者”,诋毁国民党的“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和“淆乱人心”等等都被视作“反动的宣传”。对这类宣传要“查禁查封或究办之”。[2]1934年又出台《修正图书杂志审查办法》。1938年7月制定《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同年10月在重庆成立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专门负责审查管制全国的图书、杂志、演剧、电影,并指导和考核地方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1940年颁布新的《战时图书杂志审查办法》,1944年又颁布《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禁载标准》,1947年还有《出版法修正草案》出台。在图书杂志的审查方面,国民党设置了严格的程序,如报纸上的电讯和稿件由新闻审查处审查,图书杂志类的稿件,由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剧本则要由戏剧审查委员会和图书杂志审查处共同审查。这些审查机构都直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各省市都有分处或分会。[3]除了制定政策法规、设置层层审查机构外,国民党当局还直接动用警察、侦探等强制性国家机器推行文艺上的白色恐怖,打击破坏左翼文艺运动,抓捕甚至杀害他们认为反动的作家、报人。
菲舍尔·科勒克指出:“无一社会制度允许充分的艺术自由。每个社会制度都要求作家严守一定的界限,比如,为了保护青少年、宪法、人权而绳趋尺步。然而,社会制度限制自由更主要的是通过以下途径:期待、希望和欢迎某一类创作,排斥鄙视另一类创作。这样,每个社会制度就——经常无意识、无计划地——运用书报检查手段,决定性地干预作家的工作。甚至文学奖也能起到类似的作用。”[4]38的确,对出版发行的严厉控制,对图书杂志的严格检查,是统治者加强舆论监督、控制社会舆论最为有效的办法,其根本目标是统一思想、排除异端,从而实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国家政权的维护和巩固。尽管国民党政府出台的各种政策法规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创作、出版的有序和有法可依,但同时也给现代作家的创作、发表和出版造成了极大的阻碍。尤其是书报检查制度,“它与统治、国家权力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系,能够阻碍或改变创作”,[4]37它让许多作家的作品要么被删,要么被勒令修改,要么被禁止出版,对作家的创作、读者的阅读以及信息的流通都构成了极大的制约。如沈从文的小说《长河》,由于“作品的忠实,便不免多触忌讳”而遭遇了坎坷的出版经历,“作品最先在香港发表,即被删节了一部分,致前后始终不一致。去年重写分章发表时,又有部分篇章不能刊载。到预备在桂林印行正式送审时,且被检查处认为思想不妥,全部扣留。幸得朋友为辗转交涉,径送重庆复审,重加删节,方能发还付印。”[5]252尽管饱受书报检查之苦,沈从文在抱怨之后仍能理性地指出:“国家既在战争中,出版物备个管理制度,个人实无可非难。因为这个制度若运用得法,不特能消极地限止不良作品出版,还可望进一步鼓励优秀作品产生,制度有益于国家,情形显明。”[5]252但是,事实证明,国民党对书报检查制度的运用并不“得法”,既没有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也没能限制那些不良作品的出版。书报检查仅仅是国民党当局消灭异己、实行文化专制、维护其政党政权和利益的工具。据统计,1929年至1936年,国民党政府共查禁社会科学类书刊676种,去掉重复统计的,共662种,查禁理由主要是宣传共产主义、鼓吹革命、讽刺政府。[6]而在同一时期内,被国民党当局先后查禁的文学作品有309种,其中最多的是左翼作家的作品,如蒋光慈的作品12部,几乎包括他出版的全部小说;鲁迅的作品8部(包括翻译);郭沫若的作品11部。[7]
尽管采取了方方面面的文禁措施,但总体上看,国民党政权对文学这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利用很不成功,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的勃兴和国民党推行的“民族主义文艺”的失败,就是很好的例证。
二
国家机器之外,在朝在野的政党之间的权力争夺,同样构成政治权力场域制约文学创作的重要方面。在三四十年代的政治权力场域中,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政权作为一股强劲的政治力量,与当权的国民党一直处于对抗之中。由于文学具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性质,“朝野都有人只想利用作家来争夺政权巩固政权”,[8]作家就成为双方争夺的一个重点。共产党对作家积极争取,国民党却对作家实行暴力专制。在这样的政治权力场域关系中,左翼作家尤其是有左翼倾向的“自由撰稿人”作家受到的制约就更为严重。
1930年初,“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以及鲁迅、郁达夫、茅盾、郭沫若等众多著名作家的支持,中国左翼文学在30年代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尽管没有合法的权力资本,缺乏经济资本的支撑且饱受政府当局压制,左翼文学却凭着其反叛与革命的激情,对很多初登文坛、向往革命的文学青年构成了强大的吸引力,很多青年作家都在30年代初加入了左联。左联是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核心机构,它虽然在组织上受共产党的领导,在经济上却并没有相应的经费来源,其日常经费主要来自成名作家的捐助。如鲁迅每月捐助左联20元,茅盾每月捐助左联15元。在每月定额的20元之外,鲁迅有时还要给予左联一些额外的资助。左联的刊物大多维持不久,除了政府当局的压制,也与经费有限有极大关系。胡风曾这样描述左联的办刊情况,“照例是,谁弄到了一点钱,也不过一、两百元的数目,想出刊物,发表他们自己的,不能或不愿在大刊物上发表的作品”,[9]50“这种刊物总是出过一两期,钱完了,刊物也被禁止了。”[9]51左联的经济运作状况说明,这个组织并不能为加入其中的作家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已经成名的左翼作家尚能偶尔谋得其他收入,①1933年7月,田汉、阳翰生开始担任上海艺华影业公司总顾问,月薪200元左右。1932年夏天,郑伯奇、钱杏邨、夏衍开始担任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的编剧顾问,每月有车马费50元。不久后,夏衍、周扬又担任艺华影业公司的编剧顾问,每月车马费30元。见陈明远:《文化人与钱》,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116页。1933年至1934年10月,胡风曾担任中山文化教育馆《时事类编》半月刊的日文翻译,只上半天班,月薪100元。见胡风:《胡风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但这类收入不一定能长久维持;那些初登文坛的左翼青年作家,如柔石、胡也频、丁玲、艾芜、叶紫、关露、戴平万等人,大多都来自社会底层,没有固定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生活极其贫困,卖文为生就成了他们惟一的生存方式。因此,可以说,无论名气大小,写作都曾经是大多数左翼作家谋生的主要手段。也就是说,左联存在期间,大多数左翼作家都曾经有过卖文为生的经历,曾经是“自由撰稿人”作家。
左翼“自由撰稿人”作家卖文为生的写作环境极为艰难,不仅受到文化生产场域的制约,而且还要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残酷压制。30年代,国民党政府的一系列文禁措施主要就是为了打压左翼文艺运动,“书店一出左翼作者的东西,便逮捕店主或经理。”[10]作为政治权力场域中占主导性地位的政治力量,国民党当局禁毁书籍、查封报刊书局、删改送检文章,动用各种行政手段来控制文化生产场域,压制、破坏左翼作家的创作,甚至直接以残酷的暴力手段逮捕、暗杀左翼作家。因为有左翼倾向,作品被检查和被禁的可能性就越大,如鲁迅所说:“禁期刊,禁书籍,不但内容略有革命性的,而且连书面用红字的,作者是俄国的……也都在禁止之列。”[11]而作为“自由撰稿人”作家,面临着生活的压力,要卖文为生,就必须要让作品得到发表和出版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左翼“自由撰稿人”作家只能想尽办法去应付政府机构的书报检查。“既要革命,又要吃饭,逼得大家开动脑筋,对抗敌人的文化‘围剿’,于是有各种办法想了出来:化名写文章;纷纷出版新刊物;探讨学术问题;展开大众语、拉丁化问题的讨论;再就是翻译介绍外国文学。”[12]这印证了布迪厄的判断,即:“艺术家和作家的许多行为和表现(比如他们对‘老百姓’和‘资产者’的矛盾态度)只有参照权力场才能得到解释,在权力场内部文学场(等等)自身占据了被统治地位。”[1]248茅盾上面那段话也最能说明,政治权力场域中的统治力量对文学这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掌控和干预,是如何地制约着左翼“自由撰稿人”作家写作的内容和方向。
除了占主导地位的国民党权力结构外,政治权力场域中的其他权力结构同样是制约左翼“自由撰稿人”作家创作的重要因素。在生存空间极其逼窄的情况下,左翼“自由撰稿人”作家还要接受来自共产党方面的权力与组织的规训。众所周知,左联的实际领导权主要是把持在钱杏邨、周扬等党员作家的手里。他们直接把共产党革命的群众运动模式移植到左联这一文学组织中来,对左翼“自由撰稿人”作家的创作和生活进行直接的干预。要求他们在写作上不仅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表现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而且还要表达革命必胜的理想,用以鼓舞现实革命运动。在创作之外,左联还要求左翼“自由撰稿人”作家参加集体性的政治活动,如参加游行示威、飞行集会,粘贴标语、散发传单等等,以此来张扬他们的政治身份。1932年3月,左联秘书处印发了《和剧联及社联竞赛工作的合同》,其中第八条要求左联盟员至少得动员到全体2/3参加示威,每次散发宣言1000份。而是否参加这类集体活动以及在活动中的表现如何,成为左联考查盟员和准备加入联盟的积极分子的一项重要的指标。[13]左翼的党员领导者所贯彻的共产党方面的权力与组织的规训,不仅让左翼作家失去了从容创作的可能,而且还直接把手无缚鸡之力的他们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使他们随时都面临着被捕和死亡的危险。对于这种阵营内部的权力干预,很多左翼“自由撰稿人”作家都不以为然。如茅盾就经常不参加所谓的飞行集会,而蒋光慈甚至还因此闹到宣布退党。蒋光慈的挑战政治权威给他带来了严酷的政治打击,不仅作品遭到批判,还被开除了党籍。抗战后,有不少左翼“自由撰稿人”作家投奔延安,延安工农革命政权在接纳了他们的同时,也规定了他们的写作界限。而延安实行的供给制的分配方式,则直接终结了这些作家卖文为生的生涯,进而改变了他们以往的言说方式。同样,日伪政府作为抗战时期政治权力结构中的一元,其文化统治对于身处其中的左翼“自由撰稿人”作家,也有极大的影响。40年代,左翼“自由撰稿人”作家或者韬光养晦,或者离开上海,与日伪政权统治上海时只允许文学作品粉饰太平也有极大的关系。这些文学现象无一例外地证实了布迪厄关于文学场和权力场之间的关系的判断:“文化生产场在权力场中占据的是一个被统治的地位:……艺术家和作家,或更笼统地说,知识分子其实是统治阶级中被统治的一部分。他们拥有权力,并且由于占有文化资本而被授予某种特权,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占有大量的文化资本,大到足以对文化资本施加权力,就这方面而言,他们具有统治性;但作家和艺术家相对于那些拥有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人来说又是被统治者。”[14]
三
政治权利力场对文化生产场的控制,让左翼“自由撰稿人”作家在应对的过程中逐渐分化。一些左翼“自由撰稿人”作家放弃左翼的政治文化理念,在政治权力场的压制之下转而寻求市场利益的最大化。这种投机性的人物,在每一次运动中都会出现。就像“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中的投机者“只不过是拿谈新文化运动当作职业,自己并不信仰,更不用说身体力行了”[15]一样,这些投机者打着左翼作家的旗号,把作品打上左翼的商标以增加卖点,却不见得真正信仰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他们的作品虽然染有时髦、先锋的革命色彩,但这不过是吸引读者的噱头,他们的创作在本质上与大多数通俗小说作家的创作并无区别,都是一种纯粹的商业化写作。他们的投机革命运动和投机文学,自然逃不过其他真正信仰无产阶级文学的左翼作家的犀利眼睛。比如,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发言,就明确告诫左翼作家不要把文学当“敲门砖”,等功成名遂,即弃之不顾。[16]柔石也曾指出有些革命青年“于文学,只说卖钱。一边他们相信自己是天才,一边又不肯去坚毅地做,只说将来是没有人读长篇小说与长篇诗的,我们不必再做;谁做,谁是呆子!……饭是要吃的,人不能饿死,我知道;但他们却说‘有跳舞热’,‘打小麻将’,听来真不舒服”![17]这些革命作家抱着投机性的目的,要么在获得名利之后,便不知所踪;要么一遇到压迫,便显露原形,走向革命的反面,成为统治者的爪牙和帮凶。如张资平、杨邨人之流。由于其投机性,这类左翼“自由撰稿人”作家卖文为生的生涯一般都不长久,文学方面的成就也大多无足称道。当然,真正以唤起民众、改造中国为理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左翼“自由撰稿人”作家,在政治权力场域的压制之下依然不改其本色。这些左翼“自由撰稿人”作家始终坚持启蒙式的写作,在以文学谋生的同时,又对文学的精神影响力寄予了厚望,把文学作为思想启蒙、革命启蒙的利器。无论对革命还是对文学,他们的态度都是严肃而真诚的。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在以文学谋生、以文学宣传思想与革命的同时,能够积极应对政治权力场域的限制,力争保持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
作为左联的精神领袖和从事启蒙式写作的左翼“自由撰稿人”作家的代表,鲁迅在应对政治权力场域的制约方面,就显示了机智的斗争策略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鲁迅“自由谈”杂文的成功,就是鲁迅积极应对政治权力场域,在国民党当局严密的文网控制之下,改变言说方式从而机智表达个人洞见的结果。
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勃兴引起了政府当局的恐慌。国民党政权为了维护、巩固自己的统治,采取种种文禁措施,控制公民的言论自由。作为“自由撰稿人”作家,书报审查制度直接影响着鲁迅的收入和生存。他在致日本友人的信中说,“对文坛和出版界的压迫,日益严重,什么都禁止发行,……我的全部作品,不论新旧,全在禁止之列。当局的仁政,似乎要饿死我了事。可是,我倒觉得不那么容易死。”[18]在1934年2月24日致曹靖华的信中也谈到,“上海靠笔墨很难生活,近日禁书至百九十余种之多,……但书局已因此不敢印书,……杂志编辑也非常小心,轻易不收稿。”[19]面对国民党残酷黑暗的文艺专政,鲁迅仍然保持着清醒的理性。他反对赤膊上阵,作无谓的牺牲,继续坚持“韧”的战斗精神。为了应对政治权力场域的限制和言论环境的不自由,鲁迅积极寻找钻网的法子,以突破文网的限制,尽可能地获取言说的空间。援引新闻材料入文、隐曲表达、经常更换笔名,是鲁迅应对文艺专政而改变写作策略、获得言说空间的主要方法。
鲁迅喜欢以“抄新闻”的方式来进行社会写实和时事批判。这既是为了照顾报纸的风格需要,也是鲁迅应对文学检查的重要方法。他曾说:“从清朝的文字狱以后,文人不敢做野史了,如果有谁能忘了三百年前的恐怖,只要撮取报章,存其精英,就是一部不朽的大作。”[20]鲁迅的“自由谈”杂文就称得上是一部“撮取报章,存其精英”的不朽大作。既然当局设置了重重的文网,那么就只能拿报上的新闻材料来说事了。鲁迅认为:“只要写出实情,即于中国有益,是非曲直,昭然具在,揭其障蔽,便是公道耳。”[21]援引新闻材料,更能“写出实情”,从而“于中国有益”;进行评论,“揭其障蔽”,也就更能呈现“是非曲直”,见出杂文的批评效力。面对政府当局对言论自由的限制,鲁迅以“抄新闻”的方式批评时政、成功“钻网”,既及时地表达了自己的洞见,又有效地拓展了自己的言论空间。
除了援引新闻材料外,鲁迅的杂文在行文中还特别注重语言表达的隐曲。在《南腔北调集》的“题记”中,鲁迅说:“《语丝》早经停刊,没有了任意说话的地方,打杂的笔墨,是也得给各个编辑者设身处地地想一想的,于是文章也就不能划一不二,可说之处说一点,不能说之处便罢休。即使在电影上,不也有时看得见黑奴怒形于色的时候,一有同是黑奴而手里拿着皮鞭的走过来,便赶紧低下头去么?我也毫不强横。”[22]在应对政府当局的书报检查方面,鲁迅既要发表文章,又要替报刊和编辑考虑,因此,他“毫不强横”,而是避其锋芒,“可说之处说一点”,并着重在“怎么写”上下功夫,迂回表达文章的意旨。1933年5月25日,《自由谈》编者迫于形势,曾经刊出启事,说,“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对此,鲁迅指出:“想从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好的,风雅之至,举手赞成。但同是涉及风月的‘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呢,这不明明是一联古诗么?”[23]在鲁迅看来,想从题目或题材上来限制作家的言论指向,根本就不可能。任何材料,都可以拿来做思想的载体,其关键在于“怎么写”。鲁迅收在《准风月谈》中的杂文,谈历史、文化、典故、洋人、文人、生活现象、儿童教育,题目和题材可谓五花八门,似乎都不关中国的社会时政,但文章的意旨却又无不与之息息相关。在艺术方面,比起《热风》时期的哲理化和《华盖集》时期的论辩色彩,这些文章明显地更趋隐晦曲折。鲁迅历来就反对杂文太直白,认为“猛烈的攻击,只宜用散文如‘杂感’之类,而造语还须曲折,否,即容易引起反感”。[24]运用隐曲的文笔寄托深沉的意蕴,是鲁迅杂文常用的艺术表达方式。在严密的文网之下,鲁迅的“自由谈”杂文更是经常采用戏仿、拼贴、反语、借代、比喻、象征、暗示、双关等叙述策略和修辞方法,以曲折隐晦的方式来实现对社会时政的批判和揭露。这些杂文大量运用曲笔,既能有效地逃过文艺检查官的眼睛,又能以“言外之音”的形式发人深省,给人以“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感受,从而具有了含而不露、委婉曲折的艺术风格,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经常更换笔名,也是鲁迅应付书报检查的重要方法。鲁迅一生共使用笔名140多个,1932年至1936年间使用的笔名就达80多个,[25]其中尤其以投稿《自由谈》期间使用的笔名最多。1933年5月25日《自由谈》的编者刊出了“多谈风月,少发牢骚”的启事以后,鲁迅投稿所用的笔名就更有20个之多。[26]在《准风月谈·后记》中,鲁迅说,“这六十多篇杂文,是受了压迫之后,从去年六月起,另用各种的笔名,障住了编辑先生和检查老爷的眼睛,陆续在《自由谈》上发表的。”[27]鲁迅非常理解报刊杂志及其出版事宜,经常变换笔名,能分散书报检查官的注意力,不给刊物和编辑招来麻烦,从而尽可能地获得发表言论的空间。
鲁迅积极应对政治权力场域的限制,不仅反抗强权的压迫,而且还时时警惕政治权力场域中的各种势力对作家独立人格的侵蚀,难能可贵地保持着知识分子不懈的社会思考和精神探索。在上海的最后5年中,鲁迅身处严酷的政治文化环境却依然保持自己的独立精神,以“横站”的方式对付敌人和友军射来的冷箭。他那些犀利泼辣的杂文和形式新颖、内涵深刻的历史小说,以思想启蒙和社会批判为己任,批判专制与不公,揭露一切的瞒和骗,不仅体现了一个作家的文学才华与社会担当,还体现了一个经济自主、精神独立的“自由撰稿人”作家对知识分子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的坚守。王富仁认为,左翼文学可以以鲁迅、胡风、李初梨与郭沫若、周扬等四类人物为代表分为四个层次。不管他这种划分是否合理,他指出鲁迅之所以是左翼文学中的一个特殊的层次,原因在于鲁迅一直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而“坚持着一种社会的批判”,[28]可谓真知灼见。而作为左翼“自由撰稿人”作家,鲁迅能够以“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和立场而实现其社会批判,与他应对政治权力场域的机智不无关系。
[1]〔法〕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M].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2]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524.
[3]光未然.蒋介石绞杀新闻出版事业的真相[C]//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北京:中华书局,1956:92.
[4]〔德〕菲舍尔·科勒克.文学社会学[C]//张英进,于沛.现当代西方文艺社会学探索.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
[5]沈从文.《长河》题记[C]//刘洪涛.沈从文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252.
[6]国民党反动派查禁676种社会科学书刊目录[C]//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北京:中华书局,1955:205-254.
[7]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19-120.
[8]沈从文.再谈差不多[C]//刘洪涛.沈从文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42.
[9]胡风.胡风回忆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10]鲁迅.320911致曹靖华[M]//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27.
[11]鲁迅.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93.
[12]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235.
[13]曹清华.左联组织框架中的左翼作家身份[J].深圳大学学报,2006(2).
[14]〔法〕皮埃尔·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迪厄访谈录[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86.
[15]新人社·编者说明[C]//张允侯.五四时期的社团:第3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208.
[16]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42.
[17]赵帝江,姚锡佩.柔石日记[C].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107.
[18]鲁迅.331114致山本初枝[M]//鲁迅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70.
[19]鲁迅.340224 致曹靖华[M]//鲁迅全集:第13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0 -31.
[20]鲁迅.再谈保留[M]//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55.
[21]鲁迅.340125 致姚克[M]//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7 -18.
[22]鲁迅.南腔北调集·题记[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27.
[23]鲁迅.准风月谈·前记[M]//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99.
[24]鲁迅.250628致许广平[M]//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00.
[25]林贤治.鲁迅的最后十年[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75.
[26]许广平.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51.
[27]鲁迅.准风月谈·后记[M]//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02.
[28]王富仁.关于左翼文学的几个问题[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1).
The Field of Political Power and the Left“Freelancer”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ZHANG Xia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Xihua Normal University,Nanchong 637002,China)
Various forces and relations in the political power field,such as the ruling power structure,the contention for power between political parties in or out of power,and other non-dominant power structures,etc.are major factors restricting modern writers esp.the Left“freelancers”.The control of the political power field has caused the gradu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Left“freelancers”,some of whom become speculative while others managed to persist in their Left standpoint by responding to the political power field resourcefully.
political power;the field;the Left;“freelancer”writers;restriction;response
I206.6
A
1674-5310(2012)-06-0007-06
2012-07-16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民国历史文化框架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编号:SKGT201105);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民国社会历史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框架”(编号:12AZW010)
张霞(1976-),女,四川邛崃人,文学博士,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毕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