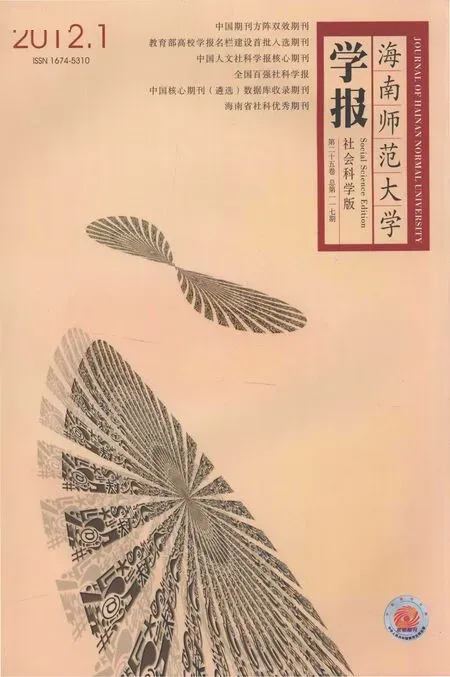文化异质的析出与翻译策略
单文波
(湖北大学外语学院,湖北武汉 430062)
文化异质的析出与翻译策略
单文波
(湖北大学外语学院,湖北武汉 430062)
异化翻译法有利于促进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丰富本民族语言的的表达。这是翻译的核心所在。另一方面,如果在翻译中,特别是在文学翻译中如果压制语言之间本身的不同,就会剥夺异域读者以另一种方式体验陌生世界的权利,这就意味着读者永远受制于包围自己的熟悉感和习惯性。同时采用异化策略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抵抗式翻译,以助于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体现他者的声音。中国翻译者们应该承担起一个新的历史使命,那就是如何在翻译过程中有效地抵制西方文化霸权以保护中国文化,抵抗英美主流语言文化价值观对他者话语的凌驾,让英美读者见识乃至接受他者的价值观。值得深思的是,国外的翻译家以及报刊已经使用异化策略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以及新词了。所以,异化代表了世界翻译的总趋向。
翻译策略;归化;异化;文化交流;殖民抵抗
一 文化全球化趋势与翻译
数字化和信息化将人类带入了一个文化全球化的时代,其结果就是人类文化相互交流、碰撞、相容和兼收并蓄,而“文化的冲突与共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的互动作用。因此如果协调得好,这种冲突可以制止或压缩到最小程度。因此未来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主要是讨论和对话关系,通过对话而达到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共融。而能够让人们相互了解和共融的最佳途径则是通过翻译作品来了解异域文化。”[1]
中外学者对翻译下过各种各样的定义,劳伦斯·韦努蒂对翻译曾作出重要定义——翻译是外来形式及意义的一种阐释,这里的阐释当然包括文化内容及形式的阐释。翻译即译意,奈达之言也可谓一语中的。奈达的翻译理论走过了如下的发展阶段:从1959年到1969年的交际理论阶段,从1970年到现在的社会符号学阶段。他把翻译中的文化问题摆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对一个译者来说,由文化差异引起的问题比语言结构差异引起的问题要多而且更为复杂”。[2]此前,泰特勒也提出如不能再现原文的思想内容,也就失去了翻译的意义。原文的思想内容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原文提供的信息和文化。当代英国译学家苏珊·巴思内特(Susan Bassnett)曾把语言比喻为文化有机体中的心脏,“如同在做心脏手术时人们不能忽略心脏以外的身体其他部分一样,我们在翻译时也不能冒险将翻译的言语内容和文化分开来处理”。[3]张今先生的定义尤为惹人注目:“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工具,它的目的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要把原作品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象或艺术映象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中译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4]
看来,不管中外的学者都是非常重视翻译研究的文化问题。尤其张今先生对翻译的定义涉及到翻译的本质是促进不同的民族文化交流,“在语言的交际过程中,两种不同的国家或民族的人能否相互沟通,不仅取决于他们对语言本身的理解,而且取决于他们对语言所负载文化蕴意的理解,因此,……主张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翻译。”[5]
同时,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桥梁正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张柏然先生在论述全球化语境下的翻译理论研究时谈到“人类翻译学史经历了神化与习俗的时代,哲学时代和语言科学时代,21世纪伊始即出现文化转向的端倪,步入文化时代。基于此,21世纪中国翻译学应该站在对20世纪乃至有史以来中国及世界各国翻译学传统进行文化批判的基础上,对现实的翻译问题进行文化(全球化)的分析,探求与(全球化)新文化发展相符合的翻译”。[6]
总之,在翻译中如此重视文化研究的今天,如何在目的语译文中处理源语中的文化价值便成了翻译中的重中之重。而将翻译研究纳入广义的文化研究认知思辨之中即将翻译置于探讨文化交融的大范畴这一翻译的本质之中,而非将其局限于“形而下”即只是单纯字、词等符号转换之中才是翻译之道。
二 文化翻译中异化策略
当今翻译的策略无外乎有两种:归化和异化。归化追求的是使译文符合目标语语言及文化的规范,使译文的表达方式趋于自然,满足目标语读者较少求新求异的阅读要求,旨在让读者安居不动。异化则是指以源语为归宿,使译文的表达方式保留原文特色。翻译的目的是使每种文化都充分吸收和借鉴其他文化的异质成分。而异化能把异域文化中的信息尽可能保留原貌地呈献给读者,大量文化异质的析出能使读者产生各种聚合和裂变,从而推动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
(一)文化翻译中异域文化因素的传递
无论是旨在向中国读者介绍异域文化的外汉翻译,还是向世界传播华夏文化的汉外翻译,要成功地实现翻译的跨文化交流功能,就不得不在翻译的策略上作出精心选择,如:英语短语fish in the air,其意思是“做不能成功的事情”,因而以归化译法将其译为“水中捞月”能够十分准确地表达其命题意义,但这样处理却截流了原语文化的背景信息,使汉语读者无法了解到在海洋国家中生活的人们心目中“鱼”的地位,剥夺了译文读者的知情权。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原则即异化可能运用得越来越广泛,最终将取代归化。因为异化能更多地保留源语文化的异域情趣,更加忠实于原文,更重要的是从异族文化中可以反观自身,从而获得更高文明的层次升华。
早在20世纪30年代,鲁迅在谈到文学翻译时提出过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7]后来有学者将“洋气”看作“西化”,如叶子南论道,“人们一般认为,翻译中的西化译法常常造成译文晦涩难懂,因此,从事翻译实践的人把以译入语为依归的归化译法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8]20 世纪 50、60 年代,傅雷提出了“神似论”,即“求神似而不求形似”,并不主张在译文中尽量保留异国语言和文化的差异。钱钟书也提出化境论,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9]换句话说,译文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国外归化的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Eugene A.Nida。他认为应该把读者放在首位,要求“译语中的信息接受者的反应应该与源语接受者对原文的反应程度基本相同”。[10]他经常举的例子是 to grow like mushroom与汉语的“雨后春笋”所提供的信息是对等的,所以在形式和功能之间,奈达最终认为功能是主要的,形式是次要的。在翻译中没有必要让对方费力地去理解和接受文化内涵的差异,用本民族的表达法一代了之即可。这些观点对于译文要归化产生了很大影响。
然而极度的归化译法会抹去源语许多风格、艺术、文化的特征,从而影响译文真正的价值。像傅东华30年代翻译的《飘》中,人们找不到嘉丽、瑞德船长,遭遇到却是郝思嘉、白瑞德这些中国味十足的名字,书中的其他人名和地名也都中国化了。如果在世界文化交流的大环境下重新审视张谷若先生翻译的《苔丝》,在读者读其译著感到顺畅的同时,是否感觉到多了点什么和少了点什么呢?例:
Some had beautiful eyes,others beautiful nose,others a beautiful nose and figure;few,if any,had all.
译文:她们里面,有的美目流盼,有的鼻端端正,有的按唇巧笑,有的身材苗条;但众美兼备的固然不能说没有,却少得很。
笔者感到读完以后,多的是感觉到远在英国威塞克斯的美人们也是樱桃小嘴,身材骨感,莫非彼时千里之外的英国人和中国人的审美观一样?中国的审美观是不是权利太大了呢?少的是张老没有深入研究当时英国人的审美观,少了份自然。张译作中的关于人名和地名的处理也进行了明显的归化处理。如将Felix译成“裴利”,Cubid译成“寇壁”,Shaston译成“沙氏屯镇”等,这些翻译就没有使译作和读者之间构成一种距离美,使人感觉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中国的某个地方,毫无异域感可言。
再如:哈葛德的爱情小说“Joan Haste”有蟠溪子和林纾两个译本,蟠译本中或省略了许多原作中与中国伦理道德文化相抵触的描写,或将其中国文化化。而林纾在其翻译中再现了被刻意删去了的情节和词语,成了一部描写西方爱情的作品,被曲解了文本的整个文化得到了恢复,被移植进了中国文化,这才起到了文化交流的作用。[11]另如《红楼梦》所包含和反映的整体文化以及它植根于其中的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文化,当它译成英语时,还应保持这个文化。如果按照归化论的提法,那么在汉译英时,《红楼梦》中的中国文化岂不是要翻译成英国的某个文化,这显然有悖于翻译的目的。那么异化的翻译要求译本尽量保留源语的语言和文化特点,借此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让读者了解异国风情、文化及语言特点,以弥补本民族文化的不足,以丰富本民族语言的表达法。再看为了贯彻向目的语读者输入汉语表达方式,旨在让译语读者有所了解汉语的文化内涵,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在翻译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时则更多地采取异化的方法,历史证明这个译本英语的可读性、可接受性在海内外得到普遍赞誉,是汉译外的经典范本。请看其中几例:
癞蛤蟆想天鹅吃
A toad hankering for a taste of swan
更有一种风月笔墨,……
Even worse are those writers of the breeze-and-moonlight school…
成者王侯败者贼
Such people may become princes or thieves,depending on whether they’re successful or not.
以毒攻毒,以火攻火
Fighting poison with poison,and fire with fire.
在译本中,杨戴夫妇采用异化策略,保留了源语文化的因素来宣扬中华文化,也实现了其面向特定的西方读者传达汉语表达式中所蕴涵的文化信息之意图,使原作品实际包含的种种内在意蕴从各个方面得以充分发展,得到逐步扩大和不断深化。
可以肯定,随着汉文学英译文本的增多,西方学界肯定会形成一种中国英语的特别文学风格。
(二)读者审美进步的需求
文学作品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内容与形式的“异化”来打破和更新重组读者原有的认知图式,那么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仍应具备这种功能,保留其“异”的成分;同时,文艺理论中的陌生化理论也支持“异化”论,陌生化作为一种艺术手法是俄国形式主义核心人物什克洛夫斯基首先提出,在西方学术界影响很大,它是指作为一种艺术手法,作家、诗人用新奇的创作手法,使所表现的客体在接受者那里显得陌生,从而达到一种新鲜的美感。而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创作,在对文本中新奇内容的表达上与文学创作活动有一定的类似性,因为文学翻译也是对文化“他者”的传达和转化过程,其目的是“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石头更其成为石头”。[12]陌生化能打破“自动化”的束缚,使读者获得异域文化的审美感受和愉悦。“同一类型的读者群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随着文化交流,翻译活动的深入,对异化的消化程度也呈逐渐加深的趋势,”原本认为“异化”的译文已被译入语读者所普遍接受。[13]陈志杰用高斯曲线描述了归化和异化比值之间的关系:“异化的趋值趋向于零,归化和异化的比量永远处于变化中。”[14]
翻译史告诉我们:外来词语特别是那些含有独特文化的外来语初次进入译入语,难免有陌生之感。但有些生硬的洋话,经过时间这个熨斗熨来熨去,也渐渐变得自然了。看一看那些我们曾经陌生的词句:“条条大路通罗马”、“一石二鸟”。现在我们已经把它们看成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了,谁会认为它们曾经是异化的词语,谁又会用“殊途同归”和“一箭双雕”去替代它们?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自两汉之际,东渐来华,历两千年漫长岁月,这本属完全不同质素的语言文化系统,已深深植根于中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十分深刻和广泛的影响。当我们谈起“一丝不挂”、“十八罗汉”或“三头六臂”时,我们不会去考虑它们来源于佛教。正是因为文化有其极高的渗透性,可凭借社会生活的契机进入其他文化,并依靠那里的文化环境维持着自身的生命力,才使得这些含有特定文化内涵的特殊表达方式深深扎根于译入语。同时,文化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而不是“闭关自守”,其具有不可估量的吸纳和包容能力。源语文化的新鲜事物的“异化”很容易被目的语文化的人们所接受,并逐渐约定俗成,吸收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也正是因为文化的这些特殊属性,说明了译者在翻译时完全可以适当地采取异化的方法,给译入语读者一点新鲜感,一点陌生感。异化的办法确实显示出其导入异域风情和照顾原文作者的独到之处。综上所述,文化的特殊属性给译者采取异化译法提供了可行性。与此同时,翻译中以此代彼,以我代人,在不少情况下既不合适,也“代”不了。不同文化间的翻译,如果任意拿自己的东西去代替别人的东西,把一种异质的文化“血液”输入到另一种文化的“血液”中去,这无异往人身上输羊血,得到的不是文化交流,而是文化“凝血”。译者也无权为了产生“等效”而随意改动形象。[15]
尤其是在今天中国处于向国外学习科学文化的开放时期,人们的文化素质较之以前大有提高,他们已不再满足译文的归化和通畅,而要更多地了解陌生的异域情调,这也可以作为译入语的“文化参数”(parameters),是对源语文化进行异化的重要依据。1995年,由南京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举办了关于《红与黑》几个译本意见的调查,虽有读者赞成归化的译文,但大多数读者认为阅读外国文学原著译本目的是通过译作欣赏原作特有的味道,若译文完全归化,则缩短了读者的审美感知历程。
诚然,归化译法会降低读者接受原文的难度,但会影响译文的充分性,使读者产生错觉,这在一定程度上欺骗了读者。在当今全球化、一体化不断发展的今天,人们的思维逐渐深化,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及自身素质也不断提升,他们对译文并非被动接受,而是更愿意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自己的知识去理解文中的“异”。如果译者仍然像保姆一样,照顾读者过周,恐怕读者非但不领情,还有讨厌译者的可能,读者渴望的是富存异国风味,洋腔洋调的译文,开阔眼界,增长知识,熟即俗。为了避免“俗”,译者应该主动接受陌生化的冲击,要给汉语和中国文化带来一股股活水,使其保持生机,常葆青春。译者绝对不能将汉语和中国文化牢牢地保护起来,使其边缘化,倘若此,他将成为“千古罪人”,中国读者是万万不会答应的。所以,译者要树立强烈的读者意识,树立为读者服务,为汉语服务,乃至为中国文化服务的态度。
(三)文化翻译中的去种族化
“五四”时期的中国人林语堂一生致力于中西方文化交流,可惜他在强势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放弃了自身的文化传统并将其边缘化,没有把汉文化同西方文化放在平等层面上进行对话,当时弱势的中国文化成了一种“打了折”的文化(discounted culture)。据崔永禄先生分析,霍克斯英译《红楼梦》时,将本国文化凌驾于中国文化之上,不接受外语文本中异于自己文化价值的异质,多采用归化翻译策略。这不仅是霍克斯一个人的做法,其他西方人翻译中国作品或处于弱势文化地位国家的作品时也有类倾向。[16]这种倾向就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采用归化翻译策略,拒绝弱势文化“陌生”之处的强烈过滤现象。[17]
“跨文化交际翻译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避免弱势文化被忽视,被肆意践踏和阉割,被压制或被歪曲利用,从而追求一种各民族间、各文化传统间的平等对话,努力建立国际交流的伦理规范,约束非理性行为,从而促进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相互吸纳和配合。”[18]随着解构主义理论的兴起,归化式翻译理论遭到了以Venuti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的批判,他们提出解构主义,反对译文通顺的翻译策略。无独有偶,2004年外研社出版的《新世纪汉英大词典》中,编者注重保留汉语词汇的文化意象,联想意义以及汉语特有表达方式的传递,多使用异化法翻译具有强烈文化色彩的词。考虑到“龙”和dragon联想意义的不同,在翻译有关“龙”的词汇时,一些译者常采取归化的策略,消解汉语词汇的文化特色,使汉语词汇的文化意象不见踪影。而该词典则利用了异化翻译策略尽量向英美读者传递“龙”的积极联想意义。如该词典大胆地将“望子成龙”译为long to see one’s son become a dragon.“龙马精神”译为vigor of a dragon horse,这不能不说为如何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差异作出了表率。Venuti也建议在那些咄咄逼人、归化译法盛行的国家中采用异化翻译,可以对当今国际事务进行策略性的文化干预,用英语进行异化翻译还可以成为抵制我族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文化自恋和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这里还可以从中看到这种不同背景后的更深层次的含义——文化不平等关系,所以他选择这一翻译策略的原因是针对不同文化间不平等关系提出的。这样就把翻译放置于文化、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大背景下,通过翻译策略的选择来反映不同文化在当今世界所处的不同地位,把翻译当作一种斗争工具,与不平等的现象作抗争。用Venuti的话来说,异化翻译是“对(译入语)文化价值观施加种族离心的压力,以在翻译作品中体现外国文本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从而把读者送到国外”。进而“抑制翻译中种族中心的暴力,抑制英语国家“暴力”地归化翻译文化价值观,最后实现保护原文本不受译入语文化意识形态的控制。[19]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进步,也是翻译的必由方向。
人们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西方学界将摒弃过去东方文化译本中的殖民主义倾向,并对以往翻译过的作品进行重译,以保留东方文化和语言在英译本中的差异,所以“在翻译实践中尽可能采用异化手法无形中起到了一种文化干预作用,同时它也是对民族中心论种族主义、文化自恋和霸权主义的一种抵抗,客观上,有利于在全球地域政治关系中推行民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归化的译本将会完成其历史使命,并代之为异化的译本。”[18]
除了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等政治因素,还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中国的翻译输入得多,输出得少,中国文化未曾在强势国家发扬光大,加上霍克斯之译《红楼梦》的大量修改,中国的文化更受到曲解。翻译中国的灿烂文化之大任应该首先落在中国翻译家身上,他们应该拿起“异化”的武器,力争改变现代“南—北”翻译的不平等。[21]毫无疑问,杨宪益夫妇为翻译家作了榜样。
再从对内来看,除了前文提到的读者审美需求进步要求异化翻译以外,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的译本也要求多些异化。多些异化译本不失为引进新思想的好方法,引进新表达方式的好渠道。“五四”以后许多作家、翻译家有意识地采取异化译法吸收了大量西方词汇和句法结构,犹如一股活水,丰富了汉语词汇和句法结构,更重要的是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文化,从而避免文化自恋,避免自我文化的丧失。所以,为民族文化输入新鲜血液的异化翻译显得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使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立于不败之地。
三 国外采用异化翻译策略的启示
《三国演义》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部伟大杰作,也是世界文库中一部辉煌的艺术瑰宝。它展示了那个时代复杂而又极具特色的军事政治冲突,展现了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有很高的文学和文化价值,有“中国史诗”之称,现在市面上最主要的英译本由Roberts翻译。它的一大特点是以源语文化为出发点,采取异化译法,竭力保留原著中的文化形象,以使西方读者能如实地了解当时社会的文化风貌;其次,对于古代王朝的年号、人物的封号、汉语的习语和典故等,译本大都保留了原来的形象,别具一番特色。如:
结为秦晋之好——bind the two marriages as the states of Qin and Jin did in ancient times.
效犬马之劳——discharge my duty with the loyalty of a dog or a horse
玉玺——jade seal
典型的异化策略还体现在其对尊谦语的翻译。尊谦语是中国社会长年累月而形成的一种规约性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只有原汁原味地译出这些鲜明民族性的文化核,才能真正起到文化传播作用。
例:庶曰:“亮子孔明,道号卧龙先生。有经天纬地之才,出鬼人神之计,真吾今奇才,非可小觑。”(第39回)
“His style is Kongming,”Shan Fu replied.“his Taoist sobriquet,Master sleeping dragon.He is one of the rarest talents of the age.He can plot the motions of sky and land and design plans of divine perfection.On no account should we belittle him.
允曰:“今日老夫贱降,晚间敢屈众位到舍小酌”(第40回)
“Today is my birthday.I should like to invite you to a little gathering at my humble home this evening.”[21]
为《纽约日报》撰写书评的帕特里克·哈南(Patrick Hanan)认为由Roberts所译的《三国演义》忠实于原著,译本译出了个性,再现了形象。试想:一个外国学者能将虽写于元末明初而故事却发生在一千八百年前的历史故事的经典名著用异化的方法翻译成英文,尽可能体现原文的民族色彩,而一些中国学者却是一味或过多地进行归化,恐怕是逆时局而动了。
难道纯属巧合吗?在具有当今中国社会特色词的英译时,美国新闻期刊也采用了异化的策略。“给力”一词本是一中国网络词汇,含义是“酷”、“捧”或“带劲”,中国网友将其翻译成gelivable,这得到《纽约时报》的认同,它甚至也认可了拼音的翻译方法:
A test of a Chinese jargon word’s trendiness is if users translate it into a foreign language,according to its pronunciation.“Geili”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the English -sounding“gelivable”,and“ungeliveble”…
But it was the word’s antonym“Bugeili”…that first grabbed wider public attention…
类似于此的Duo Maomao(躲猫猫),Tibiwangzi(提笔忘字),也都出现在外文报刊上。
正因为美国记者在面对外国的新生事物敢于用拿来主义丰富英语文化。这才使得其秉承的文化生命力得以日益增强。他们不仅没有担心移花接木过来的外来语会污染英语或稀释美国英语的纯洁性,而且引以为自豪。美国人不仅创造了许多新词,而且善于挪用外来语,实现文化嫁接。[22]
既然外国读者已经接受了异化的翻译策略,一部分中国翻译家还在犹抱琵琶半遮面,甚至将鲜活的英语表达方式看作“妖魔化”,如此,我们的语言文化注定暗淡无光。
总之,我们一方面要学习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洋为中用;另一方面要利用英语这一世界语言向世界宣传灿烂的中国文化,实施文化“送去主义”,[23]让中华文明走向世界。
四 余言
最近中央电视台正在热播纪录片《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影片用全球化的视野展现交流与碰撞,包容共同与差异,将思考隐于影像的绚烂之中。其实,影片何尝又不是对翻译策略的一次有益启示呢?就像故宫内收藏着甲骨文、卢浮宫内收藏着楔形文字泥板汉莫拉比法典,通过对两种文字的比较,揭示出世界文明发端时已然走向不同的道路。如果用归化的说法,可能楔形文字就变成了中国的象形文字,甚至法国的卢浮宫也变成了中国的故宫。中国当代艺术家徐冰关于文字行为艺术的思考:“即使打破了文字的羁绊,人类就可以沟通了么?!”我们也在思考,那么是不是翻译成了中国人理解的事物,文化就可以互相更好地理解呢?非也。归化的翻译方法无异于紫禁城里,中国皇帝把玩着西洋的钟表,却依然对西方不以为然;卢浮宫里,法国贵族欣赏着油画里的中国风情,却不知这风情原本似是而非。归化是把国外灿烂的文化置于自家的围墙里然后肆意玩弄拆解,归化也是将自家本是悠久的文化整容(其实是毁容)以后取悦于外国读者。修筑围墙以前是保护自身需要,但它也意味着保守和封闭,现在确实到了该推倒围墙似的归化翻译修建广场似的异化翻译的时候了,因为修建广场意味着拆除心理屏障,拆除内心深处最坚固的围墙,树立正确的对待国外文化和自己文化的价值观。
[1]王宁.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J].中国翻译,2000(1):11-13.
[2]Nida,Eugene A.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M].New York:Leiden E.J.Brill,1964.
[3]Bassnett,Susan.Translation Studies[M].London:Routledge,1994.
[4]张今.文学翻译原理[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
[5]王宁.文化研究语境下的翻译研究[J].外语与翻译,1998(2):5-8.
[6]张柏然.全球化语境下的翻译理论研究[J].中国翻译,2002(1):57-59.
[7]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8]叶子南.论西化翻译[J].中国翻译,1991(2):27 -29.
[9]钱钟书.林纾的翻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0]Nida,Eugene A.Taber,Charles R.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New York:Leiden E.J.Brill,1964.
[11]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12]方珊,等,译.俄国形式主义论文选[C].北京:三联书店,1989.
[13]张欣.审美等效与文学翻译:归化和异化之争[J].湖北大学学报.2009(1):115-117.
[14]陈志杰.动态的读者反应论对翻译的指导意义[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1(2):90-93.
[15]许崇信.文化交流与翻译[J].外国语,1991(1):11 -13.
[16]崔永禄.霍克斯译《红楼梦》中倾向性问题的思考[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5):41-46.
[17]李静.异化翻译:陌生化的张力[J].中南大学学报,2005(4):505-508.
[18]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续编[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19]Venuti,L.The Translators’Invisibility[M].London and New York:Rout ledge,1995.
[20]Richard Jacquemond.Translation and Culture Hegemony.the case of French - Arabic Translation[C]//Venuti Laurence.Rethinking Translation:Discourse,Subject,Ideology.New York:Routledge,1992.
[21]贺显斌.文化翻译策略归因新解——以《三国演义》Roberts全译本为例[J].天津外语学院学报,2003(6):1-4.
[22]谢萍,杨丽斌.试分析“美国人自己创造的新词”及其翻译[J].上海翻译,2005(3):52-55.
[23]沈金浩.文化“送去主义”与和谐世界建设[J].深圳大学学报,2007(2):11-16.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for Cultural Heterogeneity
SHAN Wen-bo
(Faculty of Foreign Studies,Hubei University,Wuhan 430062,China)
Foreignization helps to promot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different peoples,and maintain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urce language,thus enriching the expressions of the target language,which is the essence of translation.On the other hand,to repress the intrinsic difference between languages would deprive the readers of their chance of experiencing a new way of looking at the world others are living in,only to leave the readers in the constant familiarity and habitualization.At the same time,foreignization is advocated as a means of resisting the invasion of privileged culture in order to give voice to the unprivileged culture.Chinese translators should take up a new historical mission,that is,how to resist western cultural hegemony effectively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to preserve Chinese culture.Moreover,it’s worth thinking that foreign media and translators have begun to adopt foreignization in their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new words.Therefore,foreignization represents the general orientation of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strategy;domestication;foreignization;cultural exchanges;colonialism resistance;enlightenment
H059
A
1674-5310(2012)-01-0126-07
2011-05-12
单文波(1971-),男,汉族,湖北武汉人,湖北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文化与翻译。
(责任编辑:李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