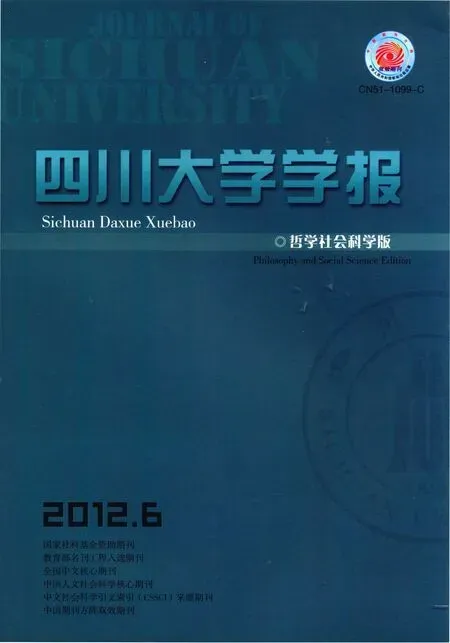重庆大轰炸中的日本国家责任——从大轰炸受害平民对日索赔的角度分析
金 明
(四川大学法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抗战时期,重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从1938年2月起至1944年12月,日本为达到“压制和扰乱敌之战略及政略中心”的目的,动用其空中打击力量,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及四川成都、乐山、自贡、松潘、合江等城市商业区、平民聚居区实施了六年又十个月的狂轰滥炸,制造了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惨案 (1939年)、重庆“六·五”隧道窒息惨案 (1941年)、成都“七·二七”大轰炸惨案 (1941年)、乐山“八·一九”大轰炸惨案 (1939年)等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大惨案,史统称之为“重庆大轰炸”。大轰炸期间,仅重庆地区,日军即出动飞机9000余架次,实施轰炸200余次,造成居民人口直接伤亡者30000余人,流离失所衣食无着的灾民无数。①重庆抗战调研课题组:《重庆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7-9页。
重庆大轰炸是日本侵华战争所犯罪行的一部分,对此日本应当承担国家责任。但是,重庆大轰炸作为日军一项具体的战略行动,还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它同时还违反了国际上早已形成的习惯战争法和习惯人道法的准则。日本对于这些“国际不法行为”同样要承担赔偿责任。那么,日本应承担国家责任的根据是什么?应当承担何种责任?以何种方式承担责任?这些都需要从国际法理论和实践层面上予以分析和回答。而在这方面,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历时半个多世纪,于1996年和2001年分别通过的《国际责任条款草案》(以下称“草案”)一读和二读本给了我们分析问题的方便,它被认为是对国家责任方面的习惯国际法规则的整理和发展。②贺其治:《国家责任法及案例浅析》,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3页。但即便如此,我们也认为“草案”条文是推证国际实践的证明之一,而不是习惯国际法规则本身。
一
从法律上看,确定一国国家责任的基本起点是其国家行为的违法性。因此,对日本国家责任的分析,应当从重庆大轰炸的违法性开始。关于这一点,“草案”中有明确的表述。
“草案”一读第19条是将“国际不法行为”与“国际罪行”相区分的。19条2款定义的“国际罪行”是指:“一国所违背的国际义务对于保护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至关重要,以致整个国际社会公认违背该项义务是一种罪行时,其因而产生的国际不法行为构成国际罪行。”可见,国际罪行是国际不法行为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1946年的东京审判即已确定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犯有国际罪行,会导致国家责任。但19条还规定了一般定义下的国际不法行为,它同样导致国家责任,这就是19条1款规定的:“一国行为如构成对国际义务的违背,即为国际不法行为,而不论所违背义务的主题为何。”这就是一条习惯国际法规则的表述了。因为在多年以来的国际法实践中,还“没有发生过一个国家仅仅由于对某一主题承担了国际义务而免除其责任的案例。也没有任何国际法庭认可这样的案例”。①贺其治:《国家责任法及案例浅析》,第25页。该条款在2001年的“草案”二读中被吸收到第12条: “一国的行为如不符合国际义务对它的要求,即为违背国际义务,而不论该义务的起源或特性如何。”这里的“义务的起源”一词,显然指的是该国际义务的所有可能的来源,即包括了习惯法、条约法,甚至包括了构成国际法律秩序的一般原则。
我们知道,近代国际法的发展和演变,大部分是以习惯法的形式表现的。而习惯法,又是以相关国家的实践活动为实证依据。即便是国际公约,多数也是相关缔约国的国家实践的实证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在1938年2月日本军机对重庆实施长期轰炸以前,国际上禁止对非军事目标轰炸的习惯法已然形成,并且日本对这一习惯法规则是非常清楚的。
1907年10月18日订于荷兰海牙的《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 (即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其章程第25条:“禁止以任何手段攻击或轰击不设防的城镇、村庄、住所和建筑物。”②王铁崖、朱荔荪等编:《战争法文献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52页。该条文就是战争法规对“军事目标主义”的明确表达。在当时,由于各大国的空军尚未组建,这里的“任何手段”涵盖了当时所能知道的所有战争武器。后来,当空战出现时,条文里的“任何手段”当然就包括了“飞机轰炸”。可见,在一战以前,军事作战中的“区分原则”作为习惯法就已经确立了。日本于1907年签署、于1912年批准该条约,是该公约的缔约国。③[英]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下卷第二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1年,第333页。
1922年2月至1923年2月,由英、美、法、意、日及荷兰等国的代表组成“战时国际法规修正委员会”,集会于海牙,拟就并通过了《战时空战规则草案》共62条。④杨泽伟:《宏观国际法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18页。其中第22条规定:“为使平民发生恐怖、破坏或损坏非军事用性质的私人财产或伤害非战斗员的目的而进行的空中轰炸,应于禁止。”⑤王铁崖、朱荔荪等编:《战争法文献集》,第131页。这就明确了空战中的“军事目标主义”,即战机不得对非军事性质的目标进行轰炸。尽管这一草案因种种原因未能成为正式的国际公约,但由于它的草拟和通过是集中了当时拥有飞机作战能力的各国法学家代表,也包括了代表国政府的意见和认可,因此应被视为习惯国际法。
此外,在重庆大轰炸实施以前的国际实践也表明了:飞机轰炸不得针对非军事目标这一原则业已成为了习惯国际法。在1937年9月27日,针对当时中国国民政府就若干城市被日机轰炸而向国际联盟提出的申诉,国联远东咨询委员会通过决议,谴责日机对中国和平城市进行轰炸的行为。⑥舍我:《国联谴责日寇暴行之后》,《上海立报》1937年 (民国26年)9月30日。这一事件同样表明了国际社会对“军事目标主义”的认同,构成了习惯国际法。
上述国际实践活动表明,在二战以前就已经确立了空战中的“军事目标主义”。而对持续近七年的重庆大轰炸,从实施轰炸的地域来看,是包括了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这片地区由于长江三峡天险为屏障,可谓远离战场的大后方,实际上,在整个战争期间日军就从未把战线推进到这片地区。再从实施轰炸的对象来看,在1937年日军进攻南京以前,就采用武力威慑的战略,以图达到心理征服、逼迫国民政府政治投降的目的。因此在从徐州作战直到南下进攻武汉三镇,日本“航空兵力不仅轰炸战场和协同地面作战的做法,不限于在地面军队作战区域内机动,而是用作发挥威力的新力量,日军将这种用法叫做‘要地攻击’或‘政略攻击’”。①前田哲男:《重庆大轰炸》,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7页。至于何谓“政略攻击”,在1937年11月日本陆军航空本部颁发的《航空部队使用法》中第103条:“政略攻击的实施,属于破坏要地内包括重要的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并且至要的是直接空袭市民,给敌国民造成极大恐怖,挫败其意志。”②前田哲男:《重庆大轰炸》,第38页。指令尚且如此,军队中无视国际法中的“区分原则”就是必然的了。最后,从实施轰炸的结果上看,由于日军采用了所谓“政略攻击”的方式,轰炸目标往往是城市平民聚居区。统计数据表明,大轰炸中人口稠密的城市商业区、住宅区、学校、医院等非军事区遭受的损失最为惨烈,据统计,日机对重庆近七年的轰炸,对平民生命财产、民用建筑设施造成的破坏达到了90%以上,而对政治、军事目标造成的破坏却不到10%。③张培田:《从1938—1945年日机轰炸川渝暴行析其违反国际法的问题》,《给世界以和平——重庆大轰炸暨日军侵华暴行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417页。这些事实表明,日机对这一地区持续实施了近7年的狂轰滥炸,显然违反了二战以前即已形成的战时国际法准则。
二
违反国际法规则的国家都是要承担责任的,这在国际法理论上没有争论。因为从法理上说,“否定这个原则将毁灭国际法,因为否定了实施的不法行为所负的责任,也就取消了各国按照国际法行事的义务”。④阿·菲德罗斯:《国际法》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445页。问题是,重庆大轰炸作为日军空军的“不法行为”,能不能归责于日本国家及其政府?这就需要有进一步的法律上分析。
从实践来看,上述问题在传统国际法里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一直到1907年的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修改1899年业已通过的《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除了其他修改变动外,此次会议通过的《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又称“海牙第四公约”)设立了第3条:“违反上述 (海牙)章程规定的交战国一方,在需要时,应负责赔偿。该方应对自己军队的组成人员所作一切行为负责。”显然,这一规定包含了两项原则,其一,违反海牙章程的交战国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二,交战国对其军队组成人员的一切行为应负责任。
先谈第一项原则,这是以公约的方式做出的一般性的规定,被认为是一项新的规则。从字面上看,第3条只规定了对违反海牙章程的行为予以赔偿,而不是对违反国际法其他战争规则的行为予以赔偿。但是,由于“海牙第四公约”的规定包括了当时战争所使用的所有方法和手段,因此应当认为“第3条的原则应该适用于其违反会致使敌国或中立国人民遭受损失的任何战争法规则,这一点是没有理由可以怀疑的”。⑤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下卷第二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1年,第103页。所以,我们有理由说,违反战争法规的一方必须承担赔偿责任这一规则,在1907年的海牙和平会议上即已确立。而且,这种国家赔偿责任的承担并不排除、也不能替代对犯有国际法规定罪行的个人的处罚。⑥1946年9月30日纽伦堡国际法庭判决,见《奥本海国际法》上卷一分册,第255-256页。这是在二战结束时即已确立的国际法原则。
再看第3条规定的第二项原则,交战国对其军队组成人员的一切行为负责。这就是一条习惯国际法原则的表述。军队作为国家机关的一部分,其行为依照国家意志而为,具体军事行动当然应由其国家承担责任。这条原则实际上包含了如下含义:军队行为无论其经过国家授权与否,国家对其不法行为后果均应承担责任。只是承担责任的程度不同而已,即未经授权的军队行为其国家应承担转承责任,经其授权的国家须承担原始的或直接的责任。英国著名国际法学者H·劳特派特在《奥本海国际法》中谈到这一习惯法规则时说:“可以稳当地定下的规则是,如果一个行为由国家所作或经其授权所作便会构成国际不法行为,这个行为就是国际侵害性的行为。”⑦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上卷第一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1年,第270页。
当代国际法对归责于国家的行为则有更为精确的表述。1999年4月29日国际法院在接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请求而做出的《关于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豁免于法律程序的争议之咨询意见》中指出:“根据已确立的国际法规则,一个国家的任何机关的行为必须视为该国的行为。这是一条习惯国际法规则,它载于国际法委员会一读通过的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6条中。”①国际法院:《国际法院判决书、咨询意见和命令摘要 (1997—2002)》,第68页。该第6条在2001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完成的“草案”二读中改为第4条,该条将归于国家的行为分为若干类,第一类即指“一国机关的行为:1、任何国家机关,不论它行使立法、行政、司法职能,还是行使其他任何职能,不论它在国家组织中具有何种地位,也不论它作为改过中央政府机关或一领土单位机关而具有何种特性,其行为应视为国际法所指的国家行为。……”。②贺其治:《国家责任法及案例浅析》(附件:一、二读通过的国家责任条款),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38页。该条款同样是一条习惯国际法规则的表述。它表明了任何提出区别国家不同职能的行为,区别上下级机关的行为,或区别中央机关与地方机关的行为的议论,在国际法上从来没有被承认过,它们统统都是一国的国家行为。
而现有的资料表明,重庆大轰炸计划的制定者和命令下达者正是日本当时的国家元首——昭和天皇本人。“1938年12月2日,日本天皇命令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由总参谋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向侵华日军传达‘大陆令第241号’敕令。战略轰炸已形成了作战命令的文字”。③前田哲男:《重庆大轰炸》,第59页。因此可以确定,日本对重庆大轰炸负有原始的、直接的国家责任。
三
在国际法上,一国因其不法行为给他国造成的损害必须给予赔偿,这是国际不法行为所必然引起的法律后果,也是一条早已确立的习惯国际法原则。1907年的“海牙第四公约”第3条就规定了:“违反该章程规定的交战一方在需要时应负责赔偿。”1927年常设国际法院在有关国际赔偿的著名案例《霍茹夫工厂案》(Case Concerning the Factory at Chorzow)的判决中提到:“只要违反义务就产生赔偿的义务,这是国际法的一项原则,甚至是一项法律的一般概念。”④P.C.I.J,.“Publications of the 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Series A-No.9,Collection of Judgments,A.W.Sijthoff's Publishing Company,Leyden,1927,p.21.这里的“违反义务”一词指的就是违反了国际法的任何义务。这段判词被后来的无数学者和判例所援引,成为经典。那么,既然“赔偿”没有疑问,赔偿的范围又如何呢?
在2001年通过的“草案”二读第31条规定了赔偿的总原则: “赔偿:1.责任国有义务对国际不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提供充分赔偿;2.损害包括一国国际不法行为造成的任何损害,无论是物质损害或精神损害。”显然,这是一条习惯国际法原则的表述。从上述第1款内容看,“充分”就是全部,这是习惯法上“充分赔偿”原则的表述。而且既然规定了一国对其不法行为造成的损失应予赔偿,也就赋予了受害国对加害国有要求赔偿的权利。第2款的规定就是对“赔偿范围”的解释了,也是对第1款“充分赔偿”原则的具体化和细化,即所谓“充分赔偿”指的是“不法行为所造成的任何损害,无论是物质损害或精神损害”。这同样是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的表述。在1927年常设国际法院审理的《霍茹夫工厂案》的判决中,法庭指出:“从不法行为这个概念本身包含的,以及似乎从国际惯例 (主要是仲裁法庭判例)得出的主要原则是:赔偿应当尽可能消除不法行为的一切后果,并且恢复到假如该行为不曾实施可能会存在的状况。”⑤Ibid.,p.47.说明法庭在当时就确认了“全部赔偿”或“充分赔偿”的原则,即责任国承担赔偿责任旨在“消除不法行为的一切后果”。也是因为有这样一条原则的指导,在赔偿的方式上,“草案”二读将“恢复原状” (Restitution)的赔偿方式放在了第一。⑥参见ILC:《国家责任条款草案》二读第34条:赔偿方式。
此外,我们还要看到,在近代国际法实践中,有关赔偿范围另一方面的发展变化。传统的战争赔款 (indemnities)是以赔偿战争费用为主要内容的。这从18世纪开始就已经成为一种一般性的做法。可是,在上个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条约中,开始使用了“补偿”(Reparation)一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过去战争有了很大的不同,采取了所谓立体战争的形式,连一般的国民也蒙受了巨大损失。因此,我们看到在1919年签订的《凡尔赛条约》中关于补偿问题一节里,已经不是单纯的军费开支的战争赔款了,德国及其盟国的赔偿责任包括了交战时其进攻造成的对一般国民的人和物的损害。①Cf.“Peace Yreaty of Versaills,”Article 231 -232.在二战结束后的《旧金山和约》里,其第五章“要求及财产”的规定内容,也都明确指出了赔偿还包括交战双方的国民所受到的损害与损失。
最近的一次关于加害国向战争受害者平民个人赔偿的案例,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战争结束后,由联合国赔偿委员会主持的战争赔偿。该赔偿委员会根据1991年4月3日联合国安理会第687号决议成立,其主要任务是处理索赔和支付因伊拉克非法入侵和占领科威特而直接遭受的损失。值得注意的是,委员会将战争赔偿分为了对政府损害的赔偿和对私人损害的赔偿。首先,在安全理事会1991年687号决议中,认定“伊拉克按照国际法,应负责赔偿因其非法入侵和占领科威特而对外国政府、国民和公司造成的任何直接损失、损害 (包括环境的损害和自然资源的损耗)和伤害”。②RESOLUTION 687(1991):Adopted by the Security Council at Its 2981st Meeting,on 3 April 1991,(S/Res/687),p.5.这一决议得到了在盟军协助下成立新政权的伊拉克与科威特双方的接受和承认,赔偿在法律上已没有障碍。后来,在具体的索赔和支付程序中,理事会将索赔类别确定为六个,这些索赔类别包括四个为个人,一个为企业,一个为政府和国际组织,由赔偿委员会主持施行。③联合国赔偿委员会:《赔偿委员会工作报告 (1997)》,http:∥www.uncc.ch/theclaims.htm(2012-7-25访问)可见,将战争赔偿区分为对政府的赔偿和对受害国民的赔偿是习惯国际法演变的趋势,早已不是传统的“整体主义”的赔偿了。不过,这种在联合国安理会主持下的战争赔偿并不是一种解决法律争端的方式,恰恰相反,它的任务是在所有的法律问题解决之后的有关索赔和支付的管理工作。正如秘书长在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中指出:“委员会不是一个法庭,也不是各方对簿的仲裁庭;它是一个政治机构,主要负责核实赔偿要求、核实其确实性、评估所受损失、估计偿付数额和解决争议的赔偿要求等调查职务。仅对最后一项才涉及准司法的职能。”④U.N.Databases,“Report of the Secretary- General Pursuant to Paragraph 19 of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687(1991),”(S/22559),p.7.因此,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对日索赔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在法律争端尚未解决、目前也看不到解决前景的情况下,赔偿委员会的案例于此并无想象中的那样有借鉴价值。
正是由于国际实践的发展变化,“草案”第33条“规定的国际义务的范围”里,其第2款指明了“本部分不妨碍国家以外的任何人或实体由于一国的国际责任可能取得的任何权利”。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对于战争中的不法行为而给一国国民带来的损害和损失,也是要由加害国承担责任的,这是“充分赔偿”原则的一部分。
四
明确了赔偿范围,还有一个赔偿方式的问题。关于赔偿方式,“草案”第34条规定:“对国际不法行为造成损害的充分赔偿,应按照本章的规定,单独或合并地采取恢复原状、补偿和抵偿的方式。”我们注意到,该条款以恢复原状为赔偿的首要方式,顺序而为补偿、抵偿,这是与历来的国际实践相一致、也是与国家赔偿的目的和宗旨相吻合的。在1928年的《霍茹夫工厂案》判决中,国际法庭就指出了“不法行为”的赔偿原则,即“尽可能消除不法行为的一切后果,并且恢复到假如该行为不曾实施可能会存在的状况”。这实际上就包含了将“恢复原状”作为赔偿的首选方式的内容。但是,在国家赔偿的多数场合,恢复原状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判决书随后又指出:“恢复原状,或在不可能恢复时支付一笔相当于恢复原状所等价的金额;必要时,在恢复原状或代替恢复原状的金额不能抵消所受损失时,准予损害赔偿——这应当成为确定违反国际法行为应付赔偿数额的原则。”①P.C.I.J.,Series A - No.9,1927,p.21.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法庭在判决中确定了两种赔偿方式,即恢复原状 (Restitution)和补偿(Compensation),补偿即指在资金上可以评估的任何损害或损失。依据法庭提出的“充分赔偿”原则,赔偿的作用是恢复到不法行为发生以前的状态,因此赔偿首选恢复原状。其次在恢复原状为不可能时,应当采用补偿,而补偿的标准包括支付恢复原状的价值再加上因不能抵消其损失时的赔偿金额。《霍茹夫工厂案》提出的这两种赔偿方式和方法,正是2001年“草案”二读中第35、36条规定所采用的。
《霍茹夫工厂案》由于只涉及了物质损害,法庭就只是采取了恢复原状和补偿两种方法。但在其他的一些国际不法行为的场合,还可能涉及到受害国的精神损害问题,例如重庆大轰炸。从国家层面上讲,重庆作为战时中国政治中心,大轰炸使国家主权尊严荡然无存、遭受羞辱;从当地市民层面上看,则每天生活在失去亲人、生命、乃至基本生活条件的无穷恐惧之中,精神痛苦不言而喻。而这些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因此,按照“充分赔偿”原则,国际法委员会认为:“可赔偿的个人损害不仅包括实质损害,如实际的收入损失及预期的收入损失、医药费等,还包括个人受到的非物质损害 (在有些国内法体系中也称之为“精神损害”)。非物质损害通常涉及失去所爱的人、伤痛、以及对个人、住宅或人身侵害有关的公开侮辱。”②I.L.C,.“Draft Articles on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with Commentaries-2001,”http:∥untreaty.un.org/ilc//texts/instruments/english/commentaries/9_6_2001.pdf.(2012-06-25访问)对于这种损害,“草案”第37条用“抵偿” (satisfaction)作为一种赔偿方式,以满足受害国及其国民在精神上受到的损害。其第2款列举了:“抵偿可采取承认不法行为,表示遗憾、正式道歉或另一恰当方式。”这样的规定显然并不包括所有可能的“恰当方式”,也不排斥采用其他可能的方式。在相关的国际实践中,要求道歉是一种常见的抵偿方式,但它往往同其他方式结合起来而加以采用。例如1999年的美国飞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中国政府就要求美国政府承担全部责任,除金钱赔偿外,还有要求美国向中国政府、人民及受害者家属表示道歉,对事件全面、彻底调查并公开结果,严惩肇事者等几项内容。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美就美国轰炸中国驻南使馆的赔偿问题达成协议》,2000-11-07,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zt/ywzt/2410/2411/t11359.htm/(2012-6-16访问)这后面的几项内容均属抵偿的方式,也是在近现代国际争端解决的实践中所经常采用的。
——《行政强制法》中的恢复原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