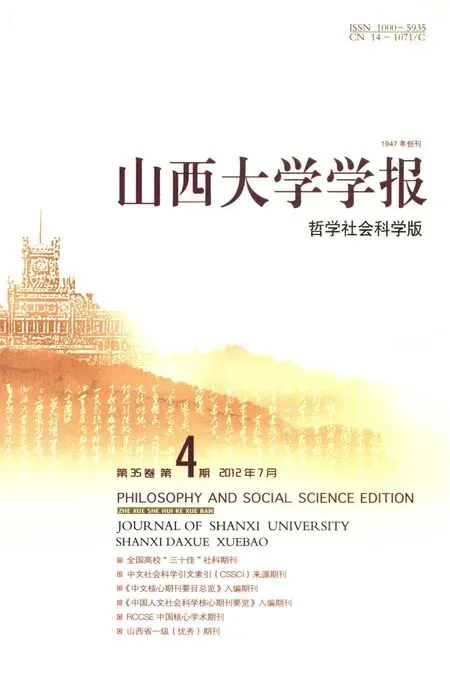评奖与“承认的政治”
——从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看50后作家的文学价值观
孟繁华
(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辽宁沈阳110034)
评奖与“承认的政治”
——从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看50后作家的文学价值观
孟繁华
(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辽宁沈阳110034)
文章结合获奖作家的具体创作体会,通过小说文本的细读,以开放的态度相对深刻地探讨分析了获奖者为什么主要是50后作家的根本原因,指出:时尚的文学引领着新的阅读趣味、展示了新的文学经验,这是文学向新的方向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作家文学观的守成姿态也于激进与新潮中适时地起到了某种“纠偏”或制衡的作用。
“茅奖”;守成;承认的政治;文学观
第八届“茅奖”获奖作者中,除了《推拿》的作者毕飞宇出生于1960年代之外,另外的四位居然都清一色地出生于1950年代。虽然这一批50后作家无论就人生体验还是艺术经验来看,都处于最圆熟的时候,但在获奖者中一下子占据五席中的四席,却很难被看做是一种简单的巧合。那么,导致一批50后作家同获茅奖的根本原因究竟何在?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11年8月26日在新闻发布厅举行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媒体见面会,专门邀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张炜、刘醒龙、莫言、刘震云、毕飞宇介绍创作经历和获奖作品情况,并答记者问。除毕飞宇在国外未能参加外,其他获奖者都参加了见面会。这是获奖作家第一次享受如此高规格的待遇,可见国家和社会对这次“茅奖”的重视程度。
需要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是,四位作家在回答记者提问的同时,也表达了他们的文学价值观。这正是本文想要思考和探讨的。根据自己阅读这些获奖作品的真切感受,并结合作家的一些言论,我以为,这些作家的文学观,既不同于80年代的“作家谈创作”,也不同于70后、80后作家对文学的理解。他们同获茅奖的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不容忽视的一点,恐怕与其共同的带有“守成”色彩的文学观不无干系。这背后,显然存在着某种所谓“承认的政治”[1]。
莫言的《蛙》,在形式上是全新的探索。五封信和一部九幕话剧构成了小说别具一格的讲述方式。“我姑姑”万心从一个接生成果辉煌的乡村医生,到一个“被戳着脊梁骨骂”的计划生育工作者的身份变化,喻示了计划生育在中国实践的具体过程。更重要的是,小说深刻地揭示了当资本成为社会宰制力量之后,生育、繁衍以及欲望满足等人类本能与日常行为中所潜藏的丑恶的人性奇观。小说实现了社会和自我的双重批判。莫言说:“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关注社会,关注他人,批判现实,我们一直在拿着放大镜寻找别人身上的罪恶,但很少把审视的目光投向自己,所以我提出了一个观念,要把自己当成罪人来写,他们有罪,我也有罪。当某种社会灾难或浩劫出现的时候,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必须检讨一下自己是不是做了什么值得批评的事情。《蛙》就是一次把自己当罪人写的实践,从这些方面来讲,我认为《蛙》在我11部长篇小说里面是非常重要的。”[2]莫言的这些说法,可以说是鲁迅先生伟大的自我批判精神在21世纪的回响。
刘醒龙的《天行者》延续的,是他著名中篇小说《凤凰琴》早已经书写过的生活题材,但它并不是《凤凰琴》的加长版。在这部长篇小说中,通过人物的添加,尤其是故事情节的明显复杂化,刘醒龙对于民办教师这个特殊的乡村知识分子群体的悲剧性命运进行了更加透彻深入的艺术表现。书名之所以为“天行者”,就是《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意思。我们总说,鲁迅先生是“中国脊梁式的人物”,不久前网络上也曾经热炒过所谓“中华脊梁”评选一事,但到底什么人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脊梁式的人物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刘醒龙笔下的这些拥有人格良知的、品格高尚的、默默奉献的民办教师才是真正的脊梁。如果中国少了像民办教师这些普通人的支撑,那我们的现代化恐怕就是无法想象的。所以,我很赞同一个评委的评价,他说:“《天行者》是一部书写中国现代化隐痛的小说。”“隐痛”就是藏起来的痛苦,表面上看它好像跟我们的现代化没什么关系,但民办教师是与乡村世界的改变、乡村孩子命运的改变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些又与中国的现代化密切相关。其实,小说在肯定民办教师的同时,对社会也进行了反思:是什么样的社会体制导致了这种现象?那群民办教师困苦的生活又是谁造成的?整部小说对中国不合理的体制表达了理性的怀疑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问题或许在于,刘醒龙怎么就能够把民办教师这些默默苦行着的民间英雄的日常生活如此生动地演绎在广大读者面前呢?只要我们看一看作家对于这些民办教师的深切感情,自然也就一目了然了。他说:“我在山里长大,从一岁到山里去,等我回到城里来已经36岁了,我的教育都是由看上去不起眼的乡村知识分子,或者是最底层的知识分子来完成的。前天的见面会上,他们之前告诉我说今天来了两位民办教师,我一进去就(对其中的两位来宾)说:‘你们二位是民办教师。’大家很奇怪,问我是怎么认出来的?(我说)因为但凡是民办教师,只要在乡村行走,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们的眼神经常会散发出卑微或者是卑谦,这种眼神和乡村干部绝对是不一样的,他们有一种孤傲,但是这种孤傲背后可以看出他们的卑微。他们两位是从几百位民办教师中推选出来的,他们背后是湖北省几十万民办教师。可能在座的记者不太知道民办教师,所以《天行者》这部小说,就是为这群人树碑立传的,可以说我全部的身心都献给了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国乡村的思想启蒙、文化启蒙几乎都是由这些民办教师完成的,我经常在想,如果在中国的乡村,没有出现过这样庞大的400多万民办教师的群体,那中国的乡村会不会更荒芜?当改革的春风吹起来的时候,我们要付出的代价会更大,因为他们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和在一个欠缺文化、欠缺知识的基础上发展代价是完全不一样的”[2]。
张炜的《你在高原》的出版,是当代长篇小说的一大事件。在当下这个浮躁、焦虑和没有方向感的时代,张炜能够潜心20年去完成它,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奇迹。这个选择原本也是一种拒绝,它与艳俗的世界划开了一条界线。450万字这个长度非常重要:与其说这是张炜的耐心,毋宁说这是张炜坚韧的文学精神。因此这个长度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高度。许多年以来,张炜一直坚持理想主义的文学精神,在毁誉参半、褒贬不一中安之若素。不然我们就不能看到《你在高原》中张炜疾步而从容的脚步。对张炜而言,这既是一个夙愿也是一种文学实践。
用20年的时间去完成一个夙愿或文学实践,几乎是一种“赌博”,他要同许多方面博弈,包括他自己。如果没有一股“狠劲”,这个博弈是难以完成的。这部长卷有强烈的抒情性和诗意,它给人以飞翔的冲动。我们时常读到类似的句子:
“我抬头遥望北方,平原的方向,小茅屋的方向。”
“你千里迢迢为谁而来?
为你而来。
你历尽艰辛寻找什么?
寻找你这样的人。”
它具体而抽象,形上又形象。一切仿佛都只在冥冥之中,在召唤与祈祷之中。许多人都担心读者是否有足够的耐心读完,我想那倒大可不必。古往今来,“高山流水觅知音”者大有人在。张炜大概也没有指望让《你在高原》一头扎在红尘滚滚的人群中。通过《你在高原》,我觉得张炜的文化信念和精神谱系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张炜的文化信念是理想主义。他的理想主义与传统有关又有区别。他坚信一些东西,同时也批判一些东西。他坚持和肯定的是理想、诗意和批判性。这些概念是这个时代很少提及的概念。我们不能因此理解为张炜与这个时代存在隔膜,事实上,正是他对这个时代生活的洞若观火,才使得他坚持或选择了那些被抛弃的文化精神。这一点张炜值得我们学习。张炜的精神谱系和他的情感方式即生活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对底层生活的关注。他的足迹遍布《你在高原》的每个角落。他可以不这样做也能够写出小说,他坚持这样做的道理,是使他的写作更自信,更有内容。张炜坚持的道路是我们尊敬的道路,他的选择为当下文学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参照。那些已经成为遗产的文化精神,在今天该怎样对待,这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也是一个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过去并没有死去,我们只有认真对待和识别过去,才能走好现在和未来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张炜对过去的坚持和修正,同样值得我们珍惜和尊重。张炜说:“我个人觉得,网络也好,纸质印刷的文学作品也好,主要在于艺术性,不能因为载体的改变而改变了几千年来形成的文学标准。它要靠近一个标准,而不是因为形式的区别改变了评价标准。至于说反映现实,我觉得写幻想、科幻、怪异的,依然要以个人现实生活的经验为基础,这是一个根本的出发点,他可以用不同的形式表达自己、表达人性、表达个人的艺术内容,但是对现实的理解深度不可以改变,那是基本的、根本的,也是一个原点、艺术的出发点。”[2]自然,张炜诚实地践行了他的文艺观。
在当下的中国,刘震云无疑是最有“想法”的作家之一。“有想法”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想法”包含着追求、目标、方向、对文学的理解和自我要求,当然也包含着他理解生活和处理小说的能力和方法。这是一个作家的“内功”,这种内功的拥有,是刘震云多年潜心修炼的结果,当然也是他个人才华的一部分。所谓的“想法”就是寻找,就是寻找有力量的话。他说有四种话最有力量,就是:朴实的话,真实的话,知心的话和不同的话。如果说朴实、真实、知心的话与一个人说话的姿态、方式以及对象有关的话,那么不同的话则与一个人的修养、见识和思想的深刻性有关。因此,说不同的话是最难的。多年来,我以为刘震云更多的是寻找说出不同的话,这个不同的话,就是寻找小说新的讲述对象和方式。
大概从《我叫刘跃进》开始,刘震云已经隐约找到了小说讲述的新路径,这个路径不是西方的,当然也不完全是传统的,它应该是本土的和现代的。他从传统小说那里找到了叙事的“外壳”,在市井百姓、引车卖浆者流那里,在寻常人家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了小说叙事的另一个源泉。多年来,当代小说创作一直在向西方小说学习,从现代派文学开始,加缪、卡夫卡、马尔克斯、罗伯-格里耶、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是中国当代作家的导师或楷模。这种学习当然很重要,特别是在过去的时代,中国文学一直在试图证明自己,这种证明是在缩小与发达国家文学差距的努力中实现的。许多年过去之后,这种努力确实开拓了中国作家的视野,深化了作家对文学的理解,特别是在文学观念和表现技法方面,我们拥有了空前的文学知识资本。但是,就在我们将要兑现期待的时候,另一种焦虑,或者称为“文化身份”的焦虑也不期而至,扑面而来。于是,重返传统,重新在本土传统文学和文化中寻找资源的努力悄然展开。刘震云是其中最自觉的作家之一。《我叫刘跃进》的人物、场景和流淌在小说中的气息和它的“民间性”一目了然,但因过于戏剧化,更多关注外部世界或表面生活的情节而淹没了人的内心活动,好看有余而韵味不足。这部《一句顶一万句》就完全不同了,他告知我们的是,除了突发事件如战争、灾害等不可抗拒因素外,普通人的生活就是平淡无奇的,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发现小说的元素,这是刘震云的能力;但刘震云的小说又不是传统的明清白话小说,叙述上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功能上是“扬善惩恶宿命轮回”。他小说的核心部分,是对现代人内心秘密的揭示,这个内心秘密,就是关于孤独、隐痛、不安、焦虑、无处诉说的秘密,就是人与人的“说话”意味着什么的秘密。在《一句顶一万句》中,说话是小说的核心内容。这个我们每天实践、亲历和不断延续的最平常的行为,被刘震云演绎成惊心动魄的将近百年的难解之谜。百年是一个时间概念,大多是国家民族或是家族叙事的历史依托,但在刘震云这里,只是一个关于人的内心秘密的历史延宕,只是一个关于人和人说话的体认。对“说话”如此历经百年地坚韧追寻,在小说史上还没有第二人。
刘震云说:“我觉得文学不管是作者还是读者,在很多常识的问题上,确实需要进行纠正。对于幻想、想象力的认识,我们有时候会发生非常大的偏差,好像写现实生活的就很现实,写穿越的和幻想的题材就很幻想、就很浪漫、很有想象力,其实不是这样的。有很多写幻想的、写穿越的,特别现实。什么现实?就是思想和认识,对于生活的态度,特别现实。也可能他写的是现实的生活,但是他的想象力在现实的角落和现实的细节里。比如今年得奖的这五个人,他们是写现实生活,但他们的想象力非常不一样,不管是《你在高原》《蛙》或者《天行者》,我觉得他们的思想都在向不同的方向飞翔,这不能用现实的或者是用其他的文学形式来归类,比如新写实,如果一个作品太写实的话,这个作品是不能看的,干脆看生活就完了。所以我的《一地鸡毛》是最不现实的,可能情节和细节是现实的,但是里面的认识和现实生活中的认识是不同的,现实中的人认为八国首脑会议是重要的,我家的豆腐馊了比八国首脑会议重要得多,我觉得这是一种偏差的思想。”[2]
这些表达,既承接了五四以来文学对社会责任的担当,有家国关怀,也发展或更深入地理解了文学自身的内在要求。他们走过的文学道路并不相同,在不同的文学路向上都有过程度不同的探讨甚至引领过潮流,比如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现实主义道路等。但是,经过不同的文学风尚的洗礼沐浴后,他们不是变得更激进、更新潮,而是更趋于“保守”或守成。他们更多讲述的是常识。这一点非常重要:时尚的文学引领着新的阅读趣味、展示了新的文学经验,这是文学向新的方向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正像五四时代,激进主义成为主流的时候,《学衡》《甲寅》等保守主义的思想起到了某种“纠偏”或制衡的作用一样,“50后”的守成姿态也已逐渐形成了这个时代的思想潜流。第八届“茅奖”选择了他们,当然也选择了他们的文学观。这,就是为什么获奖者会是50后作家的根本原因所在。
[1]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M]∥陈清侨.身份认同与公共文化.香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3-46.
[2]成功的作品需要读者认可,更需要历史的检验: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媒体见面会实录[OL].2011-08-26.http://www.Chinawriter.com.cn.
Award Appraisal and“Recognized Politics”: a Glimpse at the Literature Values of After-1950s Writers from the Eighth Mao Dun Literature Award
MENG Fan-hua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Literature,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Shenyang 110034,China)
On the basis of the specific creation experience and through the close reading of the novel text,this paper,with an open attitude,makes a relatively profound discussion on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why the award winners are primarily after-1950s writers,and it points out that the literature in fashion is leading the new reading interest and presenting new literary experience,which is necessar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in new directions.However,the conservative stance of writers’literature view has timely played a role of some kind of“correction”and balance in the radical and fashionable trend.
“Mao Award”;conservative;recognized politics;literature view
I207.425
A
1000-5935(2012)04-0042-04
(责任编辑郭庆华)
2012-03-05
孟繁华(1951-),男,山东邹城人,文学博士,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特聘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和前沿文化、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