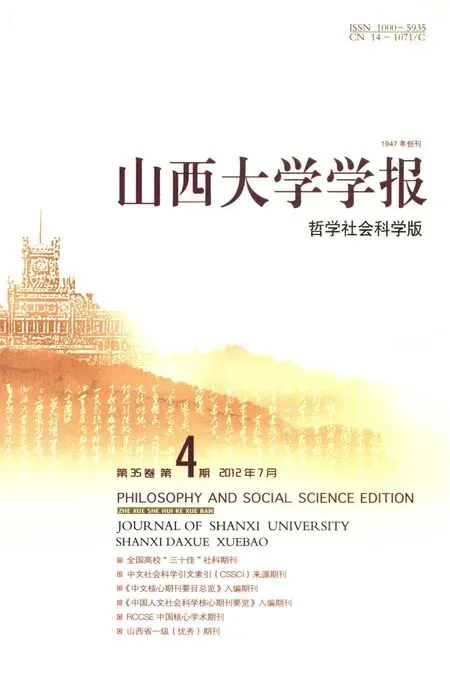文本视阈中的晋东南区域自然灾异
——以乾隆版《潞安府志》为中心的考察
王建华
(长治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系,山西长治046011)
文本视阈中的晋东南区域自然灾异
——以乾隆版《潞安府志》为中心的考察
王建华
(长治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系,山西长治046011)
个人“书法”和文本失忆是历史书写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在乾隆三十五年版《潞安府志》中有着显著的表现。受知识背景、政治立场及写作逻辑的约束,史志撰者有时会有意无意地把公共资源作为表达自我的平台,甚至针对性地将普通日常行为与政治生活妄加联系。但同时,相比基于宏大叙事的传统史书所透露的信息而言,区域背景的方志所提供的自然灾异文本,给我们展示了阅读灾害史料的独特视角。
晋东南;灾异;文本;《潞安府志》
晋东南处于山西省东南部,对应今天的长治市和晋城市。秦朝在此置上党郡,为始建三十六郡之一。历史时期,行政区划虽代有更张,但相近的自然地理、气候环境和历史渊源造就了该地区共有的文化记忆。具有悠久历史的晋东南既是自然灾害频发区域,同时也是较早保留灾异文本的地区。本文重点围绕乾隆三十五年(1770)版《潞安府志》讨论晋东南区域自然灾异。
一嬗变:意识形态与个人“书法”
(一)灾害书写的例目和内容
旁引曲取是古史表达灾异的重要“书法”。在传统史书体例中,班固创立的《五行志》,用汉代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说来推验祸福,影响政治,即是这种“书法”的表现形式。这种将灾异与政治加以联系的思想,也在方志中得到具体落实,虽然宋代之后正史中的《五行志》剔除了“事应”甚至“祥瑞”内容,但方志却直到清代仍然保留了这些内容。
中国传统史书的灾害记录模式经历了四步曲:第一步:以《汉书》为代表的“咎征是举”模式,即在灾异中找寻恶行的“事应”来警示君臣;第二步:以《宋书》《魏书》为代表的“休咎并征”模式,在灾异的例目中加入“祥瑞”的内容,既书恶行的“事应”(咎征),也书善行的“事应”(休征);第三步:以《宋史》为代表的“灾祥共书”模式,削去“事应”的内容,只记灾异和祥瑞;第四步:以《明史》《清史稿》为代表的“著其灾异”模式,只言灾异,不书“事应”及“祥瑞”。方志作为多学科、多专业的历史文献资料,其选材限定于一定的时空,其发生和发展相对于正史要晚、要慢。晋东南地方志撰修的例目演变不完全类于传统史籍,但其所受《宋书》《南齐书》尤其是《通志》的影响痕迹还是很明显的。晋东南现存较早的、较完整的方志版本系弘治八年《潞州志》,其灾害例目《灾祥志》独立成篇;万历、顺治版《潞安府志》的例目分别曰《祥异》《灾祥》,均附在《纪事》之后独立成篇。但是,乾隆版《潞安府志》的灾异例目改变了独立成篇的结构,将灾害资料以编年的方式分散插入《纪事》之中,既不同于其祖本,也不类于传统史书。
形式是服务于内容的,例目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写作思想的变化。《宋书》在《五行志》之外增加《符瑞志》,意在表达若帝王怙恶不悛则有“咎征”警示,同样,若帝王能隐恶扬善则有“休征”褒赏。但宋代之后的正史除《清史稿》外,其例目又更回《五行志》,但灾害的书写则完全剔除了“事应”,有的甚至只书“灾异”而不记“祥瑞”。乾隆版《潞安府志》则不同,它不仅“灾祥”共书,且“休咎”并举。应当说,在“事应”书写实践中,找寻重要政治事端以迁就“灾祥”并非易事,何况潞安府所属并非权力中心。但是,潞安府在历史上是出过重要政治人物的,因此,“事应”自然发生了。李隆基兼潞州别驾时,前后符瑞“凡一十九事”。这些事不仅见于《潞州志》,见于万历、顺治、乾隆版的《潞安府志》,也见于《旧唐书》。由于地缘的影响,很难再找寻玄宗这样有影响的政治人物与潞安府的联系,但我们发现,晋东南地方志中仍然存在大量的“祥瑞”和至少10条“事应”的记述。
(二)艰难的嬗变
史官修史,对材料处理、史事评论和人物褒贬各有逻辑,一般而言,后继者不去随意改变此前的相关记录甚至语言结构。《潞安府志》的万历、顺治、乾隆三个版本在相关内容书写上的高度一致性,印证了古人的书写原则,同时也说明方志祖本对后出本的影响。由于受到知识背景、政治立场的约束,撰者会有意无意地针对性书写,甚至把史书变成表达自我的平台。
《五行志》的基本思想是“示人君之戒”,这反映了官方的主流意识。但“事应”经过班固的发挥,沈约、萧子显的强化,到欧阳修那里开始消解。在相同的意识形态之下,欧阳修否认“事应”的存在,但撰者刘羲叟却在《新唐书·五行志》中保留“事应”的内容。欧阳修之后,郑樵自撰《通志·灾祥略》,“专以纪实迹,削去五行相应之说”[1],但后继史家仍然保留“祥瑞”书写一直到明代。乾隆版《潞安府志》保留并增加了“事应”的内容,这既是中国古人传统的书写习惯使然,也是意识形态所致,但这些却不是事实的全部解释。综合方志信息,姚学瑛,乾隆三十一年(1766)始任沁州府,三年后署理平定州,旋署理潞安府兼理沁州。在任期间,于乾隆三十五年修《潞安府志》(时另一主修张淑渠已离任潞安知府)、三十六年(1771)续修《沁州志》,这两部方志均以“赐同进士出身钜野姚学甲”为主撰,论者疑姚学甲为姚学瑛的兄弟。乾隆版《潞安府志》序曰:“分注历代庆典及祥异于(纪事)下”是为了“使知人事之得失,见于天象感应之理”[2];而《沁州志》序曰:“虫蝝、水旱,虽曰天行,而修省补救,转沴为祥,感应之际,捷于影响。故蝗不入境、虎北渡河,前史褒之。”[3]如果说两部志书的“序”为我们提供了创作者对灾异一以贯之的旨趣和意图的话,那么,乾隆版《潞安府志·纪事》最后一条灾异记录则为我们提供了作者是如何使用公共平台实现个人“书法”,甚至将府尹的日常行为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加以联系的。“三十五年(庚寅)八月,府堂产灵芝。产于花台间,一本三茎。署知府姚学瑛有记,载《艺文》。”[2]《艺文志》收录姚学瑛《潞安郡署灵芝记》讲述这次“瑞异”情况时写道:“郡之僚友、士大夫闻此,沓来踵视,咸耸叹惊异,额手称庆,以为今兹岁稔时和之兆。余曰:‘是矣,抑未也。方今圣天子寿逢周甲,寰宇承平,复得上奉慈宁,备隆尊养,明岁恭逢圣母八旬万寿,为从来未有之盛事。……以为圣天下达孝养老之休征也。’”[2]查晋东南方志,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以至乾隆三十五年(1770),潞安府属非但未有灾害记录者,反而有二次“有秋”的记录。乾隆任期五次普免天下钱粮,三十五年60寿辰、明年皇太后80万寿,因下诏普免全国额征地丁钱粮。出现这样的状况,当然不是潞安府堂的灵芝能够担当的。
嬗变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至民国时,虽然“灾祥”、“事应”被人讥笑为“侈谈星陨之文,真无异痴人说梦矣。”[4]但仍然有“感应之理,昭昭不爽”[5]的说法。
二失忆:历史文本的“书法”常态
(一)被遗忘的历史
“史籍是人类保留自身记忆的所有方式中最好的一种,但历史上的天灾人祸,使史籍中的大部分灭失。”[6]因此,对历史过程进行系统记录是不可能的。那么,史籍能否全面反映重大灾害的基本实际呢?晋东南方志灾异文本提供的结论是否定的。
首先,方志保留下来的文本记录的绝对数据无法反映灾害的实际。以旱灾为例,查乾隆版《潞安府志》记录,两汉无记录,唐代2条记录,北宋2条记录,金代无记录。比较中国历史灾害记录,晋东南系区域灾害发生频率较高和记录较早地区,但是,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成“害”之灾相对较少。在众多灾害中,旱灾是多发和影响区域农业生产的重要灾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见灾害记录的文本数据显然不能代表什么。如果仅将府志记录作为样本对晋东南区域旱灾进行考察,数据的畸变将会使研究无法深入。同样,府志记录的其他灾异与旱灾记录在不完整性方面高度一致,而这些数据自然无法真实反映晋东南的灾害史。
其次,方志保留的灾害记录与中国古代灾害记录在各时段密度上的不对等,证明方志记录存在严重缺失。研究发现,从16世纪开始,中国史籍灾异的记录数据突然加大,因此,本文分1-15世纪、16-18世纪两个时段,以陈高傭等编《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出版,下简称《表》)所记旱灾作为参数与乾隆版《潞安府志》列比对表如下:

表1 乾隆版《潞安府志》与《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干旱频次对照表(迄于乾隆三十五年)
中国历史灾害统计数据表明,时间愈后灾害发生的频度愈快,列表数据也反映了这一现象。但是,《表》所显示的数据,旱灾总量1 500年大于300年,而府志则正好相反,1500年小于300年,且绝对数量的差距比较大;300年占“总计”的比值,《表》不足42%,府志为73%强,府志高出《表》31%。笔者在研究府志所载其他灾异时曾经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和比对,结论是:明清时期所占历史灾异总量,要高出同一时期《表》统计数的30%强。由于历史文本所表述的相关内容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此,府志所载内容已经涵盖了此前所有类似相关的表达,就文本而言,府志呈现的相关内容是完整的。而《表》的数据来源,“明代以前以《资治通鉴》与《续资治通鉴》为主,明代以《明史》与《明纪》为主,清代以《清史稿》《清史纪事本末》《清鉴》为主。此外参考‘廿五史’之《本纪》《五行志》,《图书集成》之《庶征典》,‘十通’,各朝会典、会要、实录以及其它各种有关系之史籍。”[7]也涵盖了中国传统史书的基本史籍。旱灾是晋东南的主要灾害,民间有“十年九旱”之说,但府志提供的不足百年一遇,甚至前1500年中375年一遇的数据,是不能让人信服的。事实肯定是另外的版本。
(二)记忆的方式
文本的历史不是以清晰完整的面貌出现的,常常表现出模糊不清、残缺不全的特征。历史灾害文本又受制于书写逻辑和表达态度,使得它模糊不清、残缺不全的特征表现得更加突出。
首先,资料的残缺模糊给历史文本形成造成困难。“纂修全资文献,《潞志》文献俱不足征,自程机《上党志》、王松年《三晋纪》外,不过《壶关录》、《晋州志》以及《潞志拾遗》等书,已属少见寡闻。且志自顺治后,百余年未经采辑,中间不无遗漏。”[8]乾隆版《潞安府志》所载灾害资料,顺治及其以前的内容完全雷同于顺治版《潞安府志》,顺治版的相关内容则源于万历版。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府志中,县志大体上也是沿袭旧史、陈陈相因,甚至相沿成讹也不作任何更张。拾遗补缺的困难也反映了书写完整灾害史的窘境。
其次,信息传递使灾害资料灭失。受交通条件和通讯技术的限制,许多偏僻之地的灾害信息无法传输,有时虽然得以传输,但受到传输条件或水平的制约,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或缺失或扭曲。况且早期史籍,更注重与政治生活相关的重要灾异,余则很难进入官方书写者的视野。同时,统治者隐灾匿害也使得大量的方志灾害资料不能完全上达或完全不能上达。不可否认,历代中央政府对于灾害是比较重视的,但隐匿灾害情况仍然普遍存在。雍正元年(1723),武乡大旱民饥,“官吏匿不报请。独武乡知县揭延龄具文申报。”[3]此次灾害,乾隆《潞安府志》未有记载,毗邻武乡的潞安府属之襄垣县志也无记载,独《武乡县志》《沁州志》有载。武乡在行政建制上虽属沁州,但考虑到旱灾的发生机理,此次灾情绝非偶发于沁州。类似这样的例子在史料比对中经常被发现。
最后,受文献资料和书写逻辑的限制,灾害史料很少记忆细节甚至无法提供真实情况。正如前文所述,历史灾异书写是与政治生活伴生的,其叙事竭尽淡化情节之能事,重在揭示现象背后的政治因素,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沿着这一叙事逻辑行进。灾害虽然是志书必载之内容,但内容的增删并不一定以编纂者拥有资料的品种和数量为转移。作者在书写过程中,视写作需求必然有所载有所不载。或“削其泛其杂者,……而邑之凶丰疾苦系焉者,以志……”[9],或“有关民谋者始书”[10],或“惟父老传述远或耳闻近,则目睹其有年月可稽、事迹足异者,要亦采访者所急于存记也”[11],或“若幽异怪奇、妄诞不经之谈,似非二十世纪人民所宜复道,悉弃而不采”。[12]石璜纂修民国《平顺县志》记述清光绪三年(1877)大旱和民国二年(1913)八月一号县东暴雨,在灾害编年下附有文字记录约1380言。[5]但这样的记录为晋东南府县志中的个例。详近略远是纂修史籍的原则之一,个别情况可以详细表述,但大多数却无法铺陈,灾害文本更是如此。
灾害是一种客观事实,虽然它已经变成过去,但这一事实曾经发生过。文本的存在不等于历史的存在,同样,历史自身也不会因人的意志而改变。由于各种因素,许多历史上发生的灾害不能见诸史籍或根本无据可查,但这却不能掩盖晋东南区域灾害的真实数据远远大于文本数据的事实。
三意义:方志灾异的阅读视角
(一)方志是多姿多彩灾害史料的重要来源
虽然早在《周礼·春官》中就有外史“掌四方之志”及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的记载,但到宋代,地方志记述的重点才从地理转到人文历史方面,在内容和形式上大体定型。到明代,方志的修撰基本普及。雍正时期颁行60年修志令,方志得以空前普及。
修志最盛的清代,方志达6 500余种,占我国现存方志的70%。山西现存471种行政区划性质的方志,晋东南的长治市49种、晋城市27种。[13]方志展示微观历史,以灾害书写为己任,这是其他史书无法比拟的。以二十五史为例,有志者15部:《汉书》《续汉书》《晋书》《宋书》《南齐书》《魏书·灵征志上》《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灾异志》;无志者10部:《史记》《三国志》《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新五代史》《辽史》。无志当然无以记灾异,虽然针对前史无志的情况,后代修史者突破断代体裁,对前史进行补阙,但毕竟去日已久,佚失的内容必然更多。况且,即使有志也不可能完整地记录灾异。如二十五史,有《五行志》的15部史籍中,从《汉书》到《晋书》及《新唐书》到《清史稿》,只记灾异不记祥瑞者达10部之多,正史之外的《通志》甚至只书灾害不书变异。与传统史籍不同,灾害资料为方志必书内容,而且这些内容千奇百怪。如《潞安府志》除正常的水旱蝗震等灾害记录之外,其他的所谓“异常”“祥瑞”记录的种类不下7种200条,这些多姿多彩的内容在同时代的其他史籍中是无法获得的。
(二)方志文本在补充灾害史料不足的同时,推进灾害研究手法的更新
班固设立《五行志》其写作动机是以阐发“微言大义”来警示君臣,其政治目的是放大灾异的结果使人主实现自觉。历代史籍在组织灾异资料时虽然手法千变万化,且编纂过程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但其政治思考一以贯之。
在传统“书法”的影响下,撰者对影响重大的、特别是易与政治关联的历史灾异文献或采取“选择性记忆”,而对于那些影响不大或与政治关联度小的灾异史料则“针对性放弃”,这就使得史书内容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大打折扣(当然要求史书内容的完整和系统只是一种书写的理想)。晋东南方志记述内容虽然缺失很多,但通过与正史资料分阶段比对,元代及其以前,方志灾异与正史灾异的文本节奏基本上是一致的,且有些内容是传统史籍不载的;明代以降,由于方志的兴盛,加之参与书写的人群不断增长,大量的包括灾异资料在内的史学资源出现井喷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正史中很难容纳的区域灾异内容被方志收纳。正因如此,20世纪后半期,面对大量的方志灾异史料,史家遭遇到统计学上的难题,但同时发现,由于灾异史料的丰富,研究灾害史使用定量分析方法与使用定性分析方法变得一样容易,且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尽管单个方志的灾异文本记录模糊而有许多断点,但通过对相关方志的整合,历史灾异信息变得愈益清晰;方志不仅能够补充传统史籍的不足,而且能够互相补正、参证。史家在研究明清史料时,正是通过对方志中大量的所谓“祥瑞”和“物象异常”的研究,提出了明清宇宙期的概念。[14]
方志灾害文本虽然极不完善,但相比基于宏大叙事的传统史书所提供的信息而言,基于区域背景的个性书写所提供的自然灾异文本,给我们展示了阅读灾害史料的独特视角。
[1]郑樵著,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灾祥略[Z].北京:中华书局,1995:1907-1977.
[2]张淑渠,姚学瑛修;姚学甲纂.潞安府志·卷十一·纪事[Z].清乾隆三十五年刻本.
[3]叶士宽修,吴正纂;姚学瑛续修,姚学甲续纂.沁州志·卷九·灾异[Z].清乾隆三十六年刻本.
[4]郭蓝田,阴国垣纂;孔兆熊修.民国沁源县志·卷六·大事考[Z].凤凰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影印本,2006.10.
[5]石璜纂修.民国平顺县志·卷十一·旧闻考·兵匪·灾异[Z].南京:凤凰出版社影印本,2004.
[6]王建华.文本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历史认识论考实层面的解析[J].历史教学问题,2011(3):93.
[7]陈高傭,等.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M].上海:上海书店影印出版,1986:编纂缘起,一.
[8]张淑渠,姚学瑛修;姚学甲纂.潞安府志·潞安府志凡例[Z].清乾隆三十五年刻本.
[9]杨善庆修,田懋纂,阳城县志·卷之四·兵祥[Z].清乾隆二十年刻本.
[10]刘钟麟,何金声修;杨笃,任来朴纂.屯留县志·卷一·祥异[Z].清光绪十一年刻本.
[11]吴承恩修;骈沁,卫子良纂.沁州复续志·卷之四[Z].清光绪六年刻本.
[12]张扬祚修,郝世祯纂.(民国)武乡新志·卷之四·旧闻考[Z].民国十八年铅印本.
[13]任小燕.山西古今方志纂修与研究述略[J].晋阳学刊,2001(5):82.
[14]张建民,宋俭.灾害历史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144.
Natural Calamities in the Area of Southeast Jin Recorded in Texts: A Study Based on the Qianlong Edition of Annals of Lu-an Prefecture
WANG Jian-hua
(Department of Historical Culture&Tourism Management,Changzhi College,Changzhi 046011,China)
Subjectivity and incompleteness are important features of historical records,which are reflected clearly in Annals of Lu-an Prefecture,the edition published in the 35th year of the reign of Qianlong.Limited by their own knowledge background,political standpoint and different styles and forms of historical records,compilers sometimes,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tend to express their own opinions via the platform of public resources,even intentionally associate ordinary daily behavior with political events.However,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historical records,local annals can offer us an opportunity to underst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local calamities from a unique perspective.
Southeast Jin;calamities;text;Annals of Lu-an Prefecture
K290
A
1000-5935(2012)04-0076-04
(责任编辑贾发义)
2011-11-16
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明清时期晋东南区域自然灾害与民生研究”(2012278)
王建华(1961-),男,山西襄垣人,长治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系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地方史、灾害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