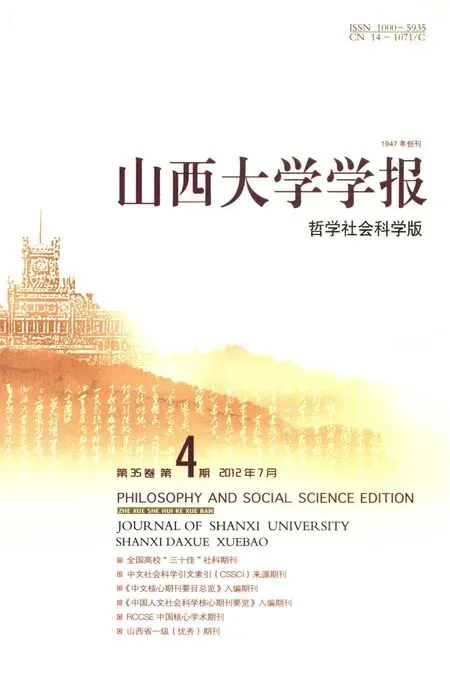诗画合璧:元代花鸟画与题画诗的结合
史宏云
(山西大学美术学院,山西太原030006)
诗画合璧:元代花鸟画与题画诗的结合
史宏云
(山西大学美术学院,山西太原030006)
元代花鸟画处于中国花鸟画发展史的变革期。其花鸟画和题画诗的结合,不仅与水墨为主的元代花鸟画形态紧密相关,而且以诗、书、画艺术融会贯通促成了写意说、墨戏、追求古意及逸气的新风尚。元代花鸟画和题画诗的“合璧”丰富了中国花鸟画艺术,对后世中国画技法和画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元代;花鸟画;题画诗
在中国花鸟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元代作为一个转折点更值得研究和关注。有人把中国画中诗、书、画、印的结合形式称之为“合金”艺术,而元代中国画就是这一“合金”艺术的定型阶段。因此,不论站在历史的角度还是在当前的形势下,研究元代花鸟画与题画诗的结合问题都是必要和有意义的。
本文选取近百幅有题画诗的元代花鸟画为研究对象,对元代题画诗和花鸟画结合进行分析探讨。
一元代花鸟画人文背景
研究元代花鸟画与题画诗离不开对其所在时代及文人心态的关注。从历史发展的纵向来看,宋元统治者对绘画的态度有很鲜明的对比。两宋时代,翰林图画院的创办标志着宫廷绘画进入了鼎盛时期,文人士大夫绘画热情空前高涨,其待遇和受重视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进入元代后,统治者对中原文化了解不多,对书画兴趣不大,画院也被废弃。虽然到了元代中后期,元文宗在宫廷中设置了收藏图书宝玩的奎章阁,还有热衷书画鉴藏的贵胄大长公主的支持,但该机构仅存了十一年(1329-1340年),鼎盛期不过两三年。因此,许多画家不愿为元代统治者服务,并隐居山林以艺术来发泄对现实的不满。
元代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把治下的臣民分为四等:蒙古人为一等,色目人为二等,汉人为三等,南人为四等;统治者提倡佛、道而轻视儒学,并废除科举制,虽然在延祐年间恢复过,但也时断时续,阻止了文人士子的传统出路。汪元量在《湖山类稿》卷二《自笑》中说:“释氏掀天官府,道家随世功名。俗子执鞭亦贵,书生无用分明。”[1]由此就能看出当时文人的无奈。王明荪通过旧元史与蒙兀儿史记资料,在对1400余人的初步统计中,得知元代政治结构:“汉人官员占领总数约近60%,蒙古与西域人占40%,其中蒙古人略多。但汉人官员中约有一半位处中下层,在三品以上官员之分配中,汉人有52%,蒙古有26%,西域人占到22%。从比例上看,蒙古人出仕者,约占四分之三可以进之高位,西域人达五分之三以上,汉人则仅有一半略多可进入三品以上。”[2]看出在异族统治下,汉人的出仕之路并不理想。
古代文人提倡“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由于异族统治,隐士在元代备受推崇,文人一直在出世入世两种心态相互交映下生存,即使已出仕者也是如此,如被封为魏国公的赵孟頫在《罪出》一诗中的表露:“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昔为水上鸥,今为笼中鸟,哀鸣谁复顾,毛羽日枯槁”[3]26即是例证。在这种心态下,许多画家不愿为元统治者服务,如南宋进士钱选入元后,归隐从事绘画,自称“不管六朝兴废事,以樽且向图画开”,这种放弃态度应该是对现实无奈的选择。因此,郑午昌曾说:“自入元后,则所谓文人画之画风,乃渐盛而炽。盖元崛起漠北,入主中原,毳幕之民,不知文艺之足重,虽有御局使而无画院,待遇画人,殊不如前朝之隆。在上既无积极提倡,在下臣民,又皆自恨生不逢辰,沦为异族之奴隶。凡文人学士,无论仕与非仕,无不欲借笔墨以自鸣高。”[4]这足以诠释元代文人画的兴盛是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文人心态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这一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大多文人借绘画来抒发情怀,文人画成了中国画坛的正统,诗、书、画真正结合在一起,从而达到艺术的变革。
二水墨为主的元代花鸟画形态
(一)文人写意花鸟画占据主流
元代文人士大夫阶层,以画“四君子”来自鸣清高,文人水墨写意画占据了主要地位。
在异族统治的特殊时期,梅兰竹菊题材的流行与其“坚韧”、“有节气”等文化内涵是分不开的。其中,尤以墨竹为盛。《图绘宝鉴》所载元代墨竹画家200余人,以赵孟頫、顾安、李衎、高克恭、柯九思等人为代表。周积寅、王凤珠编著的《中国历代画目大典——辽至元代卷》收录统计:李衎共17幅竹作品,顾安17幅竹作品,柯九思20件作品中竹有13件,赵孟頫20余件竹题材作品,可见这个时期画家对于竹题材的喜爱。朱德润《送顾定之如京师序》中评论顾安画竹:“夫竹之凌云耸壑,若君子之志气;竹之劲节直干,若君子之操行,竹之虚心有容,若君子之谦卑;竹之扶疏潇洒,若君子之清标雅致;是皆定平日意念之所及也。况定之以儒家者流,游戏弄翰,其朝夕思行之美者,至于逼真不已,今则至于……措之于临民之际,则其为助也,岂不多哉!”[5]391将顾安画竹与其济世务实思想结合起来加以分析,解释了文人画竹是士大夫的情操表征,便是对这一时期文人画以梅兰竹菊为题材的最好诠释。
(二)工笔花鸟画的水墨新风尚
元代工笔花鸟画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
前期基本上是延续宋代院体风格,但是已由一味求工丽转向文人审美旨趣的率真典雅,以钱选《八花图》、任仁发《水凫图》为代表。后期墨笔花鸟创作空前活跃,除了开拓新题材,还以其注重墨彩的浓淡干湿,变化丰富,笔墨工整中略带写意,开创了具有墨戏倾向的花鸟画新风尚,以赵孟頫《幽篁戴胜图》、王渊《竹石集禽图》、陈琳《溪凫图》以及盛昌年、边鲁等人的作品为代表。这种以无色胜有色的艺术形式正体现了元代墨笔花鸟画所追求的境界。
可以说,这一时期花鸟画从题材到艺术形态,都处于剧烈的变革之中,文人们强调个性表现,一方面梅、兰、竹、菊题材的文人写意花鸟画得到长足发展,另一方面水墨形态的工笔花鸟画拓展了花鸟画艺术的发展空间。这种变革是和诗与画的结合紧密相关的。
三元代题画诗和花鸟画结合的形式
《图绘宝鉴》载王冕“能诗……凡画成,必题诗其上。”[6]553《吴礼部诗话》:“龚开圣予,工诗善画,篆隶亦奇古。每画,题诗于后。”[6]463都是对元花鸟画家自题诗的相关记录。元代印谱学也有了很大发展,赵孟頫、王冕均为篆刻名家,题画诗、印章真正走上画面,使中国画诗书画印“合金”成为一炉。因此,潘天寿《听天阁画谈随笔》曰:“吾国唐宋以后之绘画,是综合文章、诗词、书法、印章而成者。其丰富多彩,亦非西洋画所能比拟。”[7]
虽然从宋徽宗赵佶《芙蓉锦鸡图》《腊梅山禽图》等作品可以看出诗画形式的结合,但是题画诗真正进入画面则是在元代。清代郑绩著《梦幻居画学简明》论题款:“唐宋之画,间有书款,多有不书款者,但于石隙间用小名印而已。自元以后书款始行。或画上题诗,诗后题跋,如赵松雪、黄子久、王叔明、倪云林、俞紫芝、吴仲圭、柯敬仲等,无不志款留题,并记年月。为某人所画则题上款,于元始见”[8]。
在元代短暂的九十余年中,画家们创作了大量的集诗书画印为一体的作品。从现存元代作品可以看出,那时的画面题诗已成时代风尚,除了自题诗,还有其他书画家的墨宝。往往一幅作品多人题诗,如张中《桃花幽鸟图》上有近20位文人墨迹,画面上水泄不通,以至于见缝插针。这些文人有杨维桢、袁凯、顾谨中等人,这样满题的花鸟作品,还有《式古堂书画汇考》记载的水墨画《春雨鸣禽图》等,可见当时画坛题诗的盛行。
元代题画诗多以七言、五言为主,四言形式鲜少,以补充画意,增强了画面的艺术感染力,内容以画评、画论等为主。和花鸟画有三种结合形式:
(一)自题自画
自题自画,即画与题画诗作者为同一人。
如吴瓘《梅竹图》自题《柳梢青》词一阕:“墙角孤根,株身纤小,娇羞无力。蟹眼微红,粉容未露,不禁春色。待东君汩没芳姿,渐迤逦,檀心半拆。缓步回廊,黄昏月淡,那时相得。”此画寥寥数笔,写出梅花两枝,竹叶数片,几近空梢的梅枝,矗立在晓风中,只待消息传来便破蕾而出,营造了诗书画完美结合的意境。
(二)他人题画
他人题画指诗和画不是同一个作者,从作品产生的时间顺序上看,通常是先画后题诗。如班惟志题王渊《鹰逐画眉图》:“海棠枝上语调簧,曾驻多情走马郎。鸷鸟见攻能引避,禽中真是白眉良。”由图生发出自己的见解,赵孟頫题李衎《野竹图》:“偃蹇高人意,萧疏旷士风。无心上霄汉,混迹向蒿蓬。”既是对李衎的规劝,同时也是在感叹自己。倪瓒题张逊《勾勒竹图》诗:“髯张用意铁钩锁,书法不凡诗亦工。”则是对作者及作品进行的评价。
(三)先有诗后作画
这类作品多以前人所作诗为题进行绘画创作。如坚白子《草虫图》画面上有天牛、知了、金龟子、壁虎、蟋蟀、蟾蜍、蜗牛,神态灵动,栩栩如生,每物旁用小楷录苏轼题雍秀才所画五言诗一首。
四元代题画诗与花鸟画的诗画关系
一幅好的画作应该富有“诗情画意”,二者的艺术功能是相辅相成的。以郑思肖、普明墨兰作品为例来看元代诗画并发的表达方式。
郑思肖(1241-1318),字忆翁,宋亡,隐居苏州,自号所南,以示不忘宋室。他在绘画上最大成就是画兰,多花叶萧疏,不画土、根,寓意为“土为番人夺去,忍著耶!”画《墨兰卷》,题款“纯是君子,绝无小人。”[6]749兰花在这里乃是他自我人格的象征。
现存郑思肖《墨兰图》以八分法画出两丛兰叶,一瓣兰花,既无根入土,也无石相伴,如浮于虚空。题诗:“钟得至清气,精神欲照人。抱香怀古意,恋国忆前身。空色微开晓,晴光淡弄春。凄凉如怨望,今日有遗民。”画面形象、题画诗表达了他忍受着巨大的精神苦痛。倪瓒《题所南兰》诗:“秋风兰蕙化为茅,南国凄凉气已消。只有所南心不改,泪泉和墨写离骚。”更揭示了这位孤臣逆子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以及这一思想感情所决之艺术的根本意义。郑思肖还在其《寒菊图》题:“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庭中。御寒不借水为命,去国自同金铸心。”借用菊花凋零不离枝头的特性表明其对宋王朝的一片忠心。
画僧普明,号雪窗,俗姓曹,松江人。善画兰,《元诗选》云:“家家恕斋字,户户雪窗兰”可以看出作品受欢迎的程度。其《兰石图》画面构图把兰花摆在中心位置,上方用富有弹性的笔墨表现的竹叶和下方的石头成呼应之势,虽有荆棘(喻为小人)在侧,但姿态优雅给人以脱俗出尘之感,雪窗自题“雪窗作九畹余芬,乃屈原之《离骚》意。”张渥对其墨兰的解读在《草堂雅集》卷十题明雪窗《兰》“援琴谁叹生空谷,结佩应怜感逐臣。九畹断魂招不得,墨花夜泣楚江春。”[6]757为雪窗的墨兰画作又添诗意。
元代文人及画家在花鸟画中利用其特长选用了诗画并发的艺术手法来抒发情怀,体现出了画展诗情、诗补画意的诗画关系。
(一)画展诗情
南宋灭亡之后,很多人应征去做元代官员。独有被称为“吴兴八俊”的钱选“励志耻作黄金奴”,“老作画师头雪白”[6]478,不肯出仕元朝。自题《梨华图》“寂寞阑干泪满枝,洗妆犹带旧风姿。闭门夜雨空愁思,不似金波欲暗时”。诗只字未提梨花,而写的是寂寞悲痛欲绝的宫女,宫女和画中无色的梨花融为一体。为了表露冷漠超脱的心态,画家用纤细的干笔线条加以描绘,体现出一种无精打采的情调。花瓣的形状画得极为圆润而匀称,叶子的翻转和卷曲呈现了一种发若无力的状态。画中的梨花与诗中宫女的无奈悲情,是艺术家主观情感的流露,也是他对宋王朝深切悲哀之情的抒发。

图1 元代龚开《骏骨图》
再如龚开,南宋灭亡后隐居不仕,之后所创作的诗文和书画一律不题写元朝的年号,或只写干支,以画马来表达个人的理想和抱负,借绘画宣泄对元朝统治的愤懑。龚开作品多为高古的瘦马,造型尤为奇特。代表作《骏骨图》(见图1),自题诗“一从云雾降天关,空尽先朝十二闲。今日有谁怜骏骨,夕阳沙岸影如山。”诗写的是一匹曾经器宇轩昂、骁勇善战的骏马生不逢时,抱负无从实现,只能欷歔感叹。再看画中的这匹瘦马,骨瘦如柴,马首低垂,显得十分凄楚,以层层淡墨皴擦来表现马劲健的骨骼,从笔墨到造像都是作者对其诗意的图解。倪瓒为龚开《骏骨图》题诗云:“国亡身在忆南朝,画思诗情无不至。”更直接表达了龚开的心声。
(二)诗补画意
清代方薰在《山静居画论》云:“高情逸思,画之不足,题之发之。”一语道破了题画诗补充画意的功能。
如吴镇在《雪竹图》(见图2)上题诗:“董宣之烈,严颜之节。斫头不屈,强项风雪。”董宣,曾为洛阳令,敢于搏击豪强,京师号为卧虎。湖阳公主的奴仆仗势杀人,被公主所包庇,董宣拦其车驾杀死公主奴仆。公主诉于光武帝,光武帝令其向公主叩头谢罪,董宣拒不低头。严颜,后汉刘璋使守巴郡,被张飞所擒,自称“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此图表现翠竹傲雪的场景,再加上诗中借董宣和严颜的形象,指代竹子傲雪不屈的“气节”,竹子的特征进而成为作者自己观念的化身。可见题画诗的艺术感染力在画作中的重要性。

图2 元代吴镇《雪竹图》
元代王冕以梅花明志“花卉之中,唯梅最清”,其《墨梅图卷》仅选取梅花半枝,梅影清风扑面而来。整个画面清新淡雅,寄寓了画家高标孤洁的人格。加上自题诗“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一“淡”一“满”尽显个性。“淡”字刻画出梅花的清肌玉骨、淡泊野逸的品格;“满”字,不仅传神地写出了梅香的充盈激荡,而且使得诗人的人格魅力得以凸现。
五元代题画诗与花鸟画结合所引领的艺术新思想
题诗必须有文学修养,题画必须有书法才能,元代花鸟画与题画诗的结合必然导致诗书画一体化的崇高境界。元代的画家大多都是文学家和书法家,赵孟頫便是著名的例子。
诗文家杨维桢、张雨、虞集等也擅画。很多画家都有诗文集存世,很多文学家有题画、论画的诗文存世。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元代那样,文人、画家的关系如此密切。这与当时相对自由的文化环境和文人的闲散心态是分不开的。文人们互为引荐,切磋艺事,合作书画,唱和诗文,并逐渐形成了一个个活动中心,以书法、诗词的修养来借花鸟画抒发其情怀。于是,不再追求对客观景物的忠实描绘,把出世与入世之间的矛盾惆怅体现在“有我之境”的笔墨情趣之中。
从现存诗、书、画三者结合的作品可以看出,元代诗人和画家很欣赏这种相互映发的“合金”形式,并形成了统一的美学追求。
(一)以书法入画的“写意说”
元人论画多言“写”,这既是文人对造物之形的共识“以写意为目的”,更是以书法入画传情达意的表现。
元代花鸟画梅兰竹菊题材的盛行除了象征意义深受文人喜爱,另一个原因即它们与书法的关系。如汤垕《画鉴》“画梅谓之写梅,画竹谓之写竹,画兰谓之写兰,何哉?盖花卉之至清,画者当以意写之,不在形似耳”[9]。这便是以书入画的“写意说”。柯九思有更详尽的写竹论:“写竿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或用鲁公撇笔法。”[5]326他们画竹以书入画,别具一格。
花鸟画和题画诗中体现以书法入画的作品很多,如高克恭《墨竹》画面墨竹出枝撇叶,笔法厚重。该画上有成廷珪题诗:“黄花山主澹游翁,写竹依稀篆籀工。独有高侯知此趣,一枝含碧动秋风。”一语道出其墨竹艺术的渊源关系,也对画面以书入画的笔墨技法进行了解说。赵孟頫在《秀木疏林图》题诗“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还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这一富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见解,对文人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柯九思评云:“凡踢枝,当用行书法为之……今代高彦敬、王澹游、赵子昂其庶几。”[5]323这些在其《秀木疏林图》及《窠木竹石图》的石、枯木、竹子中得到充分体现。
在士大夫看来,写的层次要高于画的层次,内涵要高于技巧。明代屠隆在《画笺》中评论元画时便很明确地指出:“评者谓士大夫画,士独尚之,盖士气画者,乃士林中能作隶家画品,全法气韵生动,不求物趣,以得天趣为高。观其曰写,而不曰画者,盖欲脱尽画工院气故耳。”[10]脱尽画工院气,在于写,写意,正是中国传统诗歌中的意境。所谓意境,指作品中描绘的客观图景与所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艺术境界,具有虚实相生、意与境谐、深邃幽远的审美特征。而元人诗与画的结合,以书入画的写意,使画的景与诗的情,画的景与诗及书的意相互交融,获得多重性的艺术形象,能使欣赏者产生丰富的联想,在思想感情上受到感染。这正是写意的魅力所在,是元代以前院画不可能具备的。
(二)“墨戏”风尚
写意必然产生墨戏的风尚。吴镇说得好:“墨戏之作,盖士大夫词翰之余,适一时之兴趣。”[11]290吴镇在《梅花庵稿》又有:“图画书之绪,毫素寄所适,垂垂岁月久,残断争宝惜,始由笔墨成,渐次忘笔墨,心手两相忘,融化同造物。”[3]106可见“墨戏”的多层含义:一是盖士大夫词翰之余,适一时之兴趣的墨戏活动;二是墨戏过程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涂鸦,实际上是指有法而无法,看似无法实乃至法,是极高的艺术境界。这和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中言诗要“优游不迫”、“沉着痛快”、“惟在兴趣”是相通的。
倪瓒《古木幽篁图》通过一石、一树、数竹极简之景构成了一个荒寒萧疏的意境。此图中上方有作者题诗:“古木幽篁寂寞滨,斑斑藓石翠含春。自知不如时人眼,画与皎溪古遗民。”不为如时人眼而作画,只为求遗民的境界,其一时之兴趣,又是何等的深厚。
钱选富有文人意趣的清雅画作《荔枝图轴》,牟献之题诗一首:“红棉花底听春歌,我为东坡织绛罗。一任馀年前后事,诗思画笔等闲过。”可以看出,在牟献之眼中,自己的诗和钱选的画都是在极度轻松心态下完成的,并且诗与画相互达到意与境谐的境界。这种“戏”又何易达到?
(三)追求“古意”
元人追求的意乃是古意,赵孟頫《自跋画卷》云:“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今人但知用笔纤细,敷色浓艳,便自谓能手。殊不知古意即亏,百病横生,岂可观也。”[9]255这正是元代诗歌尊唐复古“得古之情性神气,则古之诗在也”[12]的反映。
赵孟頫在《二羊图》跋语中云:“余尝画马。未尝画羊,因仲信求画,余故戏为写生,虽不能逼近古人,颇于气韵有得。”[11]254戏也要追求“逼近古人”,并将其看得比气韵还重。
倪瓒题张逊《勾勒竹图》诗句“清苦何忧贫到骨,笔端时有古人风。”可见求“古意”在当时无疑是对张逊画竹的赞美和肯定。而《画鉴》云:“近世龚圣予先生……尝自画《瘦马》,题诗‘一从云雾降天阙……夕阳沙岸影如山。’此诗脍炙人口,真有盛唐风致。”[6]452这些都是元代花鸟画及题画诗“贵古”、“追求古意”的例证。
(四)“逸气”说
与古意、墨戏相联系,元人还提出“逸气”说。倪瓒《答张藻仲书》:“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6]683倪瓒《自跋画竹》:“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直与斜哉。或涂抹久之,他人视以为麻为芦,仆亦不能强辩为竹,真没奈览者何!”[9]430这些论述既表明了倪瓒作画的心境与追求,也表明了其画作造物之形的态度与方法。
倪瓒作品中也印证了“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绘画思想。《梧竹秀石图》画湖石挺立,高梧疏竹映带左右。树干和秀石行笔匆匆急就,涓涓溪流,笔法雄阔,墨气湿润。虽“逸笔草草”却颇得苍润淋漓之墨趣。元代诗人杨基题《倪云林画竹》:“写竹是传神,何曾要逼真。惟君知此意,与可定前身。”[6]704“传神”、“何曾要逼真”正是倪瓒“聊写胸中逸气”的特点。
陈高华在《元代画学史料汇编》中说:“倪瓒作品追求‘写胸中逸气’,‘不求形似’,这和赵孟頫提出的‘神似’一致,代表元代画坛的一种倾向。”[6]682其实,还应注意的是,绘画的“逸气”与杨维桢诗歌“逸气飘飘然在万物之表”的特点是一致的。而且,“神似”也好、“逸气”也好,正是古代诗歌追求风格韵味的“神韵”境界的反映。
六结语
元代花鸟画与题画诗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结合,更是诗、书、画艺术融会贯通的体现。花鸟画和题画诗的结合,使元代之前以状物为多的花鸟画呈现出了抒情、明志的艺术特征。自元以后,明清花鸟画延续了这一形式。
元代题画诗和花鸟画的结合,为诗书画融合的中国画发展史抒写了精彩的一笔。在元代九十多年短暂的历史中,花鸟画与题画诗的结合留下的不只是富有诗情画意的作品,其富有理论内涵的题画诗及画作如同一把把“钥匙”,为后人打开了研究诗画融合理论的宝库。
[1][元]汪元量.增订湖山类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4: 73.
[2]王明荪.元代的士人与政治[M].中国台北:学生书局,1992:314.
[3]杜哲森.元代绘画史[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
[4]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22.
[5]陈高华.元代画家史料汇编:上卷[M].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6]陈高华.元代画家史料汇编:下卷[M].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7]刘曦林.诗画论[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6:29.
[8]许祖良,洪桥.中国古典画论选译[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85:141.
[9]潘运告.元代书画论[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6: 327.
[10]潘运告.明代画论[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6: 134.
[11]孔六庆.中国画艺术专史·花鸟卷[M].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08.
[12]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475.
The Integration of Poetry and Painting:the Combination of Flower and Bird Paintings and Poem-inscribed Paintings in the Yuan Dynasty
SHI Hong-yun
(School of Fine Arts,Shanxi University,Taiyuan 030006,China)
The flower and bird paintings of the Yuan dynasty is in the transformation period of Chinese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flower and bird paintings.Its combination with poem-inscribed paintings,not only had a close connection with the figure of water and ink-featured flower and bird paintings in the Yuan dynasty,but also helped to bring about a new practice of freehand theory,ink play and the pursuit of the ancient meaning and the unconventional temperament.Chinese arts of flower and bird paintings had been enriched by the integration of flower and bird paintings and poem-inscribed paintings in the Yuan dynasty,and it had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drawing and theory of Chinese painting in the later day.
Yuan dynasty;flower and bird paintings;poem-inscribed paintings
I207.22;J212.05
A
1000-5935(2012)04-0031-06
(责任编辑郭庆华)
2011-12-18
山西省回国留学人员科研资助项目(0905511)
史宏云(1970-),女,山西万荣人,博士,山西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中国画理论与技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