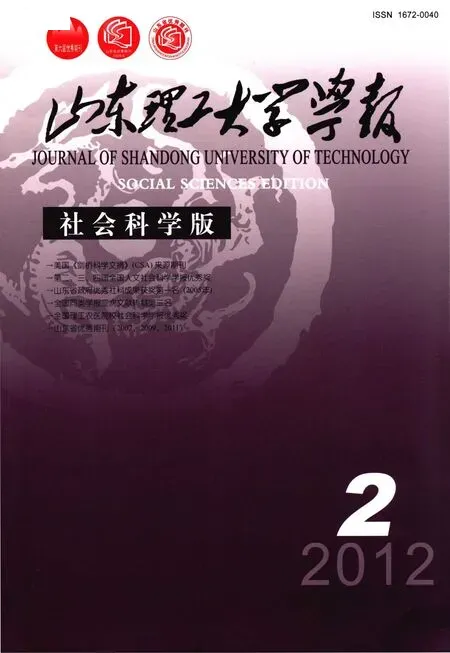《盐铁论》话语传播的文化蕴涵初探
龙剑梅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一
据《汉书·食货志》载:“昭帝即位,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视以俭节,然后教化可兴。弘羊难: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乃与丞相千秋共奏罢酒酤。”[1]117这就是西汉历史上著名的盐铁会议,召开于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是汉武帝以后国家政策和政治指导思想领域展开的一场大辩论。辩论的双方,一方是贤良文学之士,他们是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是儒家话语的最理想的代言人;另一方是汉武帝在位时长期当政的法家代表人物御史大夫桑弘羊以及御史、丞相史之辈,是法家话语的传播者、践履者。这场辩论展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大转型时期儒法两家思想的对立及其本质。《盐铁论》就是宣帝时期桓宽根据盐铁会议讨论的情况进行整理、编撰而成的一部奇书。
对《盐铁论》的研究,前人所取得的成果很多,整体上可大致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对《盐铁论》的整理、注释和翻译;二是从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哲学、文学等多个角度、不同层面对其思想内容进行研究;三是关于《盐铁论》的语言学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尝试从“话语”视角切入,在社会历史动态发展的文化层面,运用历时性的方法,纵向考察、探讨《盐铁论》所折射的汉代话语主体和形态特点;同时从横向延伸的角度,即用共时的方法,描述《盐铁论》在特定历史时空的话语表述机理以及为什么这样表述的原因,探究政治因素和社会生活对话语的制约甚至支配作用,并进而分析这些话语蕴涵的思想意识形态,从以《盐铁论》为代表的汉代话语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环境之间的共生、互动关系中探讨其话语传播及其表征的文化生态特征。
话语是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运用,是社会实践的表现形式,话语的变化是社会变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且对社会的转型、时代的进化产生影响。话语是社会时代的话语、经济文化的话语、政治生态的话语,由所在的社会时代、经济文化、政治生态环境所决定。话语具有共时性的特征,同时又具有历时性的属性。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构成了历史的轨迹,一个时代、社会的思想观念、文化特性、民族根底表述着它的话语。因此,话语是由历史决定的,受文化制约,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历史背景制约着人们说什么、怎么说、什么时候说、什么场合说、说到什么程度,以及达到什么言说目的。所以,“历史”和“文化”就具有了最高级别的话语权力和话语权威。“历史决定着话语,话语演绎着历史。没有历史也就没有话语,没有话语也就不成历史。历史的元素就是由生活在历史情境中的人们的‘言’和‘行’构成的”。“话语也是传播的产物,只有传播才产生话语,由话语研究历史,也是从传播研究历史。没有传播不成社会,假设有无传播的社会存在,那这个社会一定是一具僵尸,一定失去了表达话语的生命,当然也就不可能成其为社会”。[2]1可见,话语和社会文化传播相生相伴,是形影不离,共为一体的。我们所讨论的话语是传播学意义上的话语,是动态的活生生的话语,它伴随着文化传播,有话语就有传播,就生成文化。而我们所说的传播就是话语的传播,从表达方式看有口头话语的传播,也有书面话语的传播;从话语形态角度分析,则有政治话语、经济话语、军事话语等,其间的蕴涵就表征所在社会的特质。
《盐铁论》是西汉时的一部对话体政论性散文著作,它的出现,从西汉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衍变和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的角度来说,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从其文本的宏观和微观结构分析,其话语形式体现了中国古代散文文体的变化发展历程,又表述着西汉特定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下的话语及其蕴涵的思想文化,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作者桓宽受社会时代、文化规则的约束和限制,其话语传播表征着西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环境、思想发展潮流、人们的生活习俗和价值取向等各个方面,也形成了《盐铁论》话语传播形式的独特性,不管是其话语内容还是话语形式都与其他子书不同:既有纪实性也有鲜明的主观倾向性;既有平等对话特性,也有针锋相对的论辩个性;既体现了当时社会人际交往、面对面会话时口头话语的灵动鲜活性,也反映了汉代学者在整体谋篇布局、构架成文时对先秦诸子书面话语的吸收和利用;其话语表达视野开放开阔,既呈现典雅庄重、理论性强的风格,也具有通俗、实用、趋时的特点,正如明朝学者朱君复在《诸子斟淑》中所说:“夫《盐铁论》累累数万言,可谓闳博矣,第少古劲之气,与西汉文不类。”其中原因,笔者认为,是话语主体决定了话语的内容和形态,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决定了话语的表达特点和传播方式。
二
(一)《盐铁论》的话语体系建立在盐铁会议的真实记录之上,又体现了桓宽的文化身份特点与话语取向
桓宽作为《盐铁论》的整理、编撰者,其身份、经历史书记载不多,只知他是汝南(今河南上蔡)人,字次公,一介儒生,生卒年不详,致力于儒家著作《公羊春秋》的研究,汉宣帝时被推举为郎(即皇帝的侍从官)。能担任“郎官”的,是每年经学考试中因成绩特别优秀而留在皇帝身边的人,一般是皇帝的亲信、随从。尽管郎官级别不高,但能接近皇帝,有机会表现自己的才干,从而得到赏识和提拔。可见,桓宽在当时是一个不可小觑的人物,后曾任庐江太守丞。他著述《盐铁论》的目的,从《汉书》的记载可以略知一二。“所谓盐铁议者,起始元中,征文学贤良以治乱,皆对愿罢郡国盐铁酒榷均输,务本抑末,毋与天下争利,然后教化可兴,御史大夫弘羊认为,此乃所以安边竟(境),制四夷,国家大业,不可废也。当时相诘难,颇有其议文。至宣帝时,汝南桓宽次公,治《公羊春秋》,举为郎,至庐江太守丞,博通善属文,推衍盐铁之议,增广条目,极其论难,著数万言,亦欲以究治乱,成一家之法焉。其辞曰‘观公卿、贤良文学之议,异乎吾所闻’。”[3]269桓宽在盐铁会议记录的基础上加以扩充而成《盐铁论》,申述了个人的观点,表达了自己作为编撰者的思想倾向,正如他在《盐铁论·杂论》中所表述的:“客曰‘余睹盐铁之议,观乎公卿、文学、贤良之论,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仁义,或务权利。异哉吾所闻。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长久殊世。始汝南朱子伯为予言,当此之时,豪俊并进,四方辐凑。贤良茂陵唐生,文学鲁万生之伦六十余人,咸聚阙庭,舒六艺之讽,论太平之原。智者赞其虑,仁者明其施,勇者见其断,辩者陈其词。訚誾焉,侃侃焉,虽未能详备,斯可略观矣’。”[4]426由此可知,桓宽以“客”自称,借以体现其写作目的,对盐铁会议发表自己的评论和看法。这种方法早在《左传》中就已出现,编者和作者融为一体,类似于今天的“编后记”或“编者按”。另外,“睹”和“观”强调了现场感,说明《盐铁论》一书是在真实的会议记录基础上扩展的,讨论的是关于帝王南面之术的话题。因此,从其内容实质来看,《盐铁论》属于关系国计民生大事的政治性话语,是客观的真实性和主观的倾向性的统一。参加会议的朱子伯与桓宽是同乡,告知了他与会人员的选拔过程以及论辩的经过和情形,很显然两派势力之间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因此《盐铁论》话语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激烈的对话论辩性特点。桓宽在后面文章中又提到中山刘子雍和九江祝生,并通过他们对当时在会议上发言的内容和发言时情景的描述,进一步证实了《盐铁论》所记的内容的真实性和现场感,充满了时代气息,反映了桓宽的文化特性和个人的主观色彩,体现了桓宽深受儒家话语影响的政治观念和价值取向,同时表明桓宽是代表贤良文学的思想观点来撰写此书的,其宣扬和传播的主体取向是儒家的思想内容和话语体系。
(二)“贤良文学”与“大夫”的对话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汉代儒、法两家思想的激烈交锋,是西汉社会政治力量的现实对比与较量的集中表现,是其社会文化生态的形象写照
《盐铁论》凡六十篇,全部采用对话体,是汉代子书中独具一格的政论文,其对话主体是儒家和法家两派的代表。一派是“贤良”(已有功名但还未授予官职的读书人)“文学”(读书人)六十余人,属于饱读经书的经学之士,其思想道德的主色调是周公、孔孟之道,是儒家思想的典型代表,运用的是儒家话语;另一派是御史大夫与御史、丞相史,属于在朝的当权派、实力人物,是汉武帝所依仗的功臣,其政治信仰是管仲、商鞅、韩非、秦政之法,是法家思想的忠实继承者、实践者,宣扬和运用法家话语并加以推行。前者要求实行王道统治,以儒家之学说作为治国的思想基础和文化之根;后者则坚持以霸道或法家之术来治理国家,统一天下,控制人民意志。而从盐铁会议上双方争辩的实际效果来看,贤良文学取得了最后胜利。也就是说,贤良文学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到了话语权,因为他们所代表的儒家话语,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趋势,体现了社会转型时期思想上的大一统文化背景,成为了汉代政治舞台上的主流话语。可见,贤良文学所主控的儒家话语就是作为话语主体的编撰者桓宽所要表达的,因为话语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决定着话语主体的言说方式,话语主体所要表达的思想受制于汉代当时的社会思潮和文化环境。其表征的是社会上层知识分子、文化精英的话语特色,具有干预社会、参与政治、掌控现实的责任感和功利目的。从话语的思想内涵和深度来看,汇聚了当时社会精英的一些思想言论,具有群体性、团体性的意义,反映了汉代社会的话语特征特别是社会上层主流的话语倾向,带有强势话语的特性,具有政策的导向性和指导意义。
(三)《盐铁论》的话语是汉代儒学向广度、深度发展而成为盛世经学的产物,其话语传播的结果是儒学加速走向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儒家话语成为了政治话语
汉朝在武宣之世达到了政治、经济的全面繁荣。武帝即位,揭开了汉朝全盛的序幕,“外攘四夷,内改法度”,[5]336大兴事功,特别是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6]237这样,儒家思想成为了治国之指导思想,儒家话语成为了主流政治话语,儒学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儒士成为了汉代当时社会上重量级的思想文化精英,并被委以重任。“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7]333在公孙弘为学官时,上书汉武帝设立太学,建议为博士招设弟子。据《史记·儒林列传》载:“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臣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8]341在中央设立太学,在地方设立各级学校并规定明经者可以担任各级官吏。由于读经可以仕进,举国上下就出现了读经的高潮。正如清代学者皮锡瑞所说“此汉世明经取士之盛典,亦后世明经取士之权舆。”[9]73据《汉书·儒林传》载:“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10]333经学之兴盛,可见一斑。基于此,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一书中将武帝至宣帝时期称为“经学昌明时代”。然而经学与儒学又有何关联呢?“经学是阐释儒家经典的学问。这种阐释既有官方承认的学者,也有民间的学者。只要是以研究、诠释儒家经典为学问,就可以称为经学。它确实比孔学宽泛,比儒学狭窄。经学所用的是阐释学或诠释学方法,通过对儒家经典的诠解来表达自己的思想”。[11]103关于经学及其性质,有研究者说:“所谓‘经’,是指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编书籍的通称;所谓‘经学’,一般说来,就是历代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僚对上述‘经典’著述的阐发和议论。”[12]656可以说,经学是儒学在汉代武帝、昭帝、宣帝时期最大范围传播和最强势发展的结果,是儒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反映。这样,儒家话语就逐渐发展成了强势话语,这与经学的兴盛是密不可分的,直接影响汉代社会的政治导向、主流思想、官方话语形态。儒家精神就是以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文化道义感为核心价值的文化精神。汉代经学讲求通经致用,以治经解决现实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可以说,治经是当时社会普遍公认的一条获取功名利禄的捷径。所以,经学之士注重义理、联系实际的治学方法显然符合当政者的要求,他们政治上的得势是必然的,而且享受着政治特权,领取着国家的俸禄,占据着官场高位,垄断和把持着学术、文化资源,也就是说掌控了政治话语权力和权威。依此,儒家话语就成为了汉代政治话语的核心思想和主要内容,是儒家文化不断发展、长期积淀的产物,是儒家学术思想和时代政治的现实结合。这就决定了中国学者走上政治化、官僚化仕途的必然性。
(四)从其实质内涵来看,《盐铁论》的话语体系属于为当时统治者的现实需要提供思想指导的政治性话语
盐铁会议的召开,其背景本来就非常复杂,会议是汉昭帝下诏,田千秋丞相主持召开的,而成书却已是汉宣帝在位之时,期间相距二三十年;从会议召开前的筹备到正式举行,由会场上参与者亲历的场景到记录者的文字笔录而成为“议文”,再到宣帝时桓宽整理编次成为今天能见到的《盐铁论》,期间时空位移,传播媒介发生变化:由盐铁会议上身体、姿势、言语等“呈现性媒介”到能保存符号的文本即文字书写的“记录性媒介”,一直到流传后世,不同时代的读者接受过程中“心灵媒介”的改变,等等。这一切使文本内容本来就复杂的《盐铁论》,呈现出更加丰富多样的特点,反映了社会的变化、时代的转型和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尖锐复杂的斗争。儒家学说定于一尊,并作为举国上下共同遵守的一种话语体系,甚至作为统治者制定国家方针大略的基本依据,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儒学经典化、法制化的过程,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统一完成于儒学话语体系的过程。受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与文学观念的影响,当时文人普遍以政教实用为创作目的,促成了武帝时代的政论散文本于经术、政教色彩浓厚的新特征。后来,随着汉武帝军事征伐手段的实施,在东西南北各个方向开疆拓土,汉帝国版图扩大,加之丝绸之路的开通,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往来以及多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吸收渗透,整个汉朝社会,其话语也由丰富、多元渐趋于交融、整合,最后臻于大一统。这些具有“意识形态充盈物”特性的话语,必然符合统治者巩固自己政权的现实需要,所以,它反映到《盐铁论》文本中,就具有鲜明的现实性、政治目的性、时代大一统的话语传播特征,用桓宽自己的话来概括即“欲以究治乱,成一家之法焉”。
[1]班固.汉书二四下·食货志.二十五史·卷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2]田中阳.蜕变的尴尬——对百年中国现代化与报刊话语嬗演关系的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
[3]班固.汉书六七·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二十五史·卷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4]马非百.盐铁论简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
[5]班固.汉书八九·循吏传.二十五史·卷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6]班固.汉书五七上·董仲舒传.二十五史·卷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7]班固.汉书八八·儒林传.二十五史·卷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8]司马迁:史记一二一·儒林传.二十五史·卷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9]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0]班固.汉书八八·儒林传.二十五史·卷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11]李生龙.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M].长沙:岳麓书社,2009.
[12]周予同,汤志钧.“经”、“经学”、经学史[A].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