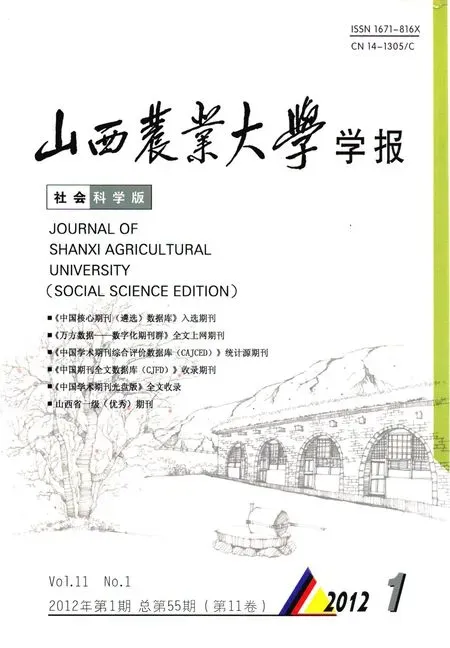人情交往在我国农村存在的价值
金梦,张蓉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100193)
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造成的后果是很多农村社区中只剩下留守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农业生产和生活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研究者提出 “农民进城”让更多的农业户籍人口能够通过土地权利的流转进入城市;或是农民上楼,甚至提出发展城市和小城镇以取代农村。实际上,农村社区的功能很丰富,绝不仅仅是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的问题,在农村中,传统的人际关系网络的不断建构,使得社区成为城市劳动力的蓄水池、社会发展的稳压器,更是区域稳定的基础。
一、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研究
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对中国传统乡土社会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体现当时最为典型的 “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农村社会人际关系—— “差序格局”理论。[1]这种理论模式勾画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逐渐向外侧推移,以显示出自我和他人关系的亲疏远近程度的关系图景。而农村的人情正是以地缘和血缘为核心内容发展起来的。翟学伟指出,传统 “中国人际关系的基本模式是人缘、人情和人伦构成的三位 (三维)一体,它们彼此包含并各有自身的功能。一般来说,人情是其核心,它表现了传统中国人以亲为核心的心理和行为样式”。[2]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3]伦理关系即 “表示一种义务关系;一个人似不为其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者”。[4]在中国社会处处见彼此相与之情者,因而,伦理社会是个人情的社会。
徐晓军指出,转型期的农村人际交往转型期乡村社会交换的变迁是网络性交换的非网络化和非网络性交换的网络化同时并存的局面,是人情与理性的融合,是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融合。[5]阎云翔认为,差序格局也是一个平面多结的网络,并且是一种立体多维的结构,包含有纵向的刚性的等级化的 “序”,也包含有横向的弹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 “差”。差序格局的维系有赖于尊卑上下的等级差异的不断再生产,而这种再生产是通过伦理规范、资源配置、奖惩机制以及社会流动等社会文化制度实现的。[6]他将差序格局理论置于更加复杂的社会网络之中,探讨农村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和多重性。
尽管谈及中国的传统社会形态和人际关系,学者们有各自不同的视角和判断,但是以血缘、地缘为核心的 “人情”始终是人际关系的重点,农村社会人际交往的核心。
二、农村人际交往中的 “人情”表现
在传统的农村社会中,礼物交换的延伸和常规化被称为 “人情”。而人情往来成为了人际关系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的形式,在农村中,人与人之间无时无刻不彰显着人情。
按照学者杨华的区分,农民生活中的人情分为日常性人情和仪式性人情。[7]日常性人情是在正常生活中进行 “给予”和 “亏欠”之间产生的人情,仪式性人情则是指红白喜事等大型活动和具有仪式性的活动中的人情往来。
日常性的人情体现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平日里的聊天、串门、打牌下棋,地头间为抢农时的相互帮忙、农具的共享,生活上帮忙、搭伙、劝架、开导、调和都是人情,它就像是农家的炊烟,弥漫环绕着村庄,人们都能感受到人情的气息。而人情是一张网,每个人都要不断去编织,去扩大这张维系个体乡村生活的网。在陕西关中地区的农村,周末有集,如果谁家去赶集没有了装货物的篓,就会向别家借,借的时候是空篓,归还的时候一定要放上几个苹果或是一把韭菜,算作是对借篓的一种感谢,是还了对方的人情;而借出篓的一方,收到了篓里的东西,便会将这看作是一种新的人情,于是不断加固着这张大网。
仪式性人情一般都是以人生大事为切入点的,比如结婚、丧事、生孩子、过寿等。仪式性人情的影响范围往往是整个村庄,甚至是乡村以外的生活情境。如果说伴随着农业机械化生产和劳动力转移,今日的农村中,人们的日常交往减少,仪式的存在是对人际关系的有效补充。通过仪式性交往,人们不断巩固和延续着人情,参加喜宴的人会依据自己与主人家的关系远近和村中的规矩行礼,以示祝贺,这便是一种有效的往来形式,不仅村民与主人家沟通了感情, “交换”了人情,其他的人也借此增进了往来。尽管近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婚丧嫁娶的消费日益增加,有些地方甚至形成了攀比之风,但仪式背后始终充满了浓厚的乡土感情,给村民提供了情感和心理的归属。
日常性人情和仪式性人情的考察是对农村人情的感性把握,这里还需要对人情进行梳理,以更加明确乡土社会人情的内涵。
(一)人情是一种交换
在乡村生活中,人情交往首先是一种交换,是一种礼物的馈赠,它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互惠。社会交换理论的假设是,社会交往的双方都是理性的,希望通过 “交换”有形或无形的资源以实现 “互惠”。其核心思想是,人类的大多数行为,其目的就是在寻求回报最大、成本最低的人际交往。[8]莫斯曾在著作 《礼物》中,就对原始社会中礼物的交换现象进行了研究,指出了礼物的交换遵循着一定的逻辑,体现了整个社会网络的内在规则和需求。在中国的乡村,“人情就是礼物交换的核心”。[9]无论是日常性人情还是仪式性人情,礼物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传递情感的媒介。农民送出去的一个苹果、一把韭菜,或是随的 “份子钱”,传递出去的无不是人情。人情的背后是一种交换的逻辑,对回报的期待,它是人们交往的动力,是维持人际关系的纽带。
(二)人情是一种关系
人情的交往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体现。礼物的交换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农村的人情往来就是建立在血缘地缘基础之上的交往关系。“在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为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叫 ‘街坊’。有喜事要请酒,生了孩子要送红鸡蛋,有丧事要出来助殓、抬棺材,是生活上的互助机构。”[1]这个圈子就是礼物交换的范围,日常交往中,圈子里的人相互走动更加频繁,人情往来更加密切。仪式性事件更能体现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社会网络,体现出一个人或一户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远近亲属都建立在这种人情搭建起来的关系网络上。
(三)人情是一种文化
人情是一个链条,人们在其中不断往复,乡土社会中,这种往复绝不仅仅是理性的互惠,蕴含着传统农村的文化智慧。正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孕育了 “人情文化”的温床。黄国光写到:“在这个社会里,个人和他的家庭世世代代定居在一定的土地上,每天接触的,除了家人之外便是亲戚、街坊、邻居等有关系的人,很少有机会与不相识的 ‘外人’打交道,所以便发展出 ‘讲人情’的文化形态。”[10]地方性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理解不同地区人情交往的形式、内容的差异,但是,无论形式如何,人情交往背后体现的是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是乡土社会悠久的“人情”智慧。
三、农村中 “人情交往”的功能分析
农村中的人情往来是乡村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以语言、行动和礼物等符号化形式联系着人与人,使乡村共同体成为可能。人情交往的社会功能非常丰富,对社区本身和对整个社会而言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人情交往对村落社区的功能分析
1.稳定农业生产
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周期性的特点,因此老百姓常说,不误农时。从播种、施肥、耕地、锄草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一旦错过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因此,无论是工具上的互助还是人力上的互助对农业生产都是必要的。费孝通在 《江村经济》中有这样的描述:“水的调节是需要合作进行的。在灌溉过程中户的成员,包括女人和孩子都在同一水车上劳动。在排水时必须把一墐地里的水从公共水沟里排出去。在同一墐地里劳动的人的命运是共同的。因此便出现了一个很好的组织起来的集体排水系统。”[11]现在的农村更是如此,随着进城务工队伍的扩大,农忙时节的互助变得更加重要。
2.促进信息交流
人情交往是社区中传递信息的重要渠道。无论是农业生产技术的使用和推广还是外出务工的就业信息,都在熟人之间流动,而且因为从众心理的长期存在,农民往往更相信熟人的经验胜过传媒的宣传。这些信息本身就是一种人情的符号。学者研究农村社会劳动力转移指出,进城农民工获得的就业信息和资源都是强关系提供的,强关系在中国表现为人情。[10]可以说,进城务工的人往往是根据村庄中已有的信息作出流动的决策。
3.维护村庄和谐
典型农村生活的形态是一种彼此熟悉且亲密互动的社区,人们在交往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矛盾问题,人情往来起着调节的作用。农村社会中,有一张人情网,每个人都在这种网中,无法割断与他人的联系,矛盾问题就像是网上的一个洞,不解决就会破坏整个 “人情网”。举个简单的例子,邻里出现了矛盾,但是一家有了红白喜事,作为人生大事,根据乡间的习俗,邻居也要“随份子”表达心意,办事的人家也就借着事,化解了矛盾。此外,互相交好的生活场景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农村公共生活的形式和内容,因为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为丰富而多样的文化娱乐活动、乡村公共生活提供了群众基础,也提供了展示的舞台。
(二)人情交往对社会发展的意义
1.人情交往形塑着人们的社会交往,维持社区整合的功能,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尽管现在的村庄不再是大集体时期的行动共同体,但却提供给一个居民在处事时所需动员的社会关系。在生产方面,他可以通过自己的渠道获得合作者;在生活中,遇到困难也可以找到心理和行动的支持;社会中存在着 “礼治秩序”,因此个人在遇到问题时不会束手无措。总而言之,一个具体的村民被种种强有力的关系挂在村庄社会这个 “人情网”上,这个网也是村民生活的一张安全网,为他提供物质、精神和情感的支持。相应地,对于他所生活的村庄而言,正是每个人拥有的网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复杂而又清晰的社会关系,构成了社区共同生活的基础。人情交往不断延续着人们的关系,增强彼此的感情,使得整个社区保持一种向心力,而正是它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农村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只有农村社区实现了团结稳定和发展,整个社会才能实现大发展。
2.“人情”为人们提供了心理的归属
对农村社区来说,随着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流向城市,留守的老人和儿童承担起农业生产的重任。一方面,他们在劳动生产的过程中相互帮忙,村中剩下的劳动力会相互帮助,另一方面,村中的其他劳动力也会提供帮助,共度难关。可以说,人情成为了非常重要的因素,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选择。而在这种互助中,人情又得到了巩固和提升。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社会网络对出门在外的人是一种强大的心理安慰,进城的人往往也是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展开自己的社会交往,甚至形成一种 “虚拟社区”建构他们在城市中的社会支撑体系,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进城务工人员的心理归属和情感需求。[12]因此,人情交往对于整个村庄社区的稳定、对于在外务工的大量流动人口、对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形塑都有着积极意义。
四、结论与讨论
对于发展中的社会而言,农村有着格外重要的作用,农村社区不但不能没有,还要建设好。当前,农村的生活条件日益改善,物质水平不断提高,然而农村的核心是 “人”,农村的生命力在 “情”,没有了 “人情”农村将成为一潭死水,没有生气。无论是农业生产、农民交往和农村社区的稳定与和谐都离不开 “人情往来”;而人情交往对村落传统文化的传承、人们心灵的慰藉以及整个社会的稳定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延续农村的人情往来,促进社区的和谐发展,值得深入思考。
[1]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6,68.
[2]翟学伟.中国人际关系的特质——本土的概念及其模式 [J].社会学研究,1993(4):79.
[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73.
[4]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醒 [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33:86.
[5]徐晓军.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交换的变迁 [J].浙江学刊,2001(4):74.
[6]阎云翔.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J].社会学研究,2006(4):201.
[7]杨华.农村人情的性质及其变化 [J].中南财经大学研究生学报,2008(1):43.
[8]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56.
[9]阎云翔,李教春,刘瑜译.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19.
[10]萧新煌,文崇一主编.中国人:观念与行为 [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44.
[11]费孝通.江村经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54.
[12]柯兰君,李培林.都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 [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40.
[13]俞军备,杜仕菊.人情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初探 [J].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5,(4):88-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