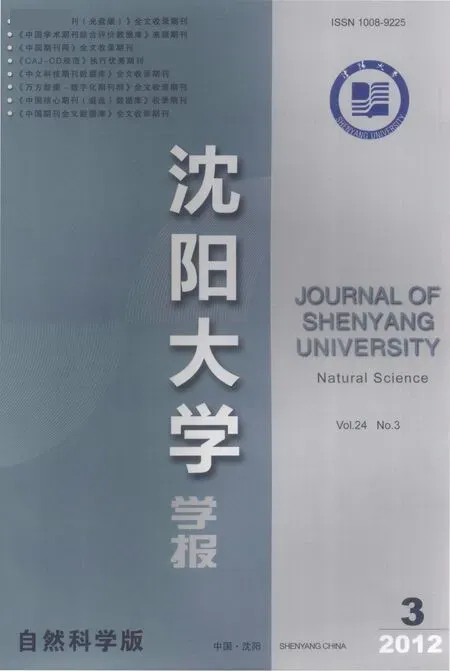在文明与生命之间小说《儿子与情人》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与反思
程 悦
(沈阳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沈阳 110041)
在文明与生命之间小说《儿子与情人》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与反思
程 悦
(沈阳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沈阳 110041)
研究了现代主义小说家戴维·赫伯特·劳伦斯的自传体小说《儿子与情人》,认为其通过描述扭曲病态的两性关系,对西方文明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与批判,分析了小说关于异化的文明已经背离了人的自然生命,西方人已经陷入深重的文明危机之中的主旨意义。
文明;生命;危机;拯救
小说《儿子与情人》是英国著名小说家戴维·赫伯特·劳伦斯的早期成名作,也是其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在这部小说中,劳伦斯以病态扭曲的两性关系为切入点,展现了主要人物内心情感的压抑、扭曲,乃至变异,以及他们的痛苦、挣扎和绝望,从而探寻西方文明危机的症结所在,并努力寻求拯救西方文明的希望与道路。
一、病态的文明
这部小说一开篇就指出矿工家庭居住的地方洼地区生活环境的丑陋。乍一看,这里的房屋还不错,构造结实,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小园子,屋子下还种满了漂亮的植物。但是紧接着作者又指出,“这只不过是外观,”日常住人的房间“看到的只是一个难看的后院,还有垃圾坑。在两排房子当中,两长行垃圾坑当中,是一条小巷,孩子们玩耍,女人们聊天,男人们抽烟都在巷子里,”“一间间厨房却面对着那条有好多垃圾的臭巷。”[1]2
这种丑陋的生活环境是矿工家庭实际生活状态的隐喻。从表面上看,这里的居民经济状况虽说拮据,但绝非赤贫。然而他们的内心却痛苦抑郁,两性关系紧张对立。在洼地区,几乎每一个矿工都不受家庭的欢迎。几乎所有的女人都厌恶那些散发着汗臭味浑身沾满了煤屑的男人,尽管这些男人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
这里的丑陋也是貌似兴旺发达实则丑陋不堪的西方现代文明的隐喻。劳伦斯在《诺丁汉矿乡杂记》中说:“……真正的悲剧在于其丑陋。……那些普通的矿工……上井来到白天的光线中看到的尽是冷酷和丑陋,面对的是纯粹的物质主义。……他们作为人是被毁了……是让铃声叮咚的寄宿学校、图书、电影院和教师给撂倒了。……工人沦落到丑陋的境地,丑陋,丑陋,卑贱,没人样儿。丑陋的环境,丑陋的理想,丑陋的宗教,丑陋的希望,丑陋的爱情,丑陋的服装,丑陋的家具,丑陋的房屋,丑陋的劳资关系。”[2]27
可见,在劳伦斯笔下,丑陋一词不仅仅指生活环境的肮脏破败,更是指工业文明甚至整个西方现代文明对人的戕害。支撑西方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石工业、宗教、婚姻、道德、政治,以及人的理性,劳伦斯都用这个词来形容,那就是丑陋。在劳伦斯看来,外表的丑陋源于内在的病态,这个病就是文明的危机。
对于西方文明危机的认识,劳伦斯深受尼采的影响。尼采哲学思想的核心,就是对生命价值的热情讴歌,对非理性的生命力的张扬,对扼制生命意志的理性主义思想的批判,以及对统治欧洲将近两千年的基督教道德观的抨击。他认为,基督教重灵性轻肉体,其道德观使人类的生命之火渐渐熄灭,使人类原本自然健康的生命变得衰败、腐朽,使人类社会到处充塞着腐朽、贪欢与纵欲,到处挤满了“灵魂的痨病者”,西方现代文明正在走向灭亡[3]42。在劳伦斯作品中,基督教道德以及理性主义思想,常常被描写成破坏人性的完整、削弱生命力的异化力量。
此外,在叔本华的影响下,劳伦斯认为生命的本质是非理性的生命意志,而生命意志的首要表现就是“性驱力”。然后又从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劳伦斯看到了文明与“性”的冲突。然而,与这位站在文明的立场、把性压抑看做是人类文明的伟大成就的心理医生不同,劳伦斯认为“性与美是一回事”,性与生命密不可分。他认为文明给人类带来的最大灾难就是压抑性、残害性,使人的性欲失去了生命的本来面目,堕落成为丑恶的淫欲[3]51。在劳伦斯的作品中,如《虹》《恋爱中的女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主人公们的爱情往往超越社会文明中的功利主义或者道德习俗,以两性之间的性吸引力为基础,闪耀出纯净的生命与灵魂之美。同时性行为也被赋予深远的意义,被作者浓墨重彩地描写。虽然这种赤裸裸的性描写即便到了今天也是值得商榷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其中的进步意义。
总之,劳伦斯认为西方文明已经背离了生命的根基,陷入危机之中。它灌输给人们僵化的观念和偏见,其正义的面孔之下掩藏的精神核心是丑陋庸俗的物质主义。它制造了痛苦的两性关系,从而给人性带来致命的损伤。难怪洼地区的生活环境会那么丑陋。难怪矿工们的家庭永远都不是温馨的港湾,而是一个令男人和女人都倍感痛苦的伤心之地。
二、病态的两性关系
在《儿子与情人》这部小说里,劳伦斯展示了一个病态的人群,他们的痛苦集中表现在人类世界最古老、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两性关系上。令读者感到尤为不安的是,劳伦斯在小说中暗示,随着文明的传承与积累,这些人的痛苦可以代代相传,不断延续下去。
保罗的母亲格特鲁德出身于一个没落的中产阶级家庭。她从家族以及整个文明世界那里继承的是道德、宗教、理性以及“上等人”的趣味与价值观。按照文明世界的评价标准来衡量,“她是一个白璧无瑕的少女”[1]10,彻彻底底地是一个西方文明的产物。而她的丈夫莫雷尔先生则完全不同,他从十岁开始就在黑暗的井下工作,文明社会在他身上只留下很少的一点印记。他“生命里那股情欲之火不断散发出幽幽的幸福的柔情,就像蜡烛冉冉发光似的从他那血肉之躯中自然流露出来”,不像“她生命里那股火花受思想和精神的压制和支配,发不出光来”[1]11。格特鲁德起初的确受到了这股生命之火的吸引,但是在她的爱情中还是道德判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她觉得他很高尚,因为他每天冒着生命危险,却还是一团高兴”[1]12。
其实,这个文明世界曾经向她展示过其冷酷无情的物质主义真面目。她的第一位恋人为了摆脱经济困境竟然放弃理想与爱情,娶了一位年过四十的富孀。虽然她也曾为此感到深深的幻灭,但文明世界的理念已经内化为她的自我,使她丧失了自然的本能与直觉,根本无法理解并接纳婚后所面对的这个依然保持着生命本然状态的矿工世界。她不可能明白,她满心渴慕的文明世界是以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为基础的,而恰恰是这种无情而沉重的工业生产使丈夫沦落到所谓“粗俗可憎”的地步,它使矿工们根本无暇顾及精神生活、文化修养以及风度仪表。并且,她更不可能明白,她所看重的所谓优雅、体面与教养,倘若背离了真实而健全的生命,将是多么虚假而肤浅,其本质是对富有阶层的趣味的趋奉,完全是物质主义价值观的间接表现。
劳伦斯在《诺丁汉矿乡杂记》中指出,井下的体力劳动使矿工们可以更真切地感知生命。他们始终与黑暗打交道,保持着生命的本能,躲避着智性的一切。而女人们则始终生活在日光下,用理性衡量着身边的一切,用物质主义的原则处理各种日常事务[2]25,其社会性已经完全湮灭了自然生命中的血性与灵性。这种本质上的差异割裂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沟通,使彼此失去两性之间的吸引,完全沦为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夫妻关系。
于是,文明成为阻碍格特鲁德理解丈夫、热爱丈夫的异化力量,使她时刻生活在强烈的幻灭感之中。她与丈夫之间毫无两性之间的爱情可言,她给予丈夫的照料仅仅出自于根深蒂固的道德感。尤其是在大儿子被文明世界的虚假爱情吞噬了生命之后,生活之于她,只是一场与贫穷、丑恶和粗俗进行的搏斗。她的心灵渐渐枯竭,只剩下一副顽强的意志苦苦支撑着,唯一的慰藉就是与二儿子之间的那份变异的感情。最后,唯有死亡才能平息她的痛苦,使她摆脱文明造成的扭曲,恢复生命最初的美好。
同时,这不仅是格特鲁德的悲剧,还是丈夫莫雷尔的悲剧。这个辛苦挣钱养家的汉子被完全排斥在家庭生活之外。妻子在感情上抛弃了他,而孩子们也在母亲的影响下对亲生父亲充满了偏见和仇恨。这或许可以看做是“文明”对生命犯下的第二宗罪。它除了压抑扭曲生命,还排斥抵制生命,使保持生命本色的人只能徘徊在文明社会的主流之外,饱受歧视和孤独。
父母的悲剧传递给了下一代。二儿子保罗对母亲的那份微妙感情,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可以称为“俄狄浦斯情结”,即恋母情结。国内外有很多著名学者断言,这部小说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将弗洛伊德的理论小说化、艺术化”,并视“这部小说为第一部弗洛伊德式的英语小说”[4]509。其实,劳伦斯本人坚决反对这样的观点[5]28。这部小说让读者看到,是病态的西方文明阻断了两性之间生命的纽带,从而制造了痛苦的婚姻。痛苦幻灭的母亲不知不觉地把内心里最后那一点柔情全部倾注给了保罗,从而阻碍了保罗的心灵成长,使他形成难以摆脱的心理障碍。通过这对母子,劳伦斯向读者展示的不仅仅是一种病态的“情结”,更是一个病态的文明。
保罗的第一位恋人米利安与他的母亲颇有相似之处,她们的直觉与感性都被病态的文明观念严重压抑扭曲了。而且,比起格特鲁德,米利安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她的生命之火完全被理性、宗教与道德熄灭了。她与保罗的爱情就是“书本点燃的一场火,书本没了,火也就灭了”[1]341。她的内心世界完全浸淫在虚幻的宗教氛围中,很少关注由真实的人构成的真实的世界,“不去关心别人,也很少有人关心她”[1]326。她的爱情没有为性留下一席之地,她从笃信基督的母亲那里听到这样的观点并深信不疑:性是女人婚后不得不忍受的东西,是女人为男人作出的牺牲。因此,尽管她拥有少女的美貌与娇艳,但保罗却说:“你是个修女。”[1]273与保罗母子一样,她也是个病人,她的病也是从文明世界那里继承而来。
三、拯救与希望
既然文明已陷入危机,劳伦斯就把目光投向了大自然。在这部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主要人物都喜欢沉浸在美丽的大自然里,让心灵的伤口得到抚慰。而作者对于大自然的描写更是细腻优美、充满诗情画意,与洼地区居住环境的丑陋以及人物内心的扭曲痛苦形成鲜明的对比。热爱大自然就是热爱生命,因为生命是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诞生的,那里保存着生命最本初最原始的记忆。与尼采的生命哲学相对应,劳伦斯提出“血的意识”。他呼吁现代人“倾听血管中黑径上高贵的野兽发出的声音”,“向内倾听,向内,不是听字句,也不是获取灵感,而是倾听内心深处野兽的吼叫。”[6]他希望现代人能够回到生命的自然状态,恢复生命最初的直觉与本能,以此来矫正病态文明对人的扭曲。
当然,劳伦斯并非是要放弃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虽然精神性的米丽安不能满足保罗,可代表肉欲的克莱拉同样不能满足保罗。他所渴望的是灵与肉和谐统一的爱情。与此种爱情观相对应的,是他的阶级观。保罗认为从老百姓那里他可以感受到生活和温暖,但是只有从中产阶级那里他才能得到思想。从保罗在人生道路上所作的选择来看,他更愿意作为一个独立于阶级而存在的人,也就是成为一个超越病态文明、独立而完满的人。对于现代大工业生产,保罗也并非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他的愿望是:工作就是人,人就是工作,人与工作浑然一体。由此可见,与其说劳伦斯反对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还不如说他意欲整合被西方现代文明割裂了的生命,从而把文明从异化的危机中拯救出来。
至于宗教,劳伦斯反对的是背离自然生命的宗教教条,实际上他“从未嘲笑过宗教情感”[5]21。主人公保罗的身上就明显带有救世主的色彩[7],他的使命是阻断人类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悲剧命运。从生命的孕育到出生,以及从被命名的过程来看,保罗这个人物具有浓厚的宗教象征意味。更为重要的是,保罗是这部小说里唯一能够进行主动反思的人,从而具备成为第一个觉悟者的条件。保罗的心灵“就像诺曼底式的教堂拱门,重重叠叠,意味着不屈不挠的人类灵魂,顽强地向前跃进,不停前进,漫无止境”[1]190。与米利安“直冲云霄”式的、脱离现实的宗教冥思不同,他的思索是以真实的人性为基础。作为一名画家,保罗充分理解“自然”的含义,他的画作常常闪耀着“生命的原生质”[1]163。他的弑母行为是一个象征,宣告他与人类病态而痛苦的过去彻底决裂,从而获得了精神的独立。在小说的结尾,劳伦斯写道:“他握紧拳,抿着嘴。他决不走那条路,决不步她的后尘,走向黑暗。他加快步伐,朝着隐约中热气腾腾、生气勃勃的城市走去。”[1]455
四、结 语
与劳伦斯其他作品明显不同的是,《儿子与情人》这部早期作品尚未出现倍受评论家们争议的性描写,因此被同时代的大师们所接纳,并受到高度赞扬。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如此赞扬这部书:“这部书的效果从未达到过稳定的地步……这部书中的世界似乎永远处于凝聚和解体的过程中……似乎充满着某种被压抑的激动、不安和欲望,就像男主人公的躯体一样……他不继承任何传统,也不属于现在,除非它影响到将来”[8]。也就是说,这部书的叙事形式本身就蕴含着主人公保罗所珍重的“生命的原生质”,流露出劳伦斯对文明的抵抗以及对生命本然状态的向往。
虽然小说中所描写的某些宗教观念和道德观念源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特殊的宗教氛围与道德观念,而恋母情结也并非人类社会中的普遍现象,但是这部小说仍然具有超越时代的思想价值,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如何才能使社会文明与人的自然生命和谐统一,在文明危机中人类将向何处去,这些问题在当代世界变得更加复杂尖锐了,是今天的人们仍然在不断思考、不断探索的重要课题。
[1]劳伦斯.儿子与情人[M].陈良廷,刘文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2.
[2]劳伦斯.劳伦斯随笔集[M].黑马,译.深圳:海天出版社,1995:27.
[3]刘洪涛.荒原与拯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42-45.
[4]侯维瑞,李维屏.英国小说史[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5:509.
[5]Fernihough,Anne.D.H.Lawrence[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28.
[6]劳伦斯.小说与情感[M].姚暨荣,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88:209.
[7]贾晓庆.工业时代的耶稣[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4(2):51.
[8]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M].瞿世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223-224.
【责任编辑 王立欣】
Between Civilization and Life Criticism and Reflection on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Sons and Lovers
CHENG Yue
(Foreign Language College of Shenyang University,Shenyang 110041,China)
The modernist novelist D.H.Lawrence’s autobiographical novel,Sons and Lovers is studied.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rough focusing,on the distorted relation between man and woman and he reflected and criticized the western modern civilization profoundly.It is analyzed that the alienated civilization has run counter to the natural essence of human life and the westerners have been pushed into the deep crisis of civilization.
civilization life;crisis;salvation
I 106.4
A
1008-3863(2012)03-0117-04
2011-09-13
程 悦(1975-),女,辽宁沈阳人,沈阳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