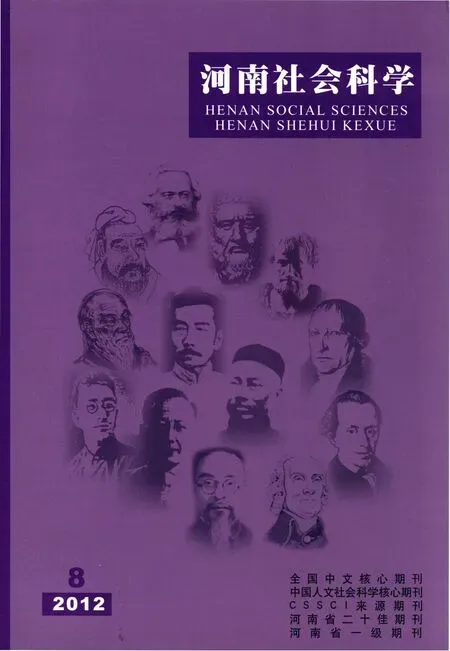论高校学报的精神内涵
——以《北京大学月刊》、《清华学报》为考察对象
晋海学
(河南师范大学 学报编辑部,河南 新乡 453007)
论高校学报的精神内涵
——以《北京大学月刊》、《清华学报》为考察对象
晋海学
(河南师范大学 学报编辑部,河南 新乡 453007)
中国高校学报的精神内蕴是对学术不懈的追求。诞生于20世纪初期的《学桴》、《北京大学月刊》、《清华学报》等期刊都以追求学术为精神旨归。在近现代知识者看来,学术精神实则等于科学精神,对学术的追求实则与振兴中华民族有着紧密的关联。以《北京大学月刊》、《清华学报》为例,它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发表那些具有“真研究”的学术文章,把追求科学精神的倡导落在实处。同时,为培养新人提供帮助。
学报精神;学术;《北京大学月刊》;《清华学报》
高校学报作为中国学术期刊当中最重要的一支队伍,正在日益“成为中国社科院系统、各省市社科院系统、各省市社科院及社科联系统之外的,一个影响较大、不可替代的学术期刊方面军”[1]。但长时间以来,人们却很少关注它的精神内涵并积极地对此加以研究。基于当前部分学报期刊学术质量下滑的现象,一些学者开始强调并呼吁学报期刊的学术特性。笔者以为,在中国高校学报发展的滥觞期,以《北京大学月刊》与《清华学报》为中心的高校学报期刊包孕着的浓厚的学术内蕴,是学报精神的真正原点。
一
中国最早的高校学报可追溯到苏州东吴大学1906年创办的《学桴》。在它的发刊词中,编者提出了这样的出版目的:“表学堂之内容,与当代学界交换知识。”[2]所谓“学堂之内容”是指东吴大学不同门类的教师们的学术精华,《学桴》意在为本校的教师与校外的教师之间搭起一座彼此沟通的桥梁,以“与当代学界交换知识”。显然,《学桴》的功能就是“交换”,而其内容则是与当代学界相关的各类知识。1915年,《清华学报》创刊,它提出:“学报者,交换知识之渊薮也。清华学子,以学报有益于学业者甚大。特于课余之暇,译述欧西有用之书报,传播学术,或以心之所得发为文词,或以平时所闻者为余录……苟以此册与各界各校所出之伟著,互相交换,互相观摩。”[3]与《学桴》一样,它也具有交换知识的功能,“能使阅者窥知本校内容,国内外各学校以杂志、报章交换者,彼此可收切磋观摩之效”[4]。1919年创刊的《北京大学月刊》将学报的功能讲得更为详细,“本月刊为北京大学职员学生共同研究学术,发挥思想,披露心得之机关杂志”[5]。在此,《北京大学月刊》将学报的“交换”功能具体化为三类,分别是“研究学术”、“发挥思想”、“披露心得”。其实,在此之前,北京大学曾经出版过《北京大学日刊》,它也是“联络感情、交换意见之机关”,但是蔡元培“顾《日刊》篇幅无多,且半为本校通告所占,不能载长篇学说,于是有《月刊》之计划”[6]。《北京大学月刊》与《北京大学日刊》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被注入了“学术”的内涵,蔡元培认为,大学“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而创办学报就是要刊载学术“长篇学说”,为“研究学术”提供及时的服务,他把这称为“尽吾校同人所能尽之责任”[6]。
在中国高校学报滥觞时期,这三家学报可算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它们之间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将“学术”当做学报生存、发展的根本。因此,有必要追问的是,“学术”缘何在当时显得如此重要。众所周知,中国近代以来一直遭受着西方文化的侵扰。作为他者,西方文明在与中华文明的碰撞中逐渐显示出其优势来,而中华文明则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学桴》在其发刊词中曾说:“揽神州之苍茫,叩人间其何世。群虎眈视,涎兹禁脔,一狮欠申,皋其坠魂,劫枰待收,舞台难下。非所谓过渡时代乎?”[2]为了拯救中华文明于颓废之中,中国近代的知识者纷纷提出向西方学习以富强中华的救国方略。于是,西方文化便成了中国知识者首先要学习的东西,王尔敏曾说:“近代之中国思想界,其感染于西方观念意识,已日渐加深,其狂热向慕,尚未有减退之征兆。”[7]
提出向西方学习知识,这一思路本身并没有错,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向西方学习什么。事实表明,中国在政治、军事方面学习得最为努力,效果也最为显著,但甲午海战的惨败再次让中国知识者陷入了反思当中。比如,鲁迅的《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便是诞生于这一背景之下的积极尝试。在这些篇章中,“他敏锐地发现了当世知识界因缺乏对西方具体分析而采取硬性模仿的错误态度,并且进一步提出了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使用客观有效的研究‘方法’远较其他东西更为重要的命题”[8]。客观地说,中国近代知识界缘于从拯救中国的实际目标出发,更多的是将西方文化的价值与内容直接照搬过来使用,而缺乏对西方文明具体理性的分析与探究。所以,鲁迅指出西方文明的价值在于其内在拥有的“不满足感”的科学精神,而它们先进的军事技术完全是基于科学精神之上的丰硕果实。爱因斯坦也曾经指出:“科学,如果要繁荣,就不应当有实用的目的。作为一个普遍的规律,科学所创造的知识和方法,只是间接地有助于实用的目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还要等到几代以后才见效。对科学的忽视,其结果会造成缺乏这样一类脑力劳动者,他们凭着自己的独立见解和判断,能给工业指出新的途径,或者能适应新的形势。凡是科学研究受到阻碍的地方,国家的文化生活就会枯竭,结果会使未来发展的许多可能性受到摧残。”[9]学报的创刊及其对学术的强调正是现代知识者在这一背景下的积极实践。正如《学桴》所说:“学桴者,预备过渡时代器具之一部分也。而何不以兵桴、以商桴,而何不以政治桴、宗教桴,而独有取于学者?盖兵、商、政、教,皆备于学,则学者载种种桴之桴也,而又可谓合种种桴而所成之桴也。”[2]
二
何谓学术?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就是:“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其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10]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学术”一直被连在一起使用,梁启超将“学”与“术”分开使用,其背后实际上有着西方文化的参照。具体来说,西方文化脉络里的“学”与“术”一直被分开使用,两者的使用范畴也完全不同,“学”具体指科学,“术”则具体指技术。后者虽然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西方知识者关心的却是前者。“科学也者,以研索事物原因结果之关系为职志者也,事物之是非良否非所问;彼其所务者,则就一结果以探索其所由来,就一原因以推断其所究极而已。术则反是”[10]。所以,梁启超认为西方文化的昌达,最重要的因素是他们对“学”的推崇,并将“学”作为“术”的基础。事实上梁启超所讲的“学”的内涵已经接近我们后来所说的“科学精神”,而“术”则相当于我们所理解的“技术”。在理解了“学”与“术”的各自内涵之后,他总结说:“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二者如辅车相依两不可离。学而不足以应用于术者,无益之学也;术而不以科学上之真理为基础者,欺世误人之术也。”[10]
关于“学”与“术”的关系,严复也有非常近似的看法:“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11]后来,这一问题延续到中国的教育领域。蔡元培指出:“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各国大学中所有科目,如工商,如法律,如医学,非但研究学理,并且讲求适用,都是术。纯粹的科学与哲学,就是学。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12]
中国近现代知识者对“学术”范畴的重新认知,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中国传统学术观念的扬弃,而是在救国的危机之下,对西方文化具体而认真的考量。换言之,西方正是由于对科学精神的重视才得以昌达,这是其“根柢”所在。中国要富强就一定要从讲究“实用”的思想理念中解放出来,转向对“科学精神”的重视。李慎之对此曾大加赞赏,并将是否拥有“科学精神”看做中国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区别的重要标志:“科学思想是我们中国学术自从轴心时代起就缺乏或者极不发达的,经清末的诸位先驱发现之后亟须补课的;民主思想也可以说是我们自古以来所没有的(从孟子到黄宗羲的民本主义毕竟不是民主主义),然而它却是培养科学思想之所必需,因此两者缺一而不可。自从清末逐渐酝酿,到五四时期经陈独秀提出要拥护德先生(德漠克拉西,即民主)与赛先生(赛因斯,即科学)的大声疾呼而成为不刊之论。从此以后,凡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不论其成熟程度如何,就是现代学术;与这个大方向违背的,就不是现代学术。”[13]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近代知识者执著于将“学术”重新定义,实在是为了中国自强的需要,“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的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尤其是在竞争剧烈的二十世纪更要依靠学术。所以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和智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14]。他们清楚地看到中国传统偏重于“术”的实用性思想,已经成为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所在,所以,对真正作为科学基石的“为求知而求知”精神的提倡便成为中国近现代知识者的主要关注所在。
三
既然学报期刊肩负了刊载学术“长篇学说”、为“研究学术”提供及时服务的责任,那么,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发表那些具有“真研究”的学术文章,把追求科学精神的倡导落在实处。1930年以前的《清华学报》,共涉及科学史、文学、数学、物理学、医学、生物学等相关学科,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王力等人都曾在此发表文章,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梁启超的《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中国奴隶制度》,王国维的《水经注跋尾》、《鞑靼考》、《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胡适的《词的起源》,顾颉刚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王力的《两粤音说》等。《北京大学月刊》从创刊至1922年共出版1卷9号,也涉及文学、物理学、经济学、化学等相关学科,蔡元培、胡适、丁绪贤都在此发表了相关的学术文章,其中较为著名的是蔡元培的《哲学与科学》,胡适的《墨子小取篇新诂》、《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马寅初的《银行之真诠》、《战时之物价与纸币》,丁绪贤的《怎么样研究化学》,何育杰的《安斯顿相对论》等。
客观地说,这些作品引领了当时的学术潮流。以梁启超的《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为例,他通过对中国具体区域与文化学术关联的分析,提出地理环境对学术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气候山川之特征,影响于住民之性质,性质累代之蓄积发挥,衍为遗传,此特征又影响于对外交通及其他一切物质生活。物质上生活,还直接间接影响于习惯及思想,故同在一国,同在一时,而文化之度相去悬绝,或其度不甚相远,其质及其类不相蒙,则环境之分限使然也”[15]。但他同时又没有将这一影响绝对化,“虽然,专从此方面观察,遂可以解答一切问题耶?又大不然。使物质上环境果为文化唯一之原动力,则吾侪良可以委心任运,听其自然变化,而在环境状态无大变异之际,其所产获者亦宜一成而不变。然而事实上决不尔尔”[15]。就这篇文章而言,无论是梁启超思考问题的角度还是他所使用的研究方法,都对中国近代人文地理研究的兴起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其他知识者的文章同样如此,他们的集体出现有效地促进了现代中国学术的繁荣。正是在这一语境之下,中国学术各类不同的学科才得以纷纷诞生,并形成了很好的发展态势。
学报在培养新人方面的贡献同样不可忽视。如果说梁启超等人在当时已经是著名学者的话,那么像叶企孙、周培源等人在当时还没有这样知名。《清华学报》为他们的成长搭建了良好的学术平台。比如,叶企孙的《考正商功》、《中国算学史略》,余泽兰的《说蚁》、《传染病之讨论》,刘树墉的《化学界待解决之问题》、《宇宙间变动之趋向》、《无线电报》、《清华学校大礼堂之听音困难及其改正》,萨本栋的《长途交流电线之算法》,张荫麟的《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李俨的《梅文鼎年谱》、《李善兰年谱》,周培源的《三等分角法二则》,吴有训的《Compton效应中变线强度与不变线强度之比率》,杨武之的《关于同余式的一个定理》,吴其昌的《宋代学生干政运动考》、《来纽明纽古复辅音通转考》,刘盼遂的《唐写本世说新书跋尾》、《段玉裁先生年谱》、《六朝唐代反语考》,吴晗的《胡应麟年谱》、《明成祖生母考》、《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南洋之开拓》、《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国》、《明教与大明帝国》等,都发表在了《清华学报》上面,这些文章的作者后来都成了相关学科的代表,但在当时,他们却非常年轻,由此也可以看到《清华学报》对年轻知识者的推介之力。
以叶企孙先生为例,他在《清华学报》发表《考正商功》时才18岁,还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他对《九章算术》中“商功”的研究应该是中国数学史最早的研究之一,尽管其中还有许多可商榷之处,但是他的老师梅贻琦先生,则高度肯定了该文章的价值:“叶君疑问之作,皆由于原书中‘刍童、盘池、冥谷皆为长方底之截锥体’一语之误。然叶君能反复推测,揭破其误点,且说理之圆足,布置之精密,俱见深心独到之处。至可喜也。”[16]
李俨先生在《北京大学月刊》发表《中国数学源流考略》时才27岁,在《清华学报》发表《梅文鼎年谱》和《李善兰年谱》时,也只不过30岁刚多一点。我们如果考察他的这几篇学术成果,就会为他的学术精神所感动。为了撰写《梅文鼎年谱》,“他征访梅氏宗谱,1918年在宣城教育会刘至纯处得到宁国县梅柏溪所藏《梅氏宗谱》、《文鼎公本传》、《成公事略》及县志中的《梅文鼎传》等重要史料。据此,他又参考215种自己所藏、传世资料或新近研究成果,终于完成。参考文献中较多引用的新近文献有他自己于1919年11月在《北京大学月刊》发表的《中国数学源流考略》、1924年6月张荫麟发表于《清华学报》的《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裘冲曼的《天文算学书目汇编》(时未刊)等”[17]。毫无疑问,李俨等人对学术精神的理解与追求和学报的精神内涵是完全吻合的,蔡元培曾说:“学生必要发布议论,断不能抄讲义,必要于人人所知的讲义以外求新材料,就不能不研究学理了。”[18]学生要发表文章,就必须寻求新的材料,而要寻找新的材料,就不得不到现有的教材之外去寻找。在这样一个学术机制中,学生们不得不主动、积极地寻求国内和世界新的科学知识,而学报则成为培养学生正确理解科学精神的重要一环。
总之,科学精神是近代中国在面临西方文化侵入时所发出的启蒙之声,它或者被启蒙者呐喊,或者成为知识者内心自觉的追求。而高校学报则与其他学术刊物一起共同担当了传播这一精神的历史使命,它们一方面发表具有“真精神”的学术文章,另一方面又通过这些文章为学人树立榜样,鼓励与发扬科学精神。如今,高校学报期刊在日益发展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重新探讨学报的学术精神内涵,一定会在倡导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营造有利于中国学术生产和传播的良好学术环境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龙协涛.《学桴》扬帆,百舸争流——纪念中国人文社科学报诞生百年感言[J].河南大学学报,2006,(6):22—25.
[2]黄振元.学桴发刊词[J].学桴,1906,(1).
[3]杨恩湛.小引[J].清华学报,1915,1(2):1.
[4]编者.清华学报之特点[J].清华学报,1916,2(2):广告页.
[5]编者.编辑略例[J].北京大学月刊,1919,1(1).
[6]蔡元培.发刊词[J].北京大学月刊,1919,1(1).
[7]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41.
[8]晋海学.《文化偏至论》与作为方法的西方文明[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4):57—60.
[9]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3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94.
[10]梁启超.学与术[J].国风报,1911,2(15).
[11]严复.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885.
[12]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4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3]李慎之.什么是中国的现代学术经典[J].开放时代,1998,(5):5—14.
[14]蔡元培.蔡元培全集(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5]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J].清华学报,1924,1(1).
[16]叶企孙.考正商功[J].清华学报,1916,2(2):87.
[17]姚远,冯立升,白欣.《清华学报》与中国数学史学科的奠基[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4):681.
[18]蔡元培.蔡元培全集(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G237
A
1007-905X(2012)08-0091-03
2011-04-10
河南师范大学新引进博士科研启动课题(092525)
晋海学(1973— ),男,河南新乡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学报编辑学研究。
责任编辑 宋淑芳
(E-mail:hnskssf@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