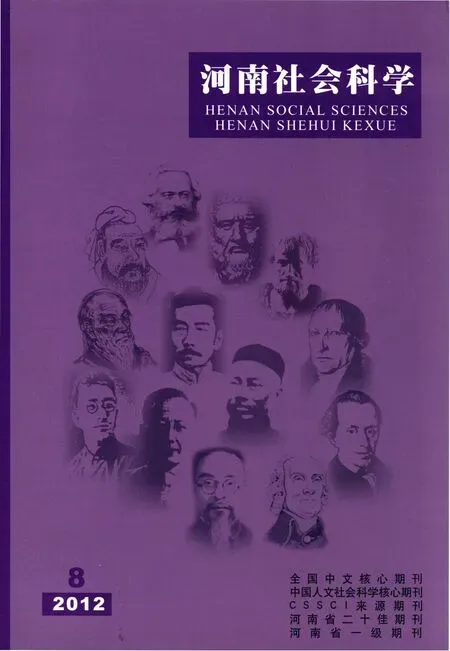20世纪英国作家非洲题材小说中的殖民话语
岳 峰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20世纪英国作家非洲题材小说中的殖民话语
岳 峰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20世纪英国作家在非洲题材小说中将非洲经历意义的颠覆和重组,他们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对欧洲殖民者在非洲原始丛林里的罪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一度将拯救英国现代文明病症的希望寄寓在非洲乌托邦里,但另一方面又难以摆脱欧洲殖民文化表征的窠臼。这些作家对殖民话语的显性描写与隐性描写杂糅在小说的叙事语言中,也造成了小说的文化逻辑与作者的主观意图的断裂。20世纪英国作家非洲题材小说中的殖民话语最终折射出英国中心论、欧洲中心论。
殖民话语;文化身份;英国中心主义
20世纪以来伴随大英帝国的逐步衰落,英国文坛再次开始关注描写非洲殖民地生活的日不落帝国叙事。与20世纪以前那些鼓吹殖民扩张、渲染异域风情的冒险小说不同,以康拉德、莱辛、奈保尔等为代表的20世纪英国作家在其非洲题材小说中更关注西方白人无止境的物质欲望与对非洲殖民地原始面貌的憧憬之间的冲突,西方知识分子已经看到20世纪欧洲工业文明高度发展带来的日趋加深的种种危机。20世纪英国作家的非洲题材小说展现的非洲不再仅仅是“原始”、“落后”的代名词,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这些小说家利用“他者”文化语境来反观西方文明的实验场所。
一、非洲丛林:欧洲殖民者的“另外一面镜子”
与维多利亚时代流行的英国传教士及探险家戴维·利文斯敦(DavidLivingstone)的《传教旅行与南部非洲研究》、奥利弗·施赖纳(OliveSchreiner)的《一个非洲农场的故事》和亨利·莫顿·斯丹利(HenryMortonStanley)的《在最黑暗的非洲》这些“青少年冒险故事”中展现的非洲不同,以康拉德、莱辛、奈保尔为代表的20世纪英国作家非洲题材小说中的非洲如同一面可以洞察英国文明实质的镜子,英国人不得不面对“在这一新的环境中重新定位,赋予自我存在的意义”[1]。这些英国知识分子传承了英国文学注重人性关怀与推崇道德关怀的伟大传统,他们“不但不崇尚虚无,而且对人类有着深切的道德关怀……道德关怀是其艺术关怀的源头”[2]。他们一方面因目睹殖民地人民所遭受的种种迫害之苦,勇敢地用自己的小说创作试图批判殖民主义的罪恶,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使用其试图批判的主流文化中的语言——英语。然而这一选择对“帝国主义批判的力度却因英语的使用而削弱,因为英语本身即体现了大英帝国的政治文化主体地位”[3]。
帝国殖民小说向来以张扬男性阳刚冒险作为其使命,莱辛的小说《野草在歌唱》(TheGrassIsSinging)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南部非洲罗得西亚为背景,小说中的大农场主查理·斯莱特完全符合大英帝国极力吹捧的“棒小伙”形象,但斯莱特恰恰是莱辛所要批判的,因为莱辛所弘扬的绝不是表层意义的阳刚之气,她用这样的语言描写这个体现了负面男性气质的斯莱特:“他是个粗鲁蛮横、心肠铁硬的人,虽然还不算太歹毒,可遇事独断专行,全凭自己的一股冲劲,不顾一切地去赚钱。”[4]从莱辛对斯莱特的叙述语言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男性阳刚之气的理解。
与同时代其他后殖民文学家一样,作为约瑟夫·康拉德的“出色继承人”的奈保尔的反抗策略也是从语言开始的,他在《河湾》中透过萨林姆之口,用主观色彩非常浓厚的叙述语言为我们展示了惠斯曼斯神父的形象。惠斯曼斯神父非常热衷于深入河湾小镇的每一个村庄来收集那些非洲历史遗物,然后放进他的非洲博物馆。当然,惠斯曼斯神父并不是出于尊敬非洲、热爱非洲的目的去收集面具和木刻的,而是为了满足欧洲人窥视非洲原始落后文化的好奇心,“在他眼中,真正的非洲已奄奄一息,行将就木。因此,乘非洲还没有死的时候,很有必要好好去了解它,并把它的物品保存起来”[5]。在他看来,这些独立的非洲国家仅仅是昙花一现,“阿拉伯人只是给欧洲文明的到来铺平道路”,“在一时的退步之后,欧洲文明会卷土重来,在河湾扎下更深的根”。所以惠斯曼斯神父“崇敬事关欧洲殖民和河道开放的一切”,他穷尽一生去收集那些历史遗物,是为了保存欧洲殖民非洲的历史,最终则暴露出新殖民主义的本质。
海德格尔曾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20世纪英国作家在创作其非洲题材小说时,正是以各种形式来维持语言的价值,然后将文本的语言变为触角,再通过这个触角使沉默无声的文本与异常活跃的话语世界紧密联系起来的,意在颠覆和改写白人读者长期形成的对黑/白、文明/野蛮二元对立关系的思维定势,以黑色的非洲丛林去映衬白色文明的瘫痪,这个已经“异化”的自然环境中,欧洲殖民话语体系鼓吹的殖民话语在非洲丛林里已经改变了其内涵,作家的反殖民主义立场与殖主义立场同样流露其间,他们对原始非洲丛林寄予了厚望,希望非洲丛林的原始生命力唤醒英国人性中沉睡的人性关怀与道德救赎。
二、“这原是老酋长的国度”:被图解的道德拯救
20世纪的大英帝国经历了纷繁复杂的内外部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大英帝国的衰落。这一衰落过程见证了英国传统价值观的变迁以及帝国殖民体系的瓦解。不断衰落的帝国迫使以康拉德、莱辛、奈保尔为代表的英国小说家在非洲题材小说中将笔触远离英国本土、欧洲大陆,这些英国小说家用充满丰富感情色彩的词汇形容非洲,希冀通过这个充满野性活力的非洲乌托邦给愚钝、冷酷、没有灵魂的英国现代社会重新注入睿智、温情和灵魂。
康拉德将这种赞扬非洲、倡导道德拯救的语言流露在其两部非洲题材小说的字里行间。欧洲布鲁塞尔就如同“白色坟墓”般:“阴暗处一条狭窄而荒凉的街道,高高的房屋,无数个挂着软百叶窗的窗户,死一般的寂寞。”[1]这座死寂黯淡的城市、当地人的冷漠自私与读者的迷惘压抑交织在一起,西方文明的虚伪、白人人性的贪婪跃然纸上。而非洲黑人“有骨骼,有肌肉,有一股狂野的生气和强烈的运动能量,这些都像那海岸边的海浪般自然而真实”。在《进步前哨》里康拉德也用类似的语言描写黑人:他们裸着乌黑发亮的身子,装饰着雪白的贝壳和闪闪发光的铜丝,手足健美。文中黑白二元对立比比皆是,黑与白的象征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原来的范畴,这种对黑与白的传统意义的颠覆和重组过程也超越了传统的意义,再现了康拉德的内心矛盾。
莱辛在其非洲题材小说创作中不断地反思20世纪40年代身处南部非洲殖民地的英国人的人性。她在《这原是老酋长的国度》1964年版的序言中写道:“我觉得,非洲赠予作家们——无论他们是黑人还是白人——最大的礼物,就是这块大陆本身。《这原是老酋长的国度》中对白人居住地的丛林与老酋长居住地的丛林的叙述语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上面的林木被人伐去矿上作柴火,丛林越长越稀疏,树木越长越扭曲;牛群把草地啃得光秃秃的,还在土地上留下无数纵横交错的蹄痕,春去秋来,雨水冲刷,又把这些蹄痕渐渐刨成沟壑”[6]。后者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和谐景象,“那是林间空地上搭建的一带茅草棚屋群落。周围一块块田地排列整齐,种着玉米、南瓜和粟米;远处的树下,牛群悠然地嚼着青草。家禽在棚屋前后抓抓刨刨,狗儿在草地上打盹儿,羊群点缀着河对岸耸起的一座小山。河流分出的支流如臂膀环抱着村庄”[6]。显然,老酋长居住地的非洲丛林让白人小姑娘迷失了自己的文化身份,这片带有田园意味的丛林迎合了作者对精神家园的想象。
在欧洲文明的强势渗透下,非洲传统文化面临重重危机,但这并不意味着非洲传统文化的彻底瓦解,奈保尔在小说中对非洲传统文化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写,其中神秘的非洲木刻和面具以其特有的魔力吸引着《河湾》中来自欧洲的惠斯曼斯神父。神父眼中的非洲完全不同于非洲本地人心目中的非洲,“他看到的非洲是丛林的非洲,是大河的非洲。他的非洲是个奇妙的地方,充满了新鲜事物”[5]。神父的感受在《自由国度》里同样可以看到:“对白人游客和移民来说,这里魅力无穷。”[7]
三、“可怕啊!可怕啊!”:非洲乌托邦的终结
与大英帝国白人至上的鼓吹者竭力用赤裸裸的殖民话语“妖魔化”非洲不同,康拉德、莱辛、奈保尔等20世纪英国小说家在其非洲题材叙事中,试图对欧洲殖民话语保持一定的反语距离,主观上也反对用过于贬义的词汇妖魔化非洲,大量使用了具有丰富感情色彩的褒义词,表现出超越其时代的民主思想,在他们看来,非洲原始丛林里生机勃勃的生命力或许正是对英国文明危机进行拯救的良药,然而在原始、神秘甚至恐怖的非洲丛林里,小说家不得不面对拯救在非洲丛林里的尴尬命运。
正如评论家卡尔所认为的,“丛林与人们的顾虑形成对应,丛林是人们恐惧之源”[8],《黑暗的心》中的库尔兹早已被非洲的黑暗丛林所俘虏,非洲的荒野“抓住了他,爱上了他,拥抱了他,侵入他的血管,耗尽他的肌体,还用某个魔鬼仪式上的种种不可思议的礼节使他的灵魂永远属于荒野所有”[1]。这里,康拉德是将“荒野”女性化了,通过“抓住”、“爱上”、“拥抱”、“侵入”、“耗尽”等一系列的动作语言,彻底阉割了库尔兹。
非洲丛林陌生怪诞、神秘莫测的异域景色无时无刻不在激发白人殖民者内心的惊恐和困惑。《野草在歌唱》中的玛丽最终完全被非洲黑色丛林所俘获,小说最后花了大量的拟人化语言描写玛丽与非洲丛林之间的战斗:“一阵恐慌向她袭来,现在她还没有死,灌木丛就征服了这片农场,派了草兵树将向这片肥沃的红土袭来,连灌木丛也知道她快要死了!”莱辛对玛丽理智与情感、需求与抗拒、内心体验与道德判断的纠结直至最终导致的人格分裂的描述可谓令读者拍案叫绝,同时也为读者再现了20世纪40年代的南部非洲。莱辛在《影中漫步》中还原了这个环境:“我生长在一个隔离制度——白人,黑人——及其结果已在关于南部非洲的新闻中凸显出来的地方:僵化的制度被暴力和战争打破。”[9]玛丽的最终命运预示着莱辛所追求的精神救赎在实践上寸步难行。
与传统冒险小说用极富煽动的叙述语言展现殖民话语表征中的“棒小伙”的勇于冒险、永不退缩的“光辉”形象不同的是,20世纪英国作家在其非洲题材小说中的叙述语言则充满了传统道德沦丧后的浓厚的悲观情绪。正如欧文·豪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发表的《强人的阴影——评奈保尔〈河湾〉》中所说的:“在《河湾》中,奈保尔完全没有透露任何希望和立场,或许是因为令他如陷泥潭的显示,只让他发得出严重不悦之声……似乎他被自己发现的真相所围堵,难以突破超越。”[10]拯救的最终尴尬命运都预示着这些英国作家所追求的“拯救”显然缺乏足够的根基让读者信服。
四、黑暗大陆:大不列颠统治下“真正的自由”之地
源自19世纪末期尼采的超人哲学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进一步强化了帝国的殖民话语体系。大英帝国的文明理念通过殖民语言的传递、土著人被迫接受,长期以往,会不可抗拒地影响非洲人对其的感受和价值判断,非洲人会不自觉地被欧洲中心、白人优越感等殖民话语所迷惑。尽管这套话语是西方殖民者为其殖民扩张寻找理论依据而创造出来,其背后隐藏着对“他者”的污蔑、歪曲以及强词夺理的霸权话语,但由于与西方相比第三世界较早发展的优势使得西方这套殖民话语依旧具有很大的迷惑性或“说服力”。因此,康拉德、莱辛以及奈保尔对殖民话语的批判和包容均流露出他们的英国中心主义观点和欧洲中心主义观点,而这正是非洲乌托邦最终走向迷惘与幻灭的根本原因。
康拉德一方面在鞭挞殖民主义,另一方面却义不容辞地捍卫了欧洲白人优越的种族观念以及大英帝国殖民扩张的“正统”意识形态。康拉德对非洲黑人“他者”形象的建构所常用语言是:“畜生”、“野蛮”、“原始”、“未开化”、“蠢货”、“黑色”、“丑陋”。这种程式化的非洲形象都是诸如马洛这样拥有话语权的殖民者创造出来的,自然这种话语被创造出来的前提是必须服务于西方的殖民利益。非洲人发出的声音,也“完全不像是人类语言的声音”。事实上,完全处于“失语”状态的被殖民者并不是没有语言,只是正如非洲著名作家齐努瓦·阿切比所指出的,康拉德根本没有赋予非洲丛林里的野蛮人以“语言能力”,阿切比这样说道:“显然,康拉德不可能赋予非洲的‘这些未开化人’以语言能力,那些人不是说话而是发出‘粗鲁的模糊不清的声音’。即使他们之间也只是‘相互交换着短促的嘟囔声’。”[11]事实上,读者仅仅能听到马洛的声音,而无从听到非洲“他者”之声。
莱辛在其非洲题材小说中所流露出的殖民倾向往往是通过小说的叙事话语,尤其是旁白这种特殊形式的叙事话语来展现的,当涉及黑白两个种族时,莱辛采取的是不同的词语和语气。尽管莱辛竭力想避免传统殖民小说的窠臼,但深受白人殖民传统所固有的观念和价值标准的影响,她的语言表现为对待白人多使用褒义词,即便进行批评,也会有所保留。显然,在南部非洲生活多年的莱辛在内心深处非常认同这套殖民说教,对白人所用词语多褒义就是试图证明白人在非洲的成功同样离不开艰苦奋斗。如果说其间有伤害非洲土著的行为,那完全是异质文化语境激发出白人人性中“恶”的因素。
尽管奈保尔在其非洲题材小说中并没有过多地描写欧洲白人是如何宣扬帝国意识形态的,但奈保尔将这一任务交给了已完成自我他者化的萨林姆,奈保尔让萨林姆压制真实自我的目的就是让其在欧洲白人不在场的情况下,担负起实现帝国文化的“在场”的重任。在萨林姆类似于“传声筒”般的帝国叙述中,非洲人的声音几乎被隐匿了,非洲人成为非理性和幼稚的代名词,处处需要帝国殖民者的监护,就如同墨迪离不开萨林姆一样。尽管奈保尔本人来自殖民边缘的第三世界,对殖民中心欧洲文明也时时批评,但其骨子里英国文明更占据主导地位,相比对第三世界专制政治制度以及落后文化的猛烈抨击,奈保尔更倾向于表达对英国文明的推崇。这显然是那些来自第三世界或拥有第三世界背景的学者所不愿意接受的,齐努瓦·阿切比直指他是“令人舒服的白种人神话的恢复者”。萨义德则指责奈保尔相当自觉地成了西方的证人,将非洲落后的原因归罪于非洲自身,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最可耻的变体”。
五、结语
以康拉德、莱辛、奈保尔为代表的20世纪英国小说家在其非洲题材小说中一度将拯救英国现代文明病症的希望寄寓在非洲乌托邦里,然而另一方面却又以西方帝王姿态君临属下非洲,以其傲慢的殖民话语向英国读者传递着这样的信息:无论是殖民时代还是后殖民时代,非洲社会依然是野蛮人出没、原始落后的丛林社会。正如莱辛曾这样谈到自己的殖民地生活:“许多人问我,在一个到处是种族歧视的国家长大,我却为什么没有种族偏见……但是我会与那些与我有着同样成长经历的人完全不同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当我生活在非洲时,我一直关注着自己的态度和反应。”[12]因此,英国小说家在其非洲题材叙事中对帝国主义批判的话语,最终只能被包容在帝国主义的话语体系之内,无论殖民时代,还是后殖民时代,英国作家非洲题材小说中的殖民话语最终折射出的都是英国中心论、欧洲中心论。
[1]Conrad,Joseph.HeartofDarkness[M].London:Penguin BooksLtd,2007.
[2]殷企平,高奋,童燕萍.英国小说批评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3]毕凤珊.疏离与融入:康拉德的矛盾情怀——康拉德殖民话语矛盾性溯源[J].河南社会科学,2007,(1):142—145.
[4]Lessing,Doris.The GrassIsSinging[M].New York:HarperPerennial,2008.
[5]V. S.Naipaul .A Bend in the River[M]. London:Picador,2011.
[6]Lessing,Doris.This Was the Old Chief's Country:Collected African Stories Volume One[M]. London:Flamingo,2003.
[7][英]VS 奈保尔.自由国度[M].刘新民,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8]Muffin,R.C.ConradRevisited:HeartofDarkness:ACase Study in Contemporary Criticism,Bedford Books[M].NewYork:St.Martin'sPress,1989.
[9][英]多丽丝·莱辛.影中漫步[M].朱凤余,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0][美]查尔斯·麦格拉斯.20世纪的书——《纽约时报书评》精选[M].朱孟勋,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11][英]巴特·穆尔-吉尔伯特.后殖民批评[M].杨乃乔,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2]Whitlock,Gillian.TheIntimateEmpire:ReadingWomen’s Autobiography[M].London:Cassell,2000.
I106.4
A
1007-905X(2012)08-0075-03
2012-05-10
2009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二十世纪英国文学中的非洲形象”(09YJC751076);201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殖民时代与后殖民时代英国小说中的非洲形象研究”(11CWW026)
岳峰(1976—),男,江苏盐城人,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博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 姚佐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