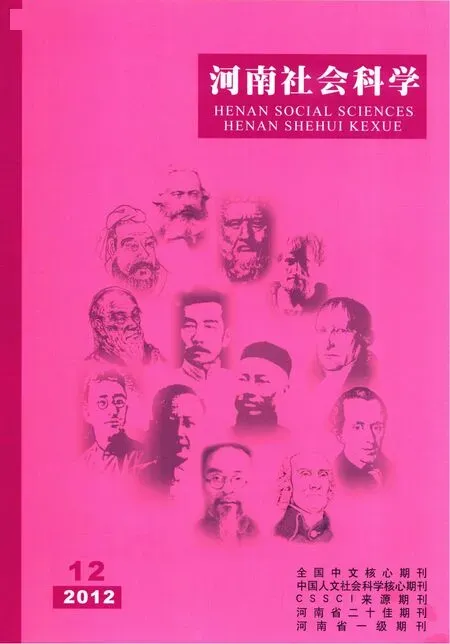检察监督民事虚假诉讼正当性研究——以构建虚假诉讼的多元防治系统为视角
周 虹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广东 广州 510623)
一、民事虚假诉讼释义
通常而言,虚假诉讼意指行为人恶意串通,虚构民事法律关系或民事法律事实、伪造诉讼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利用虚假的仲裁裁决、公证文书申请执行,使人民法院错误裁判或执行,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但根据笔者实证研究,虚假诉讼并不只是发生于诉讼阶段,也常出现于执行阶段,行为人并不仅为原、被告双方,还可能包括共同诉讼人、第三人,甚至案外人,如非实体权利主体的当事人(譬如公司清算过程中的清算组、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遗产管理人和遗嘱执行人等)、代理人、法定代表人与对方当事人串通侵害受判决约束的当事人或者实体权利主体的虚假诉讼。
虚假诉讼多发的案件类型较为集中,以广东为例,多发生在民间借贷纠纷诉讼、离婚纠纷诉讼、破产企业为被告的纠纷诉讼、认定驰名商标的诉讼等案件中,而行为人的手段也多种多样,多用制造虚假合同、虚假借条、虚假证据材料、虚假公证书等方式,发生的阶段除了在审判阶段还有出现在执行阶段。但当事人提起虚假诉讼的目的则较为单一,通常都为了转移财产或者企图以法院的裁判认定某种法律状态,如通过虚假民间借贷转移离婚财产或多分离婚财产,通过虚假民间借贷转移企业财产,通过虚假民间借贷转移即将被法院执行的财产,通过虚假诉讼认定驰名商标等。但无论虚假诉讼的行为主体范围是大或小,行为方式如何变化多样,其均分享着共同的基础特征。具体而言可概括为四点:即主体同利和非对抗性、行为合谋及违法性、结果危害性、形式隐蔽性。虚假诉讼的上述特征,不但构成了识别虚假诉讼的要义,更是识别和惩处虚假诉讼的切入口,而且人们针对以上的突破口也的确已经为防治虚假诉讼付出了大量的努力。
二、虚假诉讼防治二元制之困境
因虚假诉讼发生于法院的审判活动中,直接影响的是法院的权威性与严肃性,因此从传统而言,识别与防治虚假诉讼的主体是法院,而作为虚假诉讼直接侵害对象的案外人,也有通过各种途径参与诉讼或者另行启动诉讼程序的可能。但这种传统的二元制防治模式,在现实中难免存在诸多缺陷与不足,并成就了虚假诉讼泛滥的窘境。
(一)法院防治虚假诉讼的天然缺陷
在理论和实务界开始关注虚假诉讼现象之初,学者多根据虚假诉讼的基本特点进行了概括性描述,即以虚假诉讼多发的案由为划分,梳理虚假诉讼常发领域,并找出虚假诉讼的主要行为特征和行为模式,希翼通过法官的努力在虚假诉讼发生前或者发生之时即能够识别并阻止损害后果。但是根据笔者就广州市越秀区、天河区、海珠区、荔湾区等4个基层法院抽样调查的结果,从虚假诉讼本身的特点以及虚假诉讼发现的诉讼阶段来看,试图在损害结果发生之前就识别所有的虚假诉讼,并将其清除于司法程序,难度非常大,甚至可以说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必有漏网之鱼。因此纯粹依赖法院的虚假诉讼防治系统显然不符合实际。详而言之:一是不可过分迷信法官的经验。因为法官不可能拥有整齐划一的经验和水平,法官并不是法律适用的自动售货机,作为个体的存在,法官享有人类在情感上、认知上差异的共性,而且从业十年以上的法官难免会比刚开启事业生涯的法官对虚假诉讼更为敏感,即使是同样经验丰富的法官,也会因为情感、认知和责任心等差异而对虚假诉讼的认识有所不同。况且,在当下案多人少的司法现状下,法官即使对某些案件认为有虚假诉讼嫌疑,难免也会迫于案件数量太多的压力,而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逐一鉴别。因此,单纯寄望于法官的司法经验,实则不切实际。二是审判权被动性的天然障碍。在实践中,法官如何处理虚假诉讼并无统一范本,而处理方法无外乎继续审理、劝说当事人撤诉、向上级领导汇报或提交审判委员会进行讨论处理。识别难成了防治虚假诉讼的主要障碍,而这更多地归因于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变迁。法院在民事诉讼审理范畴的职权主义被概括性地弱化了,直接导致审判权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过分弱势,而在某部分领域却又成为阻碍当事人权利行使的强职权。法官面对疑似虚假诉讼犹如跃入雷池,前一步就可能越过尊重当事人程序主体性的边界,退一步就可能落入纵容虚假诉讼的危险境地,因此,法官并非无心卫法,而是力不从心。三是法院规制虚假诉讼的无力。虚假诉讼是一种对司法权威的挑衅,其在玩弄法律的同时也践踏了法院乃至法律的尊严。其存在的另一个诱因在于司法权威的缺失①。当前,针对虚假诉讼的行为人,法院如有处罚的,多是根据《民事诉讼法》有关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进行处理,虽然有些法院也会动用刑事制裁手段,将相关人员移送公安机关,但是处理针对的仅仅是虚假诉讼的某些行为方式,并不针对虚假诉讼的行为本身。具体而言:首先,就民事制裁而言,《民事诉讼法》对妨碍民事诉讼行为,针对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及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等几类行为虽然有规定处罚措施,但实践中真正给予制裁的非常少,而且处罚最重也仅是15天的拘留,相比起争涉的诉讼标的实在不算什么。而对原、被告双方恶意串通实施虚假诉讼、损害第三人的行为则没有处罚规定。其次,就刑事责任而言,在《刑法》中,虽然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规定也能对虚假诉讼的某些行为予以规制,且妨害司法罪中的妨碍作证罪和帮助伪造证据罪可以直接针对诉讼当事人,但这里同样存在评价不全面、不充分的问题。所以,虚假诉讼的防治不仅需要法院行使审判权,还需要一个具有足够威慑力和强制力的司法保证,以构成司法权威的威慑与制裁措施。
(二)权利受损害人的防治方法
虚假诉讼的危害性揭示出了虚假诉讼往往以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为要义。广义而言,受虚假诉讼侵害的受害人应当包括法院以及权益直接受侵害的国家、公共和第三人。但因前部分已就法院防治系统进行了阐述,这部分仅指狭义上的受害人,也就是权益直接受到侵害的国家、公共或第三人。一是纠错性救济。首先,受害人的防治系统得以运行的前提是只有当受侵害的案外人有了充分的知情权时,他才有进一步进行救济或者维护自身权益的可能,然而隐蔽性却恰恰为虚假诉讼的特征之一,因此单纯依靠受害者自行发现可以说极度困难。其次,排除了受害人无法知晓虚假诉讼行为的情形外,受害人还需要有相应的机制进入正在进行的虚假诉讼中,通过主张和举证捍卫自己的权益且证明虚假诉讼的存在。在当下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第三人制度则为这样的制度。但我国现行不完善的民事诉讼第三人制度,同样为虚假诉讼的产生留下隐患。二是补偿性救济。在民事实体法中,虽然诚实信用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均对抑制虚假诉讼行为有一定作用,但这些规定由于过于抽象且缺乏惩罚性规定,难以起到真正规制虚假诉讼的作用。而在侵权法中,因虚假诉讼并不能构成独立侵权行为,虚假诉讼受害人以此为诉因向法院起诉法院并不会受理。
三、多元制民事虚假诉讼防治系统考略
(一)检察监督民事虚假诉讼的优势
在虚假诉讼防治过程中,关注受害人、公、检、法四位一体的防治系统虽已不是新鲜事,但就当下可用及发生效力的制度运行来看,主体仍然是法院和受害人,公安机关的作用充其量只是就其中极少部分涉及刑事犯罪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相比较而言,检察机关的功能则并非仅存在于刑事范畴,它还具有民事法律检察监督的功能,这是由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行使的是司法权项下的检察权而决定的,它对法律的适用享有监督权,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保卫着司法的权威性。实务界关于多元制防治虚假诉讼的尝试,在近年就已现端倪②,但就检察机关职能的探讨,则仅限于对构成“妨碍作证罪”和“帮助伪造证据罪”的行为提起刑事公诉,对虚假诉讼本身的识别与惩处,以及在民事审判监督方面,则基本没有涉及。可见,检察机关防治虚假诉讼的职能优势并没有真正发挥出来。
(二)检察监督民事虚假诉讼的功能定位
检察监督民事虚假诉讼虽然具有上述优势,但是在具体运行机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检察机关发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线索来源具有滞后性和局限性。二是检察抗诉民事案件程序具有滞后性。三是检察机关查处虚假诉讼的部分手段具有有限性和非强制性。
(三)检察监督民事虚假诉讼的路径探索
如要全效地构建多元制的虚假民事诉讼防治系统,完全固本守旧显然并不能发挥检察机关的特殊优势,因此有必要区分检察机关在防治虚假诉讼中的不同职能方式。一是司法纠正型的检察监督民事虚假诉讼职能。就现在检察机关已经存在的监督方式看,检察民事抗诉程序已经颇为完善,并在纠正虚假诉讼裁判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检察建议则因为缺乏强制性和规范性而尚未发挥太大的效用。2012年《民事诉讼法》对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范围、方式、手段作了相关完善,并规定了检察建议的相关效力。可以预见,检察建议的改革将沿着检察院与法院更为互动的方向发展,并通过检察监督的程序规定固定着法院对检察监督的程序性回复。二是司法处罚型的检察监督民事虚假诉讼职能。司法处罚型的检察监督的实质,是对涉及犯罪的虚假诉讼行为通过国家追诉的方式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我国当下并没有针对虚假诉讼行为的刑事处罚立法,因此当务之急应当是顺应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主流观点,设立虚假诉讼罪,对严重的虚假诉讼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检察机关一旦发现涉及虚假诉讼罪行,就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并对符合犯罪构成的提起公诉,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此外,对同时存在有贪污贿赂、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渎职行为的也应当予以立案侦查并追究刑事责任。三是公益救助型检察监督民事虚假诉讼职能。对于涉及损害国家或者公共利益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以公益诉讼的形式作为国家、公共利益的代理人参与到诉讼中来。但是检察机关并不能一有损害上述利益的行为就立即以其自身名义提起公益诉讼,而应由该国家、公共利益的主管单位为参与公益诉讼的第一责任人,在该第一责任人怠于行使维护公益职责的时候,检察机关才得以提起公益诉讼。同时,虚假民事诉讼的防治系统必然是一个多元化的系统,除了当事人和公权力的共同努力外,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可谓是根本之源,但该项工程耗时相当长,而且成效也不快,需要在防治虚假诉讼和构建社会和谐稳定的工作中不懈努力。
注释:
①卞建林:《我国司法权威的缺失与树立》,《法学论坛》2010年第1期。
②如2008年8月1日浙江省玉怀县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共同制定了《关于查处虚假诉讼案件的若干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