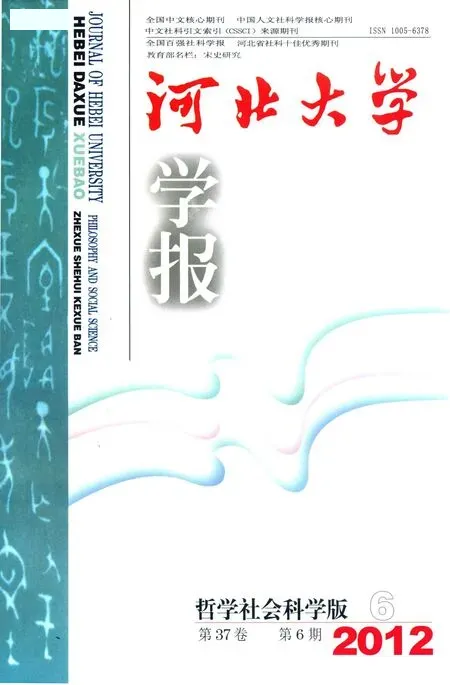《喜福会》的叙事艺术
王 毅
(北京联合大学 新闻与传播系,北京 100191)
《喜福会》是一部第一代中国人移民美国的生活纪实或者说是一部在西方人眼里称之为关于“他者”的传记文学作品。作者以真实的生活素材为基础,增添了一定的虚构情节,创新性地运用第一人称,虚实结合,撰写了“母女”的传记,主题突出、完整。在《喜福会》中,作者借别人之口,说自己的事,再现了其亲人们的过去,并使过去与现在相结合,母女同心同德,完成共同的心愿,使一个家庭从分离破碎到团圆重逢,完整了其传记主线,谱写了传记文学作品的新篇章,成为传记文学作品家族中的新成员。按照传记文学作品的特点,如果把《喜福会》翻译成《喜福会记》就更有传记文学作品的意味了。
一、《喜福会》叙事的历史性和真实性
传记文学作品的历史性在于作品或相关作者或事件的真实性和纪实性。《喜福会》的叙事是在尊重、记录历史的基础上进行的,是根据作者的母亲、外婆和一些她自己的经历撰写的。《喜福会》记录了20世纪40年代左右的中国女性在中国和移民到美国后的生活经历,只是作品中没有启用她们的真名实姓,她们不具有为其立传的的因素,但其真实性和纪实性是有一定依据的。
首先,从《喜福会》的题献就可以看出此书写的就是对她母亲的的尊敬、爱戴和记忆。《喜福会》的卷首语这样写道:“给我的母亲,且谨以此纪念她的母亲,有一次您问过我,我将留下怎样的记忆,喏,就是这本书,还有这意外的很多很多……”[1]卷首语这无疑说明《喜福会》记录了很多关于作者母亲的真实经历。
2006年9月15日,谭恩美在接受上海《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坦率地说,希望了解母亲更多,是她创作《喜福会》的最初动因。对于她来说,母亲是她灵感和创造的源泉:“我的母亲总是想感知更多,但同时她又感觉自己承受太多痛苦。我故事中的叙述者和她的情况一样,她的母亲死了,她从没感觉到什么是爱,她总是想更深地感知。”[2]而在现实中,谭恩美的外婆年轻守寡,遭强暴后被迫为妾,最后吞生鸦片而亡。谭恩美的母亲当年9岁,在一旁目睹母亲自杀的经过。这段经历被移植在《喜福会》中许安梅的故事里。对此,谭恩美在她的散文集《我的缪斯》中写道:“在写‘姨太太的悲哀 —— 许安梅的故事’一章时,我对听来的这些细节做了些修改,小说中是这样的:年轻的寡妇被富翁强奸,不得不做了地位谦卑的四姨太,还给这个富翁生了他的第一个儿子,这是那次奸污的结果。孩子从小就被地位比她高的三姨太抱走,愤怒之余,她越发感觉自己的生命毫无意义。四姨太并非意外死亡,她是出于报复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3]23谭恩美从小她就听她母亲极其生动地讲述自己的故事,对鬼魂、龙骨、妾等诸多事物有耳闻,一点都不觉得神秘、奇怪。每当听时,她就把一切记录下来,再辅以阅读,以了解当时当地发生的故事,保证细节真实准确。在小说中,作者采用了很多移花接木的写作手法,记录历史的真实。在小说中“割肉救母”时,谭恩美解释道:“读者可能认为,书中某些细节是我编造的,但它们确是事实。母亲要死了,做女儿的会从手上割一小块肉下来烧成汤喂给母亲喝,我外婆就曾这样做。有人说‘妾’很过时,我的外祖母被逼成为人家的四姨太,她住在巨鹿路(上海),后来在崇明岛自杀,这是我认为重要的事情。”[2]4这一情节写在《喜福会》的第二个故事,“伤疤——许安梅的故事”里。故事的讲述人是其母亲的化身许安梅。
此外,在现实生活中,谭恩美在上海有三位同父异母的姐姐;她幼年学弹钢琴,和母亲时常发生争执;谭恩美的母亲临终前,她为她母亲“放了一张肖邦钢琴曲的CD,并伏在她耳边小声说:这是我弹得曲子,我已经开始刻苦练琴”[1]6。这些经历都再现在《喜福会》中女儿吴精美弹琴风波、母亲去世后再次在喜福会弹奏钢琴、代替妈妈去中国见她的姐姐们等事件中。另外,在拍摄《喜福会》电影中一幕关于映映与她男友在舞会后做爱的镜头时,谭恩美也曾与导演王颖发生争执,也反映了《喜福会》中一些情节的真实性。
还有,谭恩美在她母亲生前给她读到《喜福会》中,“…… 孩子从小就被地位比她高的三姨太抱走,她越发感到自己的生命毫无意义。四姨太并非意外死亡……”时,她母亲问道:“你怎么知道你外婆事实上是四姨太?你怎么知道真相的?你怎么能写出这些你根本不知道的事情?”[3]130这真实母女的对话也道出谭恩美对实情的了解。
上述林林总总都说明《喜福会》具有相当的真实性、纪实性和历史性,用谭恩美的话概括,《喜福会》记录了:“……从六岁至今陆续发生的事情,全部都是我的想象,至于现在我是个作家,这也只是我的想象罢了。为了让我自己确信这些并不是真的,为了证明我确实仍然活在现实世界,我像所有作家所做的一样,赋予小说真实感。我开始动笔记下种种往事,往事与回忆交错,如此充斥着复杂与平庸的一生,怎么可能是一种虚构呢?”[3]23据此,我们可以完全相信《喜福会》具有真实性、纪实性和历史性,是一部关于作者亲人的传记文学作品,而不是一部虚构的小说。
二、《喜福会》叙事的完整性
《喜福会》不是仅仅记录一个人的传记文学作品,而是记录了母女三代人,这也是其有别于一般传记作品的地方。《喜福会》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记录了作者母亲和她外婆在旧中国的心酸、血泪史。这里的母亲们代表了她们那个时代部分中国女性,她们是小说中的吴素云,映映·圣克莱尔、许安梅和她的母亲,她们都是作者母亲和外婆的化身。这些母亲们用她们的亲身经历讲述了一些20世纪40年代中国女性纪实生活,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她们身上的影响和作用,让世人较全面地了解当时中国女性和她们的地位与处境,认识当时中国女性的历史;第二部分讲述了这些中国母亲和她们移民到美国后出生的美国女儿们相处的真实生活写照,记录了中美文化差异、冲突和融合。这两部分有机的结合,勾画了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国移民在美国生活画卷的一角。
《喜福会》中的母亲们把关于她们自己的故事讲给女儿们听,教她们做人、做事、懂中国文化、用中国人的智慧、做中国人,使母亲的文化、思想和精神在女儿身上得以延续,是母亲的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行为帮助她们的女儿长大、成熟,接受和继承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传统文化。《喜福会》的结尾就是母亲吴素云的女儿吴精美代替和作为“母亲”去中国,见她在那里的的女儿们,而她、吴精美则同时已成为 “一个中国人”,一个妹妹去见她同母异父的姐姐们。在中国,当吴精美和她的姐姐们相见的瞬间,她想到的是:“现在我又见到妈妈了,两个妈妈……”见到她们,吴精美感到有“一种无法描绘的亲切和骨肉之情。我终于看到属于我的那一部分中国血液了。啊,这就是我的家,那融化在我血液中的基因,中国的基因,经过这么多年,终于开始沸腾昂起”[1]216。此时此刻,母女完全融为一人,女儿成为母亲的化身,“母女”彼此拥抱着,实现了母亲的愿望和梦想,“母女”重逢,团圆。至此,母女的传记得以完成,《喜福会》叙事之完整性和其魅力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母亲的精神、文化和思想在女儿身上得以传承,在一定程度上,更是中国人、中国女人的精神、文化和思想在美籍华人身上得以传承,其传记人生又可以连绵不断、持续永远地在异国他乡续写下去,其完整性已远远高于一般传记文学作品应有的完整性。
三、《喜福会》叙事的独特性
1.《喜福会》与一般传记文学作品的差异
传记文学作品通常都是讲述伟人、名人、历史人物、有一定历史影响和地位的人或有相当成就的成功人士的故事。但是《喜福会》不然,虽然读者看到的是在讲述四位中国母亲和她们与她们四位美国女儿的故事,但实际讲述的是有关作者一家母女三代人的故事。作者创造性地把其家人:外婆、母亲和作者本人(女儿)化身为《喜福会》中的人物,把她们的故事移植在其中的两个家庭吴素云家和许安梅家中进行演绎,同时还虚构了另外两个家庭《喜福会》中的龚琳达家和映映·圣克莱尔家,借用这两位母亲的经历,补充和完整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女性相似的生活经历,以使读者较全面了解当时中国部分女性的生活状态和处境。此外,《喜福会》还清晰地记录了这些中国母亲和她们美国女儿们的纪实生活。母亲们的过去和她们与女儿的现在的结合,有机地构成“中国移民母女”的“他者”传记文学作品。
《喜福会》首次使普通百姓登上传记文坛,成为传记文学描写的对象,并使其传记内容多样化,注重对传记人物多视角、多侧面、多层次的描写,立体地展现了传记人物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此举在传记文学作品创作中,可谓开创了先河。《喜福会》是在尝试着一种全新创作理念,是在用一种平常的语言讲述母女的故事,写她们的情感,写她们的苦恼,写她们的过去和现在、写她们的文化、写她们的新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喜福会》呈现给读者的是普普通通而有个性的中国女人。
中国人在西方人眼里是神秘的,中国女人和母亲就更加神秘。《喜福会》揭开了这层神秘的面纱,让世界看到了一些真实的中国女人、中国母亲和中国传统文化对她们的影响和作用。旧社会、封建社会和解放前的中国女人是极为让人感兴趣的群体,这是《喜福会》的定位,作者写出了真实的、活灵活现的、朴实而又智慧的中国女人。与此同时,作者还写出了她们移居美国后和她们美国女儿的生活,作者通过记录母女的人生,让世人看到中美文化的差异和融合,使她们的传记人生得以发展和延续。《喜福会》以人物的过去寻觅自身的价值所在,着重表现其真实性、客观性和中国性,突出传主的个性和其延伸性,使其具有传记的文学性和完整性,成为“他者”的传记,与众不同,深得欧美读者的喜爱。
2.《喜福会》叙事中不同的“我”
传记文学作品多用第三人称写作,传者采用传主的名字或根据其性别用其代词“他”或“她”来讲述其人生,也有用第一人称“我”来叙述或自述传主人生的。《喜福会》则不然,这部传记文学作品打破了传统叙事模式,虽也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但是“我”讲的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三个人的故事,讲的是关于“母女”们的故事。故事中的“我”既是叙述者,也是被叙述者,在整部作品中,是变化的,“我”一会儿是“叙述者,讲自己的故事,一会儿是被叙述者,成为故事中的主人公或主人公的叙述者,如:吴精美在讲她妈妈初建‘喜福会’的故事时,她是叙述者,她妈妈则是故事中的主人公“我”,一个被叙述的人:“喜福会这一名字,起缘于我母亲的第一次婚姻,那还是在日军占领桂林前。所以一提到喜福会,就会使我想到她的桂林故事。每当她把碗碟擦干净,塑料台面也已擦拭了两个来回,而父亲已开始将脸躲在报纸后面,一支接一支地抽他的黑猫牌香烟——这往往是一种“不要打搅”的警告,这便是她觉得无所事事之时,于是,她便会对我讲起她的往事。这个时候她总会拉出一箱旧毛衣,那是我们在温哥华的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亲戚送给我们的。”[1]256
但当吴精美讲她妈妈去世后‘喜福会’的故事时,她则是叙述者的“我”:“我母亲总是用中国话开始她的叙述:“我在还未去桂林前,就梦见它好几回了。群山环绕中,一条小河蜿蜒而过,河上漂着青色的浮萍。天幕上衬着锯齿般的山峦,层层叠叠的,白云缭绕其间。如果你在河面上漂浮,仅以浮萍果腹,也能毫无难色地爬上山峰。如果你不慎滑跌下来,也只是坠入一张柔软的浮萍织成的大床上。一旦你爬至顶峰,你会因眼前袒露的一切而欣喜若狂,它会涤净你的一切烦恼不快,扫尽一切腌臢之气”[1]15。
但纵观全作品,“我”的角色不是母亲,就是女儿;而“我”的女儿身份随着故事的展开可以是女儿吴精美、许露丝、丽娜·圣克莱尔或龚琳达;做为母亲的“我”,在故事中也在不停地变换着角色,“我”一会儿是吴素云,一会儿是许安梅、映映·圣克莱尔或龚琳达;但故事的主线从头到尾都是围绕着“我”在讲母亲吴素云和女儿吴精美的故事;而其他母亲和女儿关于的“我”的故事则是具有史实性的虚构故事,是谭恩美的文学创作,是在补充、丰富和完善吴素云和吴精美母女相似和相同的经历,以增加其全景效果和可信度,更真实地展示“母女”的人生经历,如:龚琳达的童养媳的故事、映映·圣克莱尔婚后受丈夫虐待、杀死自己孩子的故事、薇弗莱·龚下棋的故事和许露丝离婚的故事等。
传记文学作品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多是由于叙述人是当事人,所叙述的人与事,只能是“我”所能接触的活动范围内的人物和事,但其活动范围以外的人物和事情就不能成为作品中的叙事内容。这也是第一人称写作最大的局限性和不足。但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就是其不足和局限性使得其叙事更显得自然天成,更具有强烈的逼真感,同时还有利于深入开掘“我”的内在世界,完整展示“我”的心路历程。谭恩美选择第一人称“我”的运用也从另一面说明和证实了其故事的真实性和其“亲力亲为”的纪实性。
传记文学常常是一种逆时写作。谭恩美采用第一人称“我”讲述她外婆和母亲的过去和她与母亲相处的现在独具匠心。因为谭恩美深知她在写什么,她所写的多与她的家人有关,但毕竟又不尽详细,因此,她特别选用第一人称来写,这样,她就可以驾轻就熟,只写她知道的,或是说知道的就提,不知道的就避开,这样写起来,就方便了许多,实为明智之举。如此这样,谭恩美才得以在作品中自由地穿梭于历史与现实、过去与当今之间,将深受不同文化影响下的中国母亲和她们的美国女儿两辈人的思想意识活动和行为展示在世人面前,对比东西方文化,唤起世人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自醒、反思和传承。
《喜福会》中不同的叙述者“我”和被叙述者的“我”的故事使史实、现实和虚构的情节有机统一,使现实世界与文本世界高度融合,真实地反映了在美国的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生活。这实乃第一人称“我”所特有的属性所为。在谭恩美的《命运的另一面》一书中,她对其创作有这样的观点:“记忆孕育想象”“我的想象和现实几乎无异”“我对现实和想象生活记忆的把玩犹如女孩们对于芭比娃娃、男孩们对于他们的阳物那样痴迷。”[4]因此,我们可以说,谭恩美在其作品中充分运用记忆、想象和现实材料,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元素进行利用并以服务作品的中心 —— 纪实和再现历史为其创作目的。
3.《喜福会》叙事的“他者”情结
在西方后殖民理论中,中国移民已成为当今美国社会的“他者”之一,《喜福会》也因之极具“他者性”。因此,美国人、西方人可以通过阅读《喜福会》或看《喜福会》电影可以了解和认识关于一些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文化、阶级背景以及他们在美国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和其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和的过程。客观上,小说《喜福会》本身已具有一定的功效,但更主要的是谭恩美在《喜福会》叙事中的“他者”情结使然。谭恩美的“他者”情结表现为:在母女的叙事中,她们相对彼此,都是互为“他者”被叙述着,因为在家或在“喜福会”,母亲是主人,“本地人或当地人”(native),女儿是美国人,是“他者”(the other),女儿的一切言行举止都不符合中国人的要求和标准,她们都太美国化了;而对女儿来说,在美国,她们是美国人,是“本地人或当地人”(native),她们的母亲则是“他者”,她们来自中国,有着与她们不同的文化理念,做事方法和不同的信仰,她们相差太远,彼此做事太不习惯,甚至产生反感和厌恶。
在《喜福会》中,我们随处可以看到女儿对她们的“他者”母亲的叙述和描写,她们以美国人自居,看待和评价她们的“他者”妈妈。母亲们主要被叙述为:按照中国古老的“五行”理解世事、做人做事;打麻将,谈天说地;聚会时,“她们用她们自己特殊的语言谈天:一半是洋不洋腔不腔的英文,一半是她们自己的中国方言”[1]20。她们都喜爱“都穿着有趣的硬邦邦的立领中国式衣衫,前胸绣着花卉,这样的衣服对真正的中国人来说,是太时髦了,而在美国的聚会上穿,又显得太古怪。”“我想象中的喜福会,是一个有着特殊仪式的社团,好比三K党的集会及电视片中印第安人出征前的典礼,反正有着一套神秘古怪的仪式”[1]15。“这些人的吃相,可真是不大雅观!好像人人都处在饥饿状态,一个个狼吞虎咽”[1]18。
这些都使女儿们苦不堪言。此外,她们认为美国是个让人自由、独立的国度,怎么做人做事是自己的事,其表现的方式又有个人的好恶,别人不能横加干预。可是在《喜福会》的家里,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母亲非常中国,总是强加于她们许多她们不喜欢的东西,母亲时刻进入了她们的生活,支配或左右着他们的生活,这让她们难以理解。然而,在母亲们的眼里,她们的美国“他者”女儿们又是怎样的呢?“她们,只会大口大口往肚里灌可口可乐!”[1]4母亲认为女儿总是:“与我隔着一条河,我永远只能站在对岸看着她,不得不接受她的那套生活方式——美国的生活方式”[1]224“……教不会她有关中国的气质;如何服从父母,听妈妈的话,凡是不露声色……她才不听这一套,在苦口婆心给她讲这些时,她只顾嚼口香糖,吧嗒吧嗒的,然后吹起一个比他脸还大的泡泡。”[1]227母亲们为此感叹着:“除了她的头发和皮肤是中国式的外,她的内部,全是美国制造的。”[1]227。
谭恩美通过以上种种叙述和描写,把《喜福会》中母女彼此看待为“他者”的言行和思考展示于世,清晰地表明了中国移民两代人不同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并揭示了其缘由所在。正是由于谭恩美采用这种母女互为“他者”的叙事方式,她才能游离在中国与美国,在东方与西方、过去与现实之间来回穿梭、跳跃,精心构筑美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把中美文化的差异、冲突和融合表现的淋漓尽致,让世人看到“他者”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谭恩美有这种叙事的“他者”情结,是因为她是美国人,她是美国作家,她写的是美国小说。“我是一个美国作家,我了解的中国文化是“二手信息”。我写作是从美国人的角度,着笔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家庭。我不可能有中国人的视角,我并非在中国成长”[5]“如果我不得不给自己某种身份,我会说我是一位美国作家……我相信我创作的是美国小说,因为我生长在这个国家,我的情感、想象和兴趣都是美国人才有的。我的特征可能是华裔美国人,但我认为华裔美国人也是美国人”[2]。
《喜福会》的叙事手法具有“他者性”,也是谭恩美独到的叙事艺术。在欧美人的眼里,中国第一代移民、第二代移民、第三代移民等对美国社会而言,都是“他者”,他们的生活写照、生存状况自然是欧美人所关注和感兴趣的。谭恩美的《喜福会》刚好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和猎奇,因为《喜福会》不仅展示了中国移民、中国女人、中国母亲过去的历史经历和她们具有美国公民身份的女儿们的生活和处境,还让世界看到了中美文化的差异、冲突和融合,以及今后世界的发展趋势 —— 多元文化的融合与和谐共处。因此,《喜福会》之“他者性”叙述可谓妙不可言。
《喜福会》是一部与众不同的传记文学作品,其情节构建虚实相间、写实演绎交织成辉,相得益彰,传主刻画得更加具体、鲜活、生动,其中一个个故事深深地印刻在每一个读者的脑海中 ——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那点事让人回味无穷。此外,从文学和社会角度上看,《喜福会》第一人称的运用、“他者”的叙事方式和传主的非单一性也给传记文学作品的创作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喜福会》不仅有对于“他者”生活的探求和反思,还掀开了世界多元文化融合画卷的一角,为构建和谐大同的世界开辟了一条新路,展示了光明的前景。
[1]谭恩美.喜福会[M].程乃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2]罗敏,段武宁.谭恩美访谈录 [N].第一财经日报,2006-10-01.
[3]谭恩美.我的缪斯[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
[4]余军.记忆、想象、现实——谭恩美小说的创作策略[J].译林,2006(6).
[5]张璐诗.华裔作家谭恩美专访:我是一个美国作家[N].新京报,2006-0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