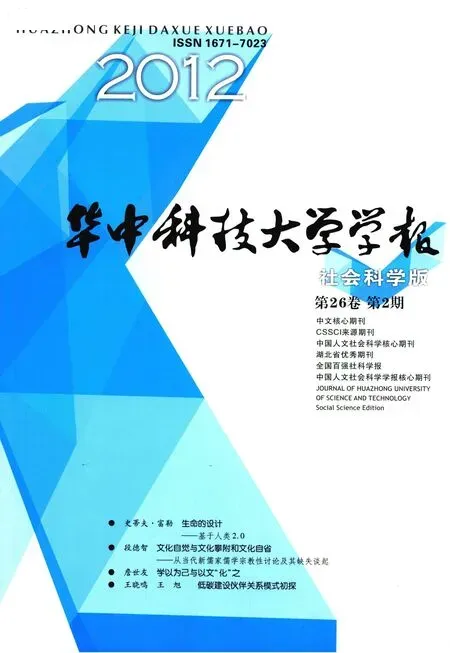对利他主义道德教育的再思考
徐萍萍,陆爱勇,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南京 211189
对利他主义道德教育的再思考
徐萍萍,陆爱勇,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南京 211189
传统利他主义伦理观在强调无私利他的同时反对一切个人利益的诉求而失去了其存在人性论基础。社会生物学认为利己与利他并非二元对立的两极,只是个体在不同环境中所采取的不同生存策略。就人类来说,亲缘范围内的利他是无私利他,而社会范围内的利他则更多是互惠利他。人类的利他行为是知与情统一,是先天与后天协同作用的结果。在一个神圣祛魅、道德世俗化的时代,我们应从内容到方法对利他主义道德教育进行合乎现实与理性的修订。
利他主义;道德教育;伦理
2011年3月日本东北部发生了里氏9级的大地震,地震引起福岛等地核电站发生严重的核泄漏事故,这是继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人类遭遇的又一场核灾难。在整个事件中,五十死士可能是最打动人心的一笔。当核泄漏不断升级,周边群众纷纷撤离之时,为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东京电力公司留下了180位工作人员,以50人为一组轮流执勤。五十死士虽然清楚地知道强辐射会给他们身体带来严重伤害甚至死亡的结果,却义无反顾地自愿留守,用自己的身体来筑起最后一道防护屏障,他们精神感动了世界。实际上,这种无私的自我牺牲行为在人类历史上并不罕见。德奥尔良说:“殉教者的鲜血是教堂的种子。”[1]135在战争中更不乏有英勇之士为保护他人而献出生命。然而,在一切神圣、崇高都遭遇了现代性祛魅的今天,很多人却不愿相信无私利他的存在,甚至对于这些崇高行为背后的动机提出了质疑。而这种质疑又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迄今为止曾引发人们无限思考的“斯密问题”上,即人在本质上究竟是如《道德情操论》所说的以利他为出发点、具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道德人,还是如《国富论》所说的以利己为出发点的经济人?人类是否具有真正的利他本性?我们肉眼可见的利他行为背后的动机又是什么?我们希望藉着对这些问题的考察来重新审视传统利他主义德育,并从中收获一些对当代道德教育有益的启示。
一、传统利他主义德育遭遇的困境
在以往的德育中,人们往往将利己与利他作为水火不相容的两极加以对待,认为利己就是着眼于自己的利益,无视道义要求或他人利益;反之,利他则是出于道义考虑,以他人利益为先,甚至为了维护他人利益不惜牺牲自身利益。由此,在伦理学中围绕着利己与利他的善恶问题曾产生了两大对立的伦理学观: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利他主义如波吉曼所言就是:“认为人们的行为有时能够以某种方式而将他人利益置于自己利益之前的理论。”[2]50而利己主义用桑德斯的话来说就是:“认为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利益而不应该牺牲自己利益的学说。”[3]250利他主义以新老儒家的“仁学”和新老基督教伦理观最为典型。其特点在于,这些学说一致认为人性本质为善,每个人都能够达到无私利他的境界;道德目的和道德终极标准完全是自律的,均在于完善每个人的品德;凡是自利为我的行为都是恶的、小人行为,惟有无私利他的行为才是善的、君子行为。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种利己主义的伦理观,即认为就本性而言人类行为的目的是利己而非利他的;而道德的目的在于保障社会存在发展或增进自我利益,所以只能是他律论。利己主义者之中既有像霍布斯和曼德维尔这样极端利己主义的倡导者,也有像爱尔维修、霍尔巴赫、费尔巴哈、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样的合理利己主义者。后者作为一种在西方被广泛接受的伦理观,其主旨可用霍尔巴赫一句名言概括:“德行不过是一种用别人的福利来使自己成为幸福的艺术。”[4]57也就是说,人虽然究其本性来说是利己的,但是由于利己的目的只能通过社会才能够实现,所以“为了使自己幸福,就必须为自己的幸福所需要的别人的幸福而工作”,从而酿就了人人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社会结果。
在两种对立的伦理观中,我们鼓励前者而反对后者。雷锋精神之所以被人们广为颂扬,是因为雷锋同志“从不利己,专门利人”,雷锋做好事不留名。时至今日,很多富有社会责任心的商业巨子荣登“胡润慈善榜单”却得不到公众认可,原因就在于人们对这些“慷慨的富人”行善背后的动机心存怀疑,质疑他们是想“以利搏名”,还是为“名利双收”。用康德的话来说这样的行为仅仅是“合乎责任”行为,而非“出于责任”的行为,但是“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5]16。“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排斥自我名利的传统利他主义对人们的影响之深可见一斑。
然而,已有学者对此种伦理学观中存在的误区提出了批评。比如,王海明教授就认为利他主义伦理学观较利己主义伦理学观更不道德和有害。原因在于它在鼓舞了人们无私奉献的至善热忱的同时,否认了一切个人利益的追求。须知生存是人类与动物所共享的自然本性,倘若没有自利自爱的本性,人类何以满足自我需要而存活于世?就连革命导师马克思都坦言:“个人总是且不可能不是从自己本身出发的”[6]274。“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6]286反而,合理利己主义者所倡导的趋利避害的人性本能与人作为社会存在所具有的相互依赖、互通有无的分工协作之间的融通似乎更能帮助我们解答亚当·斯密留下的困惑,利己的经济人与利他的道德人并不相悖,“将要取之,必先予之”,人虽是自利的,却首先需要互利,而互利的前提就在于人先天具有怜悯与同情之心,也惟有如此,才能保证人类不会自我毁灭。然而,利己主义也不全然是好的,如若人人皆以此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一味宣扬人性中的自利、享乐和拜金主义,便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二、利他行为的社会生物基础
既然传统的利他主义、利己主义皆不可取,禁锢于任何一个极端之中都是偏颇有害的,那么,我们必须在两者之间寻找某种融通,一种不仅限于合理利己主义者所强调的以利己本性为基础、也不仅限于理性思辨所获得的融通。也许最好的方法就是从人类的本性之中寻找利己与利他各自的源头,由此才能摆脱在道德问题上的偏见上狭隘。达尔文、赫胥黎、海克尔、道金斯、威尔逊等社会生物学者正是从这一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以观察和实证为基础的理论依据。
1895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创立了生物进化论,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生物进化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理预设了一个前提,即物种都有过度繁殖的倾向,在有限的环境资源中个体之间存在着为生存而展开的竞争,在此竞争中对生物有利的变异将得以保留遗传给后代,对生物不利的变异则会遭到淘汰。自然选择所赞颂的是个体的利己行为,因为利他的个体显然因难以维护自身利益而遭到淘汰,它的利他基因也无从传递给后代。于是,从理论上说,利他行为在生物界即便曾经存在过也早已绝迹。实际上,现实中的利他行为又是普遍存在的。当猛兽临近时,瞪羚会夸张地跺脚以警告同类,尽管这往往会把猛兽吸引过来;一些鸟类在发现危险时会发出警告性的鸣叫,此类事例不胜枚举。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在这里遭遇了困境。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达尔文本人在考察生物界不育的个体时,也意识到了以个体为单位的自然选择学说存在某些缺陷,因此,提出“这个难点虽然表面上看来是难以克服的选择作用,可是只要记住选择可以应用于个体也可以应用于全族。”[7]305-306上述主张开辟了群体选择理论的先河。1962年,瓦恩·爱德华兹明确提出了利他行为的群体选择理论,即认为:遗传进化是在生物种群层次上实现的,当生物个体的利他行为有利于种群利益时,这种行为特征就可能随种群利益的最大化而得以保存和遗传。这一理论无疑在种群层次上对生物的利他本性予以了肯定。
此后,在社会生物学领域中又有两种利他主义理论相继诞生。基于汉密尔顿的内含适合度概念,即一个个体在后代中传播自身基因(或与自身相同的基因)的能力,梅纳德·史密斯于1964年提出了利他行为的亲缘选择理论,其主旨是要解释种群内部利他行为发生的差异性,即利他者只为自己的亲属提供帮助或做出牺牲,并且个体之间的亲缘关系越近,彼此之间的利他倾向就越强。这是因为个体之间关系越近,彼此相同的基因也就越多,而个体行为的目的是增加与自身相同基因在后代中的传播。亲缘选择理论很好解释了工蜂、工蚁这类不能生殖后代的动物的利他行为,它们勤勤恳恳地为蜂后或蚁后及其姐妹兄弟服务,目的是让与自己相同的基因传递给后代,而且它们的利他行为只限于本群落内部,并不扩展到其他蜂群或蚁群中。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用基因观点对汉密尔顿的亲缘选择理论作了发展。道金斯认为解释进化论的最好方法应该从发生在最低级水平上的选择出发,这就是基因水平。在一个高度竞争性的世界上,“成功的基因的一个突出特性是其无情的自私性。这种基因的自私性通常会导致个体行为的自私性。然而我们也会看到,基因为了更有效地达到其自私的目的,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会滋长一种有限的利他主义。”[8]2近亲由于共有同样的基因,因此导致利他行为在彼此间普遍存在。即便其中有“一个个体为了拯救十个近亲而牺牲,操纵个体对亲属表现利他行为的基因可能因此失去一个拷贝,但同一基因的大量拷贝却得到保存。”这是利他行为的基因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8]201。
然而,人类的文明之处或许就在于人类的利他行为不仅发生在亲族之内,而且会发生在毫无亲缘关系的个体之间,甚至后者比前者更能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因为“如果利他主义都是无条件的话,那人类的历史就全是裙带关系、种族主义。”[9]147所以,威尔逊认为:“基于亲族选择的纯粹无条件利他是人类的大敌。”[9]142特里弗斯的互惠利他主义正是要对发生在毫无亲缘关系个体之间的利他行为做出解释。它的基本原理是:如果一个利他行为给受益一方所带来的好处总是大于利他者因利他行为所付出的代价,那么只要这种利他行为在以后的某个时候能够得到相应的回报,双方就都会有所受益[10]。互惠利他本质上是一种合作行为,它普遍存在于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植物到动物乃至人类的不同个体,甚至不同物种之间。特里弗斯提出互惠利他是人类合作的重要基础。他用重复囚徒困境博弈对此进行了比拟。在重复的囚徒困境中,由于博弈在反复地进行,因此每个参与者都有机会去“惩罚”另一个在前一回合中的不合作的参赛者,这时作为均衡的结果可能会出现合作行为。虽然互惠利他的模型直至20世纪晚期才得以确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理论的雏形早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那只著名的“看不见手”的论述中就已见端倪,并因此似乎与合理利己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两者的理论基础是完全不同的,并隶属于不同的学科。伦理学中合理利己主义主要基于一种抽象的人性论假设,而互惠利他则建立在更加现实的社会生物学研究的基础上。比如,社会生物学家发现蝙蝠会把自己吸食的血液吐出一些来反哺即将饿死的同伴,尽管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而且这种行为遵循着一个严格的规则,即倘若受惠个体知恩不报,那么其他蝙蝠将不会再向它提供类似帮助。互惠利他是图谋回报的,但这种回报可以是长效的。互惠利他策略行为的使用者也必须具有一种彼此辨识的能力,因此,它更有可能发生在空间邻近的个体之间。互惠利他作为一种生存策略与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并不矛盾,因为两者都是个体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所采取的不同策略。
以上各种社会生物学的理论得出了一个相同的结论:在生物学中,只有生存才是根本,利他只不过是从基因、个体乃至种群不同层面上的一种生存策略。尽管如此,每一物种利己与利他行为在表现上还是有所差异的。威尔逊将生物界中的生物根据其自利与利他行为表现排成了一个谱系,其中的一端为利己,即个体水平,另一端则为利他,即社会水平,位于两者之间的依次是核心家庭、大家庭、社群和部落。他认为,鲨鱼处于利己的一端,而水母、蜜蜂和蚂蚁则处在利他的一端,而人类居间,且处在靠近个体的位置上。他认为:“个体行为,包括施予部落或民族的表面上利他的行为是以个人及其近亲的进化优势为目的的,有时候是非常迂回曲折地达到这一目的。最高级的社会组织形式,无论其以何种面目出现,说到底是为个人利益服务的工具”。“可以预见,其结果将是个体内心斗争不断,时而自欺欺人,时而悔恨内疚,真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1]144。
三、利他行为的动机分析
实际上,利己与利他在人类身上有多种表现。王海明在《新伦理学》一书中根据手段—目的、己—他、利—害等维度将伦理行为划分为十六种类型[11]186。其中,传统利他主义所宣扬的主要是目的利他的行为,尤其推崇完全利他和自我牺牲行为,正如孔子所说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而其所批驳的利己主义则主要是完全利己、损人利己以及动机不纯的为己利他行为。可问题是,既然人类的利他性缺乏自然基础,那么完全利他和自我牺牲这样的利他主义是否又具有合理性呢?如果对此完全加以否定的话,无异于否定了人类道德的崇高性。须知,人类常常将自己设定为一个道德物种、社会性的存在,以区别于自然界的其他动物。因此,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利他行为背后的动机。
威尔逊认为,在人类自我牺牲的利他行为中,个人的虚荣心和自豪感是重要的因素。就如詹姆斯·琼斯在《二次大战》一书中所说的那样:“纯粹的战斗激情经常使得一个人自愿去死,而没有这种激情性可能会畏缩不前。”[9]138除此之外,“暗示互惠的优点、自以为公正善良、感恩以及同情加强了认可利他行为的可能性。”[9]130
威尔逊的上述观点不免让人想起孟子的“四心”说。孟子认为,人人皆有四种道德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其中,恻隐、羞恶、辞让三心为情感,是非之心为理性。四心之中又以恻隐之心最为根本。恻隐乃是一种同情或怜悯之感,类似于霍夫曼所说的移情。移情被认为是利他行为的重要中介和动机,它是指人在察觉他人情绪反应时所提验到的与他人共有的情绪反应。人类的移情具有先天基础,但更依赖于后天的发展。塞基和霍夫曼在出生仅一天的婴儿身上发现了反应性的哭泣现象,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模仿,而有可能是婴儿对另一个同类人的哭声的先天的、同型的反应[12]74。反应性的哭泣是人类移情的自然基础。霍夫曼认为人类的移情共经历四个阶段:非认知的移情(1岁以内)、自我中心的移情(1-2岁)、推断的移情(2、3岁到童年晚期)和超越直接情景的移情阶段(童年晚期之后)。而儿童在第三个阶段就开始形成初步的观点采择能力,并尝试表现出一些利他行为。霍夫曼认为,当儿童观察到他人遭遇痛苦或不幸时就会产生强烈的移情,如果此时他知道自己只要采取行动来安抚他人就能减轻或消除这种痛苦的话,个体就会表现出利他行为。
人类利他行为不仅有赖于情绪上的唤醒,还有赖于社会认知能力的发展。“四心”之中的是非之心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道德认知。年幼的儿童即便注意到别人的痛苦,并产生了相应的移情,也不知如何施加帮助,因为利他行为的发生还有赖于对众多信息的认知加工。这其中就包括社会观点采择和对社会规范的认知。社会观点采择是个体对特定情景中他人的思想、情感、动机、需要的认知理解。儿童的观点采择能力从2、3岁直到青少年期一直处于稳固发展之中。昂特伍德和摩尔通过元分析发现,观点采择与亲社会行为具有高度相关,即一个人的观点采择能力越强就越能表现出利他行为[13]323。然而观点采择作为一个信息收集的过程,只是利他行为的认知前提,其本身并不具有实质上的利他性,个体是否去帮助别人,还依赖于他对社会规范的认知以及自身的需要。
在社会化的过程中,父母、教师以及其他重要他人教导我们应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帮助我们树立起社会责任意识;在社会互动当中,儿童对于社会互惠和社会交换有了切身体验,越来越多地做出互惠利他的行为;逐渐形成了社会公平意识,开始根据情景来决定是否应该做出利他行为;通过社会学习,观察到了积极与消极的利他榜样及各自得到的后果,形成了抑制或表现利他行为的更深层次的动机。
此外,社会心理学的大量实验还揭示了利他行为与其他心理因素相关,如利他者自身心情、年龄、性别、人格特征,情境方面的物理环境、时间压力、旁观者人数,以及受助者的吸引力、与利他者的相似性等。因此,人类利他行为的做出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涉及知、情、意、个人品质、动机和价值观等一系列的复杂心理结构,它的形式与强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决定的,是后天社会教化的结果。
四、利他行为的道德教育
威尔逊早就断言:“人类的利他行为看来在指向近亲时是真正无条件的,尽管其程度还是远远低于群居昆虫和集群无脊椎动物;在其他时候则基本上都是有条件的”[9]144。社会学家帕森斯通过对加勒比地区移民习俗研究和比较研究得出:“个人的策略是使自己得到比他人尽可能多的利益”[9]144-145。,既然生活在一个神圣祛魅、道德世俗化的时代,我们就必须对以利他为内容的道德教育做出更加合乎现实与理性的重新修订,使之具有更加强大的感召力量,能对人们精神世界和伦理价值产生更加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首先,是教什么的问题,即选择何种价值观作为利他行为的基础加以弘扬。儒家强调“爱有差等”,黑格尔也认为家庭内外的伦理关系有所不同,需要加以区分。在家庭内部的伦理关系是“以爱为其规定性”[14]175的。从进化论角度来说,血亲之间的伦理行为符合“基因的自私性”,即以自身的遗传物质得以延续为目标的使人类具有强烈的自我牺牲的激情。所以,家庭伦理的基础是无条件利他。由于社会本于家庭,对于这种无私利他我们应该加以提倡。另一方面,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但由于人们之间的利益相关性,使得利己的目的需以他人为手段才能实现,所以人们“都是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14]197。社会伦理的基础是互惠利他,大多数没有明显直接动机的人类利他和合作行为以及社会规范都建立在互惠利他的社会契约之上。由于互惠利他行为既能增进自身利益,又能给他人带来好处,因而需要大力加以提倡。而且,社会是由无数的个体与群体所组成的,每一个体或群体又有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当这些不同利益诉求发生冲突时,应该教导社会成员如何取舍呢?盲目利他主义的道德观要求人们无条件地牺牲个人利益,维护集体或他人利益。这固然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公共目标的实现,但是正如前面所述盲目利他主义缺乏人性论的依据,在社会强化的作用下它或许可以成为一时的行为动机,却难以作为利他行为的持久来源,如果过分加以强求,还可能导致官民的二元道德观。互惠利他的假设似乎更能帮助我们解决这一冲突。从囚徒困境中可知,如果理性地追求个体自我利益,结果只能落得两败俱伤。所以理想的教导是为了更加长远的个人利益需暂时放弃一部分眼前的个人利益。在“一报还一报”的社会轮回中,具有良善、宽厚、助人这样品格的个体往往因自我牺牲反而收获了更多,这与孔子所说的“德者,得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其次,是怎样教的问题,即通过何种方式来引导和培养利他行为。根据对人类利他行为的动机分析得知,利他行为是知与情的统一,是先天与后天协同作用的结果。利他行为中的知包括道德推理和观点采择。在科尔伯格看来,人类道德推理以公正判断为核心,经历了三种水平的发展。道德发展的较低水平是他律与个人工具主义的道德,其次是寻求认可与遵守法规和秩序定向的道德,最高水平才是社会契约与良心原则的道德。儿童的观点采择能力同样经历了由低到高的发展阶段。所有这些道德认知皆以人类理性认知能力的发展作为基础。因此,对利他行为的培养必须遵循人类认知和道德发展的规律,不能盲目制定儿童难以理解或达到的过高原则和目标。由于包括同情、羞愧、内疚在内的很多负性情感被认为是道德基础和激发道德行为的重要动机,而且女性的道德被看成是关爱取向的道德,因此,在利他行为培养中还要特别重视道德情感和情绪唤醒的作用。另外,教育者要对利他教育的环境因素给予充分重视。家庭之中的利他以爱为基础,因此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培养爱的能力就显得极为重要;社会之中的利他基于一种平等互惠的契约,所以要为利他行为提供良好的环境支持,建立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和谐社会氛围。社会应通过一定机制特别是奖赏与处罚机制对利他行为给予回报,这既是对利他行为者的肯定与激励,又为其他人确立了正确的榜样与价值导向。政府应为利他行为提供制度保障,即建立一种以互利合作为基础的能体现公平正义价值理性的制度环境。而在道德教育方面,可供采用的具体方法也是多样化的,包括榜样模仿、移情训练、组织游戏、表扬奖励、舆论批评、道德讨论甚至公正团体法等。
[1]威尔逊:《论人性》,方画展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2]Louis P.Pojman.Ethical Theory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Belmont,California: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USA,1995.
[3]John K.Roth ed.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thics,London: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1995.
[4]爱尔维修:《精神论》,杨伯恺译,上海:辛垦书店1933年版。
[5]康德著:《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7]达尔文:《物种起源》,周建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8]道金斯:《自私的基因》,卢允中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9]威尔逊:《新的综合:社会生物学》,李昆峰编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0]李建会等:《超越自我利益:达尔文的“利他难题”及其解决》,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年第5期。
[11]王海明:《新伦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12]霍夫曼:《移情与道德发展》,杨韶刚等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3]张文新:《儿童社会性发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Rethinking of Altruism Moral Education
XU Ping-ping,LU Ai-yong
(School of Humanities,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211189,China)
Traditional altruism ethics opposes all pursuit of individual interests when it emphasizes selfless altruism,thus losing its existing basis of human nature.Social biology argues that altruism and egoism are different survival strategies for individual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rather than binary opposition.As far as human is concerned,altruistic behaviors among relatives are selfless altruism,but most altruistic behaviors in society are reciprocal altruism.Human's altruistic behaviors are the unities of cognition and emotion and the results of nature and nurture.In an era of sacred disenchantment and moral secular,we should revise the altruism moral education to more corresponding to reality and rationality in aspects of both contents and methods.
altruism;moral education;ethics
B82-064
A
1671-7023(2012)02-0037-06
徐萍萍(1980-),女,山东威海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道德心理学;陆爱勇(1979-)女,安徽六安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伦理学。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8JJD880231)
2011-12-01
责任编辑吴兰丽
-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低碳建设伙伴关系模式初探
- 论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乡土文艺观
- 文化自觉与文化攀附和文化自省——从当代新儒家儒学宗教性讨论及其缺失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