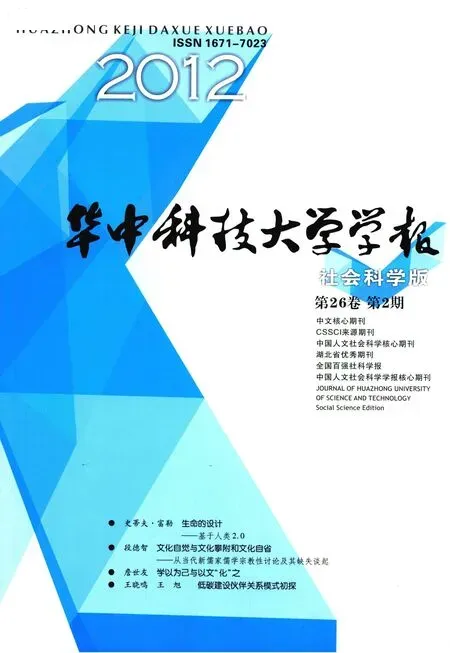论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乡土文艺观
王琼,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文学院,湖南长沙 410205
论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乡土文艺观
王琼,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文学院,湖南长沙 410205
乡土文艺已经成为当代文化变迁与文化守成的现代化进程中,世界各民族所面临的文化诀择与生存选择的叙事符号。我国的乡土文艺也在这种文化复兴的时代潮流中成为当下文学艺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其普遍把地方色彩、风俗人情、农村农民等题材或风格特征视为乡土文艺的本质特征,从而以文艺的题材、风格、表现形式等形式特征,来取代乡土社会的文化形态特征,这样研究和界定乡土文化,势必背离了乡土文艺的文化本质。本文拟从文化人类学的范畴内涵来界定乡土文艺的内容与特征,为当下的乡土文艺研究提供学理建构的理论平台。
乡土艺术;文化人类学;民俗学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现代化进程使得那些历史悠久、传统文化深厚的民族,既要面临文化对话与文化反思的文化变迁过程,又要面临恪守民族精神纽带的文化守成过程,从而使文化变迁与文化守成成为当下各民族寻求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诀择与生存选择。“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被集中体现为乡土文艺所象征与隐喻的文化叙事符号,催生出乡土文艺的趁兴与聚热,这突出表现在我国当下乡土音乐、乡土美术、乡土舞蹈、乡土建筑、乡土电影、乡土戏曲的发掘与开发上,诸如杨剑龙的《放逐与回归: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论》、杨民康的《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孙建君的《中国民间皮影》、高星的《中国乡土手工艺》、楼庆西的《乡土建筑装饰艺术》等乡土艺术研究成果蔚为壮观①有关乡土文艺理论研究的学术成果主要有:杨剑龙:《放逐与回归: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论》,上海:上海书店1995年版;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论》,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叶君:《乡土·农村·家园·荒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赵宏顺:《社会转型期乡土小说论》: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杨民康:《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高星:《中国乡土手工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楼庆西:《乡土建筑装饰艺术》,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陈捷:《第五代电影:现代性的追求与反思》,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乡土文艺研究的范围涉及了所有的艺术门类。但众多文艺理论界的专家学者对“乡土”这一学理范畴的阐述与学理建构却是模糊的,甚至含混的,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从文化人类学的学科性质来界定乡土文艺的含义与特质。
一、地方色彩之乡土文艺观背离了乡土的文化人类学本质
中国的乡土观念肇始于“救亡图存”的民族生存诀择的历史选择之中,在与五四启蒙激烈的反传统和“西学东渐”斗争中,文化守成主义者诸如晏阳初的“民族再造论”和梁漱溟的“文化再造论”,均以乡村建设运动的方式来寻求民族复兴与崛起的生存选择,从而乡土成为这一历史背景下的思想观念与社会语境,并在20世纪40年代在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学领域享有世界级声誉的费孝通先生的经典名著《乡土中国》中,成为集中代表中国传统社会与民族文化符号特征的范畴概念。乡土的历史与社会语境最早被周作人先生引入文学现象与理论研究中,他在1910年翻译的匈牙利作家约卡伊·莫尔(匈牙利人育珂摩耳)的中篇小说《黄蔷薇》最早提出了“乡土文学”概念,此后又在1923年连续发表在《旧梦》、《地方与文艺》的系列文章中,一再阐明文学是以个人情感与欲求(个性)来反映人类共通的情感和欲求(共性)的文艺主张[1]10。窃以为,周作人的“乡土色彩”、“乡土艺术”是地方色彩所呈现出的艺术趣味与个性特色,并不指向乡土的民族(族群)文化内涵与特征。此后众多的乡土文学家继承与发展了周作人的这一文艺主张,如丁帆先生在其《中国乡土小说史论》中就明确地以“地方色彩”和“风俗画面”作为“乡土小说”概念阈定的基本要义,强调“三画四彩”(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与自然色彩、神性色彩、流寓色彩、悲情色彩)作为乡土小说概念的外形内质[2]10。由丁先生的阐述不难看出其“地方色彩”与乡土文学的发韧者周作人“炉火纯青的趣味主义”文艺观,以及后来的乡土文学坚定主张者刘绍棠“乡土文学特定艺术范畴五原则”之间的渊源关系。但刘绍棠的老师孙梨先生却对以“地方色彩”为特征的“乡土文学”主张持否定意见,并再次引起当代乡土文学的有无之争。孙梨认为地方生活与民俗风情决定的“地方色彩”终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因此所谓的“乡土”也并非恒定的,没有了乡土何来乡土文学?[3]然笔者认为,孙梨先生只是一味地以时空环境变化来否定“乡土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存在的不可能性,即只是以“地方特征”来否定“乡土特征”,形式逻辑的否定支撑不了命题存在的否定,因而缺乏学理建构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地方色彩”作为一种追求艺术个性特色的文艺价值观与文艺表现论,有其艺术审美多样性与丰富性的理论合理性,但表现“地方色彩”的文学是否就是“乡土文学”呢?或者“地方文学”就是“乡土文学”呢?显然周作人的“乡土艺术”、丁帆先生的“乡土小说”把二者等同起来。对此,茅盾曾清醒地认识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地方色彩”即某地的风景之谓,只是地方色彩表面而不重要的一部分,地方色彩仅仅只是一地方的自然风景与社会背景之“错综相”而己,其本质还在于“老中国的儿女们的灰色人生”所蕴含的“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4]89。应该说,茅盾把“乡土”注解为“老中国儿女的一种生命生存方式”,使得乡土文学由地方色彩进入生命哲学主题,深化了乡土文学的艺术价值。但“老中国儿女的生命哲学”具体为何?茅盾没有明确的阐述,似乎也阐述不清,故他一方面反对使用乡土文学(只使用乡村生活小说、农民生活小说),一方面又写《关于乡土文学》。笔者以为地域民族(族群)生存生活方式只是其文化符号所外化的行为方式,其生命哲学主题决定于独特的民族文化形态本质。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被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冠以Earthbound China[5]82(一般译为“乡土中国”,中文书名为《云南三村》)题目时,这一成熟文明体系的“乡土社会”范式界定了“乡土中国”的民族文化特征,“这里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的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6]6可见,费老的“乡土中国”是指深深凝结了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特征的基层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即由民族(族群)文化决定和支配的基层“乡土社会”,因此“乡土”不是一个地位区间概念的“地方”,也不是趣味主义的“地方色彩”,而是中国传统基层社会形态与社会结构所承载的民族(族群)文化特征。“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所要呈现的正是一个民族(族群)独特的文化形态与文化特质,并由这一特有的文化生态来思考人类生命存在与生活方式的丰富性与多样性问题,肖霍洛夫、昆德拉、马尔克斯等正是以展现其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而走向世界的。因此,地方色彩只是乡土社会即民族(族群)文化的外在物化形式,而非其文化内涵本身,以外在的种族特征、自然环境与气候因素所形成的差异性“地方色彩”来置换“乡土”,从而把表现地方色彩的文艺视为乡土艺术,显然是一种由表及里的逻辑混乱。因此,“地方色彩”只是民族(族群)生活方式的物化形态,它是文化符号的而非“地理特征”的。
二、民间民俗之乡土文艺观混淆了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的学科界限
民间艺术与民俗作为下层民众生活的文化载体,直接秉承了地域民族(族群)文化的基因性特征与原发性特征,特别是那些古朴原始而又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民间艺术,已经深深地沉淀于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之中。然而在当今以工业化、城市化为特征的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在赋予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资源对话融合的同时,又不能不滋生自身文化认同的危机,因而变迁与守成成为当今世界各民族追求现代化过程的一种文化自觉行为,“求同存异”的“地方性知识”选择不能不成为各民族共同的主题与普遍的呼唤,这也是民族文化独特性与世界文化丰富性的内在要求。“技术进步、能力增强和危险把我们带入了新的相互依存之中。为了在这种依存中作为人而不是作为技术的奴仆生活,我们必须成为地球本身的世界公民。我们无法在太空中获得全球性。我们只有同时是来自某地的,才能真正成为全球的。”[7]235从而当今世界的发展一方面表现出全球化、一体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寻求文化独特性的民族性特征。这一点,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到《保护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发展过程来看,对“民间艺术”的理解,也经历了从习惯的艺术层次分类即口头与民间艺术,到民间传统文化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深化过程,最后才确定民间艺术作为民族文化符号载体的文化人类学特征的。我们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理解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他们在2006年确定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就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为民间文学、民间舞蹈、民间音乐、民间美术等,后来终于也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文化传承特征,在2008年发布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将“民间”全部改为“传统”,可见,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在知识分子精英中也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
但国内诸多乡土艺术研究者并没有把握作为艺术层次分类的“民间艺术”与作为民族(族群)文化符号载体的乡土艺术的区别,把“民间”等同于“乡土”,把民间民俗艺术视为乡土艺术,如周旭在《中国民间美术概要》中就认为,“民间美术与当地生活方式紧密联系,因地制宜地利用当地物力资源,并稳定地在此区域流传,因而有鲜明的乡土文化特征,又被人们称之为‘乡土艺术’。民间美术是艺术与生活的零距离接触点,以最原始、最朴素的方式从生活中诞生,在实践中完善,而形成独特的美术艺术。”[8]5孙建君的《中国民间皮影》也认为皮影人既是戏曲表演的道具,又是富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品,它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历史生活的生动画卷,是一种最富感染力的乡土艺术[9]1。段改芳、王江的《民间面花——中国民间工艺全集》也把民间面花称为“来自民间的淳朴的乡土艺术”[10]4。“民间民俗”是民俗学的学科研究范围,尽管其质素也体现了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形态与文化特征,但民俗只是通过一个侧面去反映民族文化,或者说一种民俗只能体现民族文化的一种或多种元素,而不能反映整体论视角下的民族文化,这正是“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的科际关系与科际分界。关于“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的科际分界,民俗学家博尔尼(现通译为班恩)对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区别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引起民俗学注意的,不是耕犁的形状,而是耕田者推犁入土时所举行的仪式;不是渔网与渔叉的构造,而是渔夫入海时所遵守的禁忌;不是桥梁或房屋的建筑术,而是施工时的祭祀及建筑物使用者的社会生活。”[11]1可见,“民间民俗”只是民族文化一个方面,以“民俗”替代“乡土”,显然是以偏概全。“民族的地域性特征有时也通过民俗的民族特征体现出来,但跨民族民俗指向的是民族本土文化的同类相生而非乡土社会的同类相生;同样,同一民族的乡土社会可能存在着不同的民俗,差异的民俗不能区别为同一民族的乡土社会的差异”[12]19。因此,民间民俗只是民俗学的学科范围而非文化人类学的学科范围,乡土艺术所要表现的是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乡土社会文化整体模式,因而不能把表现民间民俗的艺术就等同于乡土艺术。
三、农村农民生活之乡土文艺观偷换了文化形态与社会阶层概念
中国是一个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国家,中国古典文艺主题的传统几乎就是表现乡村的传统,形成了以优美、恬淡、朴素、自然为特色的自足艺术体系。五四之后,鲁迅系统地根据赛先艾、王鲁彦、许钦文等文学研究会一批青年作家所创作的农村农民题材小学特点,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里最早使用“乡土文学”来界定他们的文学特征,并立即被文艺界所接受,成为后来尤其是当代“三农问题”政治时代主题下评价反映农村农民生活艺术题材的一个文艺审美观。比如张志平在其《中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乡土小说研究》就把“四十年代充满朝气的新生活农村”与“二三十年代衰败落后的农村”相区别,而作为四十年代“乡土小说”的特质与立论依据①参见张志平:《中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乡土小说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楼庆西则把乡土建筑完全等同于农村建筑:“作为一种形象艺术,建筑装饰艺术更离不开具体形象,而乡土建筑就是展现农村村落的建筑整体和组织这个整体的各种类型建筑的具体形象及装饰式样。对乡土建筑装饰的形态、内容,装饰的用料与技艺,乡土建筑的造型观念与结构思想等的研究,就在于揭示中国传统乡土建筑装饰的艺术特征与审美价值。”[13]4此外,陈捷的《第五代电影:现代性的追求与反思》也把诸如《红高梁》、《红象》、《猎场札撒》等表现农村农民生活的电影定义为“乡土电影”,作为第五代电影“现代性意识反思”的生命寻根话语②参见陈捷:《第五代电影:现代性的追求与反思》,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而杨民康的《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试图从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的文化属性来立论,应该说他认识到民歌所承载的乡土文化属性,但其不是按照民歌所表现的乡土社会文化模式诸如信仰崇拜、仪式、生计模式、亲属关系、家庭继嗣等文化人类学范畴,来论证民歌所承载的民族(族群)文化的象征性符号,而是按照民歌所体现的农村农民生活内容来论证,这依然落入了农村农民题材的窠臼。
以农村、农民生活作为乡土文艺的题材特征与艺术风格,同样显示出乡土文艺理论与批评在“社会动力学”视域的抵牾与吊诡,诸如传统的封建宗法农村、地域特色的民族农村、四十年代的解放区农村、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转型期新农村,孰是孰非?把乡土文艺界定于历时性的时代语境或政治社会背景下的农村,则必然带来乡土文艺范畴的泛化与含混化,无疑也消弭了乡土文艺的特质。鲁迅界定“乡土文学”的本意,是要通过赛先艾、王鲁彦、许钦文等的作品以揭示农村农民的愚昧、麻木与落后,达到“引起疗救”的启蒙主题,而非追问导致乡土社会“农村农民”愚昧、麻木与落后的社会与文化原因。决定与支配农村农民全部生活现实的正是乡土社会的文化形态而非农民本身,也就是说不是农民愚昧、麻木造成农村的落后,而是乡土文化生态造成了农民的愚昧、麻木。“我要辨明的是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5]17因此,鲁迅的“乡土文学”确立的是启蒙主题,而非文化主题。乡土文艺描写地域农村农民生活是要借助这种外在的行为方式揭示其所象征与隐喻的文化符号,而不是简单地回归五四“启蒙”主题。以反映农村农民生活题材来界定乡土文艺特征的经验性描述来阈定乡土文艺的文化本质,无疑是以社会阶层偷换文化形态概念,因为乡土文艺的本质在于“乡土文化”形态而非社会阶层意义上的“农村农民题材”,即文化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所说的“文化原理的发现”:“人类学的目的是什么?是否只要像《山海经》一样说些怪异的风俗与人种,如所谓黑人鼻孔的开展呀,某种语言中连字成句的接头话的繁复呀,某处蛮人用指甲戳进木像以杀害仇人的魔术的奇异呀等不相衔接的杂事,以供普通人茶余酒后的谈资吗?这绝不然。这些杂事不是不当说,但人类学的论及它们,却是与普通的闲谈不同,是要探索其中的意义,寻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来。……文化原理的发现——这是要用综括的方法,探索人类文化所蕴藏的原理……这些问题都是人类学,特别是其中的文化人类学所希望解决的。”[14]17,18
文艺作为人类对世界存在意识反映的发生学原理,与文化人类学须从文学艺术中寻找人类文化质素,决定了文学艺术与文化人类学的内在联系,也为学科交叉提供了视域融合的学理建构资源。因此,只有从文化人类学的学科性质来解读乡土文艺,才能界定乡土文艺的特质并呈现乡土文艺的文化价值、艺术特征和审美形态,这在最近几年我国大力提倡保护与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势下,对于如何发掘乡土文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符号与审美价值,如何传承与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等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周作人:《地方与文艺》,载《谈龙集》(《周作人自编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2]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论》,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3]孙梨:《关于乡土文学》,载《北京文学》1981年第5期。
[4]茅盾:《关于乡土文学》,载《茅盾全集》(卷2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5]费孝通:《乡土中国·后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6]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7]史蒂芬·罗:《再看西方》,林泽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
[8]周旭:《中国民间美术概要》,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
[9]孙建君:《中国民间皮影》,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
[10]段改芳、王江:《民间面花——中国民间工艺全集》,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年版。
[11]博尔尼:《民俗学手册》,程德祺等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12]高俊成:《民俗文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3]楼庆西:《乡土建筑装饰艺术》,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
[14]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The Idea of Local Literature and Art with the Viewpoint of Culture Anthropology
WANG Qiong
(School of Humanity,Hun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University,Changsha410205,China)
In the course of modernization of contemporary cultural changes and cultural conservatism,the local literature and art has become narrative symbols of the cultural choice and survival selection faced by all nations.In this cultural renaissance trend,local literature and art in China inevitably becomes a hot research issue.Studies focus on local features,customs,and rural farmers as research objects.Generally,they attempts to demonstrate the locality through literary theme and style as the shape of local endoplasmic,and to replace the culture symbol of local characteristics with formal features of literature and art,resulting in a departure from the cultural essence of the local literature and art.This paper defines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literature and art from the cultural anthropology category,in hope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platform for current local literary studies.
local art;cultural anthropology;folklore
G03
A
1671-7023(2012)02-0032-05
王琼(1971-),女,湖南长沙人,博士,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乡土文学和文化人类学。
湖南省社科规划基金课题(2010YBB215);湖南省社科成果评审委员会基金课题(2010ZC063)
2011-10-12
责任编辑吴兰丽
-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低碳建设伙伴关系模式初探
- 对利他主义道德教育的再思考
- 文化自觉与文化攀附和文化自省——从当代新儒家儒学宗教性讨论及其缺失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