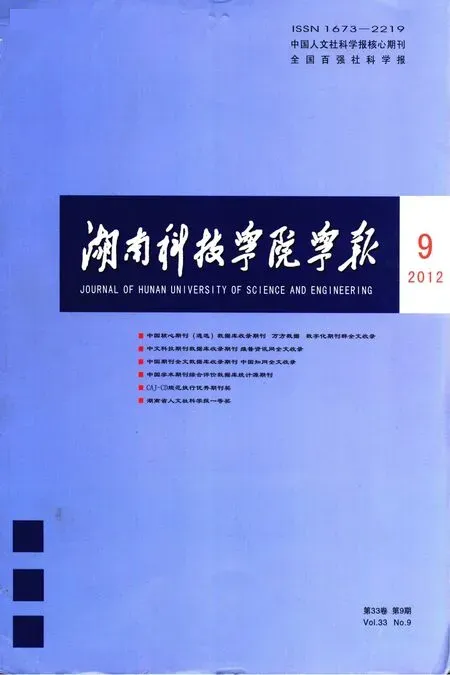隐喻的本质新探
曹群英 黄泽英
(湘南学院 大学英语教学部,湖南 郴州 423000)
隐喻的本质新探
曹群英 黄泽英
(湘南学院 大学英语教学部,湖南 郴州 423000)
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修辞手段,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隐喻的本质实际上是人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认知形式,是一个概念域对另一个概念域的映射和一种述谓现象,隐喻的理解是一个明示-推理过程。
隐喻;认知;本质
一 隐喻是一种认知方式
人类有多种认知方式,隐喻是其中重要的一种。隐喻作为人们重要的认知方式,对人们感知经历世界、对语言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隐喻不是简单的语言的产物,而是 一种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是新的语言意义产生的根源。人类的思维方式总是从已知到未知,由简单到复杂,由具体到抽象,由熟悉到陌生,这种思维模式与隐喻不谋而合。隐喻的认知力量就在于将源域的图式结构映射到目标域之上,即用一类事物来表征另一类事物。Lakoff将隐喻分为三类:空间隐喻(spatial metaphors),实体隐喻(ontological metaphors)和结构隐喻(structural metaphors)。空间隐喻以空间为参照方位,通过将空间结构投射到非空间概念上,赋予该空间概念一个空间方位,形成了用表示方位的词语表达抽象概念的语言。实体隐喻指将抽象模糊的思想、情感等概念看作是有形的实体。结构隐喻就是通过一个结构清晰、界定分明的概念去构建另一个结构模糊、界定含混、或完全缺乏内部结构的概念。Lakoff & Johnson还根据规约程度将语言中的隐喻表达分为两大类:规约隐喻(conventional metaphors)和新鲜隐喻(new metaphors)。规约隐喻是指已经成为日常语言一部分的隐喻,很多甚至已经词汇化,被收入辞典中。从认知的角度看,通过长期建立的规约关系而无意识地进入语言的隐喻才是最重要的。新鲜隐喻是出于表达新事物的需要而产生的隐喻。文学作品、科学技术和流行歌词中此类隐喻随处可见。规约隐喻和新鲜隐喻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所有的规约隐喻在产生之初都是新鲜的,但是长期的发展使新鲜感消失了。同样新鲜隐喻也会逐渐变得约定俗成。总之,隐喻语言渗透到各个领域,充分说明这不仅是语言现象,而且是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人类的思维从根本上是隐喻的。隐喻作为人们重要的认知方式,对人们感知经历世界、对语言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语言反过来成为思维的载体,词汇是语言的细胞,因此词汇中渗透着隐喻。隐喻是词汇产生、语义扩展、语言运用的重要来源。学者们通过观察大量语料后发现日常语言中70%以上的词语表达源于隐喻思维过程。这充分说明这不仅是语言现象,而且是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人类的思维从根本上是隐喻的。
二 隐喻是一个概念域对另一个概念域的映射
I.A.Richard在《修辞学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一书中说:“当人们使用隐喻时,就把表示两个不同事物的思想放在一起,这两个思想活跃地相互作用,其结果就是隐喻的意义。”[1]明确提出隐喻是借一种思想作为另一种思想,Lakoff谈到隐喻过程时认为隐喻是人们借助一个概念领域去理解另一个不同的概念领域结构。他在《我们借助隐喻而生存》一书中指出:“隐喻性是我们日常概念体系的本质,是人类主要的、基本的生存方式。人们借助一个领域的概念结构去理解另一个不同领域的概念结构,就是隐喻过程,就是隐喻思维过程。”[2]但隐喻是两个概念域的互动,有别于Richard & Black的“互动理论”(Interaction Theory),其观点认为:要判断某词是否使用了隐喻可通过它是否提供了一个本体和一个喻体并共同作用产生了一种包容性意义。如果我们无法分辨本体和喻体,我们就可以暂时认为该词用的是原义,如果我们分出至少两种作用和意义,那我们就说它是隐喻。“互动理论”主要从语法角度解释隐喻的适用性,隐喻并不能完全解释某事情,亦即不能定义某事情。隐喻只能说明某事情的某一特性,在一定环境下的源域与目标域的某种相似性,强调反映客观事物的“吻合”方式,隐喻是不可逆的。Lakoff和Johnson指出,“我们的许多概念系统是由隐喻构建的”[2]。这种隐喻式推理一是基于人的经验,二是基于具体到抽象域的投射,即从源域(source domain)到目标域(target domain)的投射。他们认为,人类有能力将一个概念域隐喻性地映射到另一个概念域,从而建立起不同概念域之间的相互联系,而这种联系是客观事物在人的认知领域里的相似联想。正是这种从具体到抽象的隐喻投射,词汇发展了其不同的义项,产生了许多隐喻含义。如:hot一词,其本义是“感觉热的”,通过隐喻影射产生了“辣的”、“热情的”、“兴奋的”、“热门的”等含义。人类在创造新的语义范畴的同时,也发展了其自身的隐喻思维能力。
Lakoff和Johnson所建立的概念隐喻理论强调人们的经验和认知能力在语义理解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经验主义的语义观。他们认为,隐喻可以通过人类的认知和推理将一个概念域系统地、对应地映射到另一个概念域。如 Love is a journey.这是英、美国家经常使用的一个隐喻,journey这个源域与 love这个目的域之间就存在实体对应的映射关系,也就是说,只要谈论爱情域中的概念,总可以在旅行域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成分。换句话说,人们总是能够通过旅行域的认识和经验来认识爱情域中的概念,如下例:
1.We’re at a crossroad.
2.We may have to go our separate ways.
3.The relationship isn’t going anywhere.
4.It’s been a long, bump road.
5.The relationship is on the rocks.
6.We are in a dead-end street.
7.Look how far we’ve come.
8.We’re spinning our wheels.
Lakoff认为这种隐喻模式也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模式,它是新的语言意义产生的根源。[3]Lakoff和Johnson的概念隐喻理论以具体概念为源域向其它认知域映射而获得抽象意义的认知方式揭示了人类思维和语言表达之间最本质的联系,他们特别强调认知主体(即人)在隐喻理解中的积极作用,认为它是隐喻理解不可缺少的因素。
三 隐喻是“明示-推理”的过程
Sperber和Wilson在关联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他们的隐喻观,他们将话语的命题形式(propositional form)和说话者思想(the thought of the speaker)之间的关系描述成隐喻过程,认为隐喻涉及到这两者之间的解释关系。[4]在多数情况下,命题形式类似于说话者的思想,但其它一些情况下并非如此,因为“交际的标准不是真实而是关联”[5]。Sperber和 Wilson认为,话语的命题形式和说话者思想之间的这种相似性的确认和理解的其它方面一样,也要受到关联原则的制约。按照关联理论的观点,关联才是交际中最基本的一条原则,因为关联是人类认知的基础,“人类的认知是以关联为取向的”[4]。他们认为,当且仅当一个假设在一定的语境中具有某一语境效果时,这个假设在这个语境中才具有关联性。“关联性”不仅取决于语境效果,还取决于处理话语时所付出的努力。在同等条件下,语境的效果越大,关联性就越强;为进行加工处理而付出的努力越小,关联性就越强。根据关联原则,每一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本身具有最佳关联性,即认为在正常交际中,听话者总是力图以付出最小的努力来获得最大的认知效果。Sperber和Wilson还在结合语码模式和推理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明示-推理(Ostensive-Inferential)的交际模式。他们认为,“明示”和“推理”是交际过程的两个方面。对说话人而言,交际是一个明示过程;而对听话人而言,交际又是一个推理过程。这个推理过程也就是听话人寻找话语和语境的最佳关联的过程。
Sperber和Wilson认为隐喻和反语等语言现象纯粹是语体学上的形象表达,属于“随意言谈”(loose talk),并不是说话人有意违反准则的表现。它们与普通的话语并无明显的分界,不是正常语言的偏离,也不是对规则的违反。关联理论认为隐喻属于一般话语,因而不需要特殊的解释能力和程序,它是言语交际中一般认知推理能力自然发展的结果。隐喻的含义也是通过寻找关联并根据一系列的语境假设推导出来的,只不过隐喻和话语的间接性有关,因此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关联理论对隐喻的阐释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1.关联理论将隐喻纳入话语现象来考察,强调用动态的明示-推理模式,在动态的语境中对隐喻进行动态的阐释,弥补了以往隐喻认知理论的不足;2.关联理论是在人类认知事物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理论,认为语言交际是一个认知过程,符合人类认知的“经济原则”(principle of economy),即交际双方总力图以最小的投入来获得最大的认知效果;3.关联理论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阐释隐喻,认为对隐喻的理解不需要特殊的程序和规则,它是人类认知能力自然发展的结果。但关联理论的隐喻观也存在着不足,如话语的“关联性”只是根据语境效果、心理投入或认知努力这两个因素去衡量,而这两者是无法进行量化的,因而无法指导具体的语言实践。此外,它强调人的认知主体的能动性的同时,忽视了人的知识结构的差异和听者的文化差异,而这两者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于隐喻的理解。但不管怎样,关联理论的隐喻观拓展了以往的隐喻理论,是隐喻理论的新发展,它使隐喻的研究步入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四 隐喻是一种述谓现象
隐喻是一种述谓现象(predication),其表达形式是句子,而不是一个孤零零的词语;隐喻是在作出一项陈述,而不仅仅是对一个实体的重命名。这样,Black就将隐喻从词语层次提升到了句子层次作为一种语义现象来考察,这一转变也将隐喻纳入了篇章的认知范畴。隐喻的语义观利用语义特征来阐释隐喻。该理论认为,隐喻违反了语义的“选择限制”(selection restriction),是一种语义异常现象(semantic anomaly)。如:The stone died.通过义素分析,发现stone具有以下语义特征:physical object;natural;non-living;mineral; Concreted. die具有如下语义特征:process with result, namely,that some living entity ceases to be living.[6]很显然,此句并不是直接可以理解,因为句中的stone是无生命事物,而die的主语要求是有生命的,因此“The stone died”便违反了语义的选择限制,由此可判断该句作隐喻解。隐喻的语义观对隐喻的理解涉及到词的语义特征从一个语义域到另一个语义域的映射,即将“次项”的语义特征影射(map onto)到“主项”上,从而产生隐喻含义。对“The stone died”的理解,就是将die的语义特征影射到stone上,从而赋予stone“living”的语义特征,由此推断出此句中的stone可能指个性强的某个人。在此理解过程中,人的思维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但Levinson认为这种理论也并不完备,表现在:1.语义特征的映射过程太有限太绝对,从而影响了隐喻的表达力;2.用于隐喻解读过程的喻体的语义特征比其它实际具有的语义特征要少,即人们总是根据具体的语境和交际场合从喻体中选择适当的语义特征来表达隐喻的即时含义。而至于为何选择此而非其它,语义理论便无法解释了;3.有些句子既可作字面意义解,也可作隐喻解,并不具备语义异常的条件,也没违反语义的“选择限制”,但在一定的情境中,我们仍能理解它的隐喻含义。如:Your defense is an impregnable castle.这里的defense既可按字面理解为具体的防御工事,也可隐喻性地理解为某人的地位很稳固,坚不可摧。
以上可见,语言中的隐喻现象是一种认知方式,是“用一种事情或经验理解和经历另一种事情或经验”[2]。隐喻是通过甲事物来理解和体验乙事物,人的概念系统就是通过隐喻建构起来的,即所谓“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本质上都是隐喻的”[2]。研究隐喻的本质不仅对语言教学有现实意义,对推动各学科协同发展、激发和形成新概念与新思路也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1]Richards,I.A.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M].London: Oxford UP,1964.
[2]Lakoff,G. & M.Johnson.Metaphor We Live By[M].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3]Lakoff,G.Women,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M].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4]Sperber,D.and D.Wilson.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86.
[5]Goatly,A.The Language of Metaphor[M].New York: Routledge,1997.
[6]Levinson,S.C.Pragmatic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责任编校:张京华)
H05
A
1673-2219(2012)09-0144-03
2012-07-27
2011年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课题(项目编号11WLH48)。
曹群英(1971-),女,湖南永兴人,湘南学院大学英语部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黄泽英(1974-),女,湖南永兴人,湘南学院大学英语部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翻译实践和认知语言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