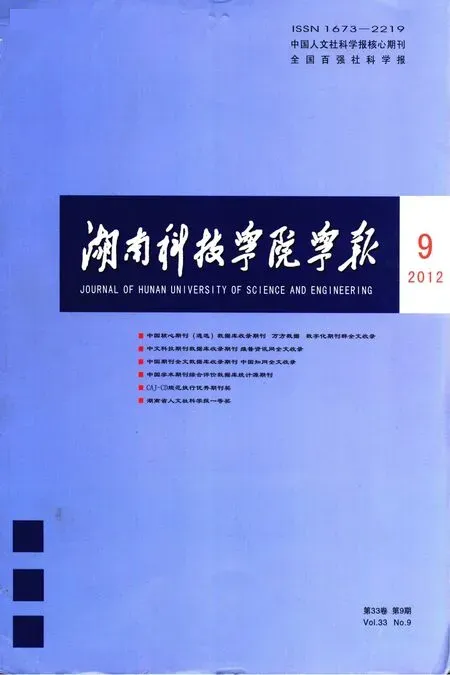互文视域下刘绶松的文学史创作
——《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与《中国新文学史稿》比较
景欣悦
(厦门大学 中文系,福建 厦门 361005)
互文视域下刘绶松的文学史创作
——《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与《中国新文学史稿》比较
景欣悦
(厦门大学 中文系,福建 厦门 361005)
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是建国以来较为重要的以现代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文学史著作。自其问世以来,曾于1956年和1979年两次被指定为高等学校的文科教材,对现代文学史教学以及学术研究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该文选取刘绶松的《初稿》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对比研究,探究特殊写作背景下刘绶松对新文学史创作的努力与尝试,在承认其创作局限性的基础上,尝试挖掘其在文学史的建构、体例结构的安排、史料运用以及文学评论等方面的价值与贡献。
刘绶松;文学史学;比较研究
20世纪中叶,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大学学科建设的需求,文学史的创作与编订呈现出一片繁荣,大量作品破土而出。以专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史作品,亦不 乏佳作,较为重要的有: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1951、1953);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第一卷(1955);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1955)和刘缓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1956)。其中尤以王瑶、刘绶松的文学史,影响巨大。王瑶创作于50年代初期的《史稿》更是被称为“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之作”[1],凭借其较强的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同时亦得到了较好的传承,由其弟子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便是对王瑶文学史观的继承与发展。与之相对,刘绶松的文学史创作及学术成就却鲜有专门论述,对其评价也往往局限于对历史话语的整体批判框架之内,缺乏对个案的具体分析,这无疑束缚了我们对于刘绶松文学史创作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基于此,本文在将在对刘绶松文学史创作客观评价的基础上,试图挖掘其作品中被历史记忆埋没的价值与贡献。然而“一个人不能基于自身而自我,只有在与某些对话者的关系中,我才是自我。”[2]同样,对于一部文学史而言,只有通过与之相关作品进行对比研究,才能够进一步接近作品内核,开拓研究视野,正如法国学者吕布奈尔所言“比较在比较文学中起着一种启发的作用”[3]。因此,本文将通过与同时期王瑶的《史稿》的彼此参照,解读刘绶松的新文学史创作。
一 创作的局限
《初稿》于1956年4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上下两卷,约55万字。这部鸿篇巨著的问世,无疑是刘绶松整个学术生涯中极具标志性的事件,同时也奠定了其新文学史家的地位。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这部作品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即鲜明的阶级立场与政治倾向。这种过分强调政治的意识形态性、用政治干预文艺、政治第一、文艺第二的文学史观,也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五十年代的文学史创作,导致该阶段的文学史著作具有普遍的历史局限性。通过对两部作品的研究,我们发现,无论是王瑶的《史稿》还是刘绶松的《初稿》均受到了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
(一)文学史研究的基本理论资源和理论范式的同质化倾向严重,理论缺乏创新性与包容性
如王瑶在《史稿》的绪论中便开宗明义地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路线也就规定了中国新文学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4]P6,“新文学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的指导思想当然是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思想”[4]P11;同样,刘绶松在《初稿》中更是具体地指出“1940年毛泽东同志的伟大论著《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和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使得我们整理和研究新文学的工作有了极其明确的指导思想”[5]P3。可见,唯物史观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两部作品共同的理论基础,而这种单调、统一的理论指导无疑束缚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势在必然。
(二)机械的“他律论”
文学史的建构与书写建立在政治话语之下,对于作家、作品的选择与评价基本依附于其所具有阶级立场与政治表达,思想性取代艺术性成为主要评判标准。两部作品中,两位作者无一例外地突出了社会政治背景对于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的影响,以1927-1937十年间的文学创作为例,在王瑶的《史稿》中,将该阶段称为“左联十年(1928-1937)”,而《初稿》中,将该阶段称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1927-1937)”,尽管具体称谓和分期略有差异,然而他们在体例安排方面却大同小异,均以大革命失败之后的“白色恐怖”这一社会背景为开端,进而谈及文学论争、左联的建立,从而确定了“鲁迅领导的方向”[4]P162。在这一过程中,文学创作与社会运动始终紧密结合,“社会决定论的泛滥,使得文学史大大地偏离其艺术的和审美的本质,同时在思想评价上也限于混乱”[6]P14。其间,现实主义创作、革命文学被赋予较高的评价,而重视艺术自律性的“新月派”和“现代派”则变成“两股逆流”,蒋光慈、茅盾、丁玲、张天翼等左翼作家被投以更多的关注,而沈从文等一批优秀的自由主义作家则无缘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舞台,严重背离了历史的客观实际。
(三)文学史作者主体性、主观创造力的缺失,文学史作品缺乏个性与活力
科林伍德认为“历史哲学是对历史思维的前提和含义的批判性探讨,是为发现历史思维在整个人类经验中的位置、它与其它经验形式的关系、它的起源以及有效性所作的一种尝试”[7]。因此,文学史创作不仅是一个努力还原文学本体及文学发展情境的过程,同时也是编著者对文学及其演变过程的再发现、再认识。而在五十年代的文学史创作中,我们很难看到个人观点、看法的表达,个性化的“我”的言说,逐渐转向了共名的“我们”的言说。此时,文学史作者的学术立场也与主流政治话语趋向一致,独立思考就此终结。
具体针对刘绶松的文学史创作而言,其特别之处何在?王瑶的《史稿》于1951年正式出版社,而《初稿》则成书于1956年,其间发生了批判《武训传》、批判胡适以及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等一系列文艺批判运动,而这些运动无疑对当时整个文艺界产生了及其巨大影响。可以说,到刘绶松创作《初稿》之时,政治对文学的干预与指导已经达到了顶峰状态。因此,相比于王瑶而言,《初稿》中所表达的阶级性和政治性更为强烈,因此文学史体例的设计以及文学作品的评价与选择也更加简单化,正如温儒敏所言:“《中国新文学史初稿》更加政治化,更能显现新文学发展作为阶级斗争历史的‘规律’,也更加富于战斗性、批判性与排他性”[8]。此时,鲜明的阶级立场与政治标签已经深入到刘绶松文学史创作的每个角落,从文学史观到编撰体例再到文学评论,甚至连行文语言都极具革命性和阶级斗争性。
二 独具特色的史学建构
我们认为,与同时期的其他文学史作品相比,《初稿》在史学构建方面具有遵循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史学体系统一完整、史料运用规范等特点,这无疑体现出刘绶松对于文学史学科建设的努力与尝试,亦成为其文学史创作中的价值与贡献。
谈及历史,便离不开“时间”意识的表达,在《初稿》中,刘绶松对于线性时间概念以及社会历史发展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这种重视充分体现在他的文学史分期上。
如前所述,无论是《史稿》还是《初稿》均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然而在具体的文学史分期上,他们又各自保持了自己的观点与立场。毛泽东在《 新民主主义论》中曾将新民主主义文化分为以下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的两年,第二个时期是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七的六年,第三个时期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的十年,第四个时期是一九三七年到现在的三年。”[9]而王瑶的《史稿》则将新文学的发展划分为另外“四个时期”:第一编“伟大的开始及发展”,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7年革命阵营分化,属于新文学的初创时期;第二编“左联十年”,从1928年土地革命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叙述以左翼文学为主流的整个新文学的发展;第三编“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1942年毛泽东发表“延安讲话”;第四编“文学的工农兵方向”,从1942 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到1949年全国首次文代会召开。通过对比可以看出,王瑶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得第一、第二个阶段合并起来构成其文学史的第一个分期,对此王瑶是这样解释的:“在‘五四’初期,还没有纯粹文艺性质的社团和期刊,许多主张都发表在《新青年》上,然而从总体看来,《新青年》到底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批判的刊物,它也注重文学,但是主要是为了反封建而攻击旧文艺,这正和为了反封建而攻击旧礼教一样;因此不可能有更多的力量和篇幅来照顾到文学,尤其是创作。所以在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的两年中,就文学史说,就不值得分为一个独立的时期”[4]P9。可见,王瑶《史稿》的历史分期主要侧重于文学自身的发展状况以及重大文艺事件(如“延安讲话)的发生。与之相对,刘绶松又是如何处理文学史的分期问题的呢?
刘绶松的文学史分期既不同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阐述,也不同于王瑶所秉持的观点。在《初稿》中,刘绶松将新文学的历史主要分为以下五个时期:1、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1917-1921);2、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1921-1927);3、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1927-1937);4、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1937-1945);5、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1945-1949)。通过分析与对比,可以发现,刘绶松的文学史分期完全与社会历史环境相一致,体现了他对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遵循与重视。在当时,文学史创作,往往为了突显《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地位和高度,从而将抗战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而《初稿》则严格按照革命史的分期来划分,将整个抗日战争作为一个统一的时期进行文学创作考察。
20世纪5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正处于初建时期,文学史的创作与编撰并无太多经验可循,因此,刘绶松完全以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作为文学史分期的依据也不失为一种大胆的尝试。尽管这种分期模式具有忽略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诟病,然而它极强的社会历史逻辑与一以贯之的唯物史观依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同王瑶的史学思维。这种历史思维不仅与当时的历史语境一拍即合,同时也与《初稿》所持的理论支持、史料基础、评判标准相契合,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相一致的史学框架。而在王瑶《史稿》中,则因其更强调文学自身的规律,破坏了理论与实践一致性、完整性。尽管,众多学者认为王瑶这种对于主流话语的背离更加体现出其独特的学术意义,然而由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脱节所造成的知识结构、评判标准的混乱无疑也是王瑶文学史创作不得不面对的一种缺憾。
除了对于历史发展的严格遵循外,《初稿》在历史体系建构方面的另一个特色便是史学体系的完整性。与王瑶的《史稿》不同,刘绶松在《初稿》中增加了一则附编,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简述。它不仅再一次呈现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分期以及新旧文学之间的本质差异,同时也追溯了新文学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文化渊源,让新文学的发生有源可寻,史学体系进一步趋向完整,学术视野得以扩展。
此外,史料使用的规范性也是刘绶松史学体系建构的突出特点。“史料是建构文学史的基础,而建构则是文学史研究主体行为的核心”[10]在《初稿》中,刘绶松对史料的处理多为原文引用,且尽量保持史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以解析曹禺的《雷雨》为例,作者为了弄清曹禺所表达的真实想法和初衷,连续引用了序言中的两大段自白,从而“引导我们对于《雷雨》一剧获得正确的理解与评价”[5]P382在王瑶的《史稿》中,对《雷雨》的解读则以评论为主,史料运用较少,且相关材料也多作为观点的论证工具而存在。在这个细节中,我们可以看出,刘绶松大量引用原文意在让读者主动进入研究和思考之中,而王瑶则凭借其出色的文学体悟能力对读者进行着“宣讲”。尽管受具体历史环境与个人文学悟性的制约与影响,刘绶松并不能对《雷雨》进行全面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在文学感性体悟上,亦不及王瑶,然而对于史料的重视与保留,无疑成为日后重要的学术资源,而运用史料的规范性操作也成为一种优秀的学术品质,流传下来。顾颉刚曾说:“然历史哲学家每以急于求得结论,不耐细心稽查,随手掇拾,成其体系,所言虽极绚华,而一旦依据之材料忽被历史科学家所推到,则其全部理论亦如空中之蜃楼,沙上之重楼,幻灭于倏忽之间。”[11]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对于具体文学作品的体会与理解或许有所改变,然而史料的保存和应用却依然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重要保障。
文学史写作不同于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研究,它应该具有鲜明的史学个性。因此如何完成统一、完整、独具特色的史学体系建构便成为衡量一部文学史作品优秀与否的重要标准。本文认为,刘绶松在史学构建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努力与尝试,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史学体系,史料运用合理、规范,理论指导与具体分析互相统一,史学逻辑清晰、明确。近年来,随着文学史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各种观点、理念、操作方法一股脑地涌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之中,因此很多文学史编著者便努力试图寻求构建文学史的最佳途径,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往往顾此失彼,前后矛盾,造成逻辑体系的混乱,而刘绶松所具有的完整、清晰的史学模式显然也将为当今的文学史创作提供一些启示。
三 全面理性的文学评价体系
“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领域,自然具有独立的发展的‘内在机制’”,[6]P15此外,学者苏永延也认为“力求客观公正地揭示文学发展规律的历史性原则、注重文学自身发展的本体性原则、注重文学史家主观能动性的主体性原则,三者的有机结合,构建了文学史的三维范式”。[12]可见,注重文学自身发展的本体性原则同样是衡量一部文学成功与否的标准之一,而这往往体现在文学史编著者对作家、作品的选择与评价上。由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原因,创作于50年代的文学史作品,显然不能脱离政治意识形态对其的制约与束缚,但这些优秀的新文学史家却并没有停止努力,而是进行了一场“带着脚镣的舞蹈”,与王瑶重视文学的内在结构和审美特征相呼应,刘绶松对于文学评论方面的贡献突出体现在其建立了全面、理性的文学评论体系上。
在《初稿》中,刘绶松一开篇便提出了新文学的概念:“我们所说的新文学,实质上就是指的那种符合于中国人民的革命利益、反帝反封建、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而且是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不断地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前进的文学。”[5]P9特定的政治立场决定了文学史叙事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决定了对于其中文学作品的基本态度。于是,该作品是否能够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继续前进”便成为评判作品优劣的重要准则。刘绶松的新文学史无形中也变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史,就连作者自己也后记中写道:“把它印出来的意思,仅仅是想给读者提供一点了解我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的参考资料”。[5]P725刘绶松文学评价的标准,随之产生。同时也正是源于其较为固定的评判立场,促使刘绶松的文学评价体系呈现出全面、理性的特点。
刘绶松在进行具体的文学批评之时,既有宏观的总体概括,又有微观的细节阐释,宏观评价与微观分析巧妙结合。由于自身所持文学观念的原因,刘绶松对于文学作品的评价往往是既有认可,也有否定,从而为读者呈现出较为全面的评论模式。例如,刘绶松在解读《雷雨》之时,既对作品做出了肯定的评价,认为“这个剧本相当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生活中的某些重要的真实的东西,而且以此教育了它的观众和读者”[5]P382,同时否定了其中的“神秘主义”,认为这种“宿命论”的气息将会“限制作品对于现实挖掘和反映的深度”[5]P383。可见,刘绶松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指导下,对于作品的点评并非简单分类,而是进行全面的总结,对于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创作予以认可,同时对于阻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因素给予批判。而王瑶在解读《雷雨》之时,则仅仅侧重于文学审美层次的评析,对其中确实存在的“神秘主义”却避而不谈。“神秘主义”本身优劣好坏,暂不判断,然而只有深入全面地挖掘作品中确实存在的文化主题,才是对于作品本身及其自律性的关注与尊重。这样的例子,同样体现在对老舍《猫城记》的评论上。老舍无疑活跃于二三十年代的重要作家之一,无论是《史稿》还是《初稿》都所有涉及,笔者选取两部作品对老舍《猫城记》的评价,尝试阐释王、刘二人不同的文学评论手法。在《初稿》中,刘绶松是这样评价《猫城记》的:“他(老舍)早期个别作品,由于当时反动宣传的影响和他自己的误解,具有严重政治错误。”[5]P362而在王瑶笔下:“《猫城记》中作者有意地向讽刺文学发展,猫城自然是象征古老的中国,代表了他对现实的不满与愤恨。但以幽默代替了讽刺,感慨代替了表现,力量就差得多;这样的作品需要更多的分析社会的能力,作者于此并不擅长,结果自然就失败了。”[4]P281同样是对《猫城记》的评价,刘绶松则通过“政治错误”的定性对老舍在《猫城记》中政治寓言给予了一种特定形式的批判,而侧重文学审美的王瑶则用“作者于此并不擅长”进行了巧妙的回避。通过以上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刘绶松受到阶级论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的束缚,然而其对于作品评价却相反得以全面和深入的展开。此时的王瑶,却往往因为既要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要求,又尝试挖掘文学审美内涵,从而对一些敏感话题避而不谈,这无疑是不利于对文学作品的全面认识和了解的。
除了解析的全面性,刘绶松在文学批评方面的价值还充分体现在其独特的理性批判上。以两部作品对巴金《家》的不同解读为例,王瑶在《史稿》中对《家》的解读更侧重于人物的心理分析,如认为觉新“是一个被旧制度熏陶而失去反抗精神的青年,内心却依然能够分清是非和爱恨的界限,因此精神上就更加痛苦了”[4]P265。可见,王瑶对人物的评价与解读往往源自文本本身的审美体验和情绪表达,而并没有站在任何立场进行道德评价或理性评判。与之相对,刘绶松则在《初稿》中从固有的阶级立场出发,对人物进行理性的评判,进而认为巴金在创造觉新这个人物形象的过程中,“倾注了过多的怜惜和温情,而没有对他的阶级本质进行严格的披露与批判”[5]P361。两部作品对于觉新这个人物的解读究竟孰优孰劣,本文不去暂不评论,但刘绶松所做的评价无疑是与其理论支持紧密相连的,是理性的。而王瑶的评价则于其开篇定义的理论范式并不相符,更多属于感性体验。尽管,刘绶松所持有的这种理性观念在当今看来具有十足的历史局限性,然而在当时却不失为一种较为先进的理性思考模式。
综上所述,刘绶松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中所创造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既具有相当的历史局限性,同时也有颇具的价值和意义,对中国新文学史创作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记录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建设之初摸索的轨迹,同时也为日后文学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1]温儒敏.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J].文学评论,2003,(1).
[2][加]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上海:译林出版社,2001.
[3][法]布吕奈尔.什么是比较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4]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5]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6]陶东风.文学史哲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7]科林伍德.历史哲学的胜质和目的[A].张文杰.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8]温儒敏.文学史的视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9]毛泽东.新民主主义[A].论毛泽东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10]董乃斌.文学史学的创建和文艺学的离合[J].上海: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
[11]谢泳.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社, 2010.
[12]苏永延.构建文学史的三维范式——关于20世纪文学史撰写的断想[J].海口: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1).
(责任编校:王晚霞)
I207
A
1673-2219(2012)09-0055-04
2012-05-15
景欣悦(1987-),女,河北秦皇岛人,厦门大学201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