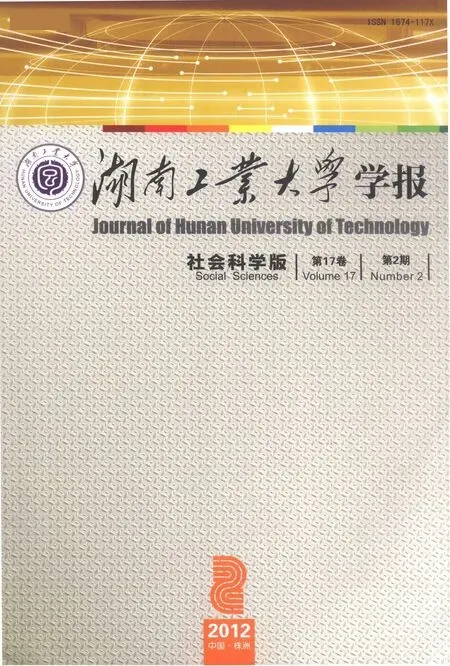真实与间离
——《追忆似水年华》内在性研究*
韩扬文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昆明650091)
真实与间离
——《追忆似水年华》内在性研究*
韩扬文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昆明650091)
马塞尔·普鲁斯特的意识流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从充满主体色彩的回忆出发,重新建构了一个与现实世界呈现明显间离色彩的“马塞尔的世界”。在后者的世界中,叙述者却再三申明自己所表现的乃是真实的生活本质。这种从内在出发,对生活本质所进行的重估,宣示了意识流小说作为一种新的小说体式对于唯一、超验之“理式”的反叛。这一反叛绝不仅是马塞尔梦幻般的私语,更体现了整个时代的精神诉求。
《追忆似水年华》;理式;内在性;心理时间;私语
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作家凭借对于“时间”的反思与重构,建立起了一个极具个人色彩的新世界。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音节,任何一种气味,都无疑被贴上了叙述者马塞尔的标签。换言之,这个世界是与他人相间离的,独具内在性的实存,它似乎仅仅属于一个敏感的、过于神经质的、才华横溢的、羸弱而不甘于轻易赴死的叙述者。然而,作家又一再重申,他所表现的乃是最为真实的现实本身。这种真实的现实何以与日常生活具有如此之大的间离性,这种最为真实的现实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它究竟是作家的一厢情愿或者是时代之所共求者?弄清以上这些问题,会使我们对于意识流小说,甚至对于现代主义思潮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一 被背叛的“理式”
“理式”是西方美学中最为重要和古老的范畴之一。对它最为著名的讨论是在柏拉图那里,但这个词的词源在古希腊早已有之。
根据赵宪章等的考据,理式“这个词在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那里已被作为‘种’、‘属’的意义在使用。但对这个概念从哲学上加以思考和分析,则是从苏格拉底开始。”[1]58而作为柏拉图美学的核心概念,“理式”也就是“美本身”,他所说的理式乃是唯一的、超验的、绝对的,是艺术作品永恒的不二来源。艺术作品通过对于现实的“摹仿”来接近“理式”,但它毕竟与“理式”隔了两层,艺术家之所为只是对于“理式”的拙劣摹仿而已,它是个别的,外在的;它学习“理式”,而不减弱“理式”的光辉,因此艺术作品在柏拉图看来并不具有内在性,艺术家也就只相当于“匠人”而已。
当然,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柏拉图“理式”说的困难,诚如罗素所言:“理念(理式)是超时间性的,是不能被创造出来的。而当神决定创造那张柏拉图式的理念的实在的床的时候,他头脑中肯定有那张床作为摹本。否则,这种创造是不可能的。”[2]
这也就是说,诚然“理式”说推翻了人的内在性,而将这种内在性赋予与人异质的、外在的神;但是柏拉图却不能够告诉我们,神的头脑中那个“床”的摹本是从何而来的。既然“理式”是超越时间的,“床”的本源就不能在时间当中去寻找。但它不在时间中,又在哪里呢?
在这里,理式是与现实世界、物质生产、感性生活相异质的,前者高尚而后者卑下。作为卑下者而又卑下者,作家不得不参照着卑下的现实不断向着崇高的理式攀登。而问题在于,理式似有莫须有之顶峰,是艺术家永生不能企及的。既然永远不能到达理式,那么追寻“无何有之乡”中的真善美又是否真的具有意义呢?
到了中世纪,在经院哲学的反复讨论中,人的内在性问题受到关注。奥古斯丁皈依基督教以后,引进了“自由意志”的概念来解释人何以会有善恶的问题。他认为,人的善恶是经其自由意志进行选择的,这也就使人的内在性具有了合理合法的地位。在此之后,以笛卡尔“我思”为起点开始的西方近代哲学中,人的主体性地位更是得到前所未有的瞩目,缺乏内在性的“理式”范畴得到矫正。诚然,笛卡尔将意识作为实体的哲学受到了康德、胡塞尔等人的批判,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笛卡尔以后,超验的、独立于人的“理式”所受到的质疑的确使得“理式”说深陷困境之中。
19世纪末以降,受到资本主义社会频繁变革的重大冲击,西方传统文化更是无所适从。“人的自信和尊严濒临危机,现实呈现出‘绝对理念的式微与衰落’,造成文化心理上的失衡与无归宿状态。”[3]1在这种状态中,“理式”作为西方古典文学风格的基础,在现代主义的大潮中遭到反抗。此时,作家纷纷在作品中凸显自我、否定传统,批判虚妄的绝对理念,希图在充满内在性的主体话语中重构真实的世界。这个世界乃是否定的世界,是超越理性的世界,是理想主义高扬的世界,是一个属于绝对私人却绝对真实的意识世界。
在这个充满内在性的世界中,“丑”作为一个重要的颠覆性范畴被重新提出。正如阿尔多诺在其《美学理论》中所指出的那样:“现代社会已进入全面异化的时代,虽然‘文化工业’竭力弥合社会的断层和裂隙,用‘幸福意识’消除矛盾,制造出虚幻的整体形象,但是,事实上社会结构已陷入更深、更严重地分裂状态之中……与‘文化工业’消解和掩盖矛盾的社会控制性手段相对立,艺术必须揭示人类真实的生存状况,展现心灵和主体、主体和自然相分离所造成的矛盾、焦灼和绝望的人类经验。很显然,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艺术欲重新成为批判性思考的武器,必须在表现新的经验内容的同时,破除以和谐和美为目标的形式创造法则,把不完满、不和谐的‘丑’引入形式律中。”[1]358
不仅是“丑”的范畴应当被重新提出,“真”、“时间”、“世界”等问题也应当在新的社会背景中得到重估。我们所见的世界就是真实的世界吗?我们的回忆可靠吗?时间真的是一维的、具有确定性的吗?现代社会作为一个巨大的整体幻象,“文化工业”声嘶力竭制造的巨大谎言,要求我们进行反思。然而,我们要以理智进行反思,还是依靠直觉呢?理性的世界果然就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吗?
在普氏的《追忆似水年华》中,叙述者就用诗化的语言回答了这些哲学问题。他不仅仅是一个离群索居的私语者,更是一个从深层思考社会问题的入世者,这就是小说基于内在而超越内在的真正意义。
二 重审时间
《追忆似水年华》(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按其法文直译,应当是《失而复得的时间》。在这部小说中,叙述者从有如神助的精妙回忆中勾连起过去与现在,在“绝世养料”的激发下唤回了完整而精确的瞬间。这种被唤醒的瞬间与依靠理智回想起的瞬间截然不同,因为后者总是经过理智的加工、臧否而变得面目全非。叙述者认为,真正的时间是永恒的,它使人忘却死亡的忧患,它就隐匿在那个充满绝望的、以理性自居的世俗时间背后,而只有真正的时间才属艺术应当表现的范围。
毫无疑问,普鲁斯特重审时间的哲学起点乃是其业师柏格森有关“两个时间”(空间时间与心理时间)的区分:“前者用固定的空间概念来说明时间,把时间看成是各个时刻依次延伸的、表现宽度的数量概念;后者则是各个时刻相互渗透的、表现强度的质量概念。”[4]
当我们用钟表的数量刻度、用理智对时间进行衡量时,时间被人为地分化为一个一个断点,我们无法解释在这一秒和下一秒中间的那些空隙是什么。空间时间就像电影中一帧一帧的画面一样,它看起来是连续的,固定的,但其中所包蕴的多种可能性却实在都是内隐的。空间时间只能展示如“我在吃饭”这样模式化的、社会化的行为,至于某一食物引领我回到某一个遥远的年代,某种气味使我想起某个人这样精微的、具有强度的“心灵事件”,某个连续不断、如潮暗涌的意识活动却是空间时间无法触及的。能够达到这种使时间“相互渗透、表现强度”的质量形式就只有柏格森所说的“心理时间”,这也就是普氏在小说中重新审定的时间。
这种以作家的主体活动为凭据,精心剪裁的“心理时间”至少具有以下特征:
(一)内在真实性
在其著名的联觉回忆实例——“小玛德莱娜点心”事件中,叙述者马塞尔展示了他重构时间的功力及方法。当然,这种重构时间的活动纯粹是偶然的,不是用某种有步骤的实验方法可以达到的;但在这种美好的偶然中,叙述者进入了有似迷幻的审美境界,这个迷狂的境界与诗人兰波的通灵时刻一样,挖掘出了心灵的深度与力量:“带着点心渣的那一勺茶碰到我的上腭,顿时使我浑身一震,我注意到我身上发生了非同小可的变化。一种舒坦的快感传遍全身,我感到超尘脱俗,却不知出自何因。我只觉得人生一世,荣辱得失都清淡如水,背时遭劫亦无甚大碍,所谓人生短促,不过是一时幻觉;那情形好比恋爱发生的作用,它以一种可贵的精神充实了我。”[5]28
在这种如梦如幻的体验中,在家里喝茶时所吃到的扇贝形点心勾连起了叙述者某个清晨,在贡布雷莱奥尼姨妈家里用茶点的回忆,继而贡布雷市镇上的灰色小楼、街道、广场、小时候所玩的游戏、已经消逝的人群、斯万的花园、村民、教堂等一切早已被空间时间宣判死亡的事物“全部显出形迹,并且逼真而实在,大街小巷和花园都从我的茶杯中脱颖而出。”
以小玛德莱娜点心和茶水为桥梁所唤醒的时间,就是被重构的心理时间。这个时间的真实性除了叙述者以外,无人能够证明,因此,叙述者说:“茶味唤醒了我心中的真实”,“只有我的心才能发现事实真相”。换言之,心理时间中的真实是内在的真实,它不必努力向社会话语或工业文明求证自身的存在。这种真实是自足的,甚至不需要向任何神祇证明,它只用语言戏仿这一被巨大的真实性所包围的心理时间便已足够;它只显现世界如此,而不必求证。因为直觉的力量早已经战胜了理智,这一刻,直觉可以向世界宣告:“我获得了真相,我获得了事实,但是你们只可观看,而永远无法明白。”
心理时间的内在真实性向读者宣示:世界可以通过人自身具有的充沛内在性被重新进入,时间也可以被重新裁夺,以直觉而不以智识。
(二)时距的跳跃性
在这部被称为“普鲁斯特个人回忆录式的小说”中,我们有时实在很难区分写作者马塞尔与叙述者马塞尔,因为作家在小说中既展示了自己内心真实的意识流动,又虚拟了一个敏感的异性恋者形象。随着叙事的展开,叙述者马塞尔渐渐长大了,他参加沙龙、恋爱、思考、见证死亡。这其中,时间也被不同程度地缩短和拉长了;而这种时距的变化与其说是小说家的炫技,毋宁说是一种象征。
在小说中确有叙事速度的双向变化:“一是变快,故事时间长而文本时间短”,“二是变慢,就是用较长的文字来叙述很短时间里发生的故事。”[6]但更为重要的是,叙述者叙事时距的变化隐含了作家的某种价值评判取向。
在心理时间的处理上,普鲁斯特有意将时距变慢,而且在同一事件上多次重复讲述,使所叙之事更具冲击效果。如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中反复写道的“母亲的吻”,少年马塞尔等待被母亲亲吻的忧郁心境,甚至是察言观色的一个微妙眼神都在心理时间中重整旗鼓,扑面而来:“即违心上楼,我的心不禁返回母亲身边,因为她还没有吻我,我的心没有得到她发的许可证,不肯跟我回房。这可恶的楼梯,我一踏上它,总是百般惆怅,它散发的清漆味儿可以说吸收了、凝聚了我每晚所感受到的那种特殊的郁闷……”[7]78
这种被无限拉长而变慢的时距,内含着叙述者对于借由心理时间的重组而得来的人生片段的无限珍惜。被叙述者反复拉长的时距体现了叙述者意识流动的精微过程,惟其不急于展示生活之全貌,生活与社会的复杂牵连,才将生活带向了片刻内在的真实。就像叙述者自己所说的那样:“需要表现的现实并非寓于主体的表象,而寓于与表象无关的深层,正如调羹碰击盘子的声响和上了浆的餐巾的硬绷所象征的那样,这些对于重振我的精神比人道主义的、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形而上的谈话更为珍贵。”[7]279
叙述者的这番识见与德国现代学者尼古拉斯·鲁曼在《艺术的功能与艺术系统的分化》中所言及的艺术功能论不谋而合:“艺术的功能是,使世界出现在世界之内,同时关注以下矛盾状况:每一次某物的观察有效时,另一物就隐退。换言之,世界上的区分和指示活动总是隐匿这个世界。毫无疑问,对完整性的追求或把自身限于本质都是荒谬的。但是艺术品能够象征世界重新进入世界,因为它看似——就像这个世界——不能修正。”[8]
的确,在现代艺术中,指向完美、整一、和谐的柏拉图式追求意义甚微,叙述者马塞尔有意延长的叙述步速,有意关注的内在世界、意识流动就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小说中当然也有疾速变快的时距,而这种处理方式多是在讲述空间时间的进程上。在平稳的叙述中,陡然加快的时距给人一种极大的紧迫感:“他(指夏吕斯男爵)在回忆他们的去世时看来更加意识到自己在恢复健康。他以一种几乎是凯旋而归的冷酷无情,用微微结巴,带有坟墓般的沉闷回声的千篇一律的声音重复道:‘汉尼拔·德·布雷奥代,死了!安托万·德·穆西死了!夏尔·斯万,死了……’”[9]一系列被例举的死亡事件所发生的故事时间有数年之久,但文本时间就只有两三行。
叙述者为何在空间时间的剪裁上,多次使用这种加快时距的方式呢?这就体匿着作者对于空间时间的针砭。与寻常的世俗认识不同,普鲁斯特并不以空间时间为生命进行的依据,他既可以在心理时间中得到无限的延展,也可以视空间时间为无物。
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时距不仅可以缩短、延长,而且可以随着回忆的穿越肆意跳跃,也就是说,小说中的时距可以在平稳叙述时突然变快或变慢。如夏吕斯男爵对于死亡事件的回忆就是在时距减慢的心理时间的描述过程中突然加快,转为空间时间的铺陈。
而保持外在的时距不变,叙述者还能够从文本时间内部穿越故事时间,将现在与未来的某一时刻相串联。如斯万以自己的爱情经历告诫马塞尔的一段:“斯万在这片刻的不快并擦拭镜片之后,对思想进行补充,而在我后来的回忆中,这番话仿佛是预先警告,只是我当时毫无察觉罢了。他说:‘然而,这种爱情的危险在于:女人的屈服可以暂时缓和男人的嫉妒,但同时也使这种嫉妒更为苛刻。男人甚至会使情妇像囚犯一样生活;无论白天黑夜都在灯光监视之下以防逃跑。而且这往往以悲剧告终。’”[5]317这段话后来直接成为第5部和第6部的标题援引,在《女囚》和《女逃亡者》两章中,斯万的话有似预言,勾连起斯万与奥黛特、马塞尔与阿尔贝蒂娜两代人的情感纠葛。这段话虽则篇幅很短,文本时间非常有限,但其内含的故事时间与画面则非常丰富,可以说对于叙述者马塞尔具有开辟鸿蒙之作用。
(三)超越有限的终极诉求
无论对于作家马塞尔还是对于叙述者马塞尔而言,死亡都如千钧压顶一般,时时悬临在生命上空,不时提醒着生的有限性。而对于死亡的巨大倾轧,叙述者马塞尔虽理智上万般不情愿地选择了“逆来顺受”,但在根本上,却还是难以解脱有可能死的苦难。叙述者一再回忆死神摩挲众人之时的痉挛可怖,持续观察着每一分每一秒众人的细微变化,已经流走的时间、年月使叙述者感到无比“困乏和恐惧”。
正是基于超越人生有限性的强烈诉求,马塞尔企图打破空间时间,重建心理时间。心理时间在叙述者的眼中深度无限,可以不断去填满;并且质量无限,可以施加无限之重压。这些凭借着气味、声响、触感等灵媒被保存下来的真实的、无间断的心理时间,无疑带有着超越生死的可能性。正像凯尔特人的巫术一样,一旦这些灵媒被以后的某人所偶然遇见,被拘禁的已死的灵魂便可以就此重生。叙述者对于超越死亡的愿望如此强烈,因此他所重建的心理时间中就自然地带有超越有限性的终极目的。
他将原先既定的空间时间概念有意抽象化了,而“普鲁斯特的抽象化的基点就是他对内在性的依赖,这对于他不仅是一种替代、一种分解、一种类似蜃景的神秘力量……这种不自觉的回忆使马塞尔能再次进入他生活中已经失去的乐园。”[3]409
回到过去对于叙述者来说之所以是重要的,正是因为通过心理时间所复现的过去,象征着最为鲜明的生的历程。某一朵山茶花馥郁的香气,某一辆马车经过的响声,都是不可怀疑的生之真实。相对于未来而言,过去总是距离死亡较为遥远的那一刻,因此其中有相,其中有精,其中有真。
三 面向世界的私语
由于慢性哮喘病的折磨,普鲁斯特年纪轻轻就不得不放弃一部分与外界接触的时间闭门谢客,将息养病;35岁以后的15年,随着病症的日益严重,他更是将自己关闭在一门窗紧闭、遮掩着厚帘子的黑暗屋子里,以阻隔外界的空气引发他体内的病菌的蔓延。正如他在《致安德烈·纪德的信》中所自称的那样:“离群索居的我除了在想象中和真理面前外,习惯总是过分地淡于世事。”[10]
即使是在普鲁斯特因病淡出上层社会交际之前,天生的敏感性格也常常使他在很多时候侧重向内追问世界的真实性,而不愿意将沙龙所论之事作为人生根本。
在关于沙龙、时事的叙述中,普鲁斯特所采用的多是正常的步速,故事时间的长短与文本时间的长短基本上是一致的。然而,在关于马塞尔的意识世界、情感世界的描述中,作家有意把叙述时距放慢,尤其在对于细致的感受、旧时景物的细节、朦胧的情感印象和一些行将消逝的人事,作家不惜重墨,反复地、多角度地讲述。他的恋人阿尔贝蒂娜神秘而叛逆,有时是个纯真的少女,有时是个极具诱惑力的情妇,有时是一个被叙述者囚禁的囚徒,有时是个女同性恋,有时是个女逃亡者,而有时则作为一个已经亡故的旧友走进回忆之中。更不用说关于外祖母之死、母亲的吻、小玛德莱娜点心的回忆,几乎成为叙述者一生回味的记忆片段,被再三诉说、重写。
这就足以证明,作家在《追忆似水年华》中着力展现的并非是如同《人间喜剧》一般的社会面貌,而是要讲述由个体心灵建构起来的内在世界。这个内在世界既与外在世界(自然、社会、他人)所融通,又时时警觉,怵惕外在世界可能对其进行的异化。普鲁斯特所重视的并不是外在世界能够对他提供多少五彩斑斓的事件、信息,而是如何从内在对其进行领悟与重组。正如安德烈·莫罗亚在《追忆似水年华序》中之所言:“他(普鲁斯特)更感兴趣的不是观察行动本身,而是某种观察任何行动的方式。从而他像同时代的几位哲学家一样,实现了一场‘逆向的哥白尼式革命’。”[11]
普鲁斯特受到亨利·柏格森的启发,所要寻找的乃是充满个性化的、不可复制的、一去无返的内在真实之世界。柏格森曾说:“艺术总是指个性的艺术……诗人歌颂的心情,是他自己的心情,只是他才有的心情,而且这种心情也是一去不复返的。”[12]这种艺术追求与古希腊摹仿理式的、向着真善美而生的艺术诉求截然不同。如果说,早先的“理式”追求的乃是肯定,那么意识流小说乃至现代主义追求的便是否定。它们拒绝向偶像低头,拒绝摹仿,也拒绝工业文明的异化。他们自珍自重,惟其充盈的内在体悟马首是瞻。他们相信艺术天才判断、觉知、重构世界的能力,因此在对于外在世界的问题上,他们审慎而又傲慢,开放而又封闭。他们当然相信外在世界的存在,然而关于外在世界只有某种特定的、被社会话语所规定的面貌这一点他们是相当怀疑的。
在艺术中,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无价值的,普鲁斯特以对个体精神状态的集中展现回答了这一点。外在世界如何显现出是其所是的样子,问题在于作家自身的着力点放在何处。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一杯茶点带给我们的回忆中时,此刻外界交加的风雨又有何意义?当这一朵花展现在我们面前时,千万朵花就隐退,这就是视角,这就是光辉的内在性。
类似的问题,与普鲁斯特同属意识流小说家的伍尔夫也这样论述过:“向深处看去,生活绝不是‘这个样子’。细察一个平常人在平常日子里一瞬间的情况吧。在那一瞬间,头脑接受着数不清的印象——有的琐细,有的离奇,有的飘逸,有的则像利刃刻下似的那样明晰……因此,如果作家是一个自由人而不是一个奴隶,如果他能够以自己的亲身感受而不是传统章法作为自己作品的基础,那么,就不必非有什么情节、戏剧性、悲剧性、爱情事件以及符合公认格式的灾难性结局不可……生活是一轮光圈,一只半透明的外壳,我们的意识自始至终被它包围着。对于这种多变的、难以界说的内在精神,无论它表现得多么脱离常规、错综复杂,总要尽可能不夹杂任何外来异物,将它表现出来——这岂不是一位小说家的任务吗?”[13]
可见,与传统小说家戏仿或摹仿世界不同,意识流小说家从内在重新建构世界;这个世界诚然是陌生化的、滞缓或扭曲的,但它的内在必被指认为真实。无论是《尤利西斯》、《墙上的斑点》还是《追忆似水年华》,小说家向我们展示的乃是生活最深处的犹疑、恐慌、疏离与最隐秘的念想。因为我们知道,生活不是彻底喜剧或悲剧的,也不一定时时有突转,不一定处处需要我们净化和陶冶自己。隐藏在这些理念背后的生活,乃是一些意识的流动,一些拒绝与社会、他人同化的直觉,而这些意识或直觉就是艺术绚烂、生活多元的根柢。
普鲁斯特之所以排斥“一般化”的倾向,排斥权力话语的介入,正是因为他坚信对于生活底蕴的主体性重构能够使他得到自由。在《驳圣伯夫》中,他这样说道:“我们所做的,是追究生活的底蕴,是全力以赴打破习惯的坚冰推理的坚冰,因为习惯和推理一旦形成立即凝固在现实上,使我们永远看不见现实;我们所做的,是重新发现自由的海洋。”[7]322在他身上所朗耀的内在性的光辉,直接指向真实、自由和不因权力而消逝的永恒。
当然,在普鲁斯特身后的世界中,“个体的独特表达”又受到了新的阻力。当代作家米兰·昆德拉在其文论《被背叛的遗嘱》中写道:“我看了新起草的有关著作权的法律:作家、作曲家、画家、诗人、小说家的问题在里头占的比重微乎其微,绝大部分的条款涉及所谓视听制品的大工业。毋庸置疑,这一巨大的工业要求有全新的游戏规则。”[14]而他所指的游戏规则不是个人的私语,而是众人的狂欢。集体衡定道德标准,集体限制作者权利的时代已经到来。正如一部电影所展示的,并非导演或者演员之个体,而是经过整个团队共同商定的价值标准。
在这个时代中,普鲁斯特式的面向世界的私语更加显得珍贵,他以沉重而坚实的内在性提示后人:我们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静观世界,言说世界。我们所说的,乃是内心的最高的真实,这种真实不因差异性而被指斥为虚假,也不因空间时间的消逝而消逝在心理时间之中。心理时间绵延无断,从其深度上宣告自身的永恒。
[1]赵宪章,张辉,王雄.西方形式美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罗素.西方哲学史[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34.
[3]弗雷德里克·R·卡尔.现代与现代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袁可嘉.外国现代派作品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23.
[5]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上)[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6]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55.
[7]马塞尔·普鲁斯特.普鲁斯特美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8]于尔根·哈贝马斯,马泰·卡林内斯特,汉斯·罗伯特·尧斯,等.文化现代性精粹读本[M].周宪,钦文,罗国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88.
[9]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下)[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1705.
[10]普鲁斯特致安德烈·纪德的信[J].袁莉,译.当代外国文学,1995(5):140-141.
[11]安德烈·莫罗亚.追忆似水年华序[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1.
[12]麦·莱德尔.现代美学文论选[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173.
[13]弗吉尼亚·伍尔夫.书和画像[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89-91.
[14]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285.
Verity and Alienation——The Internality Research of In Search of Lost Time
HAN Yangwen
(School of Humanity,Yunnan University,Kunming,650091 China)
In Search of Lost Time is a source work of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novel which written by Marcel Proust.Starting from the personal memory,the writer reconstructs an alienated“Marcel’s World”.however,the novelist insists that the alienated world reflects the essence of life.The way of internality and the revaluation of life’s essence betray the only one conception idea.This phenomenon not only indicates Marcel’s personal tendency,but also reflects spiritual needs of the whole era.
In Search of Lost Time;idea;internality;psychological time;whisper
I565.074
A
1674-117X(2012)02-0118-06
10.3969/j.issn.1674-117X.2012.02.024
2011-12-07
韩扬文(1988-),女,浙江嘉兴人,云南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
责任编辑:骆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