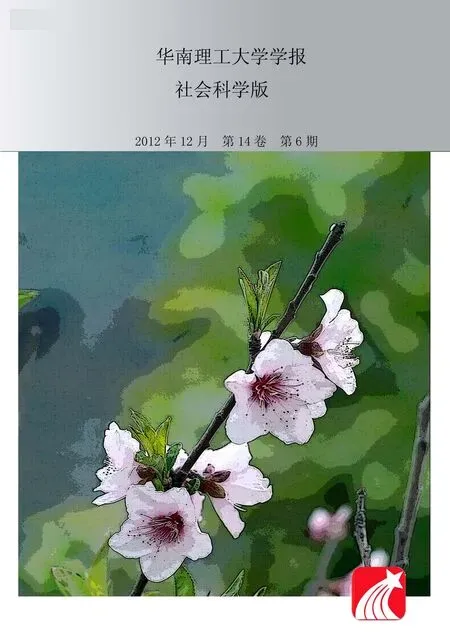生态殖民主义与生态殖民文学
罗世平
(华南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1)
通过阅读相关的文学作品,笔者发现: 在西方殖民扩张时期,欧洲疾病、动物和植物随欧洲殖民者流散到新欧洲,破坏了当地原有的生态系统,引起当地生态环境严重恶化,造成当地人口急剧下降,带给殖民地本土人重大灾难,在欧洲殖民者征服殖民地本土人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在时下(后)殖民文学研究中,欧洲疾病、动物、植物在西方殖民扩张中所产生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包括赛义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后殖民理论奠基人在内的后殖民理论专家和学者大都在系列人类文化命题中运思西方殖民主义经验,侧重于生命有机体中人类因素的作用,忽视文学作品描写的生命有机体中微寄生物病原体、动物、植物等非人类因素在西方殖民扩张中的重要作用。为此,本文通过相关文学文本透视其中的生态殖民主义,深入考察微寄生物病原体、动物和植物三个主要的生命有机体在西方殖民扩张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引起国内学者对生态殖民主义的关注。
在展开论述之前,须对本文中的“生态系统”、“生态殖民主义”和“生态殖民文学”三个重要概念做出明确界定。在本文中,“生态系统”主要指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具有特定功能的生命有机体或生物群落(如人类、微生物、动物、植物等)及其赖以生存的非生物环境(如土壤、岩石、阳光、空气、水分等)构成的系统。*“生态系统”(ecosystem)这一概念由英国人泰勒于1935年首次提出,主要指生命有机体或占主导地位的生物群落及非生物环境组成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具有特定功能的综合体; 或言之,生态系统是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非生物之间,通过不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而相互作用、相互依存所形成的一个生态学功能单位,可用公式表示为: 生态系统=非生物环境+生物群落。(来源: 阳含熙、李飞《生态系统浅说》,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页; 李振基等《生态学》,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67页)生态系统中相辅相成的生命有机体或生物群落构成环环相扣的食物链,这些食物链又纵横交织、紧密结合成复杂的食物网,维持着某一特定区域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食物链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变化都必然牵动整个食物网,打破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历史上欧洲人的殖民扩张触动了殖民地食物链中某些环节,牵动了特定区域的食物网,引起殖民地生态系统的恶化,带给殖民地本土人灾难。本文中的“生态殖民主义”主要指欧洲微寄生物病原体(疾病)、动物、植物等非人类生命有机体随欧洲人移居遥远异国所产生的结果,如欧洲疾病导致毫无免疫力的当地人大量死亡,人口急剧下降; 欧洲动物大量繁殖,贪婪地吞噬当地的植物,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系统的平衡。本文中的“生态殖民文学”则指那些描写欧洲疾病、动物和植物破坏殖民地生态系统平衡的经验和结果的文字。
此外,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彼(Alfred W·Crosby)在其《生态帝国主义: 欧洲生物扩张900-1900》(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900-1900,以下简称《生态帝国主义》)一书中,[注]该书名又译《生态扩张主义: 欧洲900-1900年的生态扩张》。杜撰“生态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来提醒世人,西方帝国主义不仅像尼日利亚后殖民文学作家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的小说《瓦解》(Things Fall Apart)所描写的那样瓦解东方被殖民地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政治体制、宗教信仰和社会结构,而且还破坏当地民族及其文化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克罗斯彼提出的“生态帝国主义”概念与本文中的“生态殖民主义”概念意义相近、关系紧密,但又有所不同。著名后殖民理论家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特意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两个概念做出区分: “帝国主义”指强势宗主国统治远方他国的实践、理论和态度; “殖民主义”则是“帝国主义”的结果,即移居于遥远的他国。[1]8但赛氏区分忽略了强势西方宗主国(如欧洲列国)的疾病、动物和植物参与其征服远方他国实践活动(即生态帝国主义)这一事实。据赛义德,“移居于遥远的他国”是“殖民主义”最基本的含义,也是“帝国主义”产生的结果。其实,不仅欧洲人移居他国,而且欧洲疾病、动物和植物亦随欧洲人移居他国; 再说,移居他国并不是帝国主义的唯一结果,殖民地生态系统的失衡及其带给当地人的灾难也是帝国主义产生的一个主要结果,更准确地说,是生态帝国主义的主要结果。所以,生态帝国主义侧重于实践,生态殖民主义侧重于结果。
一、欧洲疾病——隐形杀手
克罗斯彼生态帝国主义的一个主要命题是,促成欧洲殖民者成功征服新世界(即东方被殖民地国家)的主要因素是他们带到新世界的疾病。在《生态帝国主义》中,我们看到被称为“俄罗斯人”的西方入侵者于17、18世纪拓居于西伯利亚,他们将天花、麻疹、猩红热、伤寒等病原体带入西伯利亚。这些疾病在当地迅速而广泛地扩散,导致大量当地西伯利亚人死亡,人口急剧下降,环境急剧退化。[2]38可见,西方殖民者并非纯然无杂地拓居于东方被殖民地,随其同行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病原或病菌; 这些病原或病菌在“新欧洲”随欧洲人扩张而扩张,形成克罗斯彼所称的“欧洲生物扩张”(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克罗斯彼论述的欧洲生物扩张中的三大主要因素“杂草”、“动物”和“疾病”构成“植物(杂草)→草食动物→欧洲人(及其微寄生物病原体)”食物链。链中末端环节上的“欧洲人”是寄主及其微寄生物的合成体。此处的“微寄生物”主要指寄生于寄主体内的病毒、病菌、真菌、病原,它们随寄主扩张而扩张。故此,我们不可抛开欧洲殖民者体内所携带的病原体而单独考察欧洲殖民者的殖民主义经验。
在一般情况下,微寄生物病原体会把没有免疫力的寄主杀死。乔万尼·薄伽丘在《十日谈》引言中描写的那场在1348-1352年间蔓延整个欧洲的黑死病(又称鼠疫)短短的数月内就吞噬了10万多佛罗伦萨居民,使昔日生气怏然、人声鼎沸、繁华美丽的佛罗伦萨城瞬间变得尸体纵横、十室九空、哀鸿遍野。[3]3-9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中的忒拜城也因瘟疫肆虐而变得人畜病死、土地荒芜。但人类这一生命有机体初次被病原体感染后,其免疫记忆对同样病原体的再次侵袭产生快速反应,体内特定细胞会直接攻击并吞没病原体细胞,同时体内抗体量迅速上升,产生一定的免疫力,抑制病原体的感染,甚至杀死病原体。所以,在一定的条件下,虐杀寄主的微寄生物病原体同时又诱发寄主产生免疫力而反被寄主杀死。后来欧洲人甚至能够生产疫苗来加强寄主对某种病毒的免疫力,正如拜伦在《唐璜》中所作: “但种牛痘苗的发明确可称得起抵消了康格利夫的榴弹的祸害; 靠着从牛身上借来的新痘菌,医生倒能打发走人身上的痘病。”[4]75
受到寄主强力攻击或抵抗的微寄生物病原体的传染力急剧下降,不能随心所欲地再次享用同一寄主; 此时的病原体需要寻找还未获得免疫力的新的易感寄主,转换寄主,将其寄生的适合度重新扩大到极致,以维持其生长、发育和繁衍。欧洲人的远航探险、征战侵略、殖民扩张、旅行考察、迁徙移居、商贸往来、说教传道等使欧洲人与新欧洲本土人广泛接触。如此的广泛接触为欧洲获得免疫力的旧寄主体内的微寄生物病原体寻找新的易感寄主、实现寄主转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和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机会。这样,获得某种疾病免疫力的欧洲种群(population)[注]生态学中的种群(population)是指栖息在某一地域中同种个体组成的复合体,是在特定的时间内,由分布在同一区域的许多同种生物个体自然组成的生物系统。种群具有共同的基因库(gene pool),彼此之间能够进行自然交配并产生出有生殖力的后代,因此,种群是种族生存的前提,是系统发展的结果。自然界中任何物种的个体都不可能单一地生存于世,生物个体必然在某一时期与同种及其他种类的许多个体联系成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群体才能生存。种群的英文“population”不仅指生活于同一区域的同种个体组成的“人口”,而且还指栖息于同一地域的同种个体组成的人养或野生的“牲口”,如马群、牛群、羊群等,故早期研究昆虫、鱼类、鸟类的生态学者又将“population”译成“虫口”、“鱼口”、“鸟口”。(来源: 李振基等《生态学》,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90页)中的寄主在其殖民扩张过程中突破旧的疾病疆界,将病原体传给毫无免疫力的新欧洲种群,从而打破了新欧洲种群原有的寄主与其体内微寄生物之间的平衡关系,造成灾难性后果。于是,带给佛罗伦萨人和忒拜城人弥天大难的黑死病之类的瘟疫突破旧欧洲疾病疆界,蔓延到新欧洲或新世界,将灾难降临到对外来疾病毫无免疫力的当地人头上,为欧洲人征服当地人充当了隐形杀手,夺去数以万计当地人的生命,使得原住居民人口锐减,斗志丧失,帝国消亡。
欧洲人携带病原体到新欧洲去征服当地人的思想意识在拜伦的诗体小说《唐璜》中已有所表露: “据说那大痘(即梅毒——笔注)之患是来自美洲,看来它也许该驾返其故乡了,据说新大陆的人口已嫌太多,那么也该轮到它使人口减少,用战争,瘟疫,饥荒,用什么都成,好叫他们领略一下文明之道; 谁知道哪种祸害最削减人口——他们的真梅毒?或我们的假花柳?”[4]76众所共知,早在16世纪初,入侵美洲的欧洲士兵就将天花带入美洲,结果天花迅速在整个美洲蔓延,吞噬了半数美洲当地人口的生命。[注]1520年,西班牙王国驻古巴总督维拉斯奎斯率军队1500人讨伐征服阿兹提克帝国的科尔特斯,但被科尔特斯率军击败收编。讨伐军中一名染有天花病的士兵把天花病从欧洲传入美洲。最初天花病出现在申泼拉镇(今墨西哥哈拉帕城一带),然后迅速蔓延到阿兹提克帝国全境,进而传遍美洲大陆,在短时期内吞噬美洲半数以上的人口的生命,很多染上天花的印第安人部落消亡灭绝。因为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美洲从没有过天花病毒,所以当地印第安人对此病毫无免疫力,也不知道如何防治。又如艾勒克·博埃默(Elleke Boehmer)在《殖民与后殖民文学》(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Literature)中所言,“继16世纪初西班牙征服占领了美洲后,当地土著人就因天花、麻疹的流行而开始了所谓的‘大死亡’,这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史实。”[5]21但这个尽人皆知的史实的真正成因并非是尽人皆知的。西班牙人柯帝兹率领区区数百名随从就成功征服了统辖数百万人的阿兹提克王国的主要的、真正的原因被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在其《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中称为“史学家的漏网之鱼”。[6]显然,麦克尼尔以此提醒人们,史学家忽略了在这场以少胜多战争中起最关键作用的传染病。在麦克尼尔看来,促成几百西班牙人征服拥有数百万人的阿兹提克王国的真正原因不是西班牙人的科技优势、火药枪炮、宗教信仰,而是他们传给阿兹提克人的传染病。他在《瘟疫与人》的序言中道出这一真正的原因: “因为,就在阿兹提克人把柯帝兹及其手下逐出墨西哥城的那天晚上,天花传染病正在城中猛烈蔓延。而且,负责率队攻击西班牙人的土著将领也死于那场‘悲伤之夜’——事后,西班牙人这么称呼它。这场致命传染病所酿成的瘫痪性效果足以解释,为何阿兹提克人当时并未乘胜追击溃败的西班牙人,反而让对手有时间、有机会喘息重整,进而联合其它印地安族人来包围墨西哥城,赢得最后的胜利。”[6]毫无疑问,麦克尼尔在此道出的原因与克罗斯彼生态帝国主义的主要命题相一致,即,促成欧洲殖民者成功征服新世界的主要因素是他们带到新世界的疾病。
在克罗斯彼所描述的900-1900年生态帝国主义时期内出现的欧洲殖民者迁徙和移居类型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携带传染病原到新世界。旧世界的病原菌通常随寄主搭乘远洋航船漂洋过海,到达新世界。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哥伦布的船队到达加那利群岛,将痢疾、梅毒、花柳病等传染给岛上的关切人。例如,欧洲男子通过女关切人把当时在欧洲流行的梅毒传染给毫无免疫力的关切人,导致关切人口急剧下降、甚至灭绝。[7]122-164在17世纪末,一位德国传教士写道,“印第安人的生命力非常脆弱,西班牙人的目光或气味就足以使他们丧命。”[7]36-37虽然这位传教士的言辞过于夸张,但其所言至少说明印第安人对来自欧洲的传染病毫无抵抗力,很容易染上外来疾病而丧失生命。
在1768-1771年间,英国“奋进”号远征船船长詹姆斯·库克在其前往澳洲的划时代航行中察觉到他的船员将一种疾病带到太平洋的岛屿,并在当地迅速蔓延,他为此而深感愧疚。当“奋进”号到达塔西提岛后几天,库克写道,“我们的船只到达几天后,我们的一些人就得这种病(梅毒病——笔注),而这些在皇家‘海豚’号到来时是没有听说过的。我有理由认为(虽然不一定)是我们带来的,这一点让我丝毫轻松不起来,我所做的应该是尽我的能力阻止它的进一步蔓延 …… ”[8]131-132库克的忧虑不是多余的,因为确实有欧洲船只将某种疾病带到太平洋岛屿,如彼德·奥顿(Peter Aughton)所肯定的那样,“不能否认的是,在18世纪晚期的一段时间里,一般欧洲船只确实给太平洋的岛带来过性病。”[8]133所以,在克罗斯彼描述的“生物扩张”过程中,疾病伴随欧洲人流散而流散。
我们在达夫妮·杜穆里埃(Daphne du Maurier)的《牙买加客栈,法国人的港湾》(Jamaica Inn; Frenchman’s Creek)中看到,玛丽的母亲料理的那个“农场里不久就会有人饿死。然后瘟病开始肆虐,并残杀赫尔福德附近村庄的牲口。那是一种不知名的瘟疫,根本无以治疗。瘟疫席卷一切,所向披靡,很像不当令的晚霜,新月时分悄然而至,离去时又无影无踪,只是在它的来路上留下死物一片。”[9]13-14再者,18世纪随欧洲殖民者进入美洲的天花病导致著名智利诗人弗朗西斯科·洛佩斯的妹妹月貌花容消失殆尽,于是又见洛佩斯的诗作《致患天花病的失去美丽的妹妹》。美国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小妇人》(Little Women)中善良无私、至善至美的贝丝不幸染上猩红热而离开人世。当代墨西哥裔美国作家亚历杭德罗·莫拉莱斯(Alejandro Morales)的代表作《布娃娃瘟疫》(The Rag Doll Plagues)的第一卷描写了发生于18世纪末墨西哥的瘟疫灾害。书中主人公、西班牙王国御医团里最年轻的医生格雷高利奥·雷维尔塔斯于1788年被派往被称之为“新西班牙”的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协助新西班牙总督改善殖民地墨西哥的医疗状况。当时,墨西哥南方一种被称为“布娃娃”的瘟疫盛行,)[注]患“布娃娃”瘟疫而死的尸体软软的,像个布娃娃,因此得名“布娃娃”瘟疫。感染上“布娃娃”瘟疫的病人的手指和脚趾肿大,数日后变红,不久骨肉化脓,四肢糜烂,病毒蔓延到躯体,致使患者死亡。短短的三个月里就吞噬了数千人的生命。据诺贝尔·戴维·库克(Noble David Cook)估计,“1519年墨西哥中部人口高达1500万,但与欧洲人接触一个世纪后,其人口就减少到150万。”[10]4-5总之,欧洲殖民种群在接触新欧洲被殖民种群时将体内的微寄生物病原体传给了后者,使其人口锐减、民族衰退。但由于微寄生物病原体寄生于寄主体内,不易被人察觉,所以人们考察欧洲人迁徙过程时,往往关注于寄主的迁徙移居,却忽略了随之迁徙移居而流散蔓延的微寄生物病原体。
二、欧洲动物──不速之客
欧洲生物扩张的主要形式是多个不同的种群(如人口、牲口、植物,或人群、羊群、牛群、马群、鸡群等)一同迁徙移居,而非某个种群(如人口或人群)单独迁徙或移居于异国他乡,即,欧洲生物扩张通常以多个不同的种群组成的群落(community)为其迁徙移居的基本单位。生态学中所说的“群落”是指共同生活在同一区域的多个不同种群组成的集合整体。[11]194如果说种群是个体的集合体,那么群落就是种群的集合体。据此,欧洲殖民扩张是欧洲人连同欧洲动物和欧洲植物一起迁徙或移居到新欧洲殖民地的欧洲群落扩张。欧洲殖民者不仅随身带入新欧洲殖民地致人死命的疾病,而且还有意无意地带入同样对当地的生态系统造成灾难性破坏的各种动物和植物。我们不妨先考察欧洲动物在欧洲生物扩张中扮演的角色。欧洲动物在“植物(杂草)→草食动物→欧洲人(及其微寄生物病原体)”食物链中处于杂草与欧洲人之间的中间环节,属于第二营养级,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转化者),它一方面消费第一环节上杂草提供的食物,另一方面又生产供第三环节上的欧洲人消费的食物; 或言之,它是将欧洲人不能食用消化的植物纤维物质(如青草、树叶、嫩枝等)转化为欧洲人能够食用消化的肉奶物质(如猪肉、羊肉、牛肉、鸡肉、牛奶、羊奶等)的转化者。草食动物扮演的这一角色要求它的消费量不能超过第一营养级上杂草的生产量,否则第一环节(或第一营养级)上杂草植物就会不堪重负,终止食物供应,导致食物链断裂,食物网破损,生态环境退化。
众所周知,澳大利亚在英国人来到之前并没有本地土生土长的兔子,但在英国人殖民澳大利亚初期,欧洲兔子被引进澳大利亚。1859年一个名叫波米的农民因思乡恋井,将24只野兔从英格兰带入澳大利亚以解乡愁。出乎人们预料的是,由于这些野兔在澳大利亚没有天敌,它们以其特有的杂乱交配迅猛繁殖,泛滥成灾。它们大量吞噬庄稼牧草、啃吃树皮嫩枝,它们在地下打洞而居,破坏土壤河堤,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系统,给当地居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在考琳·麦卡洛(Colleen McCullough)的小说《荆棘鸟》(The Thorn Birds)中,鲍勃真实地道出了兔子带给澳大利亚的灾难: “兔子的祸害比袋鼠还严重,它们吃的草比绵羊和袋鼠加在一起还多。”[12]415再看:
天干得很厉害。在梅吉的记忆中,德罗海达的草地总是能设法挺过每次干旱的。但这次就不同了。现在,草地显得斑斑驳驳,在一丛一簇的草之间露出了黑色的地面。地面上网着细密的裂纹,就像是一张张干渴的嘴。弄到这步田地是兔子的过错。她不在的四年中,它们突然在一年之中大量地繁殖了起来。尽管她认为在这之前,它们就已成为了一大祸害。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它们的数量远远超出了饱和点。到处都是兔子,它们也吃宝贵的牧草。[12]416
于是,人们把罪过归于波米,鲍勃抱怨道,“上帝惩罚思乡恋井的‘波米’吧,是他第一个把兔子从英国运来的。”[12]416小说直接表明来自英国的兔子给澳大利亚生态造成的破坏: “兔子不是澳大利亚的土产。它们被多愁善感的人们引进来,大大破坏了这个大陆的生态平衡 …… 这里人太少,兔子太多了。”[12]416显而易见,兔口爆炸使兔子消费量超过杂草生产的食物量,导致食物链断裂,生态失衡,造成灾难性后果。
食物链中间环节上的动物一方面摄食前一个环节上的杂草,另一方面又被后一个环节上的人食用,即牛羊吃草,人吃牛羊。彭斯在其诗歌《赶羊上山》中唱道,“把母羊赶上山岗,赶到长着野草的地方,赶到流着溪水的地方,我的好亲人。”[13]17听罢彭斯“赶羊上山,采食野草”的诗歌,就见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的《福尔赛世家》(The Forsyte Saga)餐桌上的头菜羊胛肉: “羊胛肉 …… 这道菜在福尔赛家宴会上是公认的头菜。福尔赛家不论哪一房请客都没有不备羊胛肉的。羊胛肉又有滋味,又耐咬嚼,对于‘有相当地位’的人士特别相宜。它有营养而且——好吃; 恰恰是那种叫人吃了不能忘怀的东西。”[14]51可见,羊肉及其它草食动物肉(如牛肉、鸡肉、猪肉等)是欧洲人必不可少的食物。
无论在旧世界或新世界,牲口(如羊口、牛口、猪口等)在很多情况下是欧洲殖民者维持生计的主要来源,以致欧洲人口种群和动物种群通常组成群落一起生活。在杰弗里·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里《女尼的教士的故事》中的那个寡妇依靠其死去的丈夫留下的一块地、几只鸡、几头猪、几头牛和一只羊养活了自己和两个女儿,且过着相当富裕的生活。在故事中我们看到: “她(寡妇)小心栽培上帝所赐的一点东西,维持自己和两个女儿的生活。她只有三只大母猪,还有三头牛和一只名叫穆勒的羊 …… 她喂着一只公鸡名叫腔得克立 …… 手下管辖七个母鸡 …… ”[15]675同样,华兹华斯诗作《最后一头羊》中的那个成年汉子靠一头母羊生小羊赚钱结婚、养活6个孩子,其诗曰: “可我呀却买了一头母羊; 我把它生下的羊儿喂养,它们一头头都非常壮健; 后来我结婚,富裕起来,要多少就有多少钱; 我的羊已有二十头上下,而每年这数字还在增加。羊的头数一年年在增长; 就凭那原先的一头母羊; …… 它们越多,我们家越富有 ……”[16]36-37鲁滨孙在孤岛上驯养当地山羊,以获取羊肉和羊奶养活自己。如鲁滨孙自己所述,“我经常考虑能不能弄到一两只小羊,繁殖出一群驯羊,等我的弹药用完的时候,供我作食料。”[17]98后来他捕到一只老公羊、一只小公羊和两只小母羊,并把它们驯养起来,实现了他养羊取食、维持生命的目的。他说,“不到一年半,我已经连大带小有了十二只山羊了; 又过了两年,除了被我宰杀吃掉的几只不算,我已经有了四十三只羊了。”[17]130这也说明,欧洲人擅长驯化动物,孤岛上的鲁滨孙显然比当地土著人更擅长驯化动物。欧洲殖民者带到新欧洲并驯化的动物主要有牛、马、猪、羊、驴、鸡、猫等。鲁滨孙在荒岛上驯养山羊,建立了一个包括狗、猫、羊、鹦鹉在内的热闹家庭。[17]65-66牲口不仅被用来维持生计、赚钱致富,而且还常用来耕田犁地、载物运货。在彭斯的诗歌《老农向母马麦琪贺年》中,老农赠送礼品麦子一把给曾为其辛劳耕作的老马麦琪,并向它恭贺新年,“恭贺新禧,麦琪,请收下这点麦子喂肚皮!…… 拉犁你也肯出力,四马之中你走最里,你和我常在三月天气,连续八个钟头,一次耕十亩田地,一同把汗流。…… 你拉车也是好样,最陡的山坡也敢上; …… 只把脚步稍稍放长,车子就跑得顺利。”[18]131-134牲口种群的这些利用价值足以将人口种群和牲口种群紧紧地联在一起,共同生活。
欧洲人口种群和动物种群不仅组成群落一起生活,而且组成群落一同乘船漂洋过海、迁徙移居异国他乡。在驶往澳洲的“奋进”号船上,库克及其船员带有羊、鸡、猫、狗等动物。如奥顿所述,“从‘海豚’号上挑选的第五个成员就是船上的山羊,就是这只动物,以后被约翰逊冠以无上的荣誉,有以下文字为证: ‘环球两次,只有这只山羊,作为神的第二侍从,神灵赐以它,以后再不用产奶。’”[8]20虽然“奋进”号“在比斯开湾时,甲板上的两条狗、几只绵羊、一只山羊和船上的猫以及装着三四打母鸡的几个大板条箱也被冲跑了,”[8]34但我们由此可见欧洲人确实带着动物同船漂洋过海、驾往异国。在《鲁滨孙飘流记》中,鲁滨孙游回到斜搁在沙滩上的遇难船上,找到一些欧洲麦子,他说,“这点麦子本来是准备用来饲养我们带到船上的一些家禽的,但家禽现在已经死了。”[17]43这说明鲁滨孙等一行在从英国出航时把一些家禽带上了船。除在海难中死去的动物外,还有一条狗、两只猫幸存下来,如鲁滨孙所述,“同时还有一件不应该忘记的事情,就是我们船上还有一条狗和两只猫,…… 我把两只猫都带到岸上; 至于那条狗,它是在我第一次搬东西上岸的第二天自动跳下船来,泅到岸上,来找我的,后来做了我多年的忠仆。”[17]55-56这说明,由人口和牲口(或动物)不同种群组成的群落不仅共同生活在同一区域,而且还共乘同一船,如“海豚”号或“奋进”号远洋探险船,飘移到东方被殖民地。早在公元10世纪晚期,欧洲人来到格陵兰岛南部建立殖民地,他们不但在那里建造教堂、住宅,而且带来牛羊,在牧草稀疏的土地上放牧。15世纪欧洲殖民者将公羊和母羊、公牛和母牛投放到亚速尔群岛啃食青草、生殖繁衍。当1439年葡萄牙国王首次允准葡萄人在亚速尔群岛上定居时,那里已经牛羊成群了。欧洲人征服加那利群岛时,为使该岛“欧洲化”而引进了狗、山羊、猪、绵羊、马、驴、牛、骆驼、兔子、鸽子、鸡、鸭子等不同的欧洲动物种群。欧洲动物的到来使殖民地食物链中间环节“草食动物”的数量急剧增加,超量的动物抢食有限的牧草,导致大面积草地超载放牧,食物链始端环节断裂,杂草质量迅速下降,生态系统严重退化。
欧洲动物不仅掠食殖民地有限的牧草,而且参与欧洲帝国军队征服当地民族的战争,甚或亲自向土著人直接发起攻击。如“在1880年的马温战争中,跟随在66步兵团士兵后面的是役畜——大约2000匹骆驼、500头矮种马、100头骡子和350头驴子,加上100多头公牛 …… 它们背上驮着弹药、补给品和帐篷。”[19]9-11欧洲殖民侵略军时常利用这些身强力壮的大动物攻打本土人,例如,西班牙人利用战马进攻阿兹提克人,斯堪的纳维亚人用公牛打先锋战胜了斯库利林人。无疑,作为欧洲人坐骑的马在征服殖民地土著人的战斗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欧洲小动物也直接与欧洲殖民军士兵并肩战斗,亲自攻击殖民地土著人,且立下赫赫战功,成为沉默的战斗英雄。据伊芙琳·勒·切尼,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在各个军队中,养宠物狗是很平常的 …… 特别是大英帝国在非洲、印度和远东进行扩张时期,这种情形更是司空见惯。宠物会与它的士兵主人分享生命,分担职责 …… ”[19]2切尼紧接着举例说,“白色短毛狗鲍比是1880年马温战争中66步兵团的宠物。另外还有混血狗耐利,公狗比利,它们同它们的主人一起战斗到最后时刻。然而当其他所有的人和动物或者被杀或者因受伤绝望地躺在那儿时,鲍比还是继续撕咬,给敌人以重创,展示了战胜所有恐惧的个人勇气。”[19]2-3显然,像鲍比这样的欧洲“英雄动物”在欧洲殖民扩张、征服土著人的战斗中发挥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三、欧洲植物──秘密武器
现让我们考察欧洲植物在欧洲生物扩张中扮演的角色。克罗斯彼在《生态帝国主义》中强调欧洲人带到新欧洲的主要植物是“杂草”。克罗斯彼所称的杂草“指的是任何在乱七八糟的土地上蔓延得很快并能竞争过其他植物的植物。”[20]156-157根据这个定义,杂草包括或好或坏、有利或有弊的植物甚或作物。从生物学角度来看,杂草是生命有机体的主要生产者,由绿色植物和具有化能合成、光合作用的细菌组成,能利用太阳能把水和二氧化碳合成为有机物,为其它生命有机体(如草食动物和人)提供食物。所以,杂草在特定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能量运转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能把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其光合作用所固定的能量以化学键能的形式储存备用、或以牧草、作物和食物的形式进入“杂草→动物→人”或“作物→人”的食物链,环环传递,形成能量流。
由于杂草在生命有机体生产、食物制造和能量转化中所起的如此重要的作用,欧洲殖民者总会想方设法将欧洲杂草(包括作物)带入新欧洲供欧洲殖民动物和欧洲殖民者食用。据克罗斯比,杂草是这样移居的: “在移居的植物中,地中海地区的杂草无疑是头一个成功的横渡者; 进行短程跳跃而到达亚速尔群岛、马德拉群岛和加那利群岛那砍掉了森林的山坡上,尔后进行长途航海到达西印度群岛和美洲热带地区。”[20]157这些被引进的杂草在无人照管的情况下长得很茂盛——确实长得顶好。[21]10,97-98面对如此茂盛的杂草,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贡柴罗感叹道,“草儿望上去多么茂盛而蓬勃!多么青葱!”[22]28-29据安德鲁·H·克拉克(Andrew H·Clark)的考察,来自旧欧洲的卷叶酸模、苦苣菜、红茎法拉里是移居美洲的先驱植物。18世纪西班牙士兵和传教士有意无意地随身携带卷叶酸模、苦苣菜、红茎法拉里、野燕麦、雀麦、黑麦草等植物来到美洲。这些植物随着西方殖民者,如士兵、传教士等,沿着海滨地区的山岭进入圣华金河和萨克拉门托河流域,[23]748-751由此向其他更广泛地区拓展。
到了19世纪中叶,很多外来杂草种类适应了新欧洲的生存条件,茂盛地生长。克罗斯比很有把握地断定,莎士比亚在悲剧《李尔王》中描写的杂草(如芹叶钩吻、荨麻等)早在莎士比亚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在北美洲的土壤里扎根了。[20]162在《暴风雨》中,如果贡柴罗当上岛上的岛王,安东尼奥肯定,“他(贡柴罗)一定要把它种满了荨麻。”[22]33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一幕第二场出现的“车前草”移居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被美洲印第安人称为“英国人的脚”,[24]24因为他们相信这种杂草长在英国殖民者踏走过的地方。鲁滨孙无意中把从欧洲带来的谷粒抖落在岛上一块岩石脚下,后来鲁滨孙说,“不料过了一个多月,我忽然看见地上抽出几根青绿的茎子 …… 我看见那些茎子上又生出十几个穗子,完全和我们欧洲的大麦,甚至英国的大麦一模一样 …… 尤其奇怪的是,在大麦茎子旁边,沿着岩石脚下,我又看到几根稀疏的绿茎,显然是稻茎 ……”[17]68这样,多种欧洲植物移居于新欧洲,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据克拉克提供的数据,在圣华金流域的外来植物占草地草本植物的63%,占林地草本植物的66%,占灌木林草本植物的54%。[23]750这一切说明,欧洲植物与欧洲的士兵、商人、传教士、探险者、拓居者、殖民官一样具有侵略性。如此“植物扩张”同样侵占大片土地,抢夺庄稼地、破坏森林,帮助欧洲殖民者征服殖民地本土人。
16世纪引入秘鲁的一种叫做特雷博尔的欧洲杂草具有很强的扩张性,侵占了很多庄稼地,埋没地里的庄稼,为扩张的欧洲动物提供优质草料。另有很强侵略性的欧洲桃树、白三叶草、禾草、小檗属植物、金丝桃、麦仙翁、雀麦、野洋蓟、荠菜、繁缕等逾百种杂草在随后的世纪里进入美洲殖民地。[20]164-166这些杂草或粘附于牲口毛皮翻山越岭、或随风飞散飘落、或随河流雨水流散,向四面八方迅速传播。据克罗斯彼,当欧洲橘子落地烂掉后,其籽儿就随河流雨水流散到各地,长成橘树林。[7]66-67这样,杂草通过成千上万的杂草籽儿和大量的球茎、根茎的片断等多种方式四处传播、繁衍蔓延。例如,野生大蒜在北美殖民地以多种不同的方式繁衍,成为当地麦农的灾星。有些杂草的籽儿轻得不到0.0001克,可以随空气的运动飞散到其它地方,如苦苣菜、蒲公英的籽儿随风飘得很远。另些杂草带粘性或带钩的籽儿则抓攀上兽毛和衣服免费旅行到新地方。还有许多杂草(如匍匐冰草)通过地面或地下根茎或长匐茎的伸展来传播,以浓密的丛簇方式向前推进,把挡路的其他植物淹没闷死。[25]686-687从英国引进的“车前草”被美洲印第安人称为“英国人的脚”,其叶子把其它植物完全遮住或挤向旁边。移居到新欧洲的杂草为移居到新欧洲的牲口提供了重要的饲料,而这些牲口又为它们的主人效劳。这样杂草对欧洲殖民者是极其重要的。
在澳大利亚,“1788年英国人有意携带多种植物到达新南威尔士寻找殖民地,到1803年3月,英国人带来的植物超过200种 …… 其中一些植物立即就占据了当地杂草(如马齿苋)的地盘。由此可见,面对旧世界植物的侵略,澳大利亚的植物群显得何等脆弱。”[注]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Historical Records of Australia,Series I,Governors’ Dispatches to and From England (The Library Committee of the Commonwealth Parliament,1914-25),IV 234-41.例如,扩张性很强的“白三叶草 …… 快速前移,在气候湿润的墨尔本定居下来而‘常常破坏了其他的植被’”。[20]169“苦苣菜似乎在墨尔本及其周围的每个地方都长得很繁茂 …… 将较无侵略性的青草完全挤出一些牧场。与西北欧气候十分相似的塔斯马尼亚对于新的杂草也很相宜,因而两耳草和拳参与开拓殖民地的人们齐步前进。”[20]169根据克罗斯彼的引介,约150种来自欧洲的植物侵占了澳大利亚的土地,扎根生长。[20]170“在加拿大,有60%较重要的农地杂草来自欧洲; 在美国,500种农地杂草中有258种来自旧世界,有177种明确地是来自欧洲; 在澳大利亚,适应该地生长环境的异域植物的种类总数约为800种。”[20]171欧洲杂草的引进使美洲、澳洲等殖民地的生态系统发生变化,欧洲殖民者一般在新欧洲建立符合他们要求的生态系统,这要求他们首先要解构殖民地原有的本土生态系统。结果,殖民地本土的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例如,“在新南威尔士,定居者们飞快地砍伐树木,使土生的野草暴露在烈日下,而牲畜们也飞速地啃食着土生野草和草本植物。”[20]286在每一寸土地都被树林覆盖的马德拉岛上,欧洲殖民者为耕种作物、畜牧牲口而清理树林、开辟空地。殖民者为省力、省时、省钱,竟然放火焚烧岛上树林,严重破坏了岛上原始树林的生态环境。
在本·奥克利(Ben Okri)的长篇小说《饥饿之路》(The Famished Road)中我们看到,非洲某国一个小镇的居民原来过着平静和谐的原始生活,但西方殖民者的到来打破了他们的平静生活,使那里的道路逐渐变宽,房屋日益增多,但本土野草越来越少,树林滥遭砍伐、森林向后退缩。在加那利群岛上,欧洲人大量种植甘蔗和生产糖,结果岛上的森林让位于蔗田,而森林的减少又导致岛上降雨量的减少,降雨量的减少直接导致岛上生态环境的恶化。被称为“外来植物”或“外来杂草”的欧洲黑莓(悬钩子属植物)在加那利群岛上迅速蔓延,严重侵蚀了岛上土地,成为当地一害。在V·S·奈保尔(Naipaul)描写的《自由国度》(In A Free State)中,读者所见的是生态环境遭受破坏后的荒芜景象: “道路的一旁是一些小土丘,类似于长满了杂草的蚁丘。每一个峰丘都可以看出树木被砍伐过的痕迹。现在这片被废弃了的土地上一片荒芜 …… ”[26]136
行文至此,我们看到,杂草→动物→欧洲人(及其微寄生物病原体)食物链随着欧洲人的殖民扩张而延伸到新欧洲,食物链交织成的食物网也随之扩展至新世界。食物链中末端环节上的欧洲人把病原体传给毫无免疫力的新欧洲本土人,使其人口锐减、甚至消亡。食物链中间环节上的欧洲动物一方面掠食新欧洲杂草,增加了绿草消费者数量,使杂草不堪重负,供不应求; 一方面又将欧洲人不能食用消化的植物纤维物质(如青草、树叶、嫩枝等)转化为人能食用消化的肉奶物质,供养欧洲殖民者; 另外,许多种动物还充当役畜或兵畜,加入征服土著人的战斗。食物链始端环节上的欧洲杂草在新欧洲侵占土地,埋没庄稼,破坏森林。简言之,欧洲生物扩张导致新欧洲食物链断裂、食物网破损,解构了当地原有的生态系统,并按欧洲人的要求重构新欧洲生态系统。
参考文献:
[1] Edward W Said.CultureandImperialism[M]. London: Chatto & Windus,1993.
[2] Alfred W Crosby.EcologicalImperialism:TheBiologicalExpansionofEurope, 900-1900[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3] 乔万尼·薄卡丘. 十日谈[M]. 肖天佑,译. 广州: 花城出版社,2001.
[4] 拜伦. 唐璜(上)[M]. 查良铮,译. 王佐良,注.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5] 艾勒克·博埃默. 殖民与后殖民文学[M]. 盛宁,韩敏中,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6] 威廉·H·麦克尼尔. 瘟疫与人[ M]. 杨玉龄,译. 台北: 天下文化出版社,1998.
[7] Alfred W Crosby.TheColumbianExchange,BiologicalandCulturalConsequencesof1492[M].Westport,Conn.:GreenwoodPress, 1972.
[8] 詹姆斯·库克. 彼德·奥顿. 发现澳洲——库克船长和他的第一次划时代航行[M]. 徐瑛,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2001.
[9] 达夫妮·杜穆里埃. 牙买加客栈 法国人的港湾[M]. 王东风, 姚燕瑾, 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1.
[10]NobleDavidCook.BorntoDie:DiseaseandNewWorldConquest, 1492-1650[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11] 李振基等. 生态学[M].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0.
[12] 考琳·麦卡洛. 荆棘鸟[M]. 曾胡,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1998.
[13] 彭斯. 赶羊上山﹝一﹞[M] //彭斯诗选. 王佐良,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17-19.
[14] 约翰·高尔斯华绥. 福尔赛世家﹝第一部﹞ [M]. 周煦良,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15] 乔叟. 坎特伯雷故事集[M]. 方重,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16] 华兹华斯. 最后一头羊[M]//华兹华斯. 华兹华斯抒情诗选.黄杲炘,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36-37.
[17] 笛福. 鲁滨孙飘流记[M]. 徐霞村,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18] 彭斯. 老农向母马麦琪贺年[M]//彭斯彭斯诗选. 王佐良,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131-136.
[19] 伊芙琳·勒·切尼. 沉默的英雄: 历史上最伟大的动物战士[M]. 韩宁宁,译.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
[20] 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 生态扩张主义: 欧洲900-1900年的生态扩张[M]. 许友民,许学征,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21] Gonzalo Fernández de Oviedo.NaturalHistoryoftheWestIndies[M]. Sterling. A Stoudemire, tran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59.
[22]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全集〈一〉[M]. 朱生豪,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23] Andrew H Clark. The Impact of Exotic Invasion on the Remaining New World Mid-Latitude Grasslands[M]//Jr William L Thomas,ed.Man’sRoleinChangingtheFaceoftheEarthII.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 748-751.
[24] Edmund Berkeley,Dorothy S Berkeley.TheReverendJohnClayton,aParsonwithaScientificMind.HisWritingsandOtherRelatedPapers[M].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65.
[24] Otto Solbrig. The Population Biology of Dandelions[J].AmericanScientist,1971,59: 686-687.
[25] V S奈保尔. 自由国度[M]. 刘新民,施荣根,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