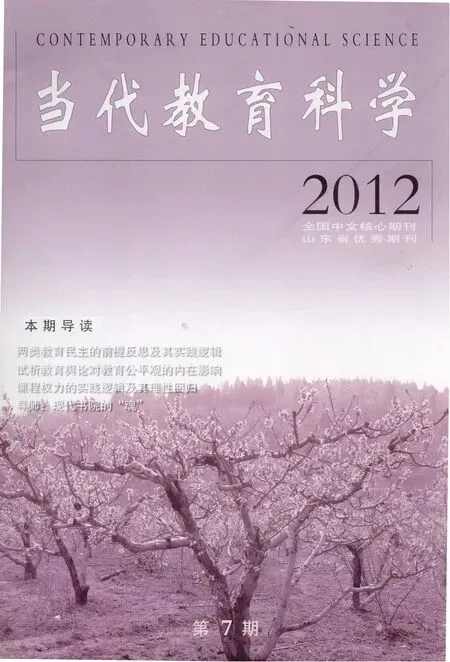两类教育民主的前提反思及其实践逻辑
● 邓 飞
两类教育民主的前提反思及其实践逻辑
● 邓 飞
教育中民主概念的模糊性来源于作为其思想前提的教育自由概念具有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双重指向,这一差异也导致了弱势民主与强势民主两类民主方式的分野。不同类型的教育民主在理论的前提、遵循的逻辑和论证的方法上都存在巨大的差异,也造成了教育民主在达成过程中的不同实践逻辑。必须在前提反思的基础上澄清教育民主的双重指向,在教育的宏观与微观语境中通过弱势民主与强势民主的协同推进,建构具有自我反思意识和自我更新能力的教育民主。
教育民主;消极自由;积极自由;弱势民主;强势民主
在考察教育民主问题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绝非教育应当如何实现民主,而是教育民主究竟意味着什么。正如同一个概念会在不同的言说者那里可以幻化出无数种形象,这些形象既保持着某种 “家族相似性”,又在指向上相互排斥。科恩因此感慨,“由于滥用词藻,认识混乱,以及某些甚至是故意欺骗,‘民主’一词已大大失去了它原有的涵义。”[1]当我们言说教育民主时,究竟我们在说什么以及我们怎么说会直接地决定教育民主理论的建构过程,在民主一词进入教育语境之前,势必先对其思想前提加以澄清。“思想前提似‘看不见的手’那样具有隐匿性和经验规范的强制性”,[2]有必要从民主理论的思想前提出发进行考察,以克服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各种隐匿的“自明性”假定,从而为教育民主的言说创造一个坚实的逻辑架构,防止种种不加区分的误用和所指的混淆,进而为教育领域的民主实践提供可能的理论支援。
一、民主前提的双重指向性
对民主(democracy)的词源分析能够表明,当希腊人将 demos(意指人民或民众)与 kratein(意为治理)组合在一起使用时,其意义指向于一种人民的治理。[3]常被人引用的林肯的名言“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and for the people)也常作为民主内涵的进一步阐释。民主的核心问题是权力的产生、使用与制约,作为民主权力来源的民众享有治权,也因此衍生出治权的冲突与享有问题。治权间的冲突包括多数人暴政的可能及对少数派的保护等常被定义为自由权利保护的问题,而治权的享有包括参与的广度、深度及具体权力的范围等常被定义为参与的自由的问题,这两类问题共同构成反思民主思想前提的基本线索。
自由权利保护的民主概念是基于对民众自由交叠、冲突的考虑,特别是可能导致的对个体自由的剥夺,这种剥夺从基本的生存权、平等表决权、思想言论自由等各个层次都可能发生。这种担忧使得托克维尔等人提出了多数人暴政的问题,由于“民主政治的本质,在于多数对政府的统治是绝对的,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谁也对抗不了多数”。[4]如果多数人可以获得无遏制的权力,那么势必产生对少数人权力的剥夺,甚至剥夺了少数人反抗的权利,构成民主制度自我消解的吊诡处境。托克维尔以及后来的自由主义者提出的基本解决办案是建立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制度,采用宪法等方式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不可侵犯性加以承诺,使得任何民主决策都不能剥夺公民的这些基本权利,这一方案也在很多国家的法律实践中得到了回应,也渐渐渗透进对教育等微观民主环境基本权利的讨论之中。
参与的自由这种民主概念则源远流长,作为民主制度历史源头的古希腊城邦,其民主雏形首先就表现为公民的自由参与。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城邦正是若干公民的组合。”“若干公民集合在一个政治团体以内,就成为一个城邦”。[5]这样的结合使得每个公民都可以对公共事务决策产生一定的维持、更改或废除的力量,作为制度性的治权体现在个人身上则被视为一种自由,而这些能够分享治权的公民也才可以因此被称为自由人。参与的自由实质上体现着共同体中参与者的主体性与自主性,正如杜威所说,“我倾向于相信,民主的核心与最终的保证在于:邻居们可以在街头巷尾自由谈论当天的那些未经审查的新闻,以及亲朋好友聚于一堂,彼此能自由地互相交谈。”[6]参与也即对争议问题的进入和辩论过程,这样的共同体通过民主参与而最终获得对问题的充分理解与讨论、反驳与妥协,于是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也同时是共同体的自我更新方式。
保护的自由和参与的民主这样一种区分可以从贡斯当以及伯林对于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讨论中得到理论共鸣与进一步诠释。贡斯当在1819年所作的《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演讲中集中阐述了两种自由的不同性质与特征,认为“在古代人那里,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但在所有私人关系中却是奴隶。……在现代人中,个人在其私人生活中是独立的,但即使在最自由的国家中,他也仅仅在表面上是主权者。”[7]这种区分在伯林那里则明确地使用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对立概念,也不仅限于历史性的指称而是推广为一种逻辑上的划分:消极自由即不受别人干涉而做事的限度,积极自由即选择做什么事的自由。[8]
自由与民主从来都不可分离,从消极自由的保护和积极自由的伸张两层面可以刻画出弱势民主与强势民主两类民主指向。对于其区别,本杰明·巴伯认为弱势民主“更多地关注促进个人自由,而不是保障公共正义,增进利益而不是发现善,将人们安全的隔离开来,而不是使他们富有成效地聚合在一起”。结果就造成了它能够 “强有力地抵制针对个人的任何侵犯——对个人的隐私、财产、利益和权利的侵犯——但是,它却无法有效地抵御针对共同体、正义、公民性以及社会合作的侵犯”。[9]而强势民主并非仅仅是生活方式(a way of life)意义上的民主,更是一种生存方式(a way of living),可以定义为“参与模式的政治,……通过对正在进行中的、直接的自我立法的参与过程以及对政治共同体创造,将相互依赖的私人个体转换为公民,并且将部分的和私人的利益转化为公共利益,从而解决冲突”。[10]也即杜威所认为的“民主将会成就它自身,因为民主是一种自由而丰富的交往的名称。……当自由的社会探求与自由而发展的交往融合之时,民主也就达到了它的顶峰”。[11]当我们讨论教育中的民主问题时,同样有必要考察并区分民主的问题、类型与指向性,进而有效地界定问题的性质和提出可能的实现路径。
二、弱势民主与强势民主的不同性质与范围
对民主所做的弱势民主与强势民主的区分内在地包含着自由类型的分离,在教育民主问题的讨论中也需要对教育自由的类型进行考察:哪些教育的自由是属于消极自由的范畴,从而不可让渡与剥夺;哪些教育的自由是属于积极自由的范畴,需要确保参与以促进相互理解和共同体发展。这两部分的考察将说明教育中的弱势民主与强势民主的范围和性质,并提供必要的理论框架对现实问题进行有效地阐释。
教育的弱势民主方面所要注意的是对于那些存在于此领域的消极自由权利的保护,而将教育作为一个社会部类和将教育主要视为一个教与学的过程,所要划定的消极自由有所不同。当将教育作为社会架构的一个部类并与经济、文化、政治等并列时,教育的消极自由意味着决策过程的合理性与公共性问题。在这一层面上,教育的目的表述、所允许的手段范围、结果的可能形式及评价的基本原则在根本上皆能够并且应当由国民参与决定,从而使教育真正体现公众意愿。当前的突出问题则是教育公共性观念被广泛接受与教育改革中缺乏公共参与之间的民主缺环。在科恩看来,问题的本质乃是在承认民众是权力来源的同时又对其有效权利范围进行了不合理的挤压。[12]教育权必须通过公意的表达来赋予自身存在合理性,教育权的范围与形式都应当有其民主过程的基础,而不能仅产生于自上而下的行政控制。而在教育过程当中,教育的消极自由则涉及教与学的自由问题,主要包括了教师的教学自主权以及学生的学习自由权,这两部分理当是教育过程自由的核心,然而历次教育改革并没有彻底解放教师的教学自由,显性的或者隐形的控制依然存在,教师对于课程知识的组织方式、呈现方式等都难以拥有充足的话语权。相对应的更为严重的是学生学习自由的狭小,从学什么、怎么学到学习的速率以及评价方式等自由权利更是无从谈起。附属于核心自由的外围自由如身心健康权利、休息权利、免受体罚的权利等等也经常被迫让渡出去。我们亟需在教育立法和教育行业规范两方面重述和承诺教与学的基本权利,以保护教育的不可让渡的基本自由,这样的基本自由权利的达成将成为教育的弱势民主达成的基石,在此之上,更多的教育自由才能够想象、获得与享有。
如果说教育的弱势民主存在着发展方向不明的疑问,教育的强势民主注重的则是教育共同体的指向性,负有推动共同体发展进步的使命。教育共同体在本质上具有共通的利益基础,在此之上所要做的是充分的参与、讨论和澄清,以消除、转化与宽容各种现实的与可能的冲突,从而获得共同体对于未来图景的一致同意和迈进。杜威认为,“一个不良的社会对内外都设置重重障碍,限制自由的往来和经验的交流。倘有一个社会,它的全体成员都能以同等条件,共同享受社会的利益,并通过各种形式的联合生活的相互影响,使社会各种制度得到灵活机动的重新调整,在这个范围内,这个社会就是民主主义的社会。”[13]这种自由的往来与经验的交流在教育场域所指向的正是教师与学生参与教学从而生成意义的过程,就师生关系而言追求的则是一种主体间关系的达成[14],要求在教育中给予对方一种主体承诺以作为教育关系展开的前提条件。这一过程重视的不是最终的结果或真理的归属,而是参与者在参与过程中通过辩论、反驳和澄清而给教育文本带来的重新阐释与意义创生,这也是杜威在民主主义的框架内论证教育无目的的真实含义。在这一过程中,民主不是体现为卢梭所批判的众意的达成,而是成为一种公意的实现。正因为民主的参与造就了共同体的意义建构过程,教育与民主才成为可以互通的概念:真正的民主一定是能够促进共同体成员心灵自由的教育,真正的教育也一定是能够参与对话和进行意义建构的民主。
从这种二分的角度来看,弱势民主与强势民主由于其不同的性质,在实践领域存在着不同的侧重点,因此有必要提出对应的制度架构与教学过程这两个教育实践领域的划分。制度架构主要是外围的教育因素,教学过程则是内在的、核心的教育因素,两个领域中的教育民主也各有其特征。就民主形式和评判标准而言,两个领域也不应该混淆。弱势民主与强势民主的区分并非仅是从不同前提引申出的逻辑上的区分,这两类民主在实践中的实现条件、过程和现实障碍都是不同的,遵循着各自独特的规律性。但二者也有如同水流与沟渠的关系,弱势民主如同沟渠一般划定了不可侵犯的教育自由权利范围,但无法保障水量的充盈,对自由权的无限回缩的保护还有可能造成共同体的分裂;强势民主则如同水流一般灌溉、养育教育的自由权利,但是不加以限制则有可能造成共同体对个体教育自由权的替代和漠视,使得共同体权利的至上性突破其治权的合理范围。没有弱势民主保障的强势民主是危险的,没有强势民主支持的弱势民主是软弱的,只有二者协同的发展,才能使教育民主水到渠成。
三、两类教育民主的不同实践逻辑
教育民主的实现有赖于弱势民主与强势民主二者的协同发展,要确保现实教育民主得到保障并充分发展,需要对现实的把握和对理想的践行,并最终依赖于民主实践的持续性。弱势民主与强势民主在前提、逻辑和方法上有着巨大的差异性,整体而言,前者更多地体现了决策的公正性,而后者更多体现了参与的有效性,这一区别也就决定了两类教育民主在实践逻辑上的不同路径取向。
弱势民主的实践逻辑包含着四个环节,即民主状况的评价、手段与条件的反思、过程的改造以及民主的再评价。民主状况的评价涉及教育民主的广度、深度及其范围,“民主是一个程度的问题,而且是多级的程度问题。评价民主是要回答的关键问题不是‘它在何处?’或‘它不在何处?’而是(在号称民主为目的和理想的地方)‘它有多深多广?’,‘在哪些问题上它确能发挥作用?’”[15]教育的民主需要询问教育决策的选择是多大范围的人们做出的,人们有没有充分理解这些决策的意义,以及是否重要的教育问题都能够通过民主决策过程做出等问题。对手段与条件的反思包括对教育决策的决定原则、代议制度的有效性等手段的反思和教育民主的物质、法制、文化、心理等实现条件的反思。前者需要对决策达成过程中的裁定规则进行细致的考察,特别是对多数原则的各种形式和局限性进行研究,防止权力滥用所造成的多数人暴政。并且需要对代议制民主在教育问题上的合理性进行反思,对地方与整体利益的决策结构和教育政策执行的授权过程作更为细致的刻画。对于教育民主条件的反思则包括对物质条件、法律条文、沟通机制和宽容精神等进行的反思。这些条件限制着教育民主展开的可能程度,不同部分的不同程度的缺失都可能影响到教育民主在广度、深度和范围上的扩展。对于手段条件的反思能够为我们勾画一个现实的、逐步推进的教育民主改造方向,并指明改造所可能遇到的阻碍与解决途径。过程的改造是在评价与反思基础上形成的未来教育民主的可能图景及其实现过程,主要是对于民主手段与条件的有目的的调整,既包括对决策程序的修正或更新,又包括对于教育民主各种制约条件的改善等。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改造过程本身必须合乎民主要求,因为“民主方式不是一种解决,而是一种寻求解决的方式”[16],过程的改造必须成为民主的自我实践,否则其自身合法性与合理性也难以确证。民主的再评价意指在改造之后再次重复对于民主实现程度的评价,这是民主持续深化的必要环节,也是民主本身逻辑所决定的必然结果。只有在不断的评价、反思与改造中,教育民主的广度、深度与范围才能够得到保障,教育共同体参与者的自由才能够获得真正的释放,教育与社会共同发展的理想也才有实现的可能。
强势民主的实践逻辑同样包含四个环节,即争议的出现、理解的达成、公意的实现以及新争议的酝酿。争议的出现表明之前的决定不能弥合不同个体对问题的理解,在共同体中产生了解决争论的必要性。其中要澄清的问题是,争议各方是否真实地在试图将共同体的发展导向自己所认同的道路,是否这一选择指向的是一种新的行为方式,选择的逻辑可否推广到共同体的其他事务上。如果回答为“是”,则表明共同体有必要认真讨论这一问题,并将这一问题列入议事日程。理解的达成包括各方对于自己立场的澄清、各方对于他人参与合法性的承认及其立场的准确理解、议事规则的完备性、议事过程的完整性与充分性以及持续的辩论、反驳和达成共识。这一阶段需要全体共同体成员的共同参与,而非依赖于各种利益代表,因为“在强势民主中,政治是公民们行动,而不是为公民们作出行动。行动是其首要美德,而参与、委托、义务和服务——共同审议、共同决策和共同工作——则是其特征”,[17]其目的在于 “保证人们参与共同了解的沟通,可以促成相同的情绪和理智倾向——对期望和要求作出反应的相同的方法”。[18]共同体审议的过程也就是共同体成员的理智探求过程,问题核心是如何让这样的过程尽可能完备,使得真正意义上有组织有系统的理智探求得以开展,从而形成最后的公意。公意的实现是指当公意得以达成时,各人的理智探求也就获得了一个暂时的成果,这一成果表现在每个人对共同体目的的重新体认和对自己与共同体关系的调整,并进而开展自己实践领域的活动。这样的实现过程并非如弱势民主那样诉诸于强制,而是出于自觉和自律,是出于理智的自然而诚实的表达,其有效性则依赖于理解达成阶段的充分性。最后的环节是新争议的酝酿,是指共同体在完成以上诸环节后,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新的争议必然会继续出现,反过来构成和体现了共同体持续的生命力和创造性契机。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杜威将共同体与教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认为共同体的发展过程就是内部成员不断地接受教育与经验生长的过程,而教育的过程也必然地表现为共同体有效参与的民主实践过程。
弱势民主与强势民主实践逻辑的四个环节并非是要将弱势与强势教育民主的各自实现过程僵化地划分为四个步骤并且不合理的要求将整体教育改造区分为总体性的和明确划分的四个阶段的循环,实践中所遭遇到的教育民主问题更多的是由分散的、微小的教育情境构成,需要持续不断地通过累积一个又一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来推动总体教育的更新。从这一角度来说,教育民主的实现过程必然是渐进的和复杂的,而其关键性的问题始终是:这样的改造过程是通过民主方式实现的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这样的改造过程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为继。民主的完善只能通过民主来实现,民主是实现民主的唯一方式,民主的核心是选择而非被选择,甚而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民主选择就产生什么样的民主,这样的结论或许可以借用科恩的一句话作结:“认识到这一点,既令人不安,又使人放心。”[19]
[1][3][12][15][16][19][美]科恩.聂崇信,朱秀贤译.论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序)6,26,38,39,39.
[2]郝文武.教育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38.
[4][法]托克维尔.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282.
[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吴寿彭译.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09,118-119.
[6]John Dewey,Creative Democracy-The Task Before Us,The Later Words of John Dewey,Vol.14,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8,227.
[7][法]贡斯当.阎克文,刘满贵译.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7.
[8][英]以赛亚·伯林.胡传胜译.自由论[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189.
[9][10][17][美]本杰明·巴伯.彭斌译.强势民主[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5,160,161.
[11]John Dewey,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The Later Woks,Vol.2,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8,350.
[13][18][美]约翰·杜威.王承绪译.民主主义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109-110,9.
[14]郝文武.教育:主体间的指导学习[J].教育研究,2002,(3).
邓 飞/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哲学和教育基本理论
(责任编辑:刘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