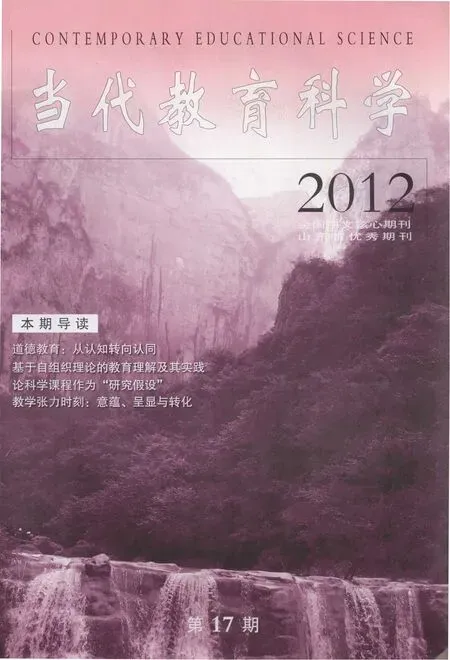教师的教育信仰:迷失、回归与重建
● 王 珊
人不能没有信仰,教育同样需要信仰。信仰本质上而言是主观的,它是主体表达超越性需求的一种方式。《辞海》里对信仰的解释是:“对某种宗教、或对某种主义极度的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教师的教育信仰即是教师在教育生活中对教育理想的极度信服和尊重,主要表现为教师所秉持的教育对社会和人发展的应然价值,并以此作为其行为准则。这种以“极度信服和尊重”为特征的精神诉求和情感认同使应然超越实然,并成为教师职业身份的标志之一。教师需要教育信仰,要有所信,才有所追求,有所敬畏,从而真正拥有属于教师与学生的教育生活,并为之建立起不亚于钱与权的第三种尊严与幸福。当代教师所面临的教育信仰危机,不仅深刻地威胁着教师的生存状态与专业发展,而且更加深刻地威胁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教育和未来。
一、教师的教育信仰迷失
有学者认为教师的教育信仰缺失是现代教育的主要问题,也是教师教育最大危机所在[1]。然而,与其说是教师的教育信仰缺失,不如说是教师的教育信仰迷失更为确切。“缺失”是失去、没有、缺乏,而“迷失”是以“存在”为前提,只是在现代社会中迷失了方向,失去了根基。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古代教师是有教育信仰的。儒家文化熏染下的中国古代教师孜孜追求的是天地万物间的“道”,他们本身所承载的道德力量远远大于其承担的传授知识的职能。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是中国古代教师的社会使命,而知识的传授与学习不过是“求道”的工具,所谓“学所以为道”。正因如此,中国古代教师能“慎独”,并以神圣的使命感追求其终极理想。中国教师的教育信仰不曾缺失,而是在现代社会中的迷失。
(一)教师的教育信仰迷失之痛
教师的教育信仰迷失之痛表现在物质与精神匮乏下教师夹缝生存的现状。经济体制的转型带来了中国教育的消费时代,市场竞争、学校自主、经济效益、教育服务的价值观渗透到教育领域,商业文化消解了神圣教育的公益性,资本的逐利性滋长了教育腐败,钱权择校为国人诟病,而教育学界关于“教育产业属性”的争论也冲击着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每根神经。是秉持独善其身的人文情怀?还是追求物欲满足的随波逐流?最终市场逻辑无限放大了教育的经济属性,教育的公益性被淹没在教育泛市场化的思潮中。伴随着对私益的追求,教育演变为无序状态,并蚕食着教师微弱的理想激情。而再次击碎教师们乌托邦情结的绩效工资制度不仅将教师视为 “经济人”、“工具人”,而且让分数、升学率改头换面,再次合法合理地成为评价教师教学的唯一标尺。教师不得不牺牲对应然价值的追求,一如既往地生活在“起早摸黑,满眼分数”的实然状态。在“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自我蹉跎中,教师最终蜕变为这种生活的寄生物。他们栖息其中,支持他们的意识形态早已失去原有的理想激情,对私利的角逐除了官能的满足并不能带来所需的价值关怀。长期生活的惯性使他们早已丧失出走的勇气,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使他们感到找不到出路的痛楚与困惑,甚至是某种程度的绝望。
(二)教师的教育信仰迷失之源
直面迷失之痛,不禁要问教师的教育信仰何以迷失?缘由是多方面的,然追本溯源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现代社会的去信仰化、无根化是其迷失的社会根源。正如韦伯指出,现代社会已经被科学理性“除魅”,但“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2]。科学也许能够解释实然世界的一切,但却无法作为应然世界里解释价值、信仰问题的工具。因而韦伯将人类理性划分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以“目的、手段和附带后果作他的行为取向”,价值理性即“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举止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3]。在被“除魅”的现代社会,价值理性黯然无光,每个人都有其特定的目标,人们只是判断目标达成的手段是否合理,从未怀疑或判断目标本身的合理性。人们被囚禁于工具理性的铁笼,至于信仰,则留给了宗教,而对于本来就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国社会更是雪上加霜。正如许纪霖指出,自从二十世纪作为宗教替代物的儒学崩溃后,在中国社会的信仰领域便出现一片真空[4]。那场旷世的科玄论争虽然以科学派的胜利,“玄学鬼”被唾弃而告终,但用理性追求信仰以指导人生的科学派仍未能解释 “科学何以能支配人生观”的问题。对科学、技术及理智化的顶礼膜拜,带来教育中极端功利主义的滥觞,它最终由基于教师信念的活动异化为种种简单的技术行为和操作的机械叠加。
自由意志与人格独立性的沦丧是教师的教育信仰迷失的本质根源。正如石中英指出,失去意志自由和认识独特性的人只能活在别人的世界,何谈信仰[5]。一些所谓“知识精英”构建的“文化霸权”支离了教师早已破碎的精神生活。课改十余载,从诸多专家堂而皇之宣称新课程改革必须大破大立、必须对教师进行彻底“洗脑”,到对新课改忽视系统知识的诘责、对课程理论基础含糊不清的争论,直至到对忽视传统本土文化的批判,教育学界已从讴歌的热情回到客观、反思、批判的冷静与清醒。战斗在课改一线的教师们却只有无数次地“被培训”、“被灌输”和“被引领”,他们的呼吁、困顿与反抗最终被淹没在学界喧声鼎沸的争论与质疑中。“教师感性经验丰富而理性认识匮乏”的陈词滥调让“知识精英”们肆无忌惮地通过学术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发展起一种比公开“洗脑”更为可怕的控制技术——对个人意志和独立认识的 “漠视”。于是,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被塞给了毫无准备的教师。知识的不确定性、价值有涉、情境性等新理念固然打破了教师坚守的“知识真理”神话,但强扭的瓜不甜,当教师精神的自由与独立性枯萎的时候,他们只能成为别人的工具。傀儡般的课堂教学如舞台表演般矫情做作,充斥着无实质意义的对话与活动;失去知识载体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也只能如同“贴标签”般的机械生硬。
二、教师的教育信仰回归
教育信仰回归的前提是它曾经存在。拨开现代社会的纷纷攘攘,探寻教育信仰的文化源,解放蕴含其中的文化力,才能最根本地解决教师存在的困境,回归到教师原有的人性丰满状态。
(一)教师的教育信仰之文化源
“道”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终极依据”。“它高居于天地人鬼之上,又与天地人鬼相应的宇宙、社会与人共有起源与图式”[6]。它几乎无所不包,构建了可以解释一切的思想体系,使人们感到安心和安全。因而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而言,“诚意正心修身”(道统)是灵魂,“齐家治国平天下”(政统)与“格物致知”(学统)都受它的制约,即“道统”成为中国古代精英意识的心理和文化基础[7]。正是对“道统”的坚持,使儒家精神超越功利的价值观念体系,成为中国古代教师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和对教育理想的承诺。他们始终是圣贤文化的代言人,以圣贤学问及其人格修养严格要求自己,而经世治国、兼济天下的社会使命感也成为中国古代教师思想的魔咒。正如孔子要求君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身自养是从政的先决条件,人格理想的追求是政治抱负实现的前提。最终,“内圣外王”的儒家理想成就了中国古代教师的君子人格,并成为他们对合乎伦理原则的理想社会的心灵献词。他们将道德伦理秩序的基础进一步推演到人内在的“人性”,把人类应有的至善行为看成教育的终极目的,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种本质存在和人文精神成为中国古代教师根本的生命态度和教育信仰的文化源。当这种最幽深的来源与最基本的依据由于历史的裂变而被摧毁的时候,教师的教育信仰也就成为飘泊的浮萍,失去理解和解释教育生活的效能。因此,现代教师必须穿越断裂的天堑,回归业已隐去的本原,重拾业已失落的人文精神,才能抵制商业社会的粗俗,超越现有体制的束缚。
(二)教师的教育信仰之文化力
教师的教育信仰不仅是教师的终极教育理想,更是其教育行为的根本准则。它不仅表现为教师的教育生活态度,更体现出一种超越性的、具有强大凝聚性的教育力量。当这种力量扎根于民族深厚的传统历史文化中,以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心理积淀作为其支持背景时,教师的教育信仰也就有了其独特的文化力。这种文化力体现为一种道德力,它是一种精神超越,始终发挥着对教师教育行为的规范和引导作用。因而教师能“以身作则、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们不仅要成“经师”,更要做“人师”;他们通过“正言”、“正行”、“正教”去教育和影响学生。这种文化力还体现为一种凝聚力。它兼容并蓄,博采众长,为教师提供了一个彼此认同的文化基础,用共同的教育信仰将他们凝结为一个共同体,为实现其共同的目标而前仆后继。他们“无玷清议”,心系天下;他们对国家与权力始终拥有批判的位置;他们无论是为帝王之师,还是讲学隐居于山林,始终以守护于心中的“道”来阐释其教育理想及政治抱负。因此,释放这种文化力,赋予堕落扭曲的教育精神之永恒动力,使之能抵抗现代社会的科学主义、功利主义与消费主义的侵蚀并超越现有体制的窠臼;释放这种文化力,才能使教师的教育信仰不至于停留在肤浅的、聊以自慰的阿Q精神层面,或退化为“孤芳自赏”、“众生皆醉,唯我独醒”的消极防御,而真正成为一种积极的入世态度,一种重要优质的文化资本。
三、重建教师的教育信仰
教育信仰的文化根源随着历史的沉淀而成为不言而喻的背景,并渐渐淡去。寻根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教育信仰的回归,更是为了在现代语境中的重建。传统与现代并非对立,回归传统并非抱残守阙,而是尊重传统文化的精髓,与时俱进地发展与创新。因而在经历迷失,探寻回归之后,重建教师的教育信仰就尤为必要。
(一)关注教师的存在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故古人将君与师并列,师与天、地、君、亲共享世人尊崇。“师云亦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教师在中国古代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与尊严。如今,在“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为了一切孩子”的豪情壮志中,教师无疑被“边缘化”,最终成为教育异化的“替罪羊”。忆古思今,就教师地位而言古之师与今之师相去甚远。在当代社会,非常有必要给予教师更多的关怀,更多地关注他们的存在,从而使教师的教育信仰得以生长。关注教师的存在,即认识到教师不仅是肩负社会使命的 “园丁”、“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更是具有独特个性的“人”;关注教师的存在,即认可教育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的灵肉交流,“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集”[8]。它要求教师撕掉面具,回到作为“人”的丰富人性状态;关注教师的存在,即是关注学生的幸福。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指出,一个有高尚精神生活的人,才是有理想的人,才能关心别人;关注教师的存在,即是要改善教师物质生活匮乏,精神世界荒芜的生存状态与存在方式,最终指向教育幸福的深层关怀与本然追求。
(二)重塑教师的自由
教师的自由体现着教师的存在,是教育信仰得以重建的基础。正如存在主义者奈勒指出,“人的存在的基本特点是他的绝对自由,这种自由绝不可以受宗教、政权、学说或另外一个人的压制而被否定”[9]。教师的自由即教师决定他自己,他是其思想意志自由的主体,他能在教育生活中诠释自己、实现自我。毋庸置疑,失去自由意志与人格独立的教师不可能拥有教育的信仰。即使有,那也不过是别人的信仰而非自己的信仰,因为真正的信仰必须在自由的精神状态才可能形成。重塑教师的自由必须保障其思想意志的独立性。真正的知识分子“绝不是完全服从政府部门、大公司甚至同行业会政策目标的职员或雇员”,而是有独立思考的个人[10]。唯有如此,教师才能坚持知识分子应有的原则与立场,能够对“强权说出真理”,能够坚守教育的终极理想。重塑教师的自由离不开民主的精神。自由与民主永远是孪生,民主尊重多样的个性并遏制绝对的权力。面对现代社会中“知识霸权”的精神屠杀,只有民主的意识、能力及信念才能保障教师的自由,抵御“洗脑”与“漠视”,保持自我精神的独立。重塑教师的自由必须唤醒教师的自我意识。自由是人类的本质,但往往被科层制遮蔽、被商业与功利腐蚀,从而被人们贬低,甚至遗忘。只有唤醒教师的自我意识才能让教师正确认识自我,主动地承担自己的责任与义务,真正地摆脱从属的地位,在成其为自己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领受到幸福与自由。
(三)提升教师的人生境界
重建教师的教育信仰离不开其人生境界的提升。人生有不同的境界,尼采提出了人的三重精神境界。从忍辱负重的骆驼境界到挑战传统、勇猛无比的狮子境界,最后到象征着精神独立、自由与创新的孩子的境界。然而,人生境界不仅指人性所能达到的“高度”,还指人生活其中的“心境”或“意义领域”,即人愿意生活其中的一种“状态”[11]。当人们认可、接受这种“状态”并愿意为之付诸努力,也就是在实现他们的信仰。有信仰的生活才是高尚的生活、文明的方式和理想的人生境界。因此,提升教师的人生境界是实现其教育信仰的重要途径。人生境界的提升是一个不断觉醒的过程,它反对灌输,需要教师人文精神的回归以获得信念的支持。人生境界的提升更离不开实践,它是基于认识基础上的行动。教师的人生境界不是喊口号,而是体现为教师能否在实践中不断反思并自觉按其要求行动。当然,教师人生境界的提升还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过程。教育改革与创新不可能在短期完成,教师不可能等看到改革的成果再考虑是否进入,改革的不确定性影响着教师对其教育理想的追求。在现实中屡屡碰壁之后,他们从理想主义变成了犬儒主义,表现出愤世嫉俗与玩世不恭。因此,重拾失落的人文精神,重视作为我们精神根基的民族文化经典尤其是教育经典的学习,强调多种教育仪式的精神陶冶力量等,都能有效地提高教师修养、提升人生境界。佛语云:“欲求净土,先净其心,随其心净,即佛土净”,只有守住心中那片教育的“净土”,才能寻觅到属于教育的美丽。
(四)建立教师对教育的科学认知
教师的教育信仰必须建立在对教育的科学认知基础上。没有科学的教育观,仅凭一腔热血的盲目相信不能称其为教育信仰,只能称其为迷信。教师的教育信仰必须是教师对教育价值理性认识上的升华,是对教育应然价值的追求,对教育本真的极度崇拜和信服,如果离开了这种科学的认识,教师的教育信仰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教育的应然追求就是学生的幸福,这种幸福不仅是教给学生何以为生的本领、生存的技能,更应给予学生生存的理由,即存在的意义。现代教育使学生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生存能力,却忽视了引导学生去思索其存在的必要,从而造成了他们精神的虚无、灵魂的漂流与流离,从根本上威胁了他们的幸福。当人生幸福成为教育的应然追求,教育的本真价值也就体现为对真、善、美的执着向往与努力践行。教育也就从生存教育升华为生命的教育、存在的教育。真是这种存在的本体,善是存在的趋势,美则是存在外在表征。这种对教育的科学认知成为教育信仰的知识基础,它虽然是缄默的知识,但更加是行动的知识,它指引着教师将其对教育的理性的认知升华为热忱的教育信仰,成为其孜孜以求的目标。
[1]张璇,高伟.论教师的教育信仰.当代教育科学[J].2010,(9):3-8.
[2]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第二版)[M].北京:三联书店,2005,34.48.
[3]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6-57.
[4]许纪霖.二种危机与三种思潮——20世纪中国的思想史[J].战略与管理, 2000,(1):66-71.
[5]石中英.教育信仰与教育生活.清华大学教育研究[J].2000,(2):28-35.
[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38-41.318.
[7]许纪霖.人文精神寻思录之三——道统学统与政统[J].读书,1994,(5):46-55.
[8]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北京:三联书店,1991,4.
[9]张斌贤.外国教育思想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476.
[10]张隆溪.走出文化的封闭圈[M].北京:三联书店,2004,99.
[11]石中英.教育哲学[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