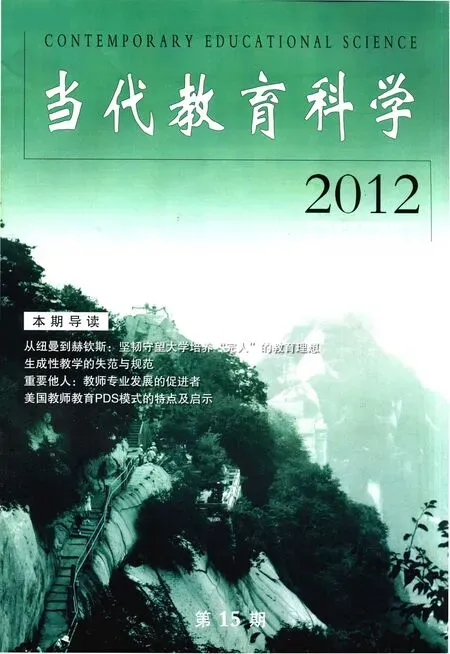从纽曼到赫钦斯:坚韧守望大学培养“完人”的教育理想*
● 张俭民
从纽曼到赫钦斯:坚韧守望大学培养“完人”的教育理想*
● 张俭民
纽曼和赫钦斯作为博雅教育发展史上两位重要的思想家,虽然各自所处的现实社会相差近一个世纪,且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但他们都坚韧守望大学培养“完人”的博雅教育理想,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大学培养“完人”的主要目标、核心任务、现实途径和主要教育方法。理解他们培养“完人”教育思想的深层内核,对于当代大学树立正确的人才培养观,把握博雅教育的本质内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纽曼;赫钦斯;完人
大学培养“完人”的教育理想起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使自由人的‘心灵’得到‘自由’的‘自由民’教育”,经由中世纪大学的“七艺教育”和文艺复兴时期 “培养掌握丰富的古典人文教养的富有活力的新人”的教育实践,已成为大学人才培养的传统价值取向。面对现代大学教育过分功利化、工具化的不良倾向,19世纪中期的纽曼以及20世纪初的赫钦斯高举“理智培育”的旗帜,坚韧守望源于亚里士多德培养“完人”的人文教育理想,对遏制大学教育过分职业化、功利化和反理智主义的不良倾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理解他们培养“完人”教育思想的深层内核,对于当代大学树立正确的人才培养观,把握博雅教育的本质内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大学培养“完人”的主要目标——拥有智慧的人
在19世纪以前的大学发展史上,大学教育以自由教育为模式,以“完人”为培养目标,并不承担培养某一特定职业人才的任务。但到了19世纪纽曼所生活的时代,专业教育逐渐兴起,一些新大学主张以市场为驱动,培养更为“实用”的专门人才。
面对新大学的冲击,英国都柏林天主教大学的校长纽曼,仍然坚守培养“完人”的教育理想,提倡大学教育的主要目标是为社会培养拥有智慧的公民。首先,纽曼认为大学应把公民的塑造放在专业利益之上。他指出,“如果我所指的哲学教育或自由教育——它正是大学担负的功能——不认可专业利益的重要地位,那么它势必会把公民的塑造放在专业利益之前。”[1]其次,他提出大学教育的主要目标不是美德,而是智慧。他坚持认为,让自由教育挑起德行或宗教的重担实在是个错误,这与让它担负起机械技术的重担没什么两样。大学所承担的理智运用既不是技艺方面的,也不是职责方面的,它的功能是理智培育。再次,纽曼认为,大学教育真正的目的也不是学问或学识,而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思想或理智。自由教育就它自身看就是智慧的培养,它的目标就是提高心智能力。他从反面描述了学究的形象:很有学问,但几乎没什么思维能力;从所学的课程中掌握了大量的事实,但没有智慧。最后,纽曼认为,大学教育的艺术是一种社会生活的艺术,它不把学生限定于特定的专业,只是为了让学生适应这个世界。“若大学课程一定要有一个实际的目的,我认为就是为了培养良好的社会公民。”[2]这种“良好的社会公民”是充满智慧和思想,富有勇敢、正直、宽容等社会优良品质的完人。
经历近一个世纪后,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校长赫钦斯,继承并发展了纽曼关于大学培养智慧的完人的教育理想。他指出,大学教育的目的不应只着眼于“人力”,而应着眼“人性”,培养有学识、有智慧、止于至善的完人。首先,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改善人。所谓改善人,就是使人的理性、道德和精神诸力量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其次,他进一步指出,大学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人类的优秀性,把人看作终极目的。“视生命为终极目的,并非工具。因此这种教育是自由人的教育,其他种类的教育或训练都把人作为实现其他目的的工具,例如赚钱谋生等,并非以人为终极目的。”[3]“教育的目的,不在制造基督徒、民主党员、共产党员、工人、公民、法国人或商人,而在培养人类的智慧,由此发扬人性,以成完人。”[4]再次,赫钦斯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有切近的和最终的之分。切近的目的是发展智性美德;最终目的是形成睿智、达于至善、成为完人。他说:“教育的目的是智慧与至善,任何不能指引学生更接近此目的的研究,皆不能在大学中立足”。[5]
二、大学培养“完人”的核心任务——理性思维能力培养
纽曼认为,大学教育的核心任务是使学生形成一种以自由、公平、冷静、克制和智慧为特征的终生思维习惯。这种思维习惯是以理性思维能力为核心的哲学习惯。在他看来,理性思维能力培养是大学培养“完人”的核心任务。大学应该教会学生怎样思维,怎样运用他们的理智。“大学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理智的培育作为其直接范畴……它所考虑的既不是道德熏陶,也不是机械灌输。……它的功能是理智培育。”[6]对于理性思维能力培养,他认为,首先要培养学生比较分析、综合理解、触类旁通的能力。只有在思考的基础上,将新旧知识进行对照、分析、综合和协调,才智才能得到真正扩展。“真正的才智扩展,是一种立即就能把许许多多零零星星的事情作为一个总体来关照的能力,是把握这些事情各自的价值并决定相互之间依存关系的能力。”[7]其次,要培养学生构建概念的能力。“这是一种习得的判断力、敏锐力、洞察力、见识力、心智的理性延伸力以及才智的自制力及沉着力。”[8]再次,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探究的能力和对事物追本溯源的习惯。最后,他强调要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判断力。他指出,“在各种智力当中,判断力在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9]因此,要重视培养学生形成判断力的两种习惯,即正确与有力。
赫钦斯坚韧捍卫了大学以理性思维能力培养为主导的价值取向。他主张理性教育应是大学教育的核心。“要正确的了解教育,便应知道教育是对理性的培养。”[10]“教育的目的在助人发挥理性,教育制度应为此目的而设。 ”[11]他断言,“高等教育的目标是智慧”[12],“大学所要解决的是思辨的问题”。[13]他从三个方面对大学的理性教育进行了深入的阐述。首先,他认为,培养理智方面优点的教育是最有用的教育,不管学生将来过思辨的生活或行为的生活。他指出理智拥有五种优点,包括三种推理的优点:直觉知识,即归纳的习惯;科学知识,即演示的习惯;哲学智慧,即科学知识和直觉推理的结合,它涉及最高层次的知识、首要原则和首要原因。再加上两种实用智力方面的优点:艺术,即根据真正的推理过程进行创造的能力;审慎,它是行动的前提。其次,大学要激发学生思考,提高判断能力。赫钦斯指出,“教育的特别功能是助人学习运用心灵思考,以至成为人之所以为人。”“属于教育者无其他,能助学生学习自己思考,且常为自己思考,而形成独立判断能力和负起公民职责。”[14]再次,大学要培养学生理解观念的能力。赫钦斯认为,教育最具体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帮助学生了解一切事物的原理、原则及原因,并非填塞大量事实或实行旁枝末节的技术训练。“通识教育的目的在于发展人的理解和判断的能力”,“在于给青年人提供他们自己所需要的习惯、观念和技能”,因为,“理解和判断能力”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是“不可能嫌多的”,是人的本性中最卓越的部分。[15]
三、大学培养“完人”的现实途径——通才教育
为了实现大学培养完人的教育目标,纽曼坚持主张大学应该提供通才教育。他首先强调,大学的通才教育以心智训练,性格修养和理智发展为目标。大学不将课程局限于特定的专业,通过传授普遍和统整的自由知识,使学生获得普遍的自由学术和观念,使人的认识或思维获得自由。其次,纽曼认为自由教育具有专业教育所具有的真实而充分的实用性,比专业教育更有用。自由教育所进行的理智训练有助于专业学习和科学研究。经过理智训练的人,“能学会如何进行思考,推理、比较、辨别及分析,并使其审美观得到锻炼、判断力得以形成,洞察力变得敏锐,虽然他不一定马上就能成为某一种专业的专家,但是他所处的智力状态,能够使他从事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或从事任何一种职业。”[16]再次,他从大学的教育性质出发,认为大学的通才教育应提供普遍性和完整性的知识,而不是狭隘的专业知识。一方面,大学所传授的知识应该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性知识,因为“当知识变得越来越特殊时,它也就不再是知识了”;[17]另一方面,大学要强调学科体系的完整性,不能将神学排除在大学之外。纽曼坚信大学应该追求知识的综合性和广泛性,否则它就不配使用“博雅”或“自由”来自我界定。
赫钦斯的通才教育观是他的理智训练学说逻辑演绎的产物。他认为大学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培养通才和发展理性的普通教育,而非培养专才、“制造机器”的专业教育。他反对大学过早专业化,要求专业化的教育必须建立在通才教育的基础上。他指出,通才教育应成为大学各门高深学问或专业研究的基础。所有学生在专业学习开始之前,都必须接受通才教育,培养与别人沟通思想的基本观念和普遍兴趣。他说:“如果没有通才教育,我们就不能办好一所大学。如果学生和教授(特别是教授)缺乏共同的理智训练,一所大学必定仍旧是一系列不相关联的学院和系科。”[18]在他看来,通才教育不仅仅是指多方面知识的传播,其核心和立足点是理性的训练和自主性培养,也就是要“帮助学生学会自己思想,作出独立的判断,并作为一个负责的公民参加工作”。[19]赫钦斯并不反对在大学中实施专业教育,但对职业教育持反对态度。他主张职业科目从大学的课程中剔除出去,另成立机构实施之。在他看来,专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区别在于这种教育是否以智力为基础。对于如何开展通才教育,他提出,大学教育可以分为通才教育和专业教育两个层次。在大学一二年级,学生主要修习通才教育课程,至大学三年级,学生主要修习形而上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三个学部开设的部级课程,这些课程涉及面比通才教育课程要窄,但比专业教育课程要宽;在大学最后阶段,再开设系级课程,接受专业教育。赫钦斯提出,通才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永恒知识的研究和理性遗产的学习。他所提倡的通才教育课程主要包括:西方古典名著,阅读、写作、思维和说话的艺术,再加上推理过程的最佳范例——数学。其中,古典名著处于核心地位。
四、大学培养“完人”的主要教育方法——对话教学
在纽曼看来,大学只有通过师生对话与沟通,才能获得真理和智慧,才能更好地培养“完人”。他认为,学生从大学里获得的主要才智收获并不主要来自他对所选具体知识分支的学习,而多是来自生活于洋溢着普遍知识的对话教学氛围之中。对于大学的对话教学,纽曼首先强调大学应通过学者之间的相互对话,为学生创造良好的思想氛围。他指出:“一大群学识渊博的人埋头于各自的学科,又相互竞争,通过熟悉的沟通渠道,为了达到理智上的和谐被召集起来,共同调整各自钻研的学科的要求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他们学会了互相尊重,互相磋商,互相帮助。这样就造就了一种纯洁明净的思想氛围。学生也呼吸着这样的空气”。[20]其次,纽曼强调了学生之间对话交流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当一大批具有青年所有的敏锐、心胸广阔、富有同情心、善于观察等特点的年轻人相聚在一起,自由地互相融合,毫无疑问,即使没有教师教他们,他们也肯定会互相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每个人的谈话对其他人都是一系列的讲座,他们日复一日使自己具备全新的观点和看法,吸收新鲜的思想,养成判断事物和采取行动的种种不同准则。”[21]再次,纽曼还强调了学生与教师之间对话与交流的重要性。他告诉学生:“你不是仅仅来听讲座或读书的,你是为了问答教学而来的,这种教学存在于你与教师之间的对话中。”[22]总之,纽曼认为,教师之间、学生之间以及师生之间如果缺少对话与交流,教育难以提升到一个理想的境界,难以培养出理智发达、才智健全的完人。
与纽曼提倡对话教学一脉相承,赫钦斯反对教师对学生进行灌输,主张大学应实施苏格拉底启发式的对话教学。他指出,“虽然可以帮助人去学习,但人只能是自己学习。要对他们进行灌输,就不可避免地要违背他们本性的规律。批评、讨论、质询、争论,乃是真正的教学方法。”[23]他倡导对话式的研讨法。班级人数以15至25人为限,由2至3名教授辅导共同讨论。课前学生阅读100页左右的指定教材,然后再进行课堂讨论。研讨时教授的责任不是讲授,而是维持研讨的热烈进行,使学生针对教学内容互相辩难质疑,教师也参与研讨。教师要不断更新教学方式,他说:“我们可以尝试各种不同教学的实验,在教诗时用幻灯片,教莎士比亚时用绘图法,并以小组讨论(Penal)及圆桌会议法(Round-table-method)来变化,以免讨论时太单调。”[24]此外,赫钦斯十分重视不同学科、专业的教师及学生之间的对话与沟通。他指出:“在大学这个社团中,即使人们意见相左,也应该把自己正在思考的,与他人在同一个方面以及与此相关的所有方面正在思考或思考过的联系起来。每个人皆应参与大学的讨论”。[25]
[1][2][6][7][8][9][16][17][20][21][英]约翰·亨利·纽曼著.徐辉等译.大学的理想[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87,97,45,56,72,93,86,4,22,66.
[3]R.M.Hutchins.The great conversation[M].Encyclopeadia Ritan.nica Ine,Vol 1952,3.
[4][11]R.M.Hutchins.The Learning society[M].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76,2,96.
[5]R.M.Hutchins.Education for Freedom[M].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43,26.
[10][12][13][18][美]赫钦斯.汪利兵译.美国高等教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9,57,63,35.
[14][23][25]R.M.Hutchins.The Conflict in Education in a Democratic Society[M].Harper and Brathers.N.Y.1953,13,96,104.
[15][19]华东师范大学,杭州大学.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流派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222,214.
[22]徐辉.一种内涵深刻的古典大学观[A].陈学飞.中国高等教育研究 50 年[C].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1911.
[24]R.M.Hutchins.Tradition in Education[M].Harvard Education Record.Vol7:301.May,1937,309.
*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纽曼与赫钦斯博雅教育思想比较研究》的成果之一。
张俭民/湖南科技学院教务处副处长、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
(责任编辑:刘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