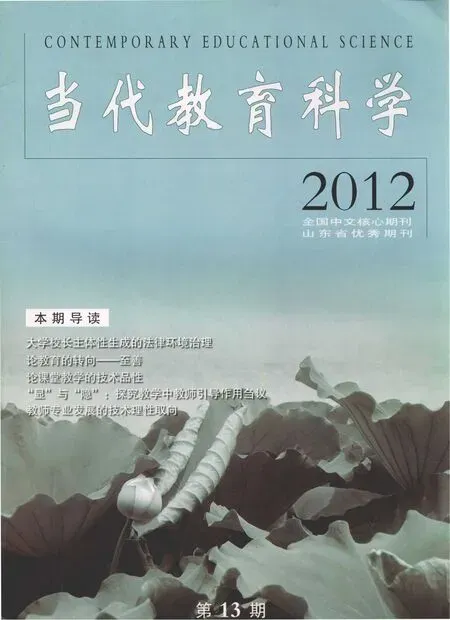大学校长主体性生成的法律环境治理*
● 王 飞 王运来
大学校长主体性生成的法律环境治理*
● 王 飞 王运来
作为一种防御性制度的法治,它并不能直接规约大学校长思想与精神的问题,但它能经过制度的安排或良善的法治渠道正确确立大学与大学校长在法律框架内的主体地位,使大学教育活动与政治活动形成一个恰当的分化状态,把两者的关系维持在一个由国家主导型文化向社会主导型文化转移的恒常框架内。
大学校长;主体性;法治;制度性条件;领域分化
“‘主体性’主要是指‘独立自主、自我决定、自由、能动性、自我、自我意识或自觉、个人的特殊性、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以个人的自由意志和才能为根据等含义。’”[1]反之,受他人支配和统治,听命于神谕、迷信和命运,受制于自然或其他外力与外在权威,或者是仅讲共性而不考虑特殊性都是主体性异化的表现。由此,大学校长的主体性是指大学校长那种永远不满足于现有的大学发展境遇而去不断创造新的生命价值,以获得一个更新的精神自我的行为和意识的特征。这是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管理领导实践活动主体的质的规定性,是大学校长在与大学发展相关影响因素的相互活动中不断得到发展的独立自主、自我决定、自由、能动性、自我、自我意识或自觉、个人的特殊性、个人的聪明才智、个人的自由意志和才能等特性。大学校长这种主体性的生成需要有清晰的法治作为制度性条件,本文试图对这种制度性条件进行探析,以构筑起大学校长主体性生成的法律环境治理架构。
一、正确确立大学在法律框架内的主体地位
正确确认当代中国大学在法律上的主体地位,必须确认大学特殊的行政主体地位。大学是根据公法规定而成立的法人,以推进公共事业的发展为成立目的,是一个公法人。具体而言,首先,大学是“非营利性机构”,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存在的主体。其存在的目的首先不是为了从事民事活动或赢利,而是为了公共利益或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其次,大学与作为行政机关法人的性质不一样。大学是国家行政主体为了特定目的而设立的服务性机构,法律赋予它行驶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服务于特定的行政目的,以执行一定的公共活动为目的与职责,在一定意义上与范围内代替行政机关行驶国家行政权;最后,大学不同于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也不同于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个人。大学被赋予一定公共权力,具有独立的管理机构及法律人格,在行政法上具有完全权利能力和责任能力,能够以自己的名义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承担责任。总之,大学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行政机关,但它应该是行政主体。[2]“行政主体是一个法律概念。就法律意义而言,行政主体是实施行政职能的组织,即享有实施行政职务的权力,并负担由于实施行政职务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主体。”[3]既然大学具有独立行政主体的法人地位,那就有以自己的名义开展活动并独立行使特殊行政权力 (这种权力是一种公权力,它既不是立法权也不可能是司法权,而是一种旨在保障学术主体性实现的特殊的行政权力)的能力,并具有为其活动独立承担法律后果的能力。但是不能因为大学是行政主体,拥有特殊的行政权力就把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定格为是以命令与服从的行政命令关系为基本特征的内部行政关系。大学教育活动中需要这种行政主体地位与行政权力的价值在于促进人的个体主体性发展,正是基于这种对大学行政主体地位和与人的主体性培养本位、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本质性关系的确认,大学的管理才是一种具有主体性色彩的管理,才能给社会培育具有主体性的人,或者说,只有大学具备主体性与进行主体性管理,培育出来的人也才是具备个体主体性的人。明确大学在法律框架内的行政主体地位,不是撇开政治与社会单纯强调大学的本位思想,而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现代性的大学主体理念。鉴于大学的行政主体地位,大学教育活动与政治活动自然就应走向分化。也正是基于此,作为大学这个行政主体的法人代表的大学校长,自然就有了主体性。
二、立法促使大学教育活动与政治活动走向分化
福柯曾经说到:“人类要想逃脱自身的不成熟状态,必须具备两点基本前提,它们既是精神性的,又是制度性的,兼有伦理意涵和政治意涵。”[4]这也就是说,人的成熟状态的获得、主体性的发展,除了精神性条件(如具有理性精神)外,还须具有制度性条件,尤其是法律制度的条件,法律制度的条件是保证人走出不成熟状态、获得主体性的前提,精神性条件与制度性条件两者缺一不可。“自觉的理性化的文化精神如果不通过制度安排而成为社会运行的内在图式和机理,也会成某种无根基的浮萍。”[5]现代大学的合法性及其制度的现代性在当代中国发展的制度性前提、制度性安排,除了应该重视大学管理的法治化、科学的科层化之外,还应该使大学活动由与政治活动的领域合一的状态走向它们之间领域相对分化的状态。不实现两者之间的领域相对分化,就不可能实现大学合法性与现代性的充分发展。因为在作为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现代性的经济基础形式中,“最为基本的变化是经济、政治、文化活动三大领域之间的结构关系从领域合一状态走向领域分离状态的转变”[6],即彼此分离,分别走向自律,而这种变化必然要求除了有精神性条件外,还要有制度性条件(尤其是法律制度的条件)的转变与之相匹配,促使领域分离与政治活动中心地位的消解。对于大学教育而言,意味着大学活动获得了作为“市民社会”的“公共空间”,意味着政治价值对于大学教育价值不再具有优先的直接支配作用,从而大学教育活动便必然趋向于一种“本色化”样态,即大学活动的价值原则退回到本己的领域,直接地只在本领域内发生作用;政治活动的价值原则也不再要求大学的价值原则从属于它,此时政治活动也不再行使教化社会的功能,不再通过“掌管教化”来达致社会控制的目的,对于大学活动所追求的价值,包括自由、个体本位的主体性发展的价值,它以宽容的方式来对待。政治主体性与大学教育的主体性由此就得到了疏离与分化,意味着大学获得了独立性,获得了主体性,进而大学教育价值也便回归了本身,“本色化”了。恰恰是这种分化告别了各个方面之间相互掣肘的混沌局面,成为其通向自律并进一步达致超越性的前提,使“所有领域均可按照完全不同的终极价值和目的取向来加以理性化”。[7]这种政治领域与大学领域分化的思想也在温家宝总理2006年与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两度提到提倡教育家办学的思想中得到了彰显。
三、立法促使大学与政治领域分化的具体思路
为了达致大学教育活动与政治活动的分化状态,国家在立法上应遵循如下思路:
首先,建立中央统一规划与地方具体负责的法治体制。中国不存在地方分权和公务分权制度。我国《宪法》第3、4条明确指出:“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为了保障大学活动主体性的落实,今后改革方向之一就是放开中央权力对大学的控制,向地方政府让权,并在二者之间选择一个平衡点。[8]对此,最重要的是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关于高等教育立法模式上需要引入“社会立法机制”,即摒弃“全能政府”管理一切的立法理念,树立“小政府、大社会”的立法思维,遵循这种思维对《高等教育法》进行修订,把其定位为“社会法”。“社会法是调整法律地位平等但实际上有一方处于弱势地位的双方关系的法律,典型的社会法是劳动法、社会保障法。”[9]高等教育法是调整关系的法律,在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学校与师生的关系中,政府处于强势,大学处于弱势,学校处于强势,师生处于弱势。与劳动关系一样,有明显的弱势方,应该纳入社会法的领域。借此,《高等教育法》应该按照社会立法机制来给予修订。根据社会立法机制来修订《高等教育法》,政府在法律中的地位自然下降,不再居于中心位序,就像政府在劳动法、社会保障法里的地位一样,可见,采用社会立法机制来促使大学与政治领域分化,是实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与大学和睦协作关系的法治渠道。
其次,政党权力在大学行政领域要做到“虚位”和在思想领域做到“实位”。大学是探索知识真理的学术研究机构和以服务社会为主要功能的精神文化生产机构,有其自身的属性与规律。对于大学而言,“泛政治化”、“唯政治化”与“去政治化”都是不科学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如果不把教育实践中的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就不可能使其获得足够的意义,因而就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如果只将教育看做是教育,与政治无关,那就无法使教育受到重视,就无法解决教育实践中的问题”。[10]因此,需要通过立法明确“政治自身的‘科学价值观’为引力介入大学发展是合理的,也是必需的,以不影响学校‘独立自主办学’为前提。任何政党的政治权力渗透都应该集中在思想领域,要‘虚位’于大学行政而不干涉大学的‘自主办学’和‘学术自由’,‘实位’于思想,有效占领意识形态领域”。[11]当然,这种占领不是强制的灌输或者限制,而是以一种正确认识政治活动价值与大学活动价值之逻辑内涵的科学价值观去发挥影响。
最后,健全法律体系并克服法律与法治不相匹配的情况。若干年来,中国已颁布多部教育法规,但与整个国家的各项法规的境遇一样,法规虽然不少,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如以个人或少数人的威权、行政手段代替法律)、法规与法治不相匹配的情况很普遍,人治僭越法治而造成的对教育权利的侵害、妨碍教育主体性、大学主体性、个体主体性的发挥的现象很普遍。就大学领域而言,要做到与政治领域分化,做到大学的自主管理,不仅政府部门应健全完善法律体系与依法管理大学,而且必须克服法律与法治不相匹配的情况。依法行政的前提是要有完善的法律体系。政府与大学关系的改革需要法律保证才能成功,新型的政府与大学关系要求政府依法行政、依法服务,大学必须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并且要通过法律来明确各自的权限、作用于责任。当前,中国的法律体系不健全,与这种要求不匹配,需要不断补充、修改与健全。一是尽快制定高等教育法的实施细则或条例,明确规定政府与大学 “做什么”、“怎么做”、“谁负责”、“如何问责”,并在“要求做”与“不能做”方面设置明确的“临界线”,以及分别制定出易于操作、便于监督的具体的法律规范,以保障落实教育家办学、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二是抓紧对现有的教育法规进行梳理,及时进行立、改、废。最需要修订的应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高等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尤其是前两个条例,是最能促使大学权力运行与社会政治体系的权力运行实现权利同构的法律制度,它使学术权力没有成为制度化的权力与主体性的权力,没有在法律精神下建构与行使。建议重新遵循学术权力高于行政权力的宗旨对这两个条例进行修订,突出与提高教代会职权,推进民主管理,确立符合新时代要求的高校设置标准。三是增加法律责任规定。现行《高等教育法》没有法律责任条款,需要在重新修订中加上。建议在重新修订中增加“法律责任专章”,明确规定违反本法各项禁止性规范的责任,真正落实监督与制约政府权力的法律机制,确保政府权力在法律轨道上运转。对违反或不依法执行者,必须追究法律责任。四是尽快制定与《高等教育法》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如制订《大学校长法》,专门对大学校长职业运作机制进行专门系统的规定。
四、促使国家主导型文化向社会主导型文化转移
有了前述立法对法律环境的治理与改善,相信就能促使国家主导型文化向社会主导型文化转移,这是前面政治领域与其他社会活动领域分化而产生的文化效应,是大学与大学校长主体性生成的法治文化环境。国家与社会的不同结构形态是由不同的文化决定的,如果从文化与制度建构的关系、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来划分,可将文化分为两种类型,即“社会主导型文化”与“国家主导型文化”。社会主导型文化导致社会与国家分离,产生的大学是社会的大学,大学围绕人的培育而开展,与此相适应的必然是社会的大学、社会的人才与社会的大学校长,这样的社会能为大学自由与独立提供良好的环境。而国家主导型文化导致国家与社会合二为一,产生的大学是国家的大学,大学教育围绕国家而开展,与此相适应的必然是国家主宰大学的一切,国家的大学与国家任命的大学校长或畸形的大学校长职业,在这种情况之下,难以产生独立的大学校长职业阶层,或者说不存在所谓的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大学校长职业,只有“国家教育工作者”。促使国家主导型文化向社会主导型文化转移,可使大学校长的主体性获得良好发挥,简言之,文化改造与制度构建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国家的制度构建必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本国的文化传统与一定时期人们的意识形态状况,中国大学校长的职业主体性状态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与人们意识形态状况某种程度的反映。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人文资源深厚的国度而言,正确认识大学校长职业这样一个发达商品经济、民主政治与多元文化的产物,的确不是一件易事。对此必须期待于文化重构或者用一个感情上较易接受的文化来改造。不管是文化重构还是文化改造,都是指在正视自己社会文化资源之于国家文化资源处于劣势前提下,深入研究与汲取西方社会文化强于国家文化的有益性,对我们的社会文化进行符合中国大学发展现代化进程的整合。如果没有文化重构的支撑,即使法律制度设计按照大学校长职业的应然主体性进行了规定,也会因为不能从社会文化土壤得到相应的、足够的养分而成长为畸形的状态。因此,中国大学校长主体性的成长成熟过程必定是一个伴随着对于中国国家主导型文化的改造过程,在这个过程里中国大学校长的主体性也必定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异化与逐步矫正的过程。
众所周知,大学校长职业群体有自身共同的知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思维、共同的认同、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理想、共同的风格、共同的气质,这些使其成为了一个职业的共同体、一个知识的共同体、一个信念的共同体、一个精神的共同体、一个相互认同的意义共同体。这样的一个职业的共同体使大学校长共同构成社会的一个有力量的独立而自主的阶层。如此一个专业、独立的、法定的、自主的、自治的、团结的阶层就可以通过集体的力量抵御外在于大学的非正当的干扰,通过职业化机制使大学体系得以独立运转,并在异质的文化土壤中扎根,进而实现大学组织的独立与自治。这表明,大学校长这种职业及其主体性的获得已经成为了一种权利,需要有清晰的法治作为制度性条件,才能达致主体性的生成。而大学校长主体性的生成及其职业的卓越发展,只能在大学教育活动与政治活动走向分化所达致的国家权力向作为社会权力中的教育权力转移的过程中,以及国家主导型文化向社会主导型文化转移的法治文化环境中才能生存与发展。而新中国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的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的一元社会,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国家职能遍及一切领域,大学校长在履行其职责过程中不能与国家利益相冲突。因此,就需要构筑一种作为防御性制度的法治环境来保障其主体性的生成,这种制度性的条件虽然不能直接规约大学校长的思想与精神的问题,但只要它是一种有序而良善的设计与安排,就能促使大学校长职业的社会性、独立性、法定性、专业性与专门性等主体性生成,进而使自己成为把国家与处于民间社会的大学联系起来的一个桥梁。在此意义上,法治这种制度性条件虽然不是大学与大学校长的福音,但它对大学或大学校长而言绝对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有了这个制度,或许大学就不再是一个政治的附庸藩属,大学校长就不再是一个官僚,而是向成为一个卓越的教育家逼近。
[1]张世英.天人之际[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1.
[2]胡发明.我国高等学校性质的行政法分析[J].时代法学,2004,(3).
[3]王名扬.法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39.
[4]转引自吴全华.教育现代性的合理性[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244.
[5]衣俊卿.现代性的维度及其当代命运[J].中国社会科学,2004,(4).
[6]郭湛.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311.
[7]张光芒.混沌的现代性——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总体特征的一种解读[J].南京大学学报,2004,(3).
[8]湛中乐,高俊杰.我国公立高校与政府法律关系的变迁[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6).
[9]俞德鹏,侯强.高校自主办学与法律变革[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91.
[10]吴全华.教育现代性的合理性[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247.
[11]严文清.中国大学治理结构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12.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中国著名大学校长办学之道研究”(批号:BIA090045),2011江苏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 “大学校长主体性生成的近代追索与当代诊断”(批号:CXZZ11_0014)阶段性成果,并受2011年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资助。
王 飞/曲靖师范学院讲师,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 王运来/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刘丙元)
——以期刊文献进行的考察